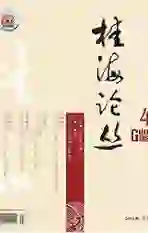碎片化背景下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建构
2014-10-17龚建华
龚建华
摘 要:当今中国城市社会正处于碎片化状态,实体空间的割裂与社群意识的淡漠正使城市这个人类产物异化为社会共同体的阻碍,城市社会的重构势在必行。从公共空间的建构出发,从公园、小区等开放性场所的公共性回归以及从虚拟社区的共同体营建中寻找让城市发展重新纳入社会轨道的途径。
关键词:碎片化;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4-0121-04
对于当下的中国城市社会而言,公共性的缺失不言而喻,一方面,原本较为完整的空间结构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狂飙突进逐渐支离破碎,另一方面,原本较为均衡的社会阶层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分配等因素分化明显,两相结合,使其整体呈现出空间割裂的“孤岛效应”及阶层隔阂的社群分化,即碎片化(Fragmentation)[1]过程加剧。碎片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创造的城市反而成为了阻扰社会共同体形成的障碍,这一异化过程的解决方案当然不是将人们赶回乡村社会,那么唯有重构城市社会,如此,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的建构就势在必行。
一、公共领域理论视野下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需求
城市社会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并无确定的概念,一般研究认为其源自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公共集会场所,如广场、公园等,城市研究者从空间角度出发,认为其是指城市中所有开敞的、没有围墙的开放空间,可供所有居民公共使用的空间[2]。而社会学者则从公共领域角度出发,更为强调公众参与及对话的实现,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认为的交往,公共空间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公共空间的特征毋宁是在于一种交往结构……是在交往行动中产生的社会空间。”[3]对照当下的中国城市社会,公共性不足毋庸置疑。从实体空间看,纯物理性空间诸如公园、广场、海滩等建筑空间受制于财富、权力等资本效应的影响越来越大,表面的开放性并不能掩饰其公共性的逐渐流失,因此,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的建构应当首先强调公共领域特性。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针对的是市民社会兴起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他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4]当前我国城市社会现状与之最为相似的特点也在于此,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比2011年增长8.1%[5]。这些社会组织,绝大多数都植根于城市社会生活,它们的蓬勃发展表明当代中国城市社会活力开始显现,城市居民主体性觉醒,结社等共同体需求逐渐成为城市社会的表征,作为与政府、市场并列的三驾马车之一的社会组织正在中国城市社会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二者不同的是,市民社会强调的是在主体性前提下的交往行为,即通过主体的自我表述、相互沟通之后达成共识行为。这种交往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就是公共空间的存在,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以后,城市居民个体对于自身的公共空间需求感大为增加,开放性的公共场所无论新建多少依然面临短缺的窘境。更为重要的是,既有的政府权威主导下的城市管理格局已处于拙于应对的局面,市民社会则为之开创了达成善治的可能,但有其前提条件,原本居于客体位置的居民群体应平等地与政府、市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活动,这就需要为之提供能够足够多的开放性场所,通过公众议题的纳入及共识行为的认可等举措赋予其公共性。
二、城市碎片化引发的社会公共空间缺失
(一)城市快速改造导致基层社会共同体的幻灭
作为社会性“动物”,共同体需求一直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我们曾经将之描绘为对故乡的怀念,或者说是文化之根的追寻,这种共同体需求表现在城市社会实体中,就是“社区”(community)实质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历史速度,使得城市社会生态基本处于一种震荡无序的状态,这其中,基层社会共同体的破灭最为明显。一方面,生产力能量的释放,工业化引领了城市化的方向。快速城市化与世界城市化进程遵循着同一个规律,即由工业化引领发展方向。工业化既是城市化的引路者,又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这样的城市必然按产业的轮廓塑造成型,打上工业化的深深印记,使其在特征上表现得更象一个庞大而畸形的产业怪物而非宜人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平衡,在放开身份约束之后,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涌入城市寻找美好生活,这一波人口流动整体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但在大量人口的城市基层单位渗入方面却是无序的,他们对于既有城市基层共同体而言是破坏性导入因素。
原本在城市基层社会单位存在的“社区”(共同体)受到了这种快速城市化的冲击而不复存在,既有的城市“街居制”格局已无法纳受这种剧烈变化带来的冲量,最小的城市社会单位原本以共同体方式存在的熟人居住院落在受到城市化的双向冲击之后——既有空间格局的重新规划以及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只能成为工业城市化的附着物,即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人口的暂时寄存地,这种依赖于产业布局形成的人群聚集地只能是机械性的人口集中,相互之间的社会联系纽带极为稀少,无法形成彼此的相互认同。同时,既有的城市基层社会共同体由于受到城市扩容以及人口涌入的影响也无法保持以往的共同体存在,虽然在政治生活层面上依然能通过两委换届选举的举措达成相互间的交往,但其他形式的沟通行为则大幅降低。以深圳为例,曾经存在的300多个村现均改为社区,但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通常一个社区中原住民约1000人,而外来人口则为20000人左右),居住格局的急剧变化都使得依托原住民社会交往网络构成的共同体幻化为泡影。
(二)地理空间的割裂凸显城市阶层的分化
当前的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型都市,空间规划基本是依据产业发展制定的分功能区布局,这在一方面使得人与事的分离,即城市居民工作、居住、娱乐等生活场景的碎片化,每个人都被空间分割成不同的时间段主体,片段之间的分离随着城市的扩大以及功能区分布的加剧逐渐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在加入阶层维度后,这种功能分区越来越细化:高档小区必然与农民房相去甚远,金碧辉煌的购物中心毗邻的一定是金领白领阶层出入的写字楼,工厂社区附近只能是简陋的篮球架。宽阔笔直的快速路将城市分割成一个个孤岛,名义上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局促于属于自己的岛屿,但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全部的城市生活中。endprint
每一座城市孤岛上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该岛的村庄——封闭型社区(是指与更开阔城市环境相隔离的有界区域,其往往被描绘成恐惧和特权的地区[6])。作为城市特有的社会产物,封闭型社区代表了城市居民的异化趋向,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因为恐惧自己的同类而将自身层层设防,以致回归个体化存在。但这种恐惧并非一般化的状态,它根据身份、阶层等的差异分级,最外围的高墙及警备装置是为了防范潜在的入侵者,同时透露出对于其他阶层或身份城市社会群体的不信任与排斥,通过这种城市建筑实体——道路、围墙、摄像头——将自身隔离于整个城市背景;其次,孤岛内往往设立社区会所、幼儿园、私有道路,加强岛内的认同并区别于其他社区,而且其往往会将一些公共资源例如学校、医院、公园等通过各种方式隐性纳入孤岛范畴,进而逐渐吞噬既有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画地为牢地分割了城市原本就极为缺失的实体公共空间。
以财富作为衡量标准的阶层分化现象日渐显现,富裕阶层往往会利用财富为自身群体营造排他的居住及活动空间,并出于对其他贫穷阶层的不信任而对城市政府提供的全社会公共空间持抵制态度,由于所占资源优势与消费社会的实践主体相结合导致其往往能将原本归属于整体城市居民的社会公共空间半公开化地纳入自身独享范畴。中低收入阶层则由于无法享有与富裕阶层相同的公共空间而产生消极情绪,并对富裕阶层整体产生排斥和归咎感,阶层之间从而丧失了对话的可能性,也使得政府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构建意图落空。
(三)人群分治理念导致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的缺失
建国以后实行的户籍制度管理沿袭至今,政府的社会管理制度设计基本上是以之为根基,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的现实却对其提出了挑战。我们通常关注到的城市人口统计常分为三类: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政府则往往根据对象采取不同的制度设计,从而在实际意义上人为地分民而治,导致人群分裂,从而无法构建共有的社会公共空间。
我们以深圳市PS街道SB社区为例,该社区总人口约18000人,其中户籍人口1465人,外来人口16535人,外来人口中约13000人是在此居住工作超过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在社区换届选举中,根据法律规定,仅有不到10%的户籍人口拥有选举权,选举产生的基层自治机构——社区居委会也因此只对10%的户籍人口负责,并在众多事关该社区民众切身利益上引发矛盾,例如公共资源的引入与利用,居委会合法地享有对政府公共资源的建议及监督权力,也因此会要求这些公共资源的受益对象进行等级排位,进而引发社区人群间的对立排斥——我们与他们的争夺,也就使得在城市基层社会中无法营造共享的社会公共空间。
三、实体与虚拟社会公共空间建构
如前所述,无论是作为实体建筑的城市,还是作为人口聚集、社会活动频繁、矛盾冲突日益激烈的社会而言,碎片化导致的公共空间已然成为稀缺资源。而现代治理理论的核心要素就在于多元主体间的平等协商,城市管理者无法依照既往模式来实现有效治理,多重矛盾的叠加效应需要各类城市主体在更多的社会公共空间中实现沟通交往,进行对话,进而达成一致的城市发展理念、思路及做法,但前提是我们的城市拥有足够的社会公共空间。构建城市社会公共空间,意味着在城市布局上的留白——为实现多元主体间的有效交往营造出必要的建筑空间,这在一方面要求包括公园、体育场馆、文体场所、代表会议厅等在内的社会公共空间的实体化,更为重要的是取消既有的城市单位之间的藩篱,打破横亘在各类城市主体间的交往障碍。
(一)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的实体性建构——开放性实体空间的建构
1. 开放性小区建设。相对而言,城市阶层之间的分化及其隔阂积重难返,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的实体性建构可以从最为基础的居民小区开始,经由开放型居住小区的营建推进公共空间的建构。出于治安的考虑,当前城市小区都以围墙栏杆等防御性装饰将自身独立于城市空间之中,形成封闭型小区,根据众多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开放型社区更易形成街道公共监视(eye on the street),也因此较封闭型小区更为安全。当然,我国城市发展尚未达到西方城市的成熟阶段,转型期引发的各类矛盾更易于在城市社会当中爆发,治安始终是城市居民较为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居住小区也无法实现完全性的开放,但突破性的尝试却势在必行,带有穿透视觉效果的围栏装置较之于高墙更易于外界所接受,小区内活动场所的公益性开放更能引发周边人群的认同,居民小区的此类实体性做法将有助于公共空间的建构。
此外,将自在自然的居民小区而非行政话语当中的社区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community)共同体,也就是说,还城市社会基层自治以其本来面目,每个居民小区,无论是富裕阶层的高档小区,还是打工仔聚集的工厂宿舍小区,抑或是村改居小区,又或者是人群混杂聚居的小区,破除身份限制,以小区内居民的合法意愿表达为前提,经由居民人群的交往沟通,达成居民小区内的基层社会自治以弥补当前的管理失灵,这是更为根本性的开放型小区建设,也在最基础的意义上形成了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的最小拼图。
2. 公共场所的开辟。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的重要载体就在于公共场所。对于目前的我国城市而言,公共场所依然是稀缺资源,无论是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等公共文体场所,还是公园、游乐场等公共游乐场所,又或者是社区服务中心、矛盾调解中心等公共沟通场所,都存在严重短缺的问题。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必须以人口分布计算结果为标准,加快这些公共场所的规划建设进度,满足城市居民公共空间需求。这其中,固定的公共场所点的建设是起点。另外,要破除既有的孤岛效应,将原本固囿于某些特定人群或某些特定区域的公共场所重新释放出来,使之成为各个居住空间以及各类人群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回归其公共性本源。与前二者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根据居民需求构建出城市社会公共空间系统,这一系统,是以宏观的城市文化(即居民认可的共同体精神)为引领设定开放的社会公共空间圈,与以中观的城市不同阶层人群追求为背景规划连通的社会公共空间带,及以微观的和谐邻里关系营建为目标的社会公共空间脉络相互贯通的立体系统,真正实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互联互通、相互补充的公共场所整体布局。endprint
当然,我们所说的实体性社会公共空间建构,是建立在这些建筑空间符合公共领域理论这一一般意义基础之上的。它们是人们的活动场所,更是不同主体间平等交往、相互沟通、论辩异同、求同存异的场域,这才是这些城市空间内在于那些钢筋水泥森林的价值所在,也是碎片化状态下城市重构的关键所在。
(二)城市社会虚拟公共空间的建构
步入网络时代的人类社会,早已将自己的社会结构乃至群体意识投射到网络这另一维度的世界,也因此,我们可以为现实世界中严重缺乏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问题寻求网络答案,相较于乡村,城市无论是网络社会所需的物质设备还是居民的网络需求都已清晰地表明在虚拟社会中构建社会公共空间的可能性。由于儒家文化背景、教育、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影响,相较于他们的前辈,当代中国城市人的现实社会交往频率呈现下降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社会公共空间需求意愿的降低,也不意味着他们只愿回归个体性需求而不再关注于周边公共事务乃至某些社会主题。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达到18.7小时[7]。在无数的虚拟社会沟通中,对于城市社会公共空间最为重要的就是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的不断涌现。城市居民在各种虚拟社区发表着小到自己对于小区养狗事件的看法,大到城市交通规则制定的意见,在这些虚拟社区中,人们经由技术手段实现了跨空间时段多群体的沟通,典型的如早期的同学录(alumni)和当下十分流行的微信群以及在城市商品房小区中普遍存在的家园网。除去建筑实体因素,虚拟社区完全符合城市公共空间的定义,因此,也有学者将之认定为这是实际意义上的“社区”(community)共同体[8]。
当然,本文所意图构建的以虚拟社区为代表的城市虚拟社会公共空间里的参与者虚拟身份与实体身份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主体唯一性。同时,不同于以道路和建筑物来点醒的实体空间,虚拟空间自有其运行规律,如何将纷繁复杂的虚拟空间建构成碎片化城市重构所需的公共空间,仍将有章可循。
首先,开放性规则的设立,与实体空间一致,虚拟公共空间建构的第一原则就是开放性,即为每个有意愿并关注其生活着的城市的参与者提供交流的可能。其次,公共精神的塑造,这就要求每个参与者在此平台上交流的内容既是关系自身的更是联系他人的,此外,开放性的交流平台拒绝话语权的特定对象把持,参与者既是评述者又是倾听者,虚拟公共空间需要的是平等的对话而非一方独大的布道。第三,公众舆论有效性,虚拟社会公共空间不同于其他虚拟社会的地方在于现实社会对于在此平台产生的公众舆论能够较为迅速地进行回应,参与者因此逐渐认同该虚拟空间,并由此与其他参与者相互间搭建起共同体的桥梁。
总之,在大踏步的工业化过程中,我们的城市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居住其间的人们由于社会公共空间的缺失而丧失了构建共同体的可能,生活在彼此隔离的城市孤岛,如何将碎片化的城市重构,使之成为人类作为主体存在其中而非受制于彼的社会空间,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发展命题,符合公共领域实质的实体建筑类以及虚拟社会类城市公共空间建构成为当下的应有举措。
参考文献:
[1]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2.
[2]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106-107.
[3]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 童士骏,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445.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
[5]黄晓勇,潘晨光,蔡礼强. 民间组织蓝皮书: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3)[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
[6]Low S M. The Edge and the Center: 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 Discourse of Urban Fear[C].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0:78-84
[7]CNNIC.第29次全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2-01-16)http://www.cnnic.net.cn/research/bgxz/tjbg/201201/t20120116_23668.html.
[8]Wellman,B.and M.,Gulia,“Virtual Communities as Communities”,in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Smith M.A.,& Kollock,P.,Ed.London, Routldge,1999:167-194.
责任编辑 张忠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