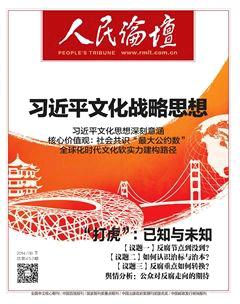旧日时光
2014-09-24毛云尔
毛云尔
旧日时光
毛云尔
蝴蝶与裸奔
第一次接触裸奔这个词大约是二十年前。那时候,因为没有现在这么多直观的、纷纭的刺激,所以,哪怕是一个简单的词语,也能够让你想入非非。而这种想象仍还停留在浪漫的层面,与时下热门的性之类的东西,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不妨这样认为,裸奔就像一片小小的月光,或者是一枝出墙的红杏,它将我带入到一个境界。这种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当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仿佛读一首古典的唐诗或者宋词,只是它比我所接触到的所有唐诗宋词,稍稍热烈一些,富有撩拨意味。事实上,我就是在一本诗集里与它不期而遇的。作者是有“诗魔之称”的台湾现代著名诗人洛夫。在那本厚厚的诗集里,我迄今仍记得其中的句子。
当时,诗人大概跋涉在一条陡峭的青石板铺成的道路上。道路的尽头,是高高在上的一座庙宇。正值黄昏时分,寺庙里钟声缭绕。太多的钟声无法盛下,便如水一样,从寺庙里溢出来,然后,顺着青石的台阶一路汩汩流淌而下。诗人在这里将钟声比喻为一只贪吃的羊,于是,便有了似乎是信手拈来的诗句:顺着台阶/一路/啃将下去。我仿佛看见,在钟声走过的地方,一些苔藓之类的植物,在它们卑微的身体上,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羊的牙齿印儿。在这首描写钟声的诗歌里,我没有读出丝毫的禅意,倒是儿时养羊的经历再一次浮现出来。
裸奔是另外一首诗歌的题目。而我仅仅记住了题目。当裸奔这个词突然跳入我的视野时,我的视线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久久缠绕其上。
如今,置身于光怪陆离中,我之所以还能够时时记起一个简单词语的原因,我想,除了它是一片让我想入非非的月光外,或许还因为它是一片带着锋芒的月光吧,如同一把柔软的刀子,曾经在我的身体里划下一道不易觉察的伤口,带给我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痛。其时,我是一个放羊少年,渴望成长为一个乡村歌手。做一个叶赛宁式的乡村歌手,是我当时最大的梦想。一如叶赛宁在俄罗斯广袤大地上漫游一样,在幕阜山脉的一个皱褶里,我漫游着,我多么希望自己的身体也是“不停歌唱的忧伤的器官”。
当时,我的歌唱几乎全部来自那些乡村美好的事物。如阳光下发烫的泥土,如磨去了棱角依然坚守着大地秘密的砾石,如一只顺着台阶一路撒欢并啃将下去的羊。而裸奔则让我看见了另一些更为美好的事物。这些事物是阴柔的、隐秘的,在乡村生活的舞台上,它们并没有显赫的位置,它们退缩在舞台的后面,处在一个似乎被遗忘的角落里。甚至可以说,它们,仅仅是人们睡梦中无意流露出来的一串梦呓而已。
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当我第一次接触裸奔这个词语时,我突然想起昙花。在深不可测的夜的底部,昙花悄然开放,就像沉寂的火焰亮了起来,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那被火焰的光芒打开的夜幕再次合拢,于是,昙花被涌上来的厚厚泥土一样的黑暗湮没。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为这个骤然出现在脑海里的比喻而暗自叫绝,至今仍然认为,昙花所指代的事物,最贴切的莫过于发生在乡村夜晚的裸奔。
那个裸奔的人,也许是一个刚刚成熟的十八岁少女,她的肌肤有着凝脂般的腻白,又像大理石一样光洁。或者一个年过四十的中年妇女,历经磨砺的身体满目疮痍。她们拥有相同的愿望,在这个恬静的夜晚,她们渴望自己的身体尽情地舒展开来,袒露无遗,没有丝毫遮拦。在她的想象中,舒展开来的身体仿佛一对能够飞翔的翅膀。然而,这仅仅是一次短暂的飞翔练习,或者说,这是飞翔的又一次夭折。在湘北大地上,在气温回升的六月的夜晚,我多次目睹过这样的飞翔。
就在某处朽旧的屋檐下。一个女人,距离和黑暗已经模糊了她的年龄。她一丝不挂地呈现在那里,映衬着四周的黑暗,她的身体有着朦胧月光的光泽,甚至让你觉得,那就是一片既古老又新鲜的月光。一天的劳作已经让她精疲力尽了,一天的汗水使得她的身体变得暗淡与黏糊,于是,她用干净的井水一遍遍洗刷自己。突然,那哗哗的水声戛然而止。她开始仔细地打量自己的身体,似乎发现了什么,或者被遗忘的又被她突然记起,她就在屋檐下,在黑暗的深处,试探着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如果继续这样奔走下去,须臾功夫,她将抵达一块开花的黄豆地。黄豆的花朵将如潮水一样翻转过来,簇拥着她。穿过黄豆地,前面不远是一座青色的山冈。耸立的山冈自始至终给人一种离天空很近的感觉。
可是,就在她刚刚走出两步的时候,也许是一个过路人无意的一声咳嗽,她迅速转身,又重蛰伏到屋檐下凝重的黑暗里。像一朵绽开的昙花,转瞬凋零;像一片刚刚展开翅膀的月光,跌落到尘埃里。
不由使人唏嘘慨叹。在这方面,一个人根本比不上一只蝴蝶。我私下认为,一只飞翔的蝴蝶才是真正的裸奔。当一只蝴蝶从蛹的包裹下脱身出来,它的身体已经无遮无拦,没有了丝毫束缚,它在天地间翩然飞行,体验着飞翔所带来的快乐。
看过一些介绍蝴蝶的书籍,得知一只蝴蝶,能够吃下许多带毒汁的叶子,能够在蛹里度过一段暗无天日的时光,如此韬光养晦,就是为了最后破茧而出。可想而知,一只蝴蝶在裸奔的道路上要历尽千辛万苦。而一个人和蝴蝶的区别,其实就在最后的这一刻。一个人在裸奔的道路上,甚至比蝴蝶要吃更多的苦,历经更多的煎熬,可是就在破茧而出的紧要关头,几乎所有的人都退缩了,没有谁敢往前再走出一步。
在火焰一样的细草中间,如果有一只蝴蝶翩飞,没有谁大惊小怪。倘若有一个人,将自己的身体从衣服的包裹中伸展出来,仿佛一只翩跹的白蝴蝶,所到之处,将会引发怎样的骚动呢?至今,多年前那场骚动的后遗症并没有在人们的心中痊愈。她是一个疯子,几乎所有的人都还这样异口同声地认为。
她是我曾经就读的一所乡村中学的代课教师。十五年前,在一个桃花盛开的日子,她用三天三夜的时间,完成了村子里前所未有的裸奔。没有谁知道她裸奔的确切原因,大家只是揣测,她是为一个男人神魂颠倒的。所幸的是,她很快又回到衣服里,很快恢复了蛹的状态。很快,她和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着。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为她感到悲哀,这是从她失败的爱情的角度来考虑的。后来,我又为她庆幸,毕竟她飞翔过,不同于大多数人那样一直蜷缩在蛹里,慢慢死去。
葱兰
用葱兰来譬喻那些乡村的女孩,似乎再恰当不过了。在我生长的湘北,随便哪一个村庄里,都可以看见这样一群女孩。一群尚未成熟丰满的女孩。离豆蔻年华还有那么一段并不遥远但也称不上短暂的距离。此时的她们,是懵懂的、混沌的,尚未知道怎样打扮自己。当你和她们在某个正午不期而遇,一定不愿多看她们几眼。确实,她们的身体是那么单瘦,脸膛那么黝黑,凌乱的头发上扎着一个廉价的蝴蝶结,她们风一样从远处的山岗跑来,又风一样消失在远处的树林里。望着她们背影消失的方向,你仅仅愣怔了片刻,就继续着你的行程。几年之后——具体是多少年呢?三年,抑或四年?你无法搞清楚了。当你再次从这里经过,你会惊讶万分,昔日那些女孩脱胎换骨,仿佛豌豆花一样,开放在村子里牵牵绊绊的藤蔓上。
无论素净还是淡紫,豌豆花一律给人明眸善睐的感觉。仔细瞧瞧吧,在豌豆花流转的眼神里,有太多热烈与奔放的成分,而缺少的,是属于这些乡村女孩的羞涩,以及被她们埋得很深很深的那份对幸福的期盼。所以我觉得,用葱兰来形容更恰当,更有入木三分的效果。
然而,葱兰是怎样一种植物呢?我想,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的。如果时间倒转到五年前,那时的我和此时的你一样,头脑里也是一片茫然。其实,即使现在,我对葱兰也知之甚少。这种植物仅看外表,俨然就是一株葱了。一株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营养不良、薄薄瘦瘦的葱。它的叶子又细又长,颜色暗绿,一点生气也没有。整整一个春天和接下来的漫长夏天,它就以这个其貌不扬的样子蛰伏在我家的阳台上。
我缺乏养花这方面的热情。在我家的阳台上,都是一些类似葱兰一样不需要过多照料的植物。一个简陋的瓦盆,一点点泥土,便是我为它们力所能及提供的一切了。在这里,因为楼房高耸,甚至整整一个冬天都漏不进一丝阳光。幸运的是,风是清新的,从远处的山谷源源不断地流淌而来。更加幸运的是,头顶的天空无遮无拦,早晨起来便可以看见植物们的叶尖上挂着颤颤巍巍的露珠。想必,它们对这样的环境毫无怨言,而且容我大胆猜测,它们是如此心满意足。多少夜阑时分,我从未听见过它们哪怕些微的抱怨和呻吟声。在缓慢的时光中,随遇而安的它们就这样卑微且宁静地生长着,于出其不意中给我一个惊喜。
葱兰的貌不惊人,经常让我忘记它的存在,一如多少次在乡村的小路走过,脚步从不会为路边那些植物——诸如匍匐的地衣和马背筋草,稍作充满敬意的短暂停留一样,我也很少在葱兰面前驻足。但葱兰,总是在秋天让我眼前一亮。当秋天在不经意中来临,一切事物都在时光的调排下无一遗漏地变化着。这种变化,或轰轰烈烈,或悄然无息。可以说,葱兰的变化属于前一种。在某个醒来的早晨,它一下子就抓住了我惺忪的视线。此时的葱兰,一改过去的低调和收敛,身体依然暗绿,骨子里却透出几分张扬。
我无比惊讶。在这个秋天的早晨,葱兰又细又长的叶子丛中,高高地顶着一个花苞。仿佛置身陌生人群之中,眼前骤然出现一个热情招呼的手势,把内心的寂寥瞬间打破了。那花苞,白得像汉白玉一样;那花苞,丰腴得如同一截手臂。那花苞,欲开未开,仿佛即将撑开的一把油纸伞。这样的花苞大大超乎了我的想象。惊讶之余,我静静地等待着它绽开的刹那。
葱兰一定是在夜阑时分绽放的。第二天早晨,当我再次来到阳台上,只见四片汉白玉一样的花瓣舒展开来了。恍惚中,那是一个长大了的乡村女孩正撑着一把好看的油纸伞,在绿色的田埂上一路走远。这样的情景,仿佛某个湖畔派诗人笔下一咏三叹的句子,深且远的意境,让你在其中难以自拔。
这些年,每年秋天,我都会到乡村走一走。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棵离开泥土太久了的树,内心里有一种焦渴。然而,乡村的秋天一年不同一年了,再也寻觅不到过去那种热闹和喧哗。接二连三的人从乡村离开了,包括那些葱兰一样的女孩子。那田埂,还在天空下弯曲着;那山坡,还在阳光下敞开着怀抱;那浅浅的小溪,依然把琴弦擦拭得锃亮……那调皮的风,还在树林里盲目穿梭,却再也捡拾不到那些树叶一样的脚印和窃窃私语了。
一株葱兰。一份念想。
我家阳台上的这株葱兰,是五年前一个乍暖还寒的初春,同事老陈送给我的。五年前,老陈还教两个班的语文,业余喜欢舞文弄墨,写一些古体诗词。五年前的老陈经常利用周末,不怕路途遥远,风雨无阻,到某个偏僻的河滩去钓鲫鱼。这株葱兰就是老陈在钓鱼回家的路上发现的。他把它送给了我。当时的我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表情,内心里还多少有些不解和困惑。常言道:送人需好物。可是,老陈竟然送了这么一株其貌不扬的葱兰给我。老陈绝对算不上文人雅士,我亦如此。老陈这样做,仅仅是好玩而已。如今,五年过去,老陈再也不能去河滩钓鲫鱼了。老陈中风偏瘫,左手臂不能抬起,沉重如铅地垂坠在胸前,左腿也有气无力,走起路来必须用右腿拖着缓慢前行。他很少出门,只是偶尔出来走一走,透透气。每当瞥见他一歪一斜的背影沐浴在晨曦或者夕辉下面,就会想起和他一起共事的情景。自然,他送我葱兰的那个乍暖还寒的初春依然历历在目。内心里顿时一片苍凉,同时会生发一些感慨,譬如时光易逝,譬如人生无常。诸如此类。
一株葱兰。一声叹息。
毛云尔,作家,现居湖南平江县,已发表作品若干。
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