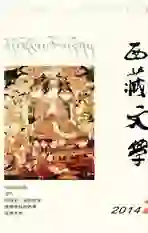西藏羊皮书
2014-09-21凌仕江
凌仕江
说来有些奇遇,在凉水滑过山沟沟的夜晚,看到喜马拉雅的那一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它根本不是画报上一次次所呈现的那种圣洁的画面,它分明是逃出森林狂想曲里的世界最后的乡村音乐景致,它是蓝星球上掉下的一颗眼泪,它是女神梦幻里的一个飞吻。
天慢慢地被金色的云朵擦黑了。当云朵完全被高耸的雪峰收容的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了挂在天边的月亮。初冬的喜马拉雅,层林尽染的肌肤,最打眼的是银色的坡地,一重一重的坡地,一直扯到了天边边,四周峰簇峥嵘,经旗随风而舞,山谷里不时掠过一缕枯木逢春的花香,所以,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经常能看见天上挂着的是一个银色的葫芦。这怪诞的比喻,一般人难以理解。但实事就是如此,在喜马拉雅的白天,太阳的形状有时也像一个成熟得快要落蒂的黄丝瓜。至少我不会认真地将它们准确地辨认为月亮或太阳。
此时,喜马拉雅也被一片银色的月光浸染。那片月光慢慢向西,向山林隐没的海子移动,它几乎是顺着坡地性感的银色线条在移动。我看到在银白色的月光移动中,喜马拉雅变得更富迷人了;由于月光在动,喜马拉雅的流水声似乎也在由重到轻地淌,这种淌如同一个白色键盘上的音符,是一团银色的星光的涌动,越来越慢,似乎已经在银色的丝绒中停滞起来。
那些丝绒就是中国唯一、世界罕见的以高山湖泊群、钙化滩流为主体的自然景观。因了冬季的来临,湖面上里面点缀着几朵舞蹈的雪花。
月光顺着那些阡陌的湖泊从我面前移动过去。此时,我发现那些丝绒犹如色彩变幻的荧光屏在眼前翻转。当它们在越过我的时候,我看见湖水的内层被银色的月光照亮,那样清水般的月亮,清纯、洁净、晶莹、剔透,看上去里面夹杂着很深,也很厚重的一缕墨色,如同水墨在宣纸上曼妙的速度。月光移动过去之后,湖面只有一层淡淡的亮光,像是经过了电光的过滤,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暖色调,好比喝了一壶润透心房的薄荷凉茶。有时,我又怀疑其中的一缕不融化的东西是传说中的蓝冰?让人觉得喜马拉雅仍不是一座山的事情,而是那个比《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小镇更遥远的西圣地。
这时候,一位满头梳着辫子的女人,一边往这边走,一边哼着无字的歌谣从叠瀑里走了出来。空旷的冬夜忽然有了她的歌声,一下子就打破了宁静和孤独。她走到我跟前,看不清她的脸,只感觉她在愣愣地望着月光中的九寨发呆。她的目光真的很深沉。我觉得她有点奇怪,怎么忽然瞅着喜马拉雅就发起了呆。过了一会儿,她表情非常复杂地看了我一下,然后转过身去,准备离去。
“哎,卓玛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和她说几句话,就使用了用来称谓“姑娘”的这句藏语,叫了她一声。在我看来,在喜马拉雅,只要见到美丽的姑娘,都可以唤她为卓玛,不管她们生为什么民族,这个如花似玉的称呼对于喜马拉雅的女人们甚至可以通用。
她听到我的叫声后,转过身来,准备去抚弄耳边的辫子,那只手在半空中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了回去。她疾步走到我跟前,也像我一样说了一句:“哦呀,难道你是在叫我嘛?”她的声音很有磁性。
我们两个人都不说话,临湖而立,望着月光中的喜马拉雅,长久地沉默着。
此时的喜马拉雅仍旧是一片银晃晃,我仍然感觉不到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绝世风景,河流边全是绚丽多彩的冰瀑,可这毕竟已然冬季呀。
这时候,我发现她的右手上有一只篮子吊在她的银色手环上。再仔细一看,她的那只篮子里也是银幽幽,一片一片的银色变出不同色彩的光从她的篮子里流出,滴在我的眼睛里。此时月光正瘦黄,因而她的那只长长的手臂看上去也是瘦黄瘦黄的,银色的浆从她长长的袖子里一直流进篮子里。
其实那不过是高山上滴落的水,好比歌中唱的一面湖水藏在地球表面的一颗眼泪。
“你的篮子里装的什么……”
她把手伸到我跟前。我看见她的手心捏着一株草。她把手翻过来,我触目惊心地发现,那是一株通体青蓝的草,还散发着泥巴的味道。我知道紧挨着喜马拉雅的背面,到处都长着三毛草。三毛草较之于其他喜马拉雅的植物花草,似乎有着不一般的意义;许多寺院周围都长满了这种草,甚至有人还把这种草挂于墙上。
“你怎么不在这个冬季上山采摘雪莲,而在夜晚来采三毛草?”
“刚才,我朝天上看了一眼,这株草就跑到我手上来了,原本我是出来找灵感的。”
“找灵感?你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
“我是画家,我有一个学生就在河的对岸,那里有一个村庄,最初它的名字就卓玛。”
“你常来这里体验生活吗?”
我扭头去看河对岸,她仍然在出神地望着喜马拉雅。看她的样子,她很想向着喜马拉雅惊讶地问一声,阿妈啦,告诉我,我这是身在何处?但她很快又将目光递给了篮子里的神秘物。
“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到这里写生,可以说每个季节的喜马拉雅我都体会过了,冬无严寒,夏季凉爽,四季景色各异,仲春树绿花艳,盛夏幽湖翠山,金秋层林尽染,隆冬冰塑自然。你不会以为我只是在向你说童话吧?告诉你,喜马拉雅之所以神奇,是因它以翠湖、叠瀑、彩林、雪峰、蓝冰、藏情‘六绝和得天独厚的动植物资源被人们誉为‘童话世界、‘人间仙镜,这是名不虚传的世界著名旅游胜地噢。”
话完,天边纷飞的雪花已经染白了她的头,如此宁静悠远,充满诗情画意的夜晚。我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望着山峦和树林银装素裹;蓝色湖面上的冰层在月光移动的温差中,变换着奇妙的冰纹;而冰凝的瀑布间,潺潺的水流发出沁人心脾的仙乐,我真想这一生就在这里不离不弃。
她问我,你怎么会选择这样的时节来喜马拉雅?
我说我正是来感受与体验藏民族风俗的最佳时节的,因为我从朋友那儿得知这个季节将有许多民间和宗教活动,其中包括神秘的宗教法会,将给蒙尘的心灵带来宁静致远的另一番激情体验。原来,喜欢艺术的人都容易在常人不喜欢靠近的季节里出没或相遇呀!
“我本来想一个人到坡地尽头去看看银月亮的,我已经在这个冬季的夜晚出没很多次了,但从没看见喜马拉雅的冬夜里居然有异乡人,因为我感觉在我写生的记录里从来都没有发现喜马拉雅的冬夜出现藏族以外的人影会是这样的神奇,他离我太远又太近,但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知道他的心懂得了一个地方的倾诉。我决定不去那个坡地了。”说完,她坐在湖边,拿出了篮子里的东西,就是和天上挂着的那个玩意一样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才记起,当时她的满头的辫子甚至全身的颜色和喜马拉雅一样,都是被银色笼罩的。事过多年了,每每想起喜马拉雅,我都深表怀疑——那个冬天的夜晚究竟是卓玛的喜马拉雅?还是本来面目的喜马拉雅?那是手持画笔跃然纸上的艺术家笔下的喜马拉雅?还是有着超现实自然派画家路易·萨贺芬之美喻采撷艺术灵感的卓玛的喜马拉雅呢?
这个梦,我不知做于何时何地,是在日喀则?还是在山南?或是在内陆的某座繁华都市的席梦丝床上,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北京,梦中的自然景致比现实的风景美得多,但我想说喜马拉雅真的可以美过梦境,因为它是圣洁的,没有人敢在它身上拔刀乱刻,它让我不屑于满身刻满了历代文士官员们颂词的五岳之泰山,我不知那些在山上五花八门的题字者真正的见了西圣地的喜马拉雅或珠穆朗玛,会不会羞愧地蒙上脸,悔当初说“登泰山而小天下”之类的话。
扎西的婚礼
原本扎西并没有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对于他的婚礼我只能算个不速之客。在西藏,我的藏族朋友很多,他们都知道我对他们的事儿很感兴趣,无论走到哪个角落,总有人牵引我认识新的藏族朋友。而在我心里头,有时一个牧童,一棵树,一只羊,或一个村庄的炊烟都能以朋友的身份进入我的视野。可以说,扎西的婚礼,是在没有任何熟人引荐的情况下,我在路上遇到的一桩喜事。
那是一条从贡嘎通往山南的路。
绚丽的晚霞给路边的村庄披上了金纱。
阵阵欢快激扬的六弦琴声吸引着幸福路上的行人。
前面的车停下来了,不少人从车窗外观望村庄里的热闹场景,我好奇地让司机停下车,迎着琴声奔去。
路边,一座贵族的藏式楼房门前,地上用白灰撒绘着莲花、海螺的吉祥图案。陪同我的司机也是个藏族人,他说藏历年春节已经过去几天了,显然,这吉祥图案意味着村庄里正逢另一喜庆事情。路边,许多未有见过藏式婚礼的路人都好奇地走到了一起。
我们跟着络绎不绝的藏族人攀着木梯而上,经过走廊,来到一间宽敞的客堂。
没错,一对藏族年轻人在举行婚礼。
新娘身着七彩藏装,戴着一对嵌着松耳石的耳环,胸前佩戴着一堆光闪闪的珠宝,脸上的胭脂和香粉让她显得格外漂亮。新郎则是一身崭新的解放军军装。很多人叫他扎西。巧的是一打听,才知扎西曾经的确是一名驻守在错那的边防军人,只不过他已经退伍两年了,还保持着军人的作风。
客堂正中长长的卡垫上,新娘和扎西俯首并坐。客人们依次手捧洁白的哈达,给他们献挂在脖颈上。也有小孩将手中采摘的格桑花撒在他们身上。不多一会,新人就给“埋”入哈达和花瓣里了!见此情景,我嘱咐司机也去车上取来哈达,献给这对幸福的新人。
新人面前有一张彩漆雕花矮长桌。桌上摆着的“竹素切玛”前放着一花瓷碗“哲斯”(白糖糯米饭)和一碗“措玛哲斯”。两旁放着彩釉高颈陶壶(藏名:来莫)和高脚大银花碗(藏名:煨波),陶壶上系着哈达,银碗缀有酥油花瓣,装满浓浓的青稞酒。这是我在西藏许多地方看到的藏式婚礼必备不少的摆设。
哈达献毕,客人们一一献礼物,把各自的红包放进一个红纸糊的箱子里。父母和来宾在人们的簇拥中致祝词。然后,新人端碗,互向对方敬酒。这时,人群中起哄的声音一浪压过一浪,甚至还伴随着尖厉的口哨,看来,这酒是必须一饮而尽的,尤其是在场的老人们绝不容忍新人碗中剩下一滴酒,因为这杯酒下肚之后就代表他们婚后敬爱终生。
随后,新郎提“来莫”,新娘端着“煨波”,来到宾客面前,向每人敬酒三大碗,感谢客人的祝贺。扎西走到我面前时,停了下来。司机上前向扎西说明来意,扎西欢喜地将我介绍给他的新娘旺姆。司机生怕我拒绝喝那么多的酒,一直在耳边提醒解释。他不知我早已熟悉藏区的风俗礼仪。这种饮三碗,三口一杯的酒礼,他们叫做“松堆聂塔”。
敬酒到了最后,一位老者在人群中弹着六弦琴欢唱起来。
这位边弹边唱的老者叫罗布次仁,是扎西家特意从山南艺术团邀来的一位民间艺人。在古城拉萨,我看到过这样的艺人表演,在一些藏人的婚庆或重大民族节日上,他们的弹唱和舞蹈是融为一体的。老人花白的胡须飘洒在胸前,能在扎西的喜典上轻抚琴弦,他心情比过任何节日都高兴。灵活的手指在弦上欢快移动,琴上系着的两支彩穗也似乎乐得跳起舞来。在老人深情的琴声中,穿着节日盛装的嫫啦(老太太)和波姆(姑娘)举杯、提壶,在新人和客人面前也尽情起舞高歌,敬劝喜酒。昔日安静的村庄就这样沸腾了。
酒歌唱得月亮圆,
云雀飞来不想走。
哈达连着颗颗心,
情与天地共长久。
天上星儿稠,
人间情意厚。
呀拉索,呀拉索……
仪式结束了,扎西与我这位不速之客开始了闲聊。他先是拉着我向他的父母做了介绍。看上去,这是一对年轻的父母,穿着都很城市化。他们一边忙着接待客人,一边朝我点头微笑,双手合十,表示欢迎。藏族同胞从来都是很好客的,何况今天又是喜庆的日子。婚礼上有不少的陌生路人来送祝福。扎西的父母拉我们坐上彩垫,敬酒的嫫啦和波姆就提壶端碗来了。在西藏,一个汉人过分的推辞是不礼貌的,尤其是面对盛大的婚礼和藏历新年,我连饮的不止三杯,而是三碗,并且双手合十向新郎扎西新娘旺姆道了:“扎西德勒!”
听我以藏语祝贺,扎西更高兴了。那么多亲人都帮着新娘新郎给我敬糖、敬酒、敬甜茶、酥油茶,不容拒绝的情谊会把我的心窝子暧成了被窝。
旺久是新郎扎西的爷爷。他,头戴狮耳金花帽,腰缠青色的氆氇藏袍。听说我想进一步了解他们当地的结婚风俗,旺久一面热情地招待我,一面兴高采烈地指着室内的各种摆设,他时而用一只手蒙住眼睛,向我介绍它们的名称和意义,声明这些是藏式婚礼不可少的。我被那些木式结构的家具久久吸引,上面有雕花的马鞍和青稞以及花朵。我入神地看着这些精美的藏式工艺,一边想着旺久那只曾被人挖掉的眼睛。
接着,新郎扎西引我参观了新房和客房。到处闪耀着彩色,到处充满了歌声,到处可闻酥油的芳香。尤其是新人的房间里,不知是谁用酥油捏了一对小新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吸引了不少看客的目光。
扎西的嫫拉(奶奶)次仁央吉,见我到处赞叹他们家的美好,她又乐滋滋地上前邀我下到底楼,让我参观了她家那堆满粮袋的仓房,参观了畜栏里的羊和一排排横木上的风干肉,又引我参观了酒库。一进酒库门就是醇甜的酒味扑鼻而来,数了数,共有二十八个大坛子的青稞酒!这真是一个富足之家呀。我问老阿妈,这酒要喝到啥时才能喝完呀?老阿妈自豪地讲,明年这个时候吧,等你路过我们村庄时,闻到酒香就一定再来呀!
次仁央吉介绍,西藏过去的婚姻制度十分复杂。当时普遍流行的有三种:一妻多夫,一妻一夫,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在贵族世家颇流行,因为世家爵位只有本家的人才能承袭,分家后财产分散,爵位不便继承,兄弟共娶一妻就利于维系世家。这种家庭多是以妻子为中心,妻子权力是大的。一夫多妻的,多是大商人在几个城镇都有老婆,协助经商。各个妻子不分谁主谁次。也有部落头人娶几家有财势的女儿为妻,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那时,婚前的男女社交活动也很自由,婚前生了孩子也不受歧视。婚后妇女地位比较高。可是,一般地讲,配偶仍要父母决定,并十分讲究门当户对。至于奴隶就根本没有婚姻自由,未经主人允许是不能相爱的。
旺久和次仁央吉给我讲了他们老俩口的“婚礼”,那是一段曲折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听上去像是传奇,又像是一部写不完的长篇小说。
旺久是日喀则一家大领主的养马家奴。五十年代的一个夏天,主人要去几十公里外的红河谷温泉洗澡派他随同当杂役。女奴次仁央吉见旺久忠厚,相处五十天中彼此爱上了。
可是,这事并没有得到主人允许。幸好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藏区进发,一些领主惊慌极了。旺久趁机约了次仁央吉偷跑到了家乡山南。因为怕领主追究,只向亲邻讨了一些吃的,提心吊胆地向父母敬了三碗青稞酒就算举行了“婚礼”。从此,新婚的夫妇便提着打狗棍,求乞度日。
不久,他俩却被主人找了回去,只得隐瞒彼此的夫妻身份,分居各方。生了笫一个男孩不敢向主人说,生了笫二胎仍然不敢承认是夫妻。但这事仍然被管家发现了,就要责打旺久。旺久急忙说生的两个都是男孩,管家才息怒。原来,按当时噶厦政府规定,奴隶夫妻,生的男孩归丈夫的主人所有,生的女孩归妻子的主人所有。两个男孩就给男奴隶的主人增加了两头“会说话的牲畜”,长到十一二岁便能接奴隶的班了。主人这才用了大约能买一只羊的藏币向另一财主将次仁央吉买来当了家奴。不过,次仁央吉每年还得给曾经的财主交人头税。
从此,这对已经举行“婚礼”的五年后并且有了两个儿子的奴隶,才被承认是夫妻。
半夜已过,客人们纷纷告辞。路上醉酒者还在欢唱,我们沿着月色,向着山南进发,心里想着扎西一家三代人如此悬殊的婚礼,是命运弄人?还是光阴可憎?耳边还有歌声在回响:
太阳是漂亮的新郎,
月亮是可爱的新娘;
新郎新娘的伴当,
由我启明星来担当。
世上最轻的船
它轻便易行,不畏惧碰撞,不怕漩涡,不担心激流,在世界船族中称得上独一无二的特色船。我想,即使走遍世界,你也很难见到这种长约三米,宽约二米,形状像北方孩童的娃娃鞋,用牛皮缝制,用枝条绷紧,用一个船夫行驶的可坐五至十人的船了,除却遥远而又苍茫的西藏。
旧年的西藏,水上的运输工具总离不开它。
或许你想到了,我要说的就是轻如蝉羽的牛皮船。这种轻,看上去如同灯光下一张染了色的宣纸,有种透明的感觉。
不知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的创造发明了,这样的创造发明现在看来实在是因地制宜创造的最佳典范。这样的创造发明在当时是否申请有专利?在漫山遍野的西藏,出现眼帘最多的当属牦牛,这些常被诗人们比作雪山上盛开黑色花朵的动物,对这样的船只贡献何等了得。由此,不难想象西藏曾经是牦牛驮在背上的民族,正如人们习惯的审美说新疆是马背上的民族一样。因为牦牛身上质地优良的牛皮,自然也就派上了制作牛皮船的用场。我一直很感激西藏人民能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既智慧又诗意。在西藏,牛皮价格便宜,制作程序简单,水上功能起到了如木船或机动船等任何船在西藏替代不了的作用。而它的灵动与自由也有着牦牛般的属性。
西藏的大江大河太多,礁石和漩涡更多。那漩涡仿若一座孤岛,从深水底下大面积一下鼓起来,又扩散开去,反反复复,像魔鬼在水底下施展魔法。而牛皮船遇此险情,总能轻轻地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潇洒地绕过去。即使逆流而上,也如真正的轻舟一叶。
如今,行走在西藏的江河边,看到的牛皮船并不多了。许多废弃的船皮搁浅在河边的沙烁上成了一种古老的摆设。而当年一只只在拉萨河里如鱼儿般游来游去的牛皮船莫非是被时光的风吹走了?当那一轮机动船播放着《泰坦尼克号》的音乐从拉萨河对岸驶来时,许多站在河边等候的人都挥动双手,大声地惊呼着,渴望上船去看水上的风景。有一对青年男女在船头拥抱着,他们的姿态与表情太想成为电影的主角了。
人群中有一位藏族老者看见男女拥抱在一起的样子笑了。我觉察到老者的笑容里有一种比空气更轻的淡然,尤其是他火光般红红的眼睛里,盛满了比拉萨河夕阳更深的忧郁。
“这船有啥好坐的呀,哎!”
我不紧不慢地接过老者的话,“对岸那边的风景比这边好看罢。”
老者有力地摆摆手,一扫我的轻浮与无知。他走了几步,又退回来,看都不看我一眼,便自言自语道:“那只船,迟早要沉的,你信不信?”
“为啥?你凭什么诅咒他们?他们不就是想充当一回电影中的主角,享受一回河风吹拂脸皮或发梢的滋味吗?”
……
一番长聊,我被老者的话语震撼了,原来他是五十年代拉萨河上的船夫。后来,我在老者的家中看到了他解开缆绳,摇起双桨的一帧黑白照片。那是一张在八寸木镜框里泛黄的老照片,老者在照片中的年轻时代可谓英俊逼人。照片上还有抱孩子的藏族妇女,以及几个手持望远镜的解放军。让我好奇的是,船舱里伫立着一头硕大的羊。见我对于那头羊的专注,老者不时地掩面而笑,看上去有种羞涩的喜悦。
“这羊是船上那位客人买的?”
老者笑而不答。他的表情隐藏了太多求知的秘密。他一边看我,一边摇动酒壶。我只好继续猜测了。
“莫非是你们船夫用来看守船的吧?”
哦呀呀,老者笑得更得意了。他一手甩动胡须,不声不响地做着自己的事,似乎他的表情还有让我继续猜想的欲望。看着他红火般的眼睛,想了又想,我仍然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答案。究竟这只站在牛皮船上的羊会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肯定是你们在船上镇邪的吉祥物。”
老者果断地摆摆手。他昂起头,饮尽一碗青稞酒,示意我不必猜测了。然后,随意把我带到客厅的另一侧。墙上除了金碧辉煌的唐卡,还有一组陈旧的照片,上面是一群背船的胴体男人,他们头上的麻花辫子,绞结着鲜艳的红头穗。他们体态强壮,一人扛着一条船,在阳光下成了一道吸引眼球的风景。他们不用拉纤,只需要在水边的拉萨河,将船扛到地面上晒干就完成任务了。记忆中,似乎在一些年老的画报上看到过如此诗意的风光画面。走在扛船男人前面的永远是一只羊。它是一个船夫的全部,背上驮着衣物,还有路上吃喝的油盐烟酒茶。
真没想到羊与人的关系会如此紧密。在西藏,一条牛皮船把人和羊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我看见了历史,也看见了历史中西藏人民经受的苦与乐。
每逢藏历四月十五日是萨嘎达瓦节,这是藏族人民为了纪念释迦牟尼降生、出家、圆寂的日子。路边随处可见桑烟飘然。男女老幼一早转完八廓街就到龙王潭游玩。湖中间修有一座4层高的古式楼房,名为“洛康”(龙宫)。这是个绿柳成荫、湖水碧波荡漾的季节,更有雄伟的布达拉宫倒影映在水中,真是一个湖光秀丽、景色迷人的游玩胜地。过去西藏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活佛、贵族,带着亲人到这里欢度节日,乘坐牛皮船便是萨嘎达瓦节的重要活动之一。宗教上把乘坐牛皮船的善男信女称作是普渡苦海、洗脱灾难,将来可以升入天堂。所以这一天游人特别多,大家争相乘牛皮船游玩。
当我带着美好愿望来到龙王潭脱离苦海的时候,已经得不到牛皮船坐了,因为我看见的“海”并不苦,彩色的鱼在清澈的水面上看人的各种表情,龙王潭早已改变书页上所记录的模样,湖边的柳絮与花朵正欣然地看着每一抹经过湖边的影子。
我又来到了拉萨河。浊浪之上,我不知看见的是羊,还是船?河边除了我,什么也没有。水中一米多长的鱼在摇头晃脑地看着我,它不怕我,我却怕它。几只红嘴鸟拍打着并不平静的水面,它们立在经杆上,被风吹得很快失去了方向。水边的经幡,不与水合作,它们总是逆水而居,唱着阿姐鼓的歌,比风更安静地凝望着河岸之上的布达拉。我想那一艘唱着《泰坦尼克号》的机动船是随风远航印度洋了吧?它会遇上大风暴,像泰坦尼克一样撞击冰山,沉入喜马拉雅海底吗?坐在那些被风沙排挤得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牛皮上,我知道历史现存的遗迹太轻太轻,而我和我的现实太重太重,纵然牛皮船被河边的沙子埋掉了一部分,可我用尽全力也抗不起。
因为那部分的西藏,我并未在场。
多年以后,我在离开西藏的日子里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在西藏,船夫与一只羊的关系密不可分
他们好比一条路与一棵树
路上没有旅店,没有饭馆,没有人烟
假如你我在水一方
一天两天的日子没有什么都可以
但一个懂生活的人绝对不能没有羊
与多年前的那只羊相遇
那是德西梅朵家的羊。
在朵底路,我远远地就认出了它。还是那一撮胡子和那一对锋利的羊角。当时,围观羊的人都围着它挤来挤去,一点声音也不发出。很快,一堆人便将一只羊围得水泄不通。透明的阳光穿过细碎的树叶子安祥地观望着羊和人群。不远处,大昭寺前白塔里的桑烟染灰了半边天,膜拜大地的人们匍匐在油亮的石板上,他们像虫子弯曲、蠕动、抬头,眼里看见山鹰抖落的灰。
风在阳光休眠的墙角转身的时候,越过斑马线的人越来越多,挤在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里面的人究竟在欣赏什么精彩的表演,只顾拼命地往里面挤。有骑自行车的人,使劲摁着铃铛路过此地,迅即停下来。楼上有人倚着窗子也在朝地上的人群张望,还有三轮车夫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来者停下来,他们围着圈子,排出几条队伍,像一个八卦图,人人都渴望成为最里面的人。
忽然有一个人从里面冲了出来,大声喊道:“就是它,尼玛,达娃,快来,就是它,我们终于找到它了!”
随之而来的尼玛和达娃,几步迈进打开渠口的人群,一下子怔在那里。那只羊像来自另一个星球,因为人群与光线的原因,它很不自在地耷拉着脑袋,漂亮的双眸像两颗墨蓝的宝石,它浑身洁白的毛和飘逸的胡子,如同一座石膏做成的白色雕塑。有时,越精彩的表演,也容易任人一言不发,这便是动物的境界。而人的某些境界往往缺失了动物的自然美。
羊在人群中一步也不曾挪动,显尽高贵之美。它真的要接受人们的审问吗?
尼玛蠕动嘴唇,眼睛不曾离开羊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他不紧不忙地踱着步子,似乎在搜索羊内心的阴谋,他怎么也想不到羊的一声“咩”会给天葬台带来如此的不安与反响,手中木质的念珠转动得飞快。
达娃认真地斜视着羊的眼睛。她在想什么?
索性,她像看出了羊的什么破绽,跑到尼玛身边,交头接耳,滴滴沽沽,四只眼睛充满了刀光剑影。
“阿爸,我真想打死这只羊。”尼玛手中的念珠停止了转动,他将手伸向屁股,握住藏刀把手。
达娃眼睛死死地盯住羊,生怕它会在瞬间飞走。可是羊看都不看她一眼。她恨不得钻进那两颗墨蓝墨蓝的宝石里,偷窥羊的秘密。太阳扬起沉重的光翼,她的情绪像是进入了回忆,一只手紧紧拉着阿爸的手,轻轻把脸避到一边去,小声地咬牙切齿道:“打死它,也不足以解恨。”
只有阿爸边巴玖美一声不吭,他的手使劲地拉住尼玛正在拔刀的手。
人群里议论纷纷。有的说,就是这只羊害了边巴玖美一家的幸福生活!也有围观者反对说,怎么人倒霉,会怪在一只羊身上来哟?边巴玖美听到这些话,默默地低下头去。
羊不理会这些声音,它目中无人地呆在人们拉长的阴影里。羊的影子有时是羊,有时更像是人,一动不动。而动的部分始终是人群,人的圈子总是离不开骚动,有的在出去,也有的在进来。羊时而将头高高昂起,它在欣赏远处的风景,风扬起它飘逸的胡子,白白的云朵在雪峰上移动,那漂亮的胡子和羊角在阳光下泛着一抹刺目而斑斓的光彩。
“你们别再看了,达娃带走它吧!”尼玛向大家拱拱手。
“哥,带走干嘛,就在这里杀死它得了,让大家也看看一只羊的下场。”达娃一脸懊恼。
“杀死它,杀死它,这犯忌的羊,让人灵魂升不了天,该死!”人群大声叫嚷,有不少道听途说者,有年老的男子,也有年轻的女子。
尼玛伸手从阿爸怀里取出粗壮的绳索,拴在羊的脖子上。
达娃拉着羊就要走。
“咩。”
羊在抗议,它的双前掌狠狠地抓着地,不愿前进半步。似乎在声嘶力竭地吼“你们凭什么要处决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有什么办法呢!这只羊在天葬台破坏了天葬师阿卡的招魂术,在阿卡朝着尸体挥舞斧头的一刹那,羊的一声尖叫,驱散了所有神招而来的鹰群,剩下尼玛、达娃的爷爷在那儿,鹰群迟迟不再来,亡者灵魂无法升天了,看来只能这样了,这只羊死定了。”这是一个年轻的红衣喇嘛说的。
羊耸耸脑袋,对说这话的喇嘛报以冷冷的一笑,然后打了一个响鼻,一声长叹“咩”。
“它是一只放生羊,决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群嚷道。
但达娃并没有停下来,她在使劲拉着羊往前走。羊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路人。当他们经过布达拉宫广场的时候,那些面朝宫殿五体投体的人们狂怒了。
“你们要把它怎么样?羊是无辜的。”人群中有人责怪。
羊在微笑,如同唐柳下一丛丛的格桑花笑得嘻嘻哈哈,它把头昂得更高。目光的尽头是光波闪闪的江流。羊不屑于为它说话的群众,甚至对尼玛一家人的行为感到荒诞。
“没错,我承认是我的尖叫,赶走了鹰群,使得它们没在预期的时间内干掉天葬台上躺着的人尸,但我也是误闯入天葬台的,因为我以为那里躺着的是我的主,德西梅朵。”羊说道。
此话刚落,离广场不远的马布日红山,在一片肃静中,忽然传来一个人的哭叫声。当人们望声而去,那声音就来到了人群中。
“咩!咩!”一个妇人在用羊的叫声唤羊,她推开人群往羊的地方靠近,“羊!我的羊,他们要把你怎么样?等一等,你们最好把我也带去,带去!”
妇人旁边的人群停止了叫喊,他们为这突然袭来的妇人受到强大的冲击,人堆里忽然之间闪开一条道来,让她往羊那边去。
“瞧这羊,多像老妇人的孩子!”一个女人说。
“你要找谁呀?”那个年轻的红衣喇嘛向老妇人俯下身去,问。
“我要我的羊!让我看看我的羊!”妇人尖声回答。
“你的羊闯大祸了?你知道吗?”达娃说。
“你们想把我的羊怎样?”妇人问。
“回家去,我的主,我们回到藏北那儿去。”羊看见妇人说。
尼玛与达娃相互对视,脸色越发阴沉了。
“她没有家,只有一只羊相依为命!”边巴玖美对两个孩子说。
妇人在人群里一直往前挤,挤到羊身边,双手捧着羊的脸。
达娃一直高叫着:“阿爸,若这只羊不死,爷爷的灵魂如何升天?”
边巴玖美一言不发地望着妇人。
“你和我一直走在一起,干嘛从我身边跑出来的?”妇人对羊说。
“我从八廓街与你离散后就到处找你,那里朝圣的人太多,我一直在找你呀,我的主,我找遍了拉萨的山山水水?”羊说。
“你现在怎么办。”妇人说。
“什么?”
“他们要处决你,说你犯了他们生活的忌。你认识那个天葬师吗?”
“那个住在药王山上的神职人员?怎么不认识,我们来拉萨朝圣的路上,多次遇见他。”
“好吧,你先到他那儿去,待在那里。我……我就来。”
“你不去,我也不去。”羊哭起来。
“你为什么不去?”
“我走了,他们会为难你的。”
“不会,他们不会的,我理解他们的信仰。”
妇人从达娃手上拉过绳索,从羊的脖子上取下来,她拍了拍羊的头,羊朝着妇人点头,转身,走了几步,回头张望着妇人。
妇人把尼玛拉到一边,“年轻人,听我说,”她说,“你们要打死我,不论怎样都行,也不论在什么地方,但就是不要当着羊的面。”她指指羊,“你们放它离开后,你们要怎么打死我,就随您们,只要你们放过我的羊。”
“不行,羊犯下的罪,怎么让你一位老妇人来顶?”尼玛十分不解。
“让羊走!”但边巴玖美同意了。
“阿爸,你,你,你……”达娃很生气。
妇人抱起羊说:“去吧,到天葬师那儿去,他会说你无罪的。”
“我的主,你呢?”
“你瞧,我同尼玛一家谈谈就来,你去吧,我的羊。”
羊盯住妇人,头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一边走,一边思索起来。
“去吧,我的羊,我就来。”
“你一定来吗?”
羊听从主的话。它的影子在暴烈的阳光下转身。
等羊看不见了,妇人说:“现在你们可以带走我了,我愿意替我的羊去死。”
这时候发生了意见完全意想不到和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所有这些一时变得残酷,对羊充满仇恨的贵族人身上,另一个神灵觉醒了。那个年轻的红衣喇嘛说:
“我说,把妇人放了吧。”
“唵嘛呢叭咪吽,”又一个人说,“放了她。”
“放了她,放了她!”人群叫喊起来。
“放了她,因为她的羊在等她。”我默默地为未来的一部西藏大片写下了这个句子,后来,又隔了几年,我已经离开西藏,便把这个句子改作了“放了她,因为羊的力量。”
你看,她朝着羊狂奔而去,像一匹马,在风中转身。是的,今天的太阳是为一个叫德西梅朵的女人升起的。同样,也是为我和一只多年前相遇的羊升起的……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