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傅惟慈
2014-09-15叶兆言
专 栏
纪念傅惟慈
翻译家傅惟慈是一个在不同的时代,都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高人。
上世纪80年代出国热潮下,熟悉的老同志中,一心想到国外去看看的,除了老画家柯明,还有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傅惟慈与柯明同年,也是今年逝世,享年92岁,能活到这把年纪,也算高寿了。
只知道傅惟慈是满族人,他的家庭背景不太清楚,想来也不会太糟糕,一个能学会几门外语的人,没点家底达不到那境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英文好,还是德文更好。傅惟慈选择作家眼光独到,我们都喜欢他看上的外国作家,顺带也喜欢上了他。
最初知道傅惟慈,是“文革”后期。他是我堂哥三午的好朋友,常在一起玩外国音乐,一起胡说八道。“文革”后期是非常特殊的年代,极“左”是大背景,没文化是总趋势,然而总会有那么一小撮人,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傅惟慈当年的标签就是“翻译过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人》”,这是他人生中得意的一笔,翻译这本书时,他不过三十多岁。
我最初的世界文学知识与傅先生有关。那时候高中刚毕业,待业在家无事可干,成天看外国小说。他知道得很多,就给我和三午布置题目,让我们写出自己最喜欢的100本外国小说。这样的题目搁今天,或许没啥意义,在1974-1975年,应该说还是有相当难度。那年头,看过100本世界文学名著的年轻人并不多,而我只是个17岁的文学少年。开始凑数字列排行榜,前50本书最容易,争议也最大。傅惟慈兴致勃勃参加讨论,以内行的语气开导我们。印象中,傅惟慈谈吐从不掩饰对西方世界的向往。“文革”年代毫无自由可言,可是心灵自由阻拦不了,黑幕下也会有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在我看来,当时的傅惟慈很像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活在“文革”中却与世隔绝,内心世界早已充分自由化了。
“文革”年代毫无自由可言,可是心灵自由阻拦不了,黑幕下也会有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文革”一结束,傅惟慈迫不及待地要往国外跑。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不抓紧不行。最初的机会是到国外讲中国当代文学,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虽然火爆,就品质而言,能入他法眼的作品很少,但是只要能出国,能出去见识见识,让他讲什么都行。我堂哥三午羡慕得不行,说这家伙终于跑了,美梦终于成真。他从三午那拿了一沓不齐全的《小说月报》,到飞机上去准备讲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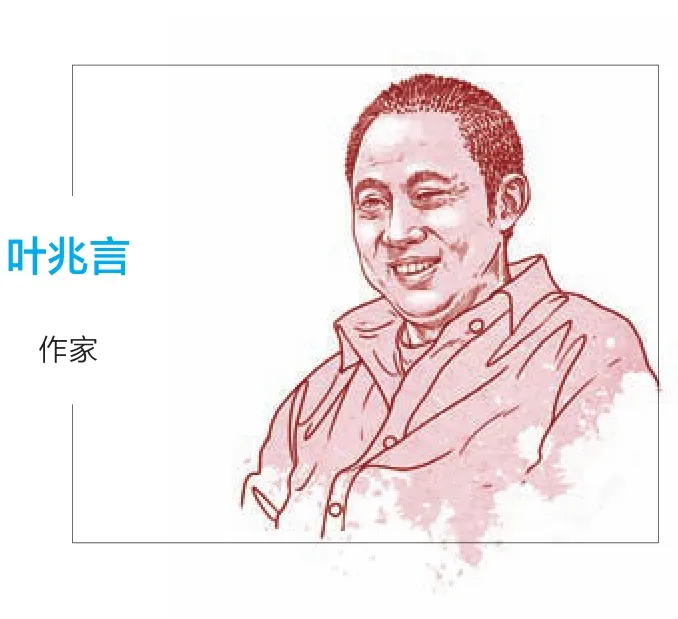
不难想象,出国会给傅惟慈带来多大欢乐。一个搞外国文学的教书匠,都快退休了,竟然还没有出过国开过洋荤。他曾悄悄地对三午说,已到这把年纪,只要能出去,出去一天是一天,快活一天是一天,多待一天是一天。这以后,傅惟慈常往国外跑,他在国外讲学,住集体宿舍,拜访心仪的作家,始终像个老顽童。因为语言优势,他很适合待在国外。三午死于1988年冬天,生前曾抱怨说傅惟慈忘了老朋友,不知道他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快活呢。
傅惟慈是一个在不同的时代,都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高人。解放前夕,选择了革命。令人压抑的50年代,选择了托马斯.曼。让人无话可说的”文革”,选择了逃避和外国音乐。粉碎”四人帮”,选择了出国,晚年又选择了留在国内养老。傅惟慈的人生虽然没有激烈对抗,却总能享受快乐和幸福。
大约是在1975年,三午带我去过傅惟慈家。他很喜欢三午的诗人气质,喜欢三午对文学的热爱,觉得三午很有写作才华。说自己年轻时也想过要当作家,终究是时代太不适合,他的性格和才华也不匹配。当年一起聊天,他和三午一致认为,在那个年代,在”文革”的沙漠中,文学也就说说而已,中国肯定不会出作家。傅惟慈不会想到,当然三午也不会想到,他们身边那个十多岁的文学少年,后来竟然成了一名作家。
几年前,译林出版社让我为蒂姆.拉瑟特的《父亲的智慧》写几句话,传了电子版译文过来,刚看到介绍,曾产生过拒绝的念头,可是内容完全吸引了我,译笔也非常漂亮,觉得非常好,很认真地作了序。当时不知道这书是傅惟慈翻译,出版社编辑根本没提。在我心目中,他是翻译界的大腕大拿,不会把兴趣转移到心灵鸡汤上。
如果知道这书是傅惟慈翻译,序中我一定会很隆重地提一笔,一定会把多年来对他的敬重写进去。文学上,傅惟慈无意中给了我像父亲一样的教诲,曾潜移默化地影响过我,有着深深的启蒙意义。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遗憾的擦肩而过。我很懊悔,当时为什么不多问一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