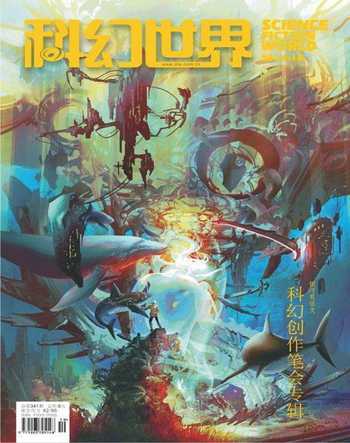又见贝蒂
2014-09-10杨潇



飞机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缓缓停稳,我匆匆赶到行李提取处,却不见贝蒂。临行前,我们曾约好在这儿见面。我一边四处张望,一边想象:七年不见,她现在是个什么样?
行李转盘处已空无一人,我慢慢转到栏杆外,见一老太太正坐在长条椅上与人聊天。我走过去细看,她华发灰白,消瘦萎矮,这就是当年那个雍容优雅的赫尔博士?
老太太显然感觉到了什么,她轻轻转过脸来,“你好啊,杨潇!”她抿嘴一笑,嘴角弯成好看的月牙。真是贝蒂。
我弯腰拥抱她,瞥见一根拐棍靠在她身边,我连忙轻轻扶起她。贝蒂拄着拐棍,领着我慢慢朝停车场走去。
坐进车,车前玻璃窗上贴着刺目的残疾人证。
唔,二十五年竟然就这样一晃而过……
1989年,应世界科幻协会WSF之邀,身为《科学文艺》(《科幻世界》前身)主编的我飞抵意大利,拖着装满刊物的沉重书箱,到圣马力诺参加世界科幻协会1989圣马力诺年会。这是中国科幻界第一次有代表出席世界科幻会议。
在会上,我结识了赫尔博士(Dr. Hull)。她的丈夫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erik Pohl)是美国著名科幻作家,也是WSF创办人之一及前任主席。赫尔博士则是美国科幻研究会(SFRA)前任秘书长、WSF美国分会理事。赫尔博士早在1981年就造访过中国,她与科幻小说翻译家吴定柏、王逢振、郭建中等一见如故;1983年美国科幻作家代表团一行七人访问上海,波尔、赫尔名列其中,著名作家叶永烈作为上海市科协常委、世界科幻协会理事在上海科学会堂接待了代表团。我仰慕赫尔博士已久,可站在她面前,才知大名鼎鼎的Dr. Hull是位女士,芳名伊丽莎白。
初次见面,赫尔博士给了我极大帮助。
当时,随行的翻译因病留在罗马,我不得不独自与会。按照会议议程,各国代表介绍本国科幻状况,最后投票决定1991年WSF第47届年会的举办国。当时,波兰、前南斯拉夫是两个竞争国。而首次参加WSF会议的我对议程一无所知。临行前,众编辑突发奇想,提议邀请WSF到中国举办年会,无知即无畏的我也贸然将此提议加入演讲稿。
WSF会议历史上首次出现中国面孔,老外纷纷表示欢迎,说中国代表与会,WSF更具世界性。
轮到中国代表发言,我走上台,宣读了精心准备、熟读多遍的英文发言稿,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向各国代表当面发出邀请。结果可想而知,我英文不好,听力尤差,面对WSF“多国部队”的连连提问,我紧张得发懵,嗫嗫喏喏,答非所问,只得重申翻译生病缺席,我英文不好,下来再与各位交流。好在WSF秘书李伍德女士善解人意,安排其他代表继续发言。我强自微笑着走下演讲台。李伍德和我走到另一间小会议室,她写下代表所提问题,我借助英汉、汉英两本袖珍字典,再加上日本科幻小说先驱《宇宙尘》创始人柴野拓美的夫人写出和中文字相仿的日文汉字,艰难地连猜带蒙地回答各种问题。
当时我无路可退,狼狈不堪,只得硬着头皮,强带微笑,操着蹩脚英语,讲述中国科幻的广阔前景,欢迎外国作家到中国体验博大的东方文化。
凭借英汉、汉英两本袖珍字典,依靠诚挚执著的态度和WSF众多代表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反而赢得了许多赞誉和尊重。WSF圣马力诺会议投票结果竟然是:中国成为WSF1991年会的举办国,年会定名为“WSF1991成都年会”!
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幻大家布莱恩·奥尔迪斯、弗雷德里克·波尔、哈里·哈里森等纷纷向我祝贺,WSF各国主席也过来握手拥抱,李伍德说我“With little English done lots of things”,赫尔博士更是赞誉我“勇敢……克服很大困难,为中国赢得举办权”,“ Admire you”。
我懵了,自觉此行丢人现眼,遭遇滑铁卢,他们却认为我克服极大困难、坚持信念,为我鼓掌颁奖。
这一懵便是许多年,之后我反反复复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1989年初夏的那个晚上,蒂塔诺山巅上的圣马力诺古堡笼罩在神秘夜色之中,月光下的WSF闭幕晚宴惬意、轻松、浪漫。我和赫尔博士端着盛有猩红葡萄酒的高脚杯,周围环绕着西装笔挺、长裙曳地的绅士和女士,我俩在玫瑰花香中穿行。她不让我称她为“Mrs. Pohl”,我叫她“Dr. Hull”,她也摇头。她告诉我,她的昵称是贝蒂(Betty),要我叫她贝蒂,让我称波尔先生为弗雷德(Fred)。
大概由于我的“勇敢、坚持”,高傲的赫尔博士对刚认识的我敞开了心扉。她娓娓讲述她和波尔的一见钟情,波尔甚至在1984年某期的《Locus》杂志公开刊载表白:“伊丽莎白·安,嫁给我吧!”这则传奇佳话风靡国际科幻界。那晚,贝蒂动情地对我说,“杨潇,你知道吗,我感到我用了一生在等他。”奇怪的是,我居然都“听”懂了。
人际间那种久违了的孩童般的透明与纯真令我怦然心动,我全然忘了她的国籍、身份和年龄。她像个小女人般喃喃细语,讲她的丈夫、她的爱情、她的女儿……说到动情处,她眼中闪烁着莹莹泪光,嘴角又抿成一弯好看的月牙。于是,我和她——WSF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倏地变为两个讲闺房悄悄话的女友。
1989年那场风波后,WSF决定1991年不在中国举办年会。四川省政府要求组团再赴荷兰,参加1990WSF海牙年会。在会上,我再次见到贝蒂、波尔、奥尔迪斯、哈里森、斯宾雷德、柴野拓美、鲍诺夫等国际科幻界名流。在激烈的1991WSF年会举办国的竞争中,WSF美国、英国、瑞典、芬兰、苏联、日本等分会主席及WSF几位举足重轻的创始人极力主张维持WSF圣马力诺年会决定。贝蒂走上讲演台,她身穿火红的西装裙,平静而有分量地阐明WSF的宗旨,讲述科技发展给人类思想带来的深刻影响,她说自己赞同奥尔迪斯的主张:“政治是暂时的,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远的。”她侧身把手中的选票交给李伍德女士,说有五位没到会的代表托她投中国一票。她走下主席台,目光扫过我,举手打了个“V”型手势,我也跷起拇指回应,贝蒂莞尔一笑,哟,又见那弯月牙。
当然,1991WSF成都年会如期召开,当届主席爱德华兹称之为WSF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年会。当时,中外科幻名流大都与会,贝蒂和弗雷德也双双赴会。宣读论文、交流创作,还参观了都江古堰、卧龙林海、国宝大熊猫;波尔、奥尔迪斯、柴野拓美分别代表美、欧、亚点燃三堆熊熊篝火,东西方文化共有的探索精神在火焰中耀眼闪烁……记得车队在卧龙遭遇暴雨突袭,泥石流塌方断路,险境中,贝蒂却依然恬静,那抹抿成弯月的笑容舒缓了我的紧张焦灼。她的老弗雷德更是不凡,所有人都在焦急讨论抢险方案,他却独自伏在卧龙招待所简陋的木桌上,手捏圆珠笔埋头写作,沉溺于思辨科学的迷人奇境。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在北京举办,贝蒂来华参加会议。王逢振、吴岩、贝蒂和我快乐相逢,吴岩家成了贝蒂和北京年轻科幻迷畅聊神侃的乐园。
那些年,大洋彼岸飞鸿频传,贝蒂告诉我,她成功地举办了约翰·坎贝尔奖的评奖活动,忧伤地诉说她的老弗雷德患了肺炎,絮絮叨叨她八十三岁老母亲来家里同住一周,童心未泯地向我炫耀母校颁给她一枚黑勋章……而落款处,总是那个秀丽而别致的签名:Fondly Betty。
1997年盛夏,数十名国际科幻界名人和五名美俄宇航员来华,'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在北京科技会堂隆重召开,成都月亮湾国际科幻夏令营也热烈开营,随太空飞船翱翔环宇的五星红旗挂在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墙上,科幻热潮席卷中国大地。在锦江宾馆四川省外办举行的告别晚宴上,贝蒂把我拉到一边,用手指轻轻梳理我无暇顾及的一头乱发,取下她头上的白色发夹给我别上,仔细把我的乱发塞进发网,温情地和我久久拥抱。
细数起来,贝蒂和中国科幻界交往频繁,她来华不下八次。
2007年,我和朋友驾车赴壶口瀑布途中遭遇车祸,躺在西安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不能动弹,我被疼痛、焦灼、无望紧紧裹缠。不料贝蒂和她的女儿芭芭拉从天而降,手捧鲜花来到我病床边!贝蒂握着我的手亲切慰问,我又听到她说“brave”,她那弯明媚的笑容,那束馥郁玫瑰的丰盈,都随着她的窃窃细语充溢流淌在周遭,我顿感生机活力缓缓注入。我为无法赶回成都参加当年的国际科幻大会而沮丧,贝蒂诚挚劝慰。原来她来华赴会,听说我在西安遭遇车祸,立刻赶来看望。我无言地握住她的手——软软的暖暖的手,久久不愿放下。
前两年,贝蒂告诉我弗雷德九十三大寿了。我寄去精美相册,其中记载着她和她的老弗雷德在圣马力诺、在威尼斯、在海牙、在成都、在都江堰、在卧龙的美好时光。
这次旅美探望弟弟妹妹,我当然要拜访贝蒂,于是专程飞赴芝加哥。
贝蒂家住在芝加哥西北的帕拉丁区。她说自从嫁给弗雷德,他俩在这儿生活了整整三十年。这是一栋美国传统风格的房子,上下两层楼,楼上有多间住房和书房,楼下有宽敞的客厅、两间大书房、女儿凯西的卧室和厨房、餐厅等,地下室还有藏书房和暖气锅炉房;前庭花园小径弯曲,绿茵茵的鹅掌楸树和灌木花丛掩映小楼;后院草坪绿草茵茵,围木栅栏一圈的各色百合花团锦簇。扶着木楼梯走上铺着地毯的二楼,凯西为我收拾的小屋整洁舒适,墙上挂着中国小朋友送给“波尔伯伯和赫尔阿姨”的国画,束着蝴蝶结的蓝色条纹布窗帘像小姑娘的发束,条纹床单和被套散发着刚洗涤过的清香。
贝蒂笑吟吟地告诉我,我是到她家的第三位中国科幻界友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定柏先生在她家住过十一天,王逢振先生也来此拜访。现在YangXiao也来了。只是,她略带忧伤地说,波尔离去近一年了。
是的,去年九月弗雷德辞世,我曾回邮件安慰贝蒂:你已尽心尽力了,你为弗雷德做了那么多,弗雷德是含笑而去的。
站在堆满书籍、杂志、报纸、信件的两间大书房里,看着墙上悬挂的叶永烈先生所赠的水墨山水画,抚摸着五排大书架上厚厚的书籍,恍惚间如同进入时空隧道,波尔与他的好友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布雷德伯里等都在隧道的那一头。面对广袤宇宙,波尔把他瑰丽而奇特的想象,把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生物圈的热爱和对未来探索的前瞻思考,凝结成几十部巨著奉献给世人。科幻世界杂志社上个世纪末曾出版了波尔系列丛书(《人变火星人》《吉姆星》《太空商人》《狼毒》《纳拉贝拉星际演出公司》),那是波尔坐在这栋富含能量场的房子里编织经纬,在键盘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出来的。
时代和生活在变幻,波尔以前瞻独到的眼光从中提炼幻化出他的科幻主题——人口过剩、环境污染、高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低温生命维持法、外太空、火星人、城市穹顶建筑等等——科幻思辨张力由此生发。
贝蒂曾说:“波尔的作品旨在规劝世人要更加和睦相处。”是的,波尔的视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国别族别,无论身处什么环境,无论和什么样的生命形式交往,他都以地球人的眼光审视地球生物群落和外星生物群落的冲突。
波尔已于去年九月以九十四岁高龄谢世,但在这栋他们曾经共同居住的房子里,波尔的气息四溢。门廊前木兰树绿荫浓郁,后花园花木缤纷茂盛,那是他们共同栽种培植的。他们的家庭照片,他的作品、书籍、书信,他的奖杯、奖牌、奖章,夫妇俩的信物、友人的赠品、他俩旅游世界各地时购买的纪念品、以夫妇俩和这栋房子设定的编码,纷纷讲述着波尔和赫尔的传奇故事。
波尔永生——在贝蒂心中,在他的书籍中,在国际科幻界。
贝蒂在家里热情款待了我。她像个干练主妇,为我烤制美国地道的烤鸡、烤鱼、烤虾,蒸南瓜泥、青豆,熬煮加夏威夷坚果和红莓的麦片,烘烤抹了奶酪的百吉饼,凯西则用卷心菜、小西红柿、奶酪做冰冻菜蔬。贝蒂还特意带我去品尝芝加哥最美味的披萨。芭芭拉也赶来看我,说我恢复得很好,一点儿也看不出遭遇过车祸。
贝蒂还拖着肿胀的双腿,驾车带我“跑车观城”。我们参观了伊利诺伊州哈泼学院——她曾是该院的文学教授。她还开车数十英里带我到芝加哥主城区参观。
真不可小觑芝加哥,它不愧为美国第四大城市,古典性和现代性融合得相得益彰,高及云天的摩天大楼栉比鳞次,冷不丁又冒出欧洲古典教堂、老式旧水塔、白金汉喷泉……另一道独特的风景,是老式铁轨横亘于堂皇的现代建筑群中,列车在大都市的繁华大街上轰隆隆地疾驰,像是从十七十八世纪驶来,让人科幻感顿生。特别吸引我的,是芝加哥湖滨城市上空变幻无穷的云,云团、云朵、云层、云片、云丝在湛蓝的天幕上幻化演绎,美不胜收。大概由于芝加哥位于密歇根湖畔,而作为北美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密歇根湖奇大无比,湖面上气流交汇穿行,才梳理变幻出如此美丽、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贝蒂故乡的云。
那天,我和贝蒂坐在后花园喝下午茶,小松鼠在花园木栅栏上翻跃,树叶在风中飒飒作响,百合花香随风飘逸。贝蒂缓缓说到她正着手筹办波尔逝世周年纪念。她慢吞吞地走下露台,拿着花剪闲适地修剪花枝,轻轻俯下身拾捡落叶——这就是那个曾活跃在国际科幻界的赫尔博士——宠辱不惊,去留无意,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上云卷云舒。
又要离去了。算起来,我在贝蒂家只待了两夜三天,老天阴雨霏霏缠缠绵绵欲留客。贝蒂驾车带我去农夫市场,我撑着雨伞、搀扶拄拐的她在农夫市场转悠。每每碰到熟人,贝蒂都骄傲地介绍:“这是杨潇,我最亲爱的朋友,她来自中国。”
是的,贝蒂, 我们是亲密的异国朋友,从1989年直至永远。
另:弗雷德里克·波尔先生,一代科幻大师,以其诙谐风趣的笔调,编织出无数精彩绝伦的科幻故事。时值波尔先生辞世一周年,本刊特选译了一篇波尔先生的短篇经典代表作,将于下期刊登,以作纪念。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