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往前走,为了尊严
2014-09-10甄静慧
甄静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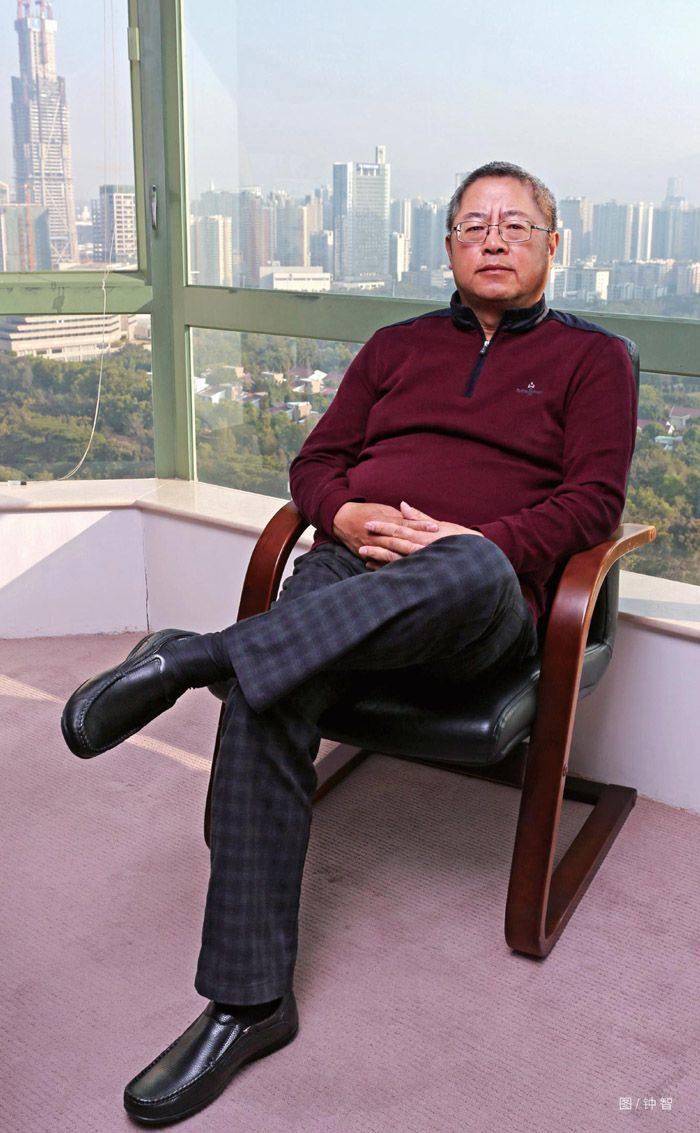
“很多人认为我是策划大师、营销大师,甚至和我攀比,我耻于和他们为伍。”王志纲声调突变,“我哪里只是一个做营销的人呢?我哪里只做房地产呢?”接受采访的大部分时间他略微侧身,抱着手臂—掌控与防御兼具的姿势。但诠释自我时他会激动,音容动作乃至空气都突然呈现出剧烈变化。
15年前独立策划人王志纲很火。
他有一个曲折的成名故事,从颇具才名的新华社记者、无冕之王,大跨度转型为地产策划,渗透着理想主义色彩;也有很多成功案例,广东碧桂园、99昆明世博会、星河湾及南国奥林匹克花园的“华南板块”之战等,至今仍被地产策划界奉为经典;加上系列财智类畅销书出版,这些都足以令他在2000年前后成为亮眼风景。
不过那是从前的事了。红了几年后,随着中国地产业成了“傻子都能赚钱”的行业,王志纲光环也渐渐不再闪耀。他渐渐淡出公众关注,虽偶然也在媒体上露面,年轻一代知道他的人已经不多。
盛名过后,是蜕变还是没落?
深圳深南大道旁一个小区楼盘的29楼,整层都租了下来,一半办公用,另一半作王志纲个人起居室,以便他随时趿着拖鞋就可以出来工作或会客。他也对自己这个习惯津津乐道,以示随意,乃至对来访者的漫不经心。
他善于掌控场面。初次见面便先声夺人,了如指掌地说出一串记者的个人资料,且抢先问:“你为什么想起我?你知道这些年我在做什么吗?”
其实,仅仅看王志纲工作室的网站,很难说出其与过往,或是其他具有一定规模的策划机构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只是2002年后,其早期以房地产业为主的业务重心显然转向了城市和区域发展领域,以及新经济、健康产业等;工作室也发展出了北京、上海、深圳等6个中心,员工接近200人。
但这些年每当王志纲在公众面前出现,都会极力强调王志纲工作室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策划公司乃至商业机构—尽管它日进斗金。
“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和省委书记、省长打交道的。‘西安与咸阳计划’是陕西省委请我们做的,成都的‘天府新居’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做的。”他说,潜台词是,虽然淡出了公众眼球,这些年他与政府的关系却日益密切,用他本人的话说,“潜得越来越深”。
所以如果你像世纪初那样,继续尊他为营销泰斗,他会显得愤怒,感到被贬低,甚至是一种折辱。
是的,哪怕只是时间不长的接触,你也能明显感觉到眼前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他是那么在意外界对他的认知是否与自我认知一致,他会通过不断“纠正”你,以体会完整的自我价值与尊严。
他并不否认,这与人生经历所带来的创伤感相关。
如果没有“文革”,王志纲本是个温室里长大的孩子。直到10岁之前,他都觉得自己很幸福,爷爷是大乡绅,80年前创办了当地第一所中学,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粮食局的中层干部,走在乡里,全家受到的都是尊敬和仰慕。
然而11岁那年,“文革”开始,“爷爷成了大地主,父亲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狗崽子”。“很多贫下中农要保他(爷爷),但在极左的年代根本保不了。最后,押送他的长工半路给了他一点鸦片,自杀了。”年幼的王志纲跟着父母去给尊敬的祖父收尸,心灵受到极大冲击。
自此,他的命运完全颠覆。父亲因为出身多次受到牵连,他在学校更受到了“另眼相看”,“同学和你划清界限,完了还有人欺负你,街坊邻居用你过往完全想象不到的态度对你,你必须努力和他们打成一片”。
而对灵魂深处最大的伤害是,当思想一度被裹挟,那个11岁的孩子真的相信自己有原罪。他跑到社会最底层做泥水工,努力“改造”自己。
“故乡、老家对我来说一直是个不能回忆的地方,是灾难的源泉,一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这些年所做的一切都和这些事有很大关系。要有尊严感,士可杀不可辱。”
在这个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王志纲一路以来的人生选择。
他在自己的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价值最大化是我内心中的一种呼唤。”
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主动选择到新华社当记者,因为这个职业在当时的人们眼中是“无冕之王”,带有特立独行、超然独立之类的理想主义色彩。王志纲在新华社10年,很多时间都住在一个阁楼里面,房子里除了一张床外,连电风扇都没有,可谓家徒四壁。夏天挥汗如雨地伏在床上写稿,实在太热就跑到厕所里面拿凉水浇一下,就是这样写出了包括广东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专题。
对他来说,这段岁月虽然艰苦,却很有成就感,因为“到哪里人家都很尊重你,从省委书记到企业家们”。
然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记者的风光与辉煌日渐不再,这个职业带来的价值感已不足以抚平内心不断反噬的痛苦与创伤。他承认,彼时的自己仍然因自卑而敏感、尖利、睚眦必报。
“但是离开要干啥呢?当时就两种选择,一个是当官,一个经商,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一个独立生存的空间。但我觉得都不适合我。”最后,他一咬牙,在名片上印上“王志纲,市场策划人,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
当时一个老板看到他的名片,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又要自由、又要挣钱、又要独立,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当时就是一个愿景,我要凭我自己的知识、思想去走出一条既不依附于官又不仰仗于商的第三种生存。”这也是当时还敏感和有点小心眼的他迂回地堵上那些讥讽他“出去后一定还要靠新华社的牌子招摇撞骗”的人的嘴,甚至给他们一个耳光的方式。正如很多年后,他还记得去问一下那个嘲笑过他名片的老板:“你说我现在做到了没有?”对方连连点头,“服输了!”他乐了。
王志纲说,工作室里的普通员工,很多都是优秀的博士生。“虽然年纪轻轻,但走出去和省长打交道都是不卑不亢的。”他尤其强调这一点。不过,当这些博士生簇拥在他身旁时又显得格外谦恭。我们整个采访过程,4位穿着深色西装的员工被要求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低调而认真地学习和记录。这里俨然一个以王志纲为中心的王国。
2014年春节前这段时间,王志纲一直呆在深圳,据说很多老板和政府项目负责人因此巴巴地跑到深圳求访。
不管其他同行是否同意,他认为是自己创立了“策划”这个行业。一开始,他在广州创立王志纲工作室,在五羊新城办公,因为新华社任职时期名声在外,生意很快就找上门来,什么都有,卖牙膏的、卖纸巾的、卖酱油的,后来才确立了房地产策划的主要方向。
“它是‘卖方市场’的。”王志纲强调。必须让老板们自己找上门来,而不是放下身段去拉生意—这对他来说永远很重要,那象征着曾被挫伤的尊严重新得到树立。
在《第三种生存》一书里,王志纲开篇就说“老板不是人”—“他们的眼睛是铜钱做的,看到的永远是白花花的银子。他们的鼻子像鲨鱼一样,能够闻到暴利的血腥气味……他们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为了利益就算是祖上的冤家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为了利益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可以撇在一边。”
此前老板们大概从未见过这种人,一边赚着自己的钱,一边还毫不客气拿自己开涮。他们大吃一惊,但还是去买书,不知真心还是违心地说“骂得好”。
这种人生酣畅淋漓,但也是危险的,需要时刻“挟持”着对方的软肋才能保持高高在上的优势。“为什么选择房地产?因为当时他们快死了。1993年政府宏观调控,这些老板们一夜之间全部懵了,我在这个背景下救他们。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否则怎么会低下高贵的头来求你呢?”
然而王志纲也很清楚,一旦自己变得可以取代,双方的关系就会发生逆转。
王志纲恐怕不会同意把“焦虑”、“恐惧”之类的形容词用在自己身上,那么换一种说法,就是他一直很有“危机感”。
2009年工作室的年会发言上,他首次向整个团队正式提出未来要花三四十年时间,把王志纲工作室打造成一个真正的“智库”的愿景。
虽然凭借着过往的成绩、声望,一直在房地产策划上吃老本甚至赚更多的钱,对王志纲本人及工作室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事实上早在2002年,他就淡出了房地产领域和公众视野。
当别的策划机构担心不能吃住市场的东风时,王志纲害怕的是被市场束缚。“我不希望员工挣钱太多、在市场中走得太远,更希望他们能拿出创新性更强的成果出来。”就像树木太茂盛时需要剪枝,才能逼着它往上长。
他说“非新勿扰”—不创新者死。
他花大量人力物力,做了很多对中国新经济和前沿产业的研究工作,他设立了战略研究院,集中探讨居民城镇化、金融、新经济、创新四大热点问题,出了一本几十万字的白皮书,正准备在媒体平台上发布。他希望一直走在中国经济发展、走在新产业破题的前面,这样才能在客户心中一直保持无可取代的地位。
但放眼更长远的未来,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是真正的智库。
“它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点,立场要超脱,不能仰人鼻息,要第三方生存;另一个是卖方市场,你选择客户,而不是客户选择你;要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要能抵御诱惑。”
事实上,淡出房地产业后,王志纲的业务重心就在不断往城市和区域发展领域偏移。这意味着,他的客户不再是企业而往往是政府;对手也包括了各个政府智囊机构,以及众多专家学者。
然而凭着20年来与市场的无缝对接,他几乎不将对手看在眼里。
“西部有一个很大的开发区,我不喜欢那个书记,他也知道。于是他就说,不信没有了王志纲就吃不了灰毛猪,要找个超过王志纲的最好的机构做规划。”王志纲说,后来他们找来北京一个研究院,给他们150万。对方很兴奋,从没接过这么大的单子啊,弄了50多人过去,光博导就10多个,花了3个月,真的下了很大功夫。“但后来那个书记又来找我了,我说你不是找了中国优秀的学者吗,怎么还找我呢?他就说,‘他们的确很下功夫啊,搞了一屋子资料,但现在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把这一屋子资料变成一张纸’—他要的是一张可以操作的纸。学者们对这个没办法,他们论证、阐述,讲得很好,但就像国足一样,只见到他们传球,就是不进球!”他哈哈大笑。
这就是王志纲这些年来保持下来的最大优势:比市场人更有思想,比学者更懂市场。“(做智库)让企业埋单不算本事,让政府埋单才算!现在我们的政府埋单率达到70%。”
“关键一点是,现在我们的案例库已经积累了上千个案例,如果真的再走30年,整个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和美国一样甚至超过美国,那时候西方将会对东方刮目相看,不会认为西方人的规则才是规则。这时我们的智库拥有这个风云激荡30年最丰富的案例库,参与了今天激变的整个过程,我想这家机构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和美国对话,去阐述中国的故事、东方的故事。”
以这样的方式,他觉得自己终于超越了早些年噩梦一样缠绕着他的自卑,守护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尊严,姿态高傲得有如一个精神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