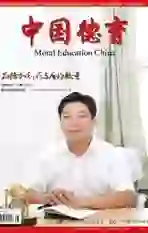教育,要回到人!要慢慢来!
2014-09-09魏贤超
摘要 在教育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由工具决定。实物工具决定了传统教育是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递知识或文化的活动。数字化工具使获得知识和文化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技术似乎可以取代教师、学校和教育。但是,教育不是训练、培训和塑造。教育需要回归,要回到人!要慢慢来!
关 键 词技术;教育的本体危机;超越技术;回到人
作者简介 魏贤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实物工具与师道尊严
教育是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递知识或文化的活动。从孔子、苏格拉底至今,都是如此。作为教育者的基本上都是年长者,作为受教育者的基本上都是年轻者。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年长者比年轻者拥有更多的知识、文化。为什么?答案同样很简单:知识、文化的获得需要很长时间。但是,进一步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为什么知识、文化的获得需要很长时间?
这涉及教育理论中一个被忽视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处理知识或文化的过程中,人类使用的工具(媒介)是什么?在古代农业社会,有甲骨、木石等原始工具,后来,出现了纸、笔、黑板等工具。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实体媒介、实物工具。这些实体媒介、实物工具的科技含量低,运用它们来传递、获得、积累和应用各种知识或文化,特征是:速度慢,结果是:效率低。一直到几十年前,大多数人使用的还是这些实体媒介、实物工具。比如过去的大学师生,大都要通过做文摘卡的方式积累知识。“字要一个一个地写,话要一句一句地说。”这里就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文化、经验、知识、信息都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一个人要成为一名教师,没有二三十年的学习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工具起着哲学意义上的基础性或者决定性作用。一般说来,一个人学习的时间越长,拥有的知识、文化就越多,也就越有资格做教师。因此,年长者有较多知识、文化,教师由年长者担任。如果在天资、勤奋等方面没有特别大的差异,15岁的学生或孩子要在信息、知识、文化方面超过50岁的教师或父亲,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复杂的教育现象内部,最为核心的就是这种知识或文化的非对称、不平衡关系,这种关系取决于学习时间,最终又取决于学习活动所使用的工具。换句话说,在教育劳动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代表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决定了教育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教(育)者和学(习)者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教育实践和教育制度(上层建筑),并且进一步形成诸如“教育是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递文化和知识的活动”的观念(概念、命题和理论)和“师道尊严”之类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
二、数字化工具与教育失语
历史在发展。在近代工业社会,人类发明了照相机、广播电视等模拟工具。到了现代所谓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人类又发明了电脑、网络等数字化工具。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我们似乎已经全面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最新的手机、电脑、网络等数字化媒体和工具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工具。
工具决定速度和效率。在人类的学习和教育中,新的工具大大提高了获得知识和文化的速度和效率。过去,人们首先要找到一本书,然后翻到某一页,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听,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因此,学习和教育,只能是慢慢来。现在,通过上网搜索,我们可以迅速获得需要的信息和知识,在信息海洋中“大海捞针”,瞬息之间就可以完成。
除了加快速度、提高效率,数字化工具还给教育带来了什么?
要达到孔子这样的伟大教师所拥有的知识量,如果说使用实物工具至少需要30年,那么,使用数字化工具可能只需要3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花大量时间来获得同量的知识,数字化工具使他们可以越来越快地拥有越来越多的知识。于是,在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以前存在的那种知识上的非对称、不平衡关系开始产生变化。在过去,年长者对于年轻者具有知识、文化的绝对优势,两者呈现非常倾斜的非对称、不平衡关系;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年轻一代在知识上的相对地位上升,两者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不那么倾斜甚至是基本平衡的关系;将来,有可能(或必然)出现反转的关系:年轻一代反过来对于年长一代具有知识、文化上的优势。年长者原来对于年轻者具有的知识、文化的绝对优势,已经、正在并且会继续经历着一个逐步失势的过程,甚至现已或者将会处于劣势地位。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一系列其他的变化也会随之出现。请看两个真实场景—
13岁的儿子对爸爸说:“爸爸,吸烟有害健康!不要吸了!”爸爸大声呵斥:“小孩子懂什么?走开!”
妈妈小心翼翼地推开13岁女儿的房门,问在电脑前面的女儿在做什么,女儿说:“你不懂的!不要问!”
从“小孩子懂什么?走开!”到“你不懂的!不要问!”,多么巨大的转变!作为年长一代的教师与家长,作为教育者的传统资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受到了来自学生和孩子的严峻挑战!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工具。工具的改变是一切变化的基础!工具的变革动摇了传统的代际关系,挑战了已有的教育哲学。在过去,父亲教育或者训斥儿子的话通常是:老子走过的桥,比你(小子)走过的路还多!我们可以对此做一个望文生义的解释。在20世纪以前,这种教育或者训斥的方式是有客观的基础的,是正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在空间上移动自己的方式就是用双脚走路。通常情况下,一个15岁的学生或孩子所走的路不可能超过一个50岁的教师或父亲所走的路。因为后者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更因为前后两代人走路使用的工具是一样的,都是“11号”—自己的双脚。进入20世纪,特别21世纪以后,一个15岁的孩子有了自行车,有的20岁的青年有了汽车,很多年轻人还可以坐飞机。现在,父亲用他的“11号”走他的路,儿子骑自行车,甚至开车,父亲怎么可能比儿子走的路多?因此,当年轻一代创造、拥有和使用了新的工具,年长一代对待他们的方式就不得不改变了。可见,一切的一切都在于工具—这个重要的物质基础!你提前走30年,哪怕提前走300年也可能是没用的。工具的变革彻底颠覆了教育中的关系和理念。
不管人类社会是否进入了“文化反哺”时代,现在的教师和家长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毋庸置疑的“话语权”了,在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教育失语”的尴尬处境。对于懂得不多或者不懂装懂的教师和家长,学生和孩子常常会不以为然,甚至会觉得长辈很“好笑”。哲学家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现在,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家长(教师)一开口,孩子(学生)就(会)发笑。
工具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的工具引发了教育领域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和问题:今天,我们还有资格像过去那样做教师吗?我们应该怎样做教师?过去那种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教育实践和理论还能成立吗?
三、技术进步与教育本体危机
数字化媒体和工具的发明使用,一方面使人类掌握信息、知识、文化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了;另一方面,引发了教育领域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和问题:今天的教师(家长)还有资格像过去那样做一个教师(家长)吗?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教师(家长)?教育,还是过去那种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递知识或文化的活动吗?
这是科技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化工具的出现对于迄今为止的教育的第一个严峻挑战!作为年长一代的教师与家长,作为教育者的传统资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受到了来自学生和孩子的严峻挑战!
可是,挑战还不止于此!
借助于现代化的数字化工具,人们已经可以通过各种课件、网络和终端,实现非学校化的学习和教育。换句话说,从单纯技术和狭义知识技能学习的角度看,人类已经可以不需要学校而完成学习和教育的任务。新的网络学习,这种现代升级版的自学考试和远程教育,已经严重地挑战甚至否定了传统的教师和传统的学校的存在价值。今天,已经有很多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获得了大学文凭,但是,他们没有见过他们的老师,他们也没有进过学校。
于是,问题在一步一步地推进:今天,应该怎样做教师?
还有更为严重的挑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假设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现实,只要我们愿意,各种“体能药片”“智能药片”“道德药片”“美育药片”或者“体能芯片”“智能芯片”“道德芯片”“美育芯片”等新工具的出现是完全可能的,它们可以用十分便宜的代价迅速地解决人类的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问题。这个时候,人类的学习和教育,几乎完全可以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和工具,在一刹那之间完成。人类文化传递方式除了遗传和教育,是否还有第三种方式:生物-电子的传递?大概15年前,我们曾经思考过是否有这个可能性,现在看来,的确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传统的学习和教育是否会被彻底替代、抛弃和否定?人类还需要学习吗?人类还需要教育吗?教育的本体价值还可以继续存在吗?这样,自然需要我们去考虑需要不需要教师、需要不需要学校的问题了!
总而言之,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工具的产生和应用,如果从单纯技术和狭义知识技能的角度看,传统的教师、学校和教育的确是遭遇了严峻的挑战。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遭遇了本体危机!
四、超越技术的教育:回到人!慢慢来!
在高科技时代,人类真的可以不再需要教师、学校和教育了吗?科技和工具真的是教育的决定因素吗?人类真正的需要和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这是一些需要超越技术,把技术、工具与教育、人的问题结合起来加以深入思考的深层次的重大哲学问题。
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问题,或者说,就是如何“与人共处”的问题。同样,教育的本质也在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或者说,教育的本质就是“对话”,因为,人的本质就在于“对话”(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近现代教育的进步,简要地说,受惠于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认为,人与物是一样的;二是认为,人与人是一样的。这两个观点的背后是很大的理论靠山—哲学的和心理学的。从笛卡尔到拉•美特利,从华生到斯金纳,共同的观点是:人是物质,是机器,是动物;人和物是一样的。因此,可以用自然科学的还原方法分析人;因此,可以通过条件反射作用训练和塑造人。而且,又因为人与人是一样的,标准化的、大规模的、高效率的近现代教育(训练)制度成为必要并得以实施。”“但是,这种进步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因为人与物被认为是一样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目中无人,见物不见人,‘物性取代了人性;既然人与人是一样的,共性自然可以代替个性。这种人性与个性的双重缺失,加上作为教育的物质基础发展水平的限制,使得古代的教育的概念以及实践,从近现代开始,被理解和实施为通过条件反射作用来传递(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灌输(道德)、训练(技能、能力)和塑造(行为习惯)的活动和过程。”“从更为重要的物质层面看,当人类从农业时代走进工业时代并进一步迈向后工业时代时,当人类逐步从实物媒体、模拟媒体时代走向数字媒体时代时,教育的物质、技术和工具基础已经并且必然会继续发生根本的改变,有关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将会出现:曾经和仍然被作为教育之主要任务的知识(传递),对于真正的教育来说,是否可能只是沧海之一粟,冰山之露出水面之一角?人类的教育和学习过程应该像迄今为止认为的那样‘快一点(掌握各种科学、技术、文化、知识),还是应该‘慢慢来(人生的展开,生命的成长)?经过数字媒体的加速,‘文化反哺或‘后喻文化使教者和学者之间传统的非对称关系被明显颠覆,从而是否可能导致严重的‘教育失语?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因为将可以塑造人的一切从而在根本上把教育从人类历史舞台中驱逐出去?人类教育继续存在的基础和魅力究竟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需要深入的哲学思考。”(以上是我们在《教育原理散论》中的表述。其中涉及了很多有关教育的本体、本原或本质的重大问题)
在最为“现代化”的养鸡场里,原来需要12个月才能长大成熟的鸡,一两个月就来到了人类的餐桌上!在最近几十年的所谓的现代化的(现代的电脑和网络等工具取代了过去的粉笔、黑板、毛笔、钢笔)学校里,中小学生们的生活与此何其相似!除了电脑、网络、手机,除了听课、作业、考试,这些孩子们还有什么生活?几十年以后,当他们回顾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有什么是值得回忆和珍惜的?那时,还有人能够写出鲁迅笔下的《社戏》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吗?
我们可以用各种“药片”或者“芯片”快速地解决人类的教育、成长和发展问题吗?如果可以,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人的本质在于人是“自由自觉的动物”(马克思语)?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人是目的”(康德语)这个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可以容忍由工具决定教育,那么,教育本身也就成了工具。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格言曾经成为几乎所有教育人的共识。体验重于知识,感受先于认知,情感大于理智,过程高于结果,这些要素本来应该是教育的本质所在,但是,在所谓的教育中,人们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狭义知识的传递和接受实际上占据了整个教育的80%~90%的份额,实质上已经成为教育的中心任务和核心目标;品德教育和美育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没有多少人会说“品德就是力量”“美就是力量”。很少有人注意,“当知识越来越变得专门时,它就不再是知识了”(纽曼语)。这样的所谓的教育,基本上与真正的教育—“人文化育”无关。这样的所谓的教育,是一种残缺的、畸形的、丑陋的“教育”,是一种无德的“教育”,无品质的“教育”,无价值的“教育”(它真正的名称应该是“训练”)。
有文学家描述牛津大学的导师制—
在教授的办公室或者书房,一个教授架着二郎腿,叼着丘吉尔式的大烟斗,若干个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在那里讨论着问题。其间,教授主要是在抽烟,也听学生的讨论,偶尔插话讲两句,可谓“抽为主,听为辅,讲再次”。经过三五年的时间,在教授烟斗喷出的烟雾的系统熏陶下,这些年轻人心灵深处的火苗就被点着了。
教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通过人与人之真实的生活、共同的生活以及交流与合作,通过相互启发、接受熏陶、酝酿发酵,从而引发生命的成长、人生的展开。
在这样一种教育生活中,我们自然也不能追求“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的格言完全不能适用于这样的教育。教育,本来就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人倡导的“慢的生活”。教育,不是像巴甫洛夫、华生、斯金纳所说的训练、培训、塑造,而是孔子、苏格拉底和雅斯贝尔斯等人心目中的培育、培养、唤醒;教育,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就像酿酒一样,是一个慢慢的熏陶、酝酿、发酵的过程,需要一个自然的过程,要慢慢来!
看来,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不能用技术和工具解决人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的,我们需要对技术与教育的关系观来一个否定之否定,把教师、学校和曾经的、本来的那个教育找回来,或者说,要回到过去,去找回那个曾经的、真正的、本来的教育;要面向以人为中心的未来,去找到那个应该的、真正的、本来的教育。
教育,要回到人!
教育,要慢慢来!■
责任编辑/刘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