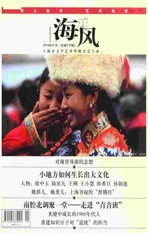孙颖迪:在上海遇见李斯特
2014-09-07刘莉娜
文/本刊记者 刘莉娜

孙颖迪
2005年4月在荷兰乌德勒支举行的极富盛名的第七届弗朗茨·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上夺得金奖,成为第一位摘取此项桂冠的华人钢琴家。之后他的巡演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音乐舞台。他因对李斯特作品的出色演绎而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原色李斯特”。自2006年始,孙颖迪在母校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并成为中国文化部“东方快车”推广计划的艺术家成员;2009年,荷兰Brilliant Classic唱片公司在全球发行了孙颖迪的个人首张专辑。2012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十大青年钢琴演奏家”。
2011年10月,为纪念李斯特诞辰200周年,孙颖迪应邀再次回到乌德勒支举办音乐会,结束之后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时光犹如穿梭的机器,时常将我在现实与记忆的纽带上传送。时隔经年,再回到古城乌德勒支,参加纪念李斯特诞辰两百周年音乐会,曾经追风的少年忍不住,稍稍放缓了脚步。蓦然间,我想起独自漂泊的日子,在教堂广场前的黄昏里徘徊不去,那滋味曾经馥郁,如今些许冲淡了。但你可知道,艺术家的行囊里,总有一件东西叫做孤独,那是用来发现美的。正如我看见落日的余晖投洒在玫瑰窗上,绽放出一朵七色的花;正如我听见塔楼的乐钟每逢半点或正点,便演奏起巴赫或亨德尔。深秋的暖光里,你可以选择聆听孤独,或孤独的聆听……”这一段文字精致利索、错落有致,几乎可以媲美专业的写作者,却让我在约见孙颖迪之前隐隐生出一些担忧——孤独的艺术家什么的,最难采访了。然而在音乐学院门前的咖啡店见这个头发卷卷的年轻人之后,我的顾虑完全消失了,眼前这位年轻的钢琴家不仅热情开朗、有问必答,简直可以称得上侃侃而谈了。对于这个评价,“孙老师”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啊呀,我的学生们也说我是话痨呢。”
是的,孙颖迪的另一个身份,就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青年教师,以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成绩已然不凡,但如果我们留意到一个时间上的细节,就会发现他是2006年开始任教的,而2005年他刚在第七届弗朗茨·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上夺得金奖,成为第一位摘取此项桂冠的华人钢琴家——也就是说,一个26岁的年轻人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居然选择了寂寞的讲台而不是闪亮的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孙老师”果然是一位孤独的艺术家呢。
不做王子,边走边弹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把朗朗、李云迪称为“钢琴王子”,而孙颖迪却有一个很文艺很特别的称号,叫做“原色李斯特”。对于称号这件事,孙颖迪颇有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音乐的高雅高贵和地位的高贵是两码事,并且我的成长经历与养尊处优、众星捧月的王子没有半点相似之处,所以请不要叫我王子。”在孙颖迪看来,所谓“钢琴王子”只是一个符号,它可以冠于任何一位年轻、帅气、有才华的男性钢琴家头上。然而“原色李斯特”则不一样,“它是个听起来很不错的名声,也许是指我的演奏,比较能够体现出李斯特作品的原汁原味。我几乎从不把李斯特简单地看成一个键盘上的神,刻意去表现他炫技的那一面,我个人认为那是一种廉价的辉煌而已;更多时候我喜欢李斯特,因为他是那样一个真实的艺术家、一个有着性格弱点的人,正因为我注意到了他人性上的特点,并在演绎他的艺术作品时加以展现,因此才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吧。”
有趣的是,对于孙颖迪来说,“李斯特”还是一道学琴过程中的分水岭:“在弹李斯特之前都是看谱的,而之后全部背谱,从那以后再也没谱了。”这句话虽然是玩笑,但他真的在小时候独创了这种“没谱”的练习方式,“我是近视眼,把眼镜摘了本来就看不清,有时候还会蒙上手帕,用这种方式来练习李斯特那些跳跃的八度。”
几乎所有的钢琴家都没有童年,即使百年一遇的神童如莫扎特,也是从三四岁起就被困于琴凳上老实练琴过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孙老师”并不回避那一段琴童生涯的“凄惨心境”——每天的练习很痛苦,看到小朋友在外面玩也很羡慕;但乐观的人总是会在逆境中生出更多正能量来,孙颖迪小朋友并没有因此怨恨弹琴,却因此衍生出关于长大的理想:“小时候被练琴占用了很多时间,哪里也不能去,于是就想,长大后一定要从事可以带我去很多地方的职业。”而如今蓦然回首,儿时那恼人的矛盾却奇迹般得到了圆满的统一:“因为比赛和表演,我去到了全世界的很多地方,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小时候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旅行与音乐一点也不矛盾。”
在孙颖迪看来,学习古典音乐,首先需要了解并且十分尊重西方音乐教育上的许多传统,但也不必盲目迷信国外的教育,好技术并非只有在国外才能练就,而学好古典音乐,也远非只要掌握了好技术那么简单。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眼界,决定了什么样的思维。身边也有朋友,虽然没在国外定居,但他们的思想也非常国际化。最好的状态,是可以游走在国与国之间——周游列国,不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这样的话,你不会固守一种思维模式。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特的文化,每个国度的人民,也会对相同的事物拥有不同的视角。这对于艺术家开拓视野、发散思维、促发灵感、创造作品,是有很大帮助的。“我的职业还是比较幸运的。演出的时候常常即是旅行,而旅行的时候便可以接触许多不同的文化,接触许多不同的人群。”孙颖迪认为,边旅行边演出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因为李斯特也好,莫扎特也罢,当年众多的音乐家们长期都是在旅行中演出,甚至作曲也是在旅行中,而不太会像现在一些人,为了某部作品的创作闭关修行。“况且人生有限,趁现在还不觉得累的时候,多游历游历挺好。”
“钢琴不是竞技体育”
如今的孙颖迪也算是上音里一位教龄8年的“老教师”了,但在他的恩师盛一奇教授的记忆里,8年前这个孩子气的少年一个人去荷兰参加李斯特钢琴大赛的情形却还历历在目。她说,孙颖迪是自己报名参赛的。李斯特大赛是先从各国的数百报名选手中进行筛选的,孙颖迪顺利入围首轮48个名额。因为参赛费用昂贵,只能由孙颖迪独自一人开赴荷兰乌特勒支——李斯特的故乡。盛一奇帮弟子编排了足以演奏3个小时的参赛曲目,4月2日,目送他远去。到了荷兰才知道,这次比赛很多选手有导师陪同,包括深圳的但昭义教授(李云迪的老师)也亲临现场,指挥弟子参战。
这一场长达半个月的比赛分四轮展开。第一轮,小孙不声不响进了前18名;第二轮,再进前9名。之前入围的几位中国选手,只剩他和但昭义的一位弟子。最后两轮赛事空前激烈,赛场从四五百人的剧场挪到了专业音乐厅,选手在交响乐团前演奏,观众的掌声非常内行挑剔。然而孤身一人的孙颖迪并没有出现心理波动——也许孤独会放大胆怯者的胆怯,却让坚定的人更坚定,孙颖迪发挥平稳地跟两位外国尖子选手闯进了前三。当地时间16日决赛当晚,孙颖迪以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二匈牙利钢琴狂想曲出场。比赛最考验人的地方,就是在第二首曲目的华彩段落要求“选手写作”,即用自己的理解和发挥,创造一段演奏。这一天在台上,孙颖迪不再有东方人的内敛,他释放出所有的热情,以准确而有感染力的演奏,打动了所有评委。赛后,所有评委意见一致— —“声音非常漂亮,变化非常多”。
在老师的记忆里,他一个人赢得了这场孤独的比赛,然而在孙颖迪看来,虽然自己是孤身前往赛场的,却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半个月赛程里,他一直通过手机跟导师保持联系,国际长途不舍得多打,就用短信。对此盛一奇笑说,“收到一百多条了吧”,但这些短信里从来都没有示弱、怯场,只是有时候碰到场地、乐器不一样,他会讨教如何调整。盛教授说,她从不担心孙颖迪的临场发挥,尽管他羸弱、单薄,自己甚至经常提醒他多吃点长壮点,但是只要一摸到琴,他对音乐的敏感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就会超乎寻常地发挥出来。平时,他喜欢看书,爱思考,能吃苦。尤其是到哪儿都能适应,这在学琴者中很难看到。
当然,如果你因此把孙颖迪看作一个一路保送到研究生最后留校的乖孩子,那就未免小看了他。赛场之下、课堂之外,曾经的孙颖迪可是爵士酒吧的常客:白天端坐学校琴房,勤练古典,晚上潜入CLUB JZ,用爵士的随心所至放逐心灵,一周三四次,一晃两三年。虽说大学生校外兼职并不出格,可是古典音乐科班的种子选手却随随便便跑到酒吧去玩爵士,这多少还是让上音的一些老师觉得不妥。而那段时日在如今自己也做了上音老师的孙颖迪看来亦有些不可思议,愈夜愈美丽本不符合他的生活轨迹。孙颖迪至今也无法说清那一段的“偏离”究竟出于怎样的心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绝非单纯为了生计:“我到底是喜欢爵士乐的,家中的爵士唱片甚至多于古典唱片。又或许,出于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慨,在爵士乐低回而忧伤的格调中聊以自遣——爵士乐本是一帖疗伤妙剂。”午夜过后,客人渐渐散去,酒吧变成音乐人的jam sessions(即兴演出),每个人都上台,用最真实的音乐挥洒真性情。那是最令孙颖迪享受的一段时光——脱下假面,他任由自己变成一个音乐疯子。孙颖迪记得,临赴荷兰参加李斯特大赛的前一晚,自己还在CLUBJZ演奏。
如今自己做了老师,遇到这种“走偏”的学生可会吼他?拿这个问题去“为难”孙颖迪,孙老师当即神色一正:“会吼的。”原来这位娃娃脸笑起来还有点卡通的青年教师,在学校里还是一位让学生生畏的“严师”呢。据说做孙颖迪的学生最是辛苦,因为比起一直在教育岗位上的其他教师,孙老师还是位专业的钢琴演奏家,所以他对演奏过程中的各种细节都更加追求完美:“舞台对一名演奏者的要求很高,因为我自己已经习惯了那一套标准,所以常常不自觉的就用这个标准去要求我学生。”说起做老师的体会,自己看起来还像个学生的孙颖迪已然深有感触:“中国的老师是全世界最敬业的,但是每个行业都需要用成绩来说话,这就给了老师很大的压力。”但即便如此,孙颖迪对于以拿奖为目的的参赛一直持保留态度:“虽然中国的琴童数量庞大技艺也强大,但在海外很多学琴的孩子却更为幸福,因为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不是为了考级、加分而学习一门乐器,而是尽可能地享受音乐的快乐,体悟音乐的美和真,这比能够快速准确的弹奏车尔尼显得意义更大。”对此,身为教师的孙颖迪希望大家不要给音乐赋予过多的附加值,“希望大家都能平和一点,慢一点,毕竟钢琴不是竞技体育”。
记者: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2005年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的那个桂冠仍然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据说你决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而你小时候曾经一度非常沉迷于写作?
孙颖迪:是的。我当时相当热爱文学与历史。读史、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尤其偏爱中国的经典著作如《红楼梦》等,也很早开始读一些钱钟书、林语堂和梁实秋的文字,如《围城》《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等。后来有一阵爱好过散文,《当代台湾散文选》在当时几乎是手不释卷的一套书。读后有感,就在一些无需太用心听讲的课上写写随笔性的东西,更有一时居然想构思侠义小说。但是渐渐的,我意识到自己的文字功力还是不够,在表情达意上总是无法接近创作时的第一感觉——中国文字虽然无穷深奥,但是文字是有明确界定的,是有形的,我自己觉得无法很好的运用它深入、贴切地表达我内心的情感。而音乐则虽说是不可复制的,是无形的,但因此留给人更大的空间,某一刻的情绪,当“词不达意”的时候,唯有以音乐来表达,甚至有时候只有休止符能表达,这大概就是所谓“无声胜有声”了。因此在生活中,我离不开音乐,真正能贴近我内心的唯有音乐。
记者:你在附小、附中、大学阶段是一路保送的,一直是被看作获奖的“种子选手”,可是你自己却一直表示“并不喜欢参加比赛”,为什么会这样?
孙颖迪:直至今日,我始终没有把比赛获奖作为衡量艺术家成功的唯一标准。这么说吧,艺术之路多荆棘,很早获奖固然可喜可贺——谁都愿意走得顺坦些,相对而言我花了更长的时间。而我走的这条路,在当时甚至有些师长觉得是“弯路”、“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却能看到更多,看到我们这个狭窄的专业领域里的学子们通常不太能看到的美丽风景。我觉得一个人搞艺术工作,首先要健全自身的人格,保持灵性,从而成为一个完整的音乐人。我需要的是一个完整而不一定完美的人生,这个人生不是仅仅有古典音乐,更不仅仅只有音乐。对于艺术,我的理解是:“术”是可以习得的,但“艺”不可传,需要悟,需要灵性,需要风骨。
记者:但毕竟对于大多数琴童甚至钢琴专业的学生来说,参加比赛尤其是国际比赛然后得奖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作为上音的老师,你对此怎么看?
孙颖迪:比赛的游戏规则就是优胜劣汰,这是你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有的时候,这种残酷性能够逼使一个人发奋图强,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但是,这不应该是音乐演奏的常态,人不能总在一种鱼死网破的状态底下搞音乐、搞创作。音乐的发生,主要是心灵的诉求,是心声的传递、情感的延伸——有的时候为了追求特定的表达效果需要做出冒险的尝试;而比赛则讲究安全、稳妥,中庸之道盛行于世。由此我们不时会看见一些个性突出天赋出众的年轻演奏家在比赛中落马,正因为他们鲜明的艺术棱角,触碰到某些大评委们的神经,并有可能造成某种不良反应使然。从中可以看到,比赛可谓成功的一种捷径,但绝非一条易走的通途。这么说吧,比赛本身不可能促生真正的大音乐家,它主要是给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没有特殊背景但才华横溢有梦想的年轻人,一个展示的机会,一个冒头的机会。真正要成为艺术家,还需要长时间在舞台上的锤炼,在生活经历中的跌打,以及老天的眷顾。
记者:再请孙老师谈谈古典与时尚。

演奏中的孙颖迪
孙颖迪:流传至今的古典音乐,其中有不少都曾是风靡一时的流行音乐。就像现今早有人迫不及待地把蔡琴、李宗盛也划入经典音乐领域那样。当社会精英们与平民百姓们都意识到该去听某个人写的歌剧或看某个人的演出时,被特指的某个人便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时代文化生活里一个标志性的时尚人物——人人以没看过“他”或“她”为耻。一些人,把自己偶然听、曾经听、间歇性听、从来一直都听、从来也没听明白也不求听明白但就是喜欢听古典音乐的经历拿来说事儿,当作自己脚下的填充物,仿佛就此自己在道德上、知识上、品味上、乃至经济上就上了一个台阶,比别人高了一截——这好像也成为了苍白空洞的都市生活里的一种时尚。古典音乐家理应拥有卓尔不群的品味,高端的品味才能引领真正的时尚,真正的时尚一定包含优质的品味。只有这样,当前的时尚才有可能成为日后的经典。
记者:近年在艺术领域流行跨界,好像你也有过若干尝试,但似乎很谨慎。
孙颖迪:即便我承认眼下自己对于跨界的尝试,更多的是出于在音乐上不甘寂寞的一份玩心,但毫无疑问,玩好跨界仍需要匠心独具。搞古典的人,偶尔在公众场合唱一首流行歌,弹一支爵士乐曲子,或许还真谈不上跨界,充其量不过是玩票。如何在一次成功的跨界、甚至跨多界的合作中,迅速而准确地找到不同艺术之间的平衡点,与合作的伙伴保持既和谐又对立的微妙关系,并以随之产生的艺术感染力秒杀现场的观众,不但是件饶有趣味的工作,更是智慧的体现。事实上,我曾经婉拒过各种跨界演出的邀约,在这方面我自己是谨慎和担心的。原因很简单,做跨界的初衷,不是去制造更易为人接受的快速精神消费品,而是追求某种更具特质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