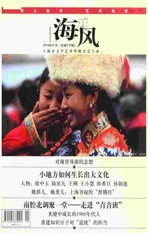难忘爱护关切情——忆郑拾风和乔奇两位前辈
2014-09-07陈清泉
文/陈清泉
最近,在整理我的藏品时,一块郑拾风先生赠给我的手绢进入眼帘,那上面留有拾风先生的手迹,称得上龙飞凤舞。
首行六个大字是:“今日无话可说”,一旁有四行字体略小的字作注,曰:
“一九四六年六月廿四日,南京下关事件次日,我在南京人报发表六字短评以示抗议。拾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在签名下印有篆体印章,那鲜红的色彩好似拾风先生沸腾的鲜血像烈火般地在燃烧。
我不禁回想起与他的相识和相交。
1989年秋,调我去文联工作的事,经我多次找上级反映,恳请他们收回成命,但陈至立同志对我下了“通牒”,我知道我是非去不可了,只是以需要陪接替我工作的李民权同志到北京熟悉部、局的各种关系如何衔接为借口,似乎拖一天“好”一天。但内心的忐忑、种种的忧虑并未消除。虽然我已向巴金、于伶、贺绿汀、张骏祥、徐桑楚等老同志请教过,他们也都曾面授机宜,我也作了去文联的准备,但我的“自我感觉”仍然不好。
一天,突然接到了乔奇的电话,他对我说:“知道你要到文联工作了,拾风和我想找你聊聊。”并邀我于后天中午到一家餐馆“餐叙”。

乔奇要找我,我并不奇怪,因为他与我岳父同为电影界同仁,又曾在我编辑并执笔定稿的剧本——电影《平鹰坟》中担任过角色。我在电影厂和电影局工作时,他就对我十分关切并不断给予鼓励。
孙景璐因肾病进行血透,我曾多次去医院探望,与医生研究治疗方案,表示要尽一切力量来救治这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这一切,乔奇这位“老阿叔”看在眼里,常常流露出感激之情。他要找我“聊聊”也属“人之常情”。但我与拾风先生素昧平生,他竟也有兴与我见面,我不仅感到事出意外,还有点受宠若惊!
拾风先生的大名我是在解放后才知道的,那时,他在《新闻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曾引起我这个进入广播新闻界不久的青年的注意。对他气贯长虹、一针见血的宏论钦佩不已。虽然解放前在报上读到过南京事件的报道,对国民党中那些人的倒行逆施十分义愤,但我未看过《南京人报》,也不知道他在这一事件中的遭遇。直到我调上海,才听一些电影界的人士(记不清是卫禹平还是孙道临了)做过介绍。
那时,在《南京人报》任总编之职并专写评论文章的郑拾风,在南京下关车站发生国民党当局指使军警殴打“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及随团记者,著名的民主人士马叙伦、雷洁琼、浦熙修等人被打伤住院。事发之后,国民党当局为掩盖罪行,命令各报刊不得报道这一事件。素以笔锋犀利,秉笔直书而闻名的郑拾风偏不买这个账,写下了消息并发表了评论刊在报纸头版。国民党的审查机构下令删除,郑拾风则以“开天窗”来针锋相对,并在被开了“天窗”的空白处写下了“今日无话可说”这六个遒劲的大字替代那则消息与短评。被人们誉为“中国杂文史上最短、最有力度的一篇杂文”,这当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与恼怒,他们为维持假民主的面貌,一时不敢采取行动,便授意军统控制的《救国日报》对《南京人报》及总编郑拾风和他的支持者、老报人张友鸾进行恫吓和谩骂。拾风以自己的一身正气、毅然应战,不仅独家报道了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示威游行的消息和照片,还连续揭露了国民党的种种丑行。
拾风和他的朋友们知道,在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一定会狗急跳墙,以白色恐怖来对付进步人士。果然,风声传来,国民党当局即将对拾风采取行动。
1949年的2月,他们悍然下令查封了《南京人报》,通缉郑拾风。拾风早有准备,在友人的协助下,连夜搭乘英国军舰逃往香港,躲过了一劫。由此可见他的机敏,也证实了得道多助的真理。
在听说了这个故事后,我对拾风先生就不只是钦佩而是深为敬重了。他与乔奇一起邀我一叙,到底想说什么呢?我这个后生小子竟劳动他大驾与我“聊聊”,是不是也会像巴老他们那样地对我面授机宜呢?
乔奇笑呵呵地向他介绍了我,然后说:拾风听说你要来文联就找我了解你的情况。我们欢迎你来,文联需要有新的力量加入;又有点儿担心,因为文联的事有时候不太好办,所以就想和你当面聊聊。
拾风先生大概怕我对乔奇所说“文联的事有时不太好办”而产生负担,便解释说,主要是交流交流,没有什么太难办的。我们俩对文联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也许可以让你参考参考。他的浓厚的四川口音娓娓道来,显得铿锵有力且节奏感很强,听起来很舒服。也许,因为我的祖先也来自四川,我的血管里有四川山川大地给予的营养,所以他的话语又增添了不少亲切感。
接着他便叨叨不绝地讲了一些话,这些话大概有三层意思,可用“语重心长”来加以概括。他说:
“八九风波”过去不久,文联的人中,有的参加过游行,有的表现得行为有些激烈,因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点抬不起头来,当然也有被批得很不服气的。无形中被批的与批人的情绪就不那么协调,感情不那么融洽,思想也就比较混乱,说得重一点,队伍有点散了!有些人在混日子过了,工作也停顿多时了。这种情形下你到那里去,面对“散”了的队伍,怎样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把消极的东西去掉,积极的东西恢复起来,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即使是说错了话、办错了事,甚至于有些过激行动的同志,批也批了,检讨也检讨了,究竟怎么对待他们?照我看,他们大都是爱共产党、爱新中国的。不能让他们永远背着个包袱,不能让人们被排斥在正常生活之外。过去搞运动的教训应当记取,不要在伤疤上撒盐。对他们你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不能让这些人处在游离状态,要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文联的领导结构和你们电影厂、电影局不一样。它既是松散的,主席团、全委会的人都不在文联拿工资,不吃文联的饭,他们散属在上海文艺界的许多领域。但又是权威的,这其中有不少全国性的知名人物,有的还是资历很老的老革命。你这个党组书记,既是单位的第一把手,许多事都应拿主意,但在这些同志面前,你可能还是个中学生或者是小学生。你要学会如何与这些人相处。特别重要的,有的老同志、老资格,他们的话,有的也会不合时宜,你听还是不听?你要尊重他们,还要妥善处理一些不够妥当或无法执行的意见。要学会做“难人”,其实难也不难,在尊重他的前提下要坚持原则,这就必须耐心细致地做解释,决不可大而化之!
这些话,在巴老等人那里也曾涉及,但拾风先生的话直截了当,称得上入木三分,既有情况的分析又有解决之道,让我听得如醍醐灌顶。
在拾风先生说话时,乔奇不断插话。如实名介绍了某同志被某人、而且是拥有一定权力的同志揪住不放,弄得此人远走他乡了——惹不起我躲到起呀!某同志在挨批后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对人说:谁对谁错二十年以后再看。并问我,你怎么对待他?但我未回答,因为我还未想过应对之道。在拾风说到我可能做“难人”时,乔奇补充说,文联有的人会与你唱反调,你可不能将这种同志当“刺儿头”看,你给他定了“刺儿头”的性,就会阻碍你们的相处,就真正地成了对立面,等等。他还告诉我某些权威人士,往往会“一言九鼎”,你如何看待并且处理好这种关系,要好好想想。
我认真地思考了他俩的意见,并且与巴金、于伶、贺绿汀、张骏祥、徐桑楚等老同志的话联系起来加以梳理,腹中打好了预案。后来,在我到了文联接手工作后,他们介绍的情况一一得到印证,他们教授的应对之道都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从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结束了过去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状态。文联,又像过去那样活跃在文坛、活跃在艺术界了。
这里,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位坚持“二十年后再看”的同志,可能抱着必定“倒霉”的想法准备进一步挨整,因而有消极情绪。我与他谈心时首先说了我的看法,我表示“先不谈谁对谁错,既然党组织允许在党内可发表各种意见,你的那些话又是在组织生活中说的,是应该得到允许的,因此,我们不会整你。”接着,我安排他参加研究工作,后来在他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又安排他担任一个处的领导工作,他的情绪扭转了过来,工作得十分认真而积极。由于他的“示范”,有些抱有消极情绪的人也纷纷改变了原先的状态,这种从一个人带动一批人的景象,让我着实高兴了好些天。
我到文联不久,在周六举行的有各处室领导、各协会秘书长参加的“中心组”学习会上,有位同志给我提了四条意见,而且很尖锐。我内心中想:“好家伙,当着这么多人敢提新来的党组书记的意见,是个‘角色’。是不是乔奇说过的“刺儿头”呢?”这些内心活动在一瞬间闪过后,我马上表示要与他详细聊聊。
遵照乔奇的嘱咐,我首先把脑子里的“刺儿头”排除掉,与他十分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可能他察觉到我的认真和诚意,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刹不住了,第一次谈了两三个钟头,大家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又约谈了一次,又是两三个钟头。这两次谈话让我获益匪浅。这是一位善于仔细观察,又能从诸多现象中抽丝剥茧找出要害的有心人。从他的谈话中,我不仅了解到很多情况,明确了各个工作环节运作的特点,而且还知道了一些同志的特长,甚至爱好与趣味,我感到收获太大了。
他提供的情况给了我“知人”的机会,也给我创造了条件,让我可以努力去做到“善任”,我之所以后来能对文联的机构、人员进行必要的调整,就是他让我找到了依据。后来,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心,而且谈得很投机,我们便成了朋友,这友谊一直维持到我离开文联多年之后。
好些老同志包括拾风和乔奇,都对我说过如何对待一些资历很深的老同志的问题,我虽然很重视他们的意见,但当着矛盾纠缠着我的身心时,我不冷静了,要“据理力争”,以至发生人们不愿看到的正面冲突了。在这方面,我的教训是深刻的,我应该换一种形式,以拾风告诫的多做解释工作才是消弭矛盾的正确途径。至今反思这事仍觉十分歉疚。不仅对老人,也对关心我的这两位前辈感到歉疚。
上面的种种都表明,两位前辈与我的此次“餐叙”,是赠给我的一份厚重而珍贵的礼物,他们的关切之情、爱护之意和谆谆教导,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九泉之下的两位前辈先生,请接受我的思念之情和感恩之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