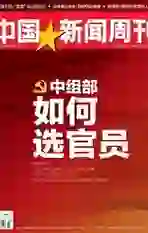念斌案这8年:悲剧仍在继续
2014-09-06陈薇
陈薇
恢复自由一周了,但念斌觉得自己还在囚牢里。半夜醒来,他发现自己身体蜷曲,手腕交叉在胸前——这是常年戴手铐脚镣形成的姿势。以前的视线只能看到两三米外的墙壁,如今一眼望见百米之外,他也不习惯,双眼布满红丝。
命运对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2006年7月底发生的一场投毒案,他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8年中历经8次审理10次开庭,先后4次被判死刑,3次被撤销判决;直到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一纸终审判决,裁定他无罪,当庭释放。
念斌想给服刑期间去世的父母上坟,却回不了平潭老家。那场投毒案的受害者俞家,在村里设了灵堂、拉上横幅,挂上念斌和律师张燕生的照片。他们还在村里超市门口摆了电视,将念斌供述投毒过程的26分钟录像反复播放。
为免报复,念斌仍躲藏着过活。借住在朋友那里,每次出门多绕几圈,一旦发现俞家人的身影,即刻折返。网络上讨论着“疑罪从无”,对他是真凶的怀疑仍在持续。喜悦没有持续多久,他愤恨不平:“如今,我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已。”
更加不满的是俞家。俞家仍然认定,念斌是唯一的凶手。从判决念斌无罪的那天起,俞家儿媳丁云虾就“住”进了福建高院,想讨个说法。
这场持续8年的命案官司,如今看似结案,在北京律师的努力下,不实的证据被逐一推翻,不公的判罚得以纠正,但凶手仍未见踪影,受害者的家庭伤痛未平;官司,仍将在双方的心中长久继续。这个在刚开始立案就疏漏百出的案子,在没有找到真相之前,注定没有赢家。
12天速破命案
平潭县位于福建省东部,是大陆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距离县城约15公里,开车20分钟,就到达澳前镇。镇子很小,一条主街道,有海鲜酒楼、超市和各类小店,从南走到北只需要五分钟。投毒案发生地,是一座二层灰色砖瓦房,一楼临街店面,如今已是手机店、水果店。
澳前村民念斌,南赖村民丁云虾,租下了房东陈炎娇的两个店。只相隔一堵墙,都卖水果日杂。澳前村在镇北边,念斌住家中;南赖村在镇南边,丁云虾家的石头房年代久了,成了危房,便租住在店铺楼上。
2006年7月28日中午,丁云虾的公公俞兆发像往常一样,从饵料中挑拣出新鲜的鱿鱼、杂鱼,送到店铺。晚饭时,丁云虾和房东陈炎娇两家一起吃了青椒鱿鱼、炒杂鱼和各自家的稀饭。不料,晚上9点多,丁云虾的3个孩子突然喊肚子痛,接着开始口吐白沫、腿脚抽筋。送到医院后,10岁的大儿子俞攀、8岁的女儿俞悦先后停止心跳。
这一年,丁云虾只有33岁,距离丈夫在海难中丧生不过3年。
福州市、平潭县两级公安迅速组成联合专案组。起初,怀疑对象是二楼另一家住户陈某某。这位住户曾买过4包毒鼠强和一瓶液体鼠药,在接受调查时还一度晕倒。
然而,调查很快转向。7月29日,福建省刑警总队经过化验排除了毒鼠强的可能性,并在两名死者的呕吐物、尿液、血液中检出了氟乙酸盐鼠药。鼠药不一致,最初的怀疑对象被排除嫌疑。
念斌也是被怀疑对象之一,他没能通过测谎。念斌解释说,公安问他,国家总理是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不知道该答温家宝还是朱镕基,觉得不好意思,有些慌张。接着,念斌店铺通往丁云虾厨房门的门把手,被福州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分析意见书认定为“倾向于认定含有氟乙酸盐”。
氟乙酸盐是一种A级有机剧毒品,以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脏损害为主。2003年起,被国家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买卖和使用这类剧毒杀鼠剂。
案发12天后,8月10日,公安人员在店铺对面,当着一百多名村民的面,宣布投毒案告破,凶手是念斌。愤怒的丁家人和俞家人,一起打砸了念斌与父母共居的家。这是一幢农村标准的二层小楼,至《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达时,屋里仍满是灰尘、一片狼藉。念家8年未动过的冰箱、彩电碎片一地,一楼客厅还有黑色焚烧物——两个孩子出殡后的遗物,被俞家人带来烧掉。
俞家人自此认定了凶手是念斌。他们分析说,因为村民照顾孤儿寡母,丁云虾的生意比念斌好,这让念斌怀恨在心。10岁的俞攀特别懂事,只要一有主顾,便会主动上前招呼。就算不买东西,也会搬个凳子给对方坐。
两家此前关系怎样,众说纷纭。念家人说,念斌结婚时,丁云虾的弟弟做过念斌的伴郎;俞家人反驳,当地风俗根本没有伴郎这一说,无非是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帮忙去接新娘而已。俞兆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案发之前,念斌就曾倒污泥、拆阳棚,有意无意地为丁云虾添堵。为此,事发前两三个月左右,他还跟丁云虾商量,把现货卖完之后就关门不做。

事发后念斌帮忙叫车送医院的小举动,两家人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念家人说,念斌说要赶紧送医院,还帮忙收拾了丁云虾的水果摊。俞家人却说,这是念斌心虚,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后果严重。
一份审讯录像更加坚定了俞家人的判断。念斌在录像中承认,一个男人来他店里买香烟却拐进了丁的店里,于是他想“教训”一下丁,深夜潜入厨房,将氟乙酸盐鼠药投入矿泉水瓶里,再将水瓶倒进楼梯口煤炉上的铝制水壶中。但他这么做,只是想让对方吃了拉肚子而已。
据当地媒体报道,2006年8月23日,平潭县委、县政府召开表彰大会,对侦破“7·27”投毒杀人案等3起特大刑事案件的有功人员通报表彰。主办此案的平潭县公安局侦查员翁其峰,被提拔为刑侦大队的中队长。
“被刑讯逼供的”死刑犯
“被告人念斌,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意见?”
念斌回答:“不属实,我是被刑讯逼供的。”
2007年3月,福州中院首次开庭审理此案。念斌当庭翻供,表示自己是在遭受了警方严重的刑讯逼供后承认的。比如,吊起来打他,只有脚尖能勉强够到地面;“隔山打牛”,即用书垫着上身用锤子打,用竹片插肋间,生不如死。身体的疼痛,他因难以忍受甚至曾咬舌自尽。侦查人员翁其峰还扬言将他老婆也抓进来,这让他极为恐惧。
2008年2月1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看守所一间囚室约20平方米,住着十几个人。念斌全身佝偻着,戴着只有死刑犯才戴的重刑镣铐,即手铐和脚镣之间还有一段几十厘米长的铁链子,站起来手抬不过腰部。穿衣服时,衣服都被紧紧地卡在手铐一边,要从缝隙里慢慢拉过去。夏天还可以,冬天的厚衣服拉不过去,只能披在身上。
在牢里,念斌的工作是做工艺品满天星。每周能吃到一块肉,周五可以有两个鸡蛋;菜最多的时候是年夜饭,但也是凉的。
看守所里不让写信,但可以寄明信片,他就把明信片当信纸,每次总是连着两三张,密密麻麻的字,每年他都会寄出30张这样的明信片。他并不甘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事实。他写信给姐姐时,让她给自己送一套红色衣服,“我被冤枉儿(而)死,做鬼也不会放过公安那几个冤枉我的人。我会一辈子跟着他们!”
丁云虾一家也很不好过。出事后,她关掉了店铺,靠低保和接济生活。为了唯一剩下的小儿子,她去了平潭县城租房陪读。一年中,她搬了6次家。有房东被她哭得心烦,还有房东知道了她的遭遇,嫌弃她是“扫把星”、不吉利。
公公俞兆发有次帮她搬家,看见家里最值钱的不过是一台14寸电视,一阵心酸。
为弟弟申冤
念斌的姐姐念建兰,承担起了为弟弟申冤的重任。她一头短发,干净利落。她是全家中学历最高的,那时她在福州做会计,没有结婚,生活无忧,直到被卷进这场投毒案中。
她与弟弟感情最深。小时候姐弟俩一起去海边玩耍,将彼此的书包藏起来;无论她多晚回到平潭,弟弟总会骑着摩托车去车站迎接她。夏天傍晚,全家人会在房顶上乘凉,爸爸躺在藤椅上,侄儿骑着小单车绕在身旁,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念斌被捕后,她还时常回想这一幕。
她开始搜寻鼠药,希望模拟起诉书中公布的案情做试验。她不知道氟乙酸盐是什么,至今,她清楚地记得化工词典538页说,以氯化镉加烧碱制成。为此,她还假称研究机构人员,打电话去上海一家生产厂家询问。
她完全不认可起诉书上“向铝制水壶投毒”的事实。开庭前,一位曾去陈炎娇家的姑姑告诉念建兰,在陈炎娇家里,陈一边织着渔网,一边告诉姑姑,案发当天的中午陈就从念斌涉嫌投毒的铝壶中倒了三碗水煮丝瓜汤,如果有毒,中午就该出事了。
念建兰特意买了一支录音笔,让姑姑再去找陈炎娇录下这段话。不料姑姑年纪太大,不懂操作,露了馅。念建兰自己去找陈炎娇,却吃了闭门羹。
宣判前一天,念建兰刚做了阑尾炎手术。听到这消息,她没等拆线,捂着肚子从医院赶到法院,匆匆拟好上诉状让念斌签字。

接着,她揣着2000多块钱,坐火车到北京,去见从网上找的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的张燕生律师。
张燕生看过判决书后,第一句问的是:“如果铝壶的水有毒,那铝壶呢?为什么没有检测?”
一审判决书原文称:“丁云虾的铝壶内的水、高压锅残留物、铁锅残留物均检出氟乙酸盐成分。”
这正是困扰念建兰许久的问题。她问过念斌一审的辩护律师,律师让她“不要多事”,说她“自己找死”,别人没注意到就谢天谢地了。
2008年2月底,张燕生看到了全部案卷材料,产生了更多疑问。比如,念斌供述说,他将买回来的鼠药放在电视机上的货架上,事后将没用完的收拾干净。但是,念斌店内货架、抽屉、地面等等细微之处的土都被公安机关扫走了,却没有发现毒物——警方使用的质谱仪,对毒物分辨率高达500亿分之一克。
“看到货架上全是土却没有检测出毒物的那一刻,我深深确信念斌是无罪的。”张燕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此,张燕生一直坚持为念斌作无罪辩护。
“看到货架上全是土却没有检测出毒物的那一刻,我深深确信念斌是无罪的。”张燕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此,张燕生一直坚持为念斌作无罪辩护。
疑点
“他的表情很麻木,很悲观、很失望,对律师也没有表现出太多期望。”2008年2月中下旬,张燕生第一次在看守所见到了念斌。第一次交流并不畅快,念斌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张燕生只听得懂三成。
被判死刑的念斌,整个人都透着绝望的气息。
2008年12月31日,福建高院二审。张燕生带着锅碗瓢盆上了庭。
此前,她提交了一系列证据。如,据福建省立医院病历记录,丁云虾在事发入院后的12小时内,“无四肢抽搐、无口吐白沫”,这说明她很可能没有中毒。丁云虾只吃了稀饭,没有吃鱿鱼,而氟乙酸盐溶于水,如果水壶有毒,稀饭不可能无毒。
他们进而发现,中毒程度和吃鱿鱼的多少呈正比,和稀饭没有关系。因此,问题可能出自鱿鱼,而不是水壶里的水。
为此,她特别申请,恳请法院向公安部门调取毒物鉴定所依据的质谱图——这一要求,直到5年后的2013年才得以实现。
张燕生还做了一场现场模拟实验。在陈炎娇家,一个与案发日相似的阴雨天凌晨,3人尝试着用矿泉水瓶向水壶嘴倒水,水都从壶嘴溢出了壶外。张以此证明,念斌不可能在相似条件下将水一滴不漏地倒进水壶里。
对这些疑点,检察员并不买账。如,念斌食杂店内没有找到鼠药成分,说明其对现场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清理和打扫;模拟实验无法排除个体差异,不够客观、公正,不应采信;丁云虾作为一名成年人,自身抵抗力高于三名未成年人,因此中毒症状并不明显……
不过,这次庭审还是让念家人第一次看到希望。回到福州的路上,张燕生与念建兰一起,在闽江边点燃了许愿灯。12月,福建省高院果然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福州中院重审。
2009年4月29日,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此前张燕生又有新发现:在翻阅案卷时,张燕生意外发现,房东陈炎娇最早的一份口供笔录是在7月31日,也就是说,事发三天后才录口供,不合常理。
她和助理公孙雪律师去找陈炎娇。陈不太耐烦,让她们找公安去。
“陈炎娇证言缺少案发当天的陈述。”张燕生正式提出新疑点。
当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法医处原处长何颂跃、公安部毒物鉴定处原处长张继宗等4位专家共同出具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公安机关对“门把”的理化检验分析意见书缺乏一级质谱结果,且缺乏杂质峰的结果,因此,不能作为判定毒物种类的依据。
绝望
可这些发现没有改变原定的结果。2009年6月8日,念斌第二次被判处死刑。第二年,福建高院维持了福州中院的死刑判决,直接宣判,没有开庭。案子被送到最高法死刑复核,随时可能执行。
这意味着,死神的呼吸已逼近念斌。
那是个下雨天。听到案子进入死刑复核阶段,念建兰终于倒下了。她失去了斗志。
她辞去工作,大病一场,两周不出家门。害怕接电话,担心一接通,那头就让她去拿骨灰。第一次她挂掉张燕生的电话。甚至不再愿意给弟弟写信。
“我无处可逃,我很累。我想忽略掉所有关于弟弟的消息。”她写信给张燕生,“我已编不出那种虚伪的场景,告诉弟弟‘我们一定会团聚!我已不会鼓励他,因为我都不知道路在哪?我一句话都写不出来啊。”
她苦苦支撑着的世界就要倒塌。念斌出事三个月后,父亲离世。母亲精神失常,天天出去找念斌,迷路回不了家。她不得不把家里的门闩反锁,只能从外面打开。她还告诉念斌的儿子,爸爸去国外打工了。
侄子长大,慢慢不再相信。有一次,侄子考了100分,问她能不能给爸爸打个电话?念建兰只能回答,爸爸那儿没有电话。侄子说,没有电话,怎么能赚到钱?
囚牢里的念斌,也开始害怕天亮,因为死刑执行总是在清晨,特别是在节假日前,“白天怕黑夜,黑夜怕白天”。大概是已经绝望,他开始为身后事做准备。他劝念建兰放弃,“不要把申冤当作你此生的目标,我已经欠你太多。不要让我走了不放心,亲爱的姐姐,你一定要答应我去找你的幸福”。
张燕生同样难受。她和念建兰都不敢接对方电话。她也不敢跟任何人提这个案子,“一提就哭”。一直以来,她坚信,不走后门、不拉关系,凭着良好的职业道德、精湛的技艺和不屈不挠的职业精神,辩护就会取得成功。
然而,事实却是:哪怕法官也听懂了、明白了,就是不采纳。她据此写成《刑辩的绝境》,“所有东西都是违背良知的,没有公正感可言,内心是一种扭曲,人性的扭曲,非常痛苦,摧残一个人的良心。”说着这些,她在一次公开的演讲活动中泪流满面。
为念斌辩护,还为她招来网络谩骂,“杀人犯律师”“无良律师”“丧失职业道德的律师”……
三次重审、四判死刑
等待死刑复核期间,俞家人也在为他们想要的公正而活动。俞兆发及妻子、儿媳妇丁云虾三人第一次到了北京,也是坐的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住在30块钱一晚的北京火车站旁小旅馆,坐公交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门口。
手捧孙子孙女的照片,俞兆发站在门口大哭一场。他70岁了,身上带着老渔民的所有特征:面色黑红,双手粗大。出事那天的鱿鱼是他送去的,这让他有着莫名的负疚感。
他们要求见最高法的主审法官,可惜没能如愿。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失望而归。
不过,这应该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他们如此安慰自己。
念斌清楚地记得,那个等待死刑复核的初夏,夜里11点多快到午夜时,看守所警卫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让他坐下,这是很少碰到的情况。房间里等着的人对念斌说,他是最高人民法院下来复核的,念斌再一次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重复着自己的冤情,他清晰地听到对方的话:他说念斌你放心,即使你今天说这件事都是你做的,我们也是按证据来说话,这个你放心。
那是从2006年被判死刑之后,念斌第一次感到了“高兴”,“ 从2006年到2010年,这是我关在死牢里面第一次见到法院(的人)下来,第一次感到正义的力量。”
2010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核准死刑,将案件发回福建省高院重新审判。
第二年5月,福建高院也撤销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念斌的死刑判决,发回福州中院重新审判。
正是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念斌案恰是有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查机关证据因相继多处出现疑点,法院都没有采信。念斌不死,得益于此。
然而,念斌的命运仍未改变。2011年9月,该案再次开庭审理,11月,福州中院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是念斌获得的第4次死刑判决。他甚至有些习惯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有一天,所有的真相都会告白与(于)天下的。”在一张明信片中,他这样写道。他是一位基督徒,抚摸着姐姐念建兰送进去的一本《圣经》,默默祈祷。
决定性证据
张燕生多次申请后,平潭警方终于提供了房东陈炎娇案发前3天口供笔录。这三份笔录中,陈炎娇说,自己是用“红塑料桶里的水”做的鱿鱼,并证明丁云虾也是使用“红塑料桶里的水”做的白米稀饭。
这与警方提出“念斌向铝制水壶投毒”的说法自相矛盾。这几份笔录因与认定事实不合,被平潭警方藏匿了3年,直到2009年才提供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那之后,陈炎娇的口供多次更改,变成“从红桶舀到铝制水壶”,或者“用铝制水壶的水”。她还说明,之前说红塑料桶,那是侦办人员听错了。2014年福建高院终审判决书因此说明,“证人陈某娇证实是使用丁某虾家铝壶的水还是红桶的水捞鱿鱼,说法不一,难以采信”。
警方提取铝制水壶的时间也很可疑。根据警方现场勘察记录,7月28日,警方就提取了5项物品,其中包括铝制水壶。现场照片中,水壶并没有水。
之后,平潭警方又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水是在2006年8月9日念斌招供之后才提取的,并具体说明是8月9日下午2点提取并送检的。然而,送检报告的鉴定时间是在8月9日凌晨——东西还没到,检测结论已做出。
于是,下一次法庭调查中,警方又在出庭作证时一致改口称“是8月8日下午提取的,提取时有水,3500毫升”。
水壶和高压锅的提取日期被反复改了3次,最终被“统一”为8月8日。
然而,张燕生在另一段现场侦查录像中发现了新破绽。这段由警方录制的画面中,时间标明是8月9日。当镜头滑过厨房现场时,应该在“8月8日”晚上被提取的高压锅,竟然赫然在目!张燕生将其截屏,在法庭上公布。
“法官半天没有说话。”一位在场人士透露。
随着对案情侦查过程的反调查越深入,当年侦查机关的问题暴露得越多。同一天上午,不同地方的五份笔录与活动记录,竟然是同一个公安人员的签名;将委托检验机构的时间涂改,擅自提前;现场勘察提取了150多件物品却只记载5件……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联系福州市公安局内部人士时,得到的回答是:福州市公安局此前已下达命令,禁止评论。据悉,系统内部普遍相信念斌是凶手,但证据链有问题,“当时破案太粗糙”。
事实上,持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疑罪从无”,有人认为,这或许是当年混乱的基层公安状况所要付出的司法成本。
律师斯伟江、张燕生不同意这一观点。8月27日,他们特意发表长微博,再次梳理念斌案的种种矛盾与疑点,“整个故事的每一个情节,包括毒药种类、毒药来源、投毒工具、投毒过程……全部被戳穿和否定,因此可以说是彻底否定了所有指控的全部链条。”
前些天,张燕生去开会,听到有法官讨论念斌案,也说“疑罪从无”。她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招呼人家过来,与对方好好讨论一下。
完全摧毁案件根基的最关键点,莫过于今年初的质谱图分析。
质谱是一种通过制备、分离、检测气相离子来鉴定化合物的一种专门技术。质谱图就是检测物的离子被分离后,被检测器检测并记录下来、经计算机处理后形成的图,是确认毒物的重要依据。
警方一直只提供结论、不提供质谱图。从2008年起,张燕生一再向法院要求调取,法院也下过公函,被公安机关以“内部资料”为由而拒绝。直到福建高院第三次二审、第一次开庭的前一天,2013年7月3日,警方才终于提供。
这一次庭审持续了4天。受益于2013年施行的新《刑诉法》,当年的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和毒物专家得以出庭,当面对质。侦查人员翁其峰出庭时,旁听席上,念建兰情绪激动,大骂其刑讯逼供、冤枉念斌;另一边,受害人的家属则高喊“人民的好警察”。
然而,对关键证据质谱图的辩论,双方久持不下。
今年2月6日,张燕生与念建兰到达香港。一位专家告诉张燕生,质谱技术由国外传来,我国内地很多毒物检验和质谱技术分析专家是在香港接受培训的。通过网络上的工作电话,她们找到了皇家澳洲化学学会院士、香港政府化验所高级化学师莫景权。
莫景权等香港专家的结论是,这26张质谱图根本不含有任何氟乙酸盐!
听到这话时,坐在莫景权对面的两人几乎蒙掉了。“这么多年以来,不仅是我没有怀疑过,我敢说包括各级参与审理的法官在内,没有人怀疑过,死者不是死于氟乙酸盐。”张燕生事后在博客中说。
她的疑问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常识中,如果是吃进了毒物,肯定是胃中的检测浓度大于肝,肝大于血,血大于尿。如果死者的心血、尿液检出毒物,为什么胃、肝脏没有检出来?
莫景权向她们解释,从质谱图上记录的时间可以看出,两个尿液样本和实验室氟乙酸盐标准样品检测的开始时间及结束时间完全一致,而福州市公安局所使用的仪器同一时间只能检测一个样本,因此可以认定三张质谱图来自同一个样品,即实验室氟乙酸盐标准样品。
专家打比方说,这相当于把心脏病患者的心电图给了另一个人,然后说那个人有心脏病。
2014年2月9日,张燕生发表博客文章披露了此事,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结尾甚至失态地连续骂了三句脏话。
莫景权、张继宗等8位专家共同出具了一份《北京香港两地专家关于念斌投毒案理化检验报告的意见》,其中结论是:现场物证(如肝、胃、心血、尿液、呕吐物、制造鼠药工具、铁锅、高压锅残留物、铝壶内的水、门把及陈玉钦家中的鼠药和黄色液体等)的检验结论,应该皆为未发现氟乙酸盐,本案件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氟乙酸盐曾被使用过。
这些疑点,最终被终审判决采信。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榕刑初字第1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上诉人念斌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现场物证的检验结论,应该皆为未发现氟乙酸盐,本案件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氟乙酸盐曾被使用过。
由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被害方诉讼代理人、福建信哲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自生、李莉,委婉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约访请求。他们称,案件已经结束,不希望在媒体上继续争辩。他们尊重法院判决,认可在程序、证据等环节上,公诉方确实存在问题。
无法挽回的人生
当念斌步出法庭,念建兰与他抱头痛哭。此前,她已48小时没有合眼。
为了弟弟,她成长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女斗士”。全国两会期间,她搜索两会代表的通讯地址,寄出救助材料。发外省的EMS起步价23块,发本地18块,这么些年,光邮费就花了一万多块。到后来,快递小哥忍不住劝她不要寄,因为他送到信访单位的材料,人家拆都不拆开。
念建兰还是要寄。她买了打印机和墨盒,朋友偶尔送一些打印纸。以前每寄出一份材料,心里就多了一份希望;后来则是为了说服自己已经尽力。总是要做些什么,如果停下来,她会有深深的负罪感。
8年间,她渐渐失去笑容,仇恨在脸上挂了相。身边人说她面相很凶,说她的微博都是咆哮体。她不修边幅,一位朋友的孩子甚至说,“建兰姨是拉板车的。”这名字她自己后来很少用了,一切以“念斌姐姐”示人。
她的性格,自尊而又自卑。她上访过,但明白不能因此失去自由,从不做过激行为。有一次,与其他两位上访者在北京街头合影,她一再说,要笑,“如果你看见我哭了,第一次会怜悯,但到了第三次你会烦的。”
如今,她终于可以放心微笑了。在蜂拥而至的闪光灯下,与弟弟念斌合影时,念建兰每次都露出笑容。
按平潭风俗,死里逃生的人应该放鞭炮、戴红布庆祝,但为了不刺激俞家,念斌只换了一套新衣,吃了一碗“平安面”。他身体虚胖,上楼梯时膝盖僵硬而需要搀扶。老家的紫菜汤,有一天他多吃了一碗,便堵在胃里难受得很。
他不会用智能手机,一黑屏就手足无措;现在手上拿的,是一部早已淘汰的黑白屏诺基亚。儿子已经12岁了,沉默着,不愿意也不敢跟他多说话。他记得以前儿子“很聪明,很活泼的”,现在眼前的孩子内向,看见陌生人很害怕。作为父亲,他的心里很难受;有一次,儿子让他帮忙拧开饮料瓶盖子,他却怎么也做不到,这让他充满挫败感。
他还没有想好怎么开始以后的人生,“或许会去学习种点大棚蔬菜。平平淡淡,家人平安健康就可以了。”
俞家人却不那么容易放过他。听到终审判决时,俞兆发直挺挺地晕了过去,“就像又吃了一次毒药一样”。
2007年第一次在平潭开庭时,俞、念两家人只是语言争执,没有拳脚相向。而越到后来,双方恶意渐深、事态逐渐升级。在双方唯一直接接触的庭审现场,念建兰曾被俞家亲属追打,丁云虾也在休庭时将矿泉水瓶砸向张燕生的头。
如今,俞家人对媒体记者的态度很是矛盾,一方面希望传达声音,另一方面又认为记者都被念家买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俞兆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时不时地提高音量:“说这么有什么用?你们都在帮他们,不帮我们!”
南赖与澳前,两个村子的气氛透着些许诡异。有人看到俞家播放的念斌审讯录像,认为念斌还是凶手,也有人摇摇头说不知道。房东陈炎娇仍住在事发楼房里,房屋已装修,厨房移到了门外。她阴沉着脸,不发一言,拒绝记者探问。
8年后,案情又回到原点。事实上,中毒原因仍没有查清,是何毒物也无法确定,整个事件回归到案发时的混沌未知。
伤害最大的,还是被害者俞家。俞兆发常常想起两个乖孙。他记得有一年过生日,俞攀拿了一张白纸,写上“爷爷生日快乐”送给他。他有三个儿子,俞悦是他唯一的孙女,如今却不在了。
他做梦,梦见俞攀俞悦站在身边,只是哭,不说话。他问,你们做什么?两人也不回答。
他的儿媳丁云虾,至记者发稿时止,还没有走出福建高院大门。据说,高院为她准备了一间上访室,送东西给她吃。她不愿离开,因为“出来就进不去了”。
有次庭审结束后,丁云虾指着念建兰破口大骂。念建兰将背包放在胸前,一时无言以对,站在原地听着。她明白,对方也需要发泄。
几分钟后,念建兰突然觉得凄凉——“你我不过都是被命运玩弄、被他人掌控的小人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