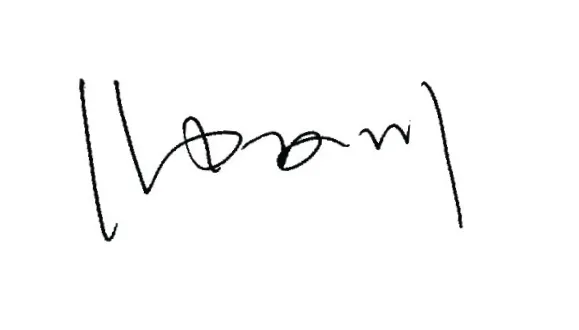故乡,只在审美中
2014-09-03本刊编辑部
故乡,只在审美中
“母亲织布的机子和父亲坐着的老椅子,奶奶拧麻绳的拨架和那一摞摞粗瓷黄碗,老屋木梁上吊着的蜘蛛残网以及这老宅古屋所散发的气息,都使他潜藏心底的那种悠远的记忆重新复活。尤其是中午那顿臊子面的味道,那是任何高师名厨都做不出来的。只有架着麦秸棉征柴禾的大铁锅才能煮烹出这种味道。”
这是陈忠实描述的一次回乡感受,主角是已晋升为保安团长的白孝文。白团长带着新婚媳妇,骑着高头大马,回到白鹿原故乡祭祖。
这是文学与传统里的故乡。
张季鹰在洛,见秋风起,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辞官回江南。
余杰访问瑞典,城堡上俯瞰北欧大地绿茵如画,忍不住感叹:“此地风景大好,叹无回锅肉!”于是回国。
去年10月,我在这里写下一篇《昨夜寒蛩不住鸣》,思念故乡的霉豆腐、剁辣椒,于是埋头继续码字。
这是长在胃上的故乡。
1980年代的流行歌曲《我的故乡并不美》,旋律铿锵,节奏古怪,借冒犯传统中那个美丽的故乡意象,将那个时代既盛极一时又远不够彻底的反思气氛推到极致。
互联网初起时的BBS时代里,70后才子王怡引领,天涯社区那一波网友们竞相同题撰文《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这是在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痛苦反省,三步一徘徊的故乡。
我总在想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农民工孩子眼里的故乡是什么样。他们生长于都市,其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回到从无印象的故乡,以准备迎接高中生活和高考。
我还在想东莞性服务行业里的姑娘们眼里的故乡是什么样。都市丛林里,她们也许是最不喜欢谈论故乡的人。常人回乡,是近乡情怯。她们总是要努力将故乡和熟人彻底赶出日常生活图景。
这是在现实煎熬中的故乡。
社交工具陌陌在文宣中预言:“中国在进步,个体信任必将要过渡到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包含了对城市文明和陌生人的信任,相信与陌生人的互动是平和与无害的。”
我认同这种判断。问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既未挣脱农业文明的襁褓,工业化还在进程中,现代化又远未完成。我们就是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时代里的一群尴尬人。既留恋故乡的温情与乡情,又无法远离城市的资源与文明。
在这里,故乡,成为一种纯粹的审美,一种精神存在,一个文化符号。
这就是春节返乡大潮结束后,不少人感叹“故乡,我只爱你三天”的缘故。
白孝文确实也只待了三天。祭祖完毕准备打道回府的白团长清醒地发现,他的故乡也回不去了:
“这些复活的情愫仅仅只能引发怀旧的兴致,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了,它还是更喜欢跳上墙头跃上柴禾垛顶引颈鸣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