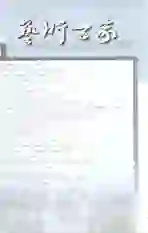中国古代画者身份与社会地位辨析
2014-09-02梁振忠
梁振忠
摘要:在“诗性时代”,巫有着与神灵沟通的能力和敏感,几乎是集后世的“圣”、“王”于一身。东汉以前的画者多是朝廷、官府人员;后世文人画家对于“士气”的强调和追求,不是出于自我标榜以排斥职业画家这样的鄙俗理由,而是有其内在的文化性格需求。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绘画艺术;巫史;士;文人画;身份;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Identity and Social Status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ers
LIANG Zhen-zh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Industry,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250022)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亦即尚其所志之道也。在中国历史上,“士”对文化传统有着特殊的意义与特殊的价值,可以说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离不开对士大夫的研究,士大夫一身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甚至在士大夫的祖先——巫的时代,因为他们有着与神灵沟通的能力和敏感,所以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几乎是集后世的“圣”、“王”于一身。所以,无论任何时代,或是垂文、明道,或是创典、述训,几乎是士大夫创造、记录并传续着每个时代的文明,保留了文化传统。所以,《文心雕龙·原道》中说: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1]
这里的“文”包括了“形文”、“声文”与“情文”,“形文”就是指形体方圆、玄黄五色等所有可视之“文”。 其中,对“文”的理解之一是指天地万物一切的自然表象。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只有贤哲之人才能借此“文”窥到无形的阴阳之数,而庸愚之人仅能感知到表面现象。士人这一身份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观念及形式的成熟有着深厚的关系。
1.东汉以前画者的身份
关于东汉以前画者的身份问题,葛路的《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说:“至于文人介入绘画从何时而起,据史料记载,可能至少要追溯到汉代的蔡邕,据魏孙畅之《述画记》说:‘灵帝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与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之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从事绘画已是普遍的现象,有的甚至在绘画实践的基础上开始了理论的总结和探讨。”[2]这种观点是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张建军也根据现存最早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历代名画记》中记有文人士夫“擅画”,来用以说明:“至迟在东汉,一些文人士大夫已经开始涉足到绘画领域一展风采。”[3]另外,还有观点认为魏晋以前绘画乃工匠之事而从魏晋开始文人“参与”绘画所以才提高了绘画的地位这种无稽之说。其实不然。一则并没有明确史料记载说文人就是从某个时期(比如说东汉)才开始参与到绘画中来的,即使有但也不足以说明此前绘画就是工匠的事情;再则,《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治,由是文籍生焉。”《周易·系辞》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从这些关于开书画之先河的记载我们知道,书画本同源而生,更何况文字也有始于象形(含有图画之意)之说。正如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中所说:“文字与图画初无歧异之分。迨后制作日繁,绘画之事则以五彩画十二章,藻火、粉米、山龙、黼黻之属为旗常、衣服之装饰,彩色之用,因以发达。华丽壮美,以兴起诚敬欢悦之感情。凡文字之所不能表明者,借此以表明之。”
艺术是思想的东西,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心灵的历史,从书画产生开始,用以表达思想感情的书画是与那些“识天象,知天道”的巫史、圣贤、士夫、儒者浑然一体的,“文以载道”,也可以理解为书画是他们明道、呈道、示道的载体。张建军先生也认为:“我们以前的美术史研究中,过多地强调了早期画家地位之低、画为贱技之类的看法,认为在文人画兴起之前的早期士大夫不会放下架子去从事绘画,其实这是并不全面的。”[3]
按照雅斯贝斯的看法,在“哲学突破”的时代以前,有着漫长的“神话时代”,这一时代又被维柯称为“诗性时代”。我国文化有着巫史的传统,李泽厚则将远古到殷、春秋末期定为巫史阶段。巫便是后世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祖先。四川大学的童恩正教授《中国古代的巫》一文中对巫作了全面的考察,认为,仅仅将中国巫的研究作为宗教史的一部分来看待是不够的,夏朝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就是由巫的后继者祭师构成。[4]文中他引用李安宅先生的话说:“我们不要以为现在留下来的巫术是迷信,轻视它的历史价值。迷信固是迷信,但它有过它的光荣历史。”[5]当时人人都可以执行仪式,但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巫。关于巫的主观条件,《汉书·郊祀志》有一段很好的概括:“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而关于“巫”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司马迁曾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史记·龟册列传》中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矣。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盆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盆,断以曹龟,不易之道也。”
正如童恩正得出的结论那样,“在原始社会里,巫是氏族的精神支柱,是智慧的化身,是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一切撅难的解答者。很多后世分化出来的独立的科学,如天文、历算、医学、法律、农技、哲学、历史,以及文学和艺术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歌咏、音乐、舞蹈、绘画、神话传说等等,当时都是由巫所掌握。”[4]列维·斯特劳斯也曾提到过在原始部落中,画家、雕塑家等艺术家具有类似于巫师的崇高地位。[6]endprint
刘泽华先生《先秦士人与社会》里就统计有“巧士”、“伎士”、“技艺之士”等,都是能于技艺之人。现代考古中发现的各地文化遗址出土的绘有人像、猪、鸟、虎、鱼等小型石雕刻品,以及文化建筑遗址等都说明是巫的时代由巫图画出来的图案,融入了他们的思想,也反映了他们的审美。
从材料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画者多是朝廷、官府人员。《周礼》载:“冬宫设色之工,画绩钟筐。”“春宫司常掌九旗之物。”“冬宫梓人掌五彩之侯。”
《周礼·考工记》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还说,“知者创物,巧者述而守之,世谓百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注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车服器械间百工者。”从这里可以看出,首先,百工是属于司空属下之职位,这说明早期画家身份并不尽如当前流行的观点认为的那样是低贱的;其次,“知者创物”、圣人“作”而百工“述而守之”,也就是说,将思想情感等观念以形象呈现出来的工作非圣人、知者而不能为,而这恰恰就是艺术的创造性所在,足以看出“圣人”、“知者”一直是与艺术创作相伴的。
另外,《庄子·田子方》载:“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史”为古史官,也是“巫”的一种。中国古代有左图右史之说,中国传统文化首重史学,“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中国文化甚至被径称为“史官文化”,所以,画家被称为“画史”,可见在先秦时期其地位之尊重。
2.绘画是神圣的事情
在历代画论中,绘画一直被很普遍地认为是神圣的事情。南朝宋之王微,赞同颜光禄的观点认为:“以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陆机也有“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的看法。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说:“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 在张彦远看来,绘画“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是“国之鸿宝,理乱之纲纪”,是一种神圣而又须“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必须要学养方能成就的一门艺术。
据刘泽华先生的研究,“岩穴之士”是“隐士”的一种,另外有“高士”、“闲居之士”,“居士”“处士”等,“这些人并非绝对远离尘世,不问世态炎凉,其中有些人还颇为关心社会、时政”,是典型的志于道的士大夫。[7]
不同的历史时期,“士”始终在参与着绘画,只是时代的限制下,在绘画自身成熟的过程中,使目前能看到的东汉前的画作以其特有的载体和形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的确是出现在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更多地从事文学艺术确实与东汉中期以后的风气有关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东汉前画者就是工匠,或从东汉开始才有士夫文人参与到绘画中来。从上文所引材料来说,本文不认为东汉以前“士”没有参加到绘画中来,恰恰相反,蕴含思想、表达理念的绘画图案一直都是“士”的分内之事,无论是原始艺术中各类图案,或是三代时候钟鼎彝尊上各种饕餮、螭文、雷文、云文等等,从中我们看到的是高度理性的思考,周密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秩序,是体道至深的思想的呈现。若非有智慧有思想、能见文而明道者,决不能有这些图案的产生。 (责任编辑:帅慧芳)
参考文献:
[1]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3]张建军.中国古代绘画的观念视野[M].济南:齐鲁书社,2004.22.
[4]童恩正著.中国古代的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
[5]李安宅.巫术的分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31.11.
[6]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看·读·听[M].北京:三联书店,1996.166.
[7]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