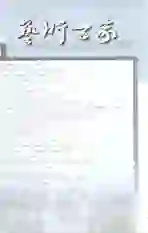从内容到形式:南通童子戏的审美形态嬗变
2014-09-02马鑫明
马鑫明
摘要:本文围绕南通童子戏形态的演变过程,提出童子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审美嬗变,并分析其嬗变的三个阶段,即戏剧化祭祀、戏仪合一及祭祀的戏剧。
关键词:南通童子戏;祭祀仪式;戏剧艺术;内容;艺术形式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From Content to Form: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Nantong Boy Opera
MA Xin-ming
(School of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01)
南通童子戏属香火戏、傩戏一族,是由古代通州民间的“上童子”、“童子会”等祭祀仪式演化而成。
南通在唐以前是长江入海口的一块沙洲,称胡逗洲,“胡逗洲上多流人”,楚越的巫觋也随着流人进入,并逐渐被当地的文化同化,产生了古巫觋和江淮傩的又一分支——南通童子。在南通地区,童子充当神与人的中介,通过仪式、唱诵、歌舞,呈表人的愿望,传达神的旨意,从而达到消灾避祸、纳吉颂祥的目的。其上传民意、下授神旨的仪式活动,称为“做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类叫“上童子”,也有的叫“谢神”、“除疫”、“还愿”、“烧纸”,也有的干脆叫“童子上圣”,是单个家庭为家人祛疫、治病或求子、祈福等举行的仪式活动;还有一类叫“童子会”,这是以几户农家联合举办,或者由村里统一代办的祈神活动,俗称“做大劝”,土话叫“串戏”。“做会”的祭仪流程,由数十个单元串连而成,每个单元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戏剧元素,民间称之为“做愿”、“做执事”。这一活动到近代发展为巫术与戏剧的原始结合,一般称为“童子戏”——祭祀仪式剧。20世纪50年代以后,童子戏中的巫术成分被剥除,发展衍变为一个地方剧种——通剧。20世纪80年代后,通剧的现代剧目逐渐减少,复以传统戏、祭祀剧为主,逐步回归童子串戏的传统套路,又恢复了“童子戏”的称谓,但已带上了鲜明的实验通剧的印记。
(一)内容中孕育形式:童子祭祀仪式中的歌舞说唱、做劝演戏等形式孕育着民间戏剧的胚胎,并因其娱人因素而不断地发展着
王国维认为戏剧的主要特征是“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就是扮演人物讲故事。南通童子祭祀活动最早的是后周显德年间,巫人“潘烂头,名桂源”,“善驱役鬼神,嗜酒不羁。一日,乘醉如厕,书符招将,将怒以笔触额,额随溃烂不愈……”巫人潘烂头——童子的巫傩祀神活动中已有行动“书符”和简单的情节“招将”。
明代,童子活动十分活跃。嘉靖六年(1527),钦差雷应龙下令:“民庶祭祖先,岁除祀。春秋祈土谷之神,凡有灾患,祈于祖先。苦乡属邑属之祭,明里社群县则自举之……巫觋扶鸾祈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这时,童子消灾祈神的仪式活动主要是扶鸾祈圣、画符、唱念、咒语等,可以说集巫歌、巫乐、巫舞、巫技、巫戏于一体。官府虽然禁止,但这些祭神活动却融入迎神赛会之中,在娱神的内容中增加了娱人的形式。万历四十四年(1616),“城隍会上,装饰诸魑魅魍魉之状,游行于衢市,易人于幽冥。”天启二年(1622)通城“香火撮土于墙角,鼓角雷霆,旌旗日月,傀儡男妇,面目牛马”。此时的祭祀仪式已带有明显的戏剧因子。童子已经是出于不同的目的“扮演人物”,如或“装饰诸魑魅魍魉之状”,或“傀儡男妇”,“面目牛马”,要把驱鬼护佑生灵等形象化地“演”出来。随着童子这种故事化情节戏剧因素的增多,祭祀仪式的某些内容逐渐发展成具备“扮演人物、表演故事”等因素的戏剧。但由于它又是祭祀活动的一个内容,不能独立存在,“表演者”、“参与者”、“观众”都虔诚地把它当作祭仪,所以它还不能算是戏剧,只能称为具有戏剧因素的祭祀仪式。
(二)内容即形式:祭祀活动以戏的形式行仪的内容比重逐渐增大,表现为亦仪亦戏,仪戏合一,由祭祀仪式向戏剧形式过渡
在童子的祭祀仪式中,以戏剧的形式宣传鬼神的威慑力有着特殊的意义,且具有观赏价值,能吸引更多的观众。于是,童子在祭祀中自觉地增加对这种形式的利用,并逐渐提高其表演艺术和表演技巧,从而不知不觉地引发其内核的变化,即祭祀性质逐渐退却,表演性、娱人性在增强,虽然其核心内容仍然是祭祀活动,但是形式上则相当接近于演戏,审美上日益倾向于世俗化,成为既是祭仪,又是演戏,亦仪亦戏,仪戏难分的形态。
清代童子艺人有文武之分和内外坛之分。艺人乡间做会,演出驱邪纳吉的童子会戏,四时八节不见间断。乾隆五十八年(1790年),白蒲人姜恭寿目睹巫人求雨时的傩舞戏演出:“小巫击钟,大巫击鼓。披发旋旋作鬼舞,欲雨不雨神其吐。(二解)儿呼父,妇呼姥。老翁手捧香,前设鸡与。”这里已蕴含着现在南通童子祭祀仪式中的戏剧形式,如:供奉鸡与猪羊,焚香设坛,坛场作戏场,仍是今天南通童子演出场所的基本格局;“小巫击钟,大巫击鼓”的打击乐伴奏样式今天的南通童子仍然沿用;“披发旋旋作鬼舞”是一种装扮、表演,还有驱赶旱魃,迎接龙神的歌舞动作,这标志着迎神赛会中的南通童子已迈上戏剧化仪式与仪式化戏剧的门槛。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集祭祀与戏剧为一身的南通都天会十分兴盛。十番锣鼓、抬阁等行街表演在包容量极大的综艺形式框架中,有舞龙、舞狮、舞滚叉、鼓锣班、吹鼓乐、挑花担、倒花篮、跑马灯、花鼓灯、踩高跷等,有戏剧表演如八仙过海、唐僧取经等,名为娱神,实为娱人。可以说,都天赛会有些表现形式已经具备了简单的故事情节,有了角色的简单分工和戏剧化的表演,形成傩戏的雏形。如鬼班中“摸壁鬼”、“醉汉佬儿”的驱鬼逐疫;“烧马夫香”者在神轿前的往复奔波;“抬判”中的判官、钟馗与“蝴蝶”中的“人物”冲突;“地理鬼”戏“马叉鬼”中的插科打诨等等,他们通过简单的情节、戏剧冲突和艺术形式来表现明确的祈神驱鬼的目的意图,既是仪式,亦为戏剧。
戏剧性的娱人效应也是赛会盛行的原因之一。清盛行各种赛会,如“村部平安时作会,巫现歌舞历万年”,“万宝秋成祝满仓,村村赛鼓觋巫忙”,便是农村做会盛况的真实写照。农家麦收时节颂神媚圣则是“石首鱼来麦迎秋,迎赛年年歌舞剧”。童子的祭祀仪式活动通过戏剧不间断地表现出来,具有完整的情节,其中的祭祀内容、意义也有所变化,更趋向于世俗化、娱人化。endprint
(三)形式中积淀着内容:祭祀意义与戏剧因素手段相易位,戏剧化的祭祀演变为含有祭祀内容的戏剧、“祭祀的戏剧”
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童子戏艺人不断吸收融汇其他艺术样式如京剧、徽剧的某些成分,增加了“开坛、上圣、莲花、捉鬼、添寿”以及内坛的唱书、外坛的杂耍等,表演越来越生活化、社会化、艺术化,从娱神到娱人,神圣氛围逐渐淡化,世俗娱乐的成分不断增加。如早年“十三部半巫书”,童子只唱无白,以后为加强演出效果和满足观众需求,增加了少许韵白和简单的表演。清末民初,个别书目分角色表演,演变发展为童子戏。民国年间,演戏祈神已开始从迎神赛会中剥离出来。1921年,通州秦灶童子艺人徐长元,学习京剧的穿戴,自苏州、上海购得戏曲服装,勾画脸谱,在龙潭庙串演传世文《唐僧取经》,开童子舞台演出之先河。这一革命性的举措,使童子戏套上了双重外衣。剧目既可作为童子祭祀活动中的仪式戏剧敬神娱人,也可列入世俗乡土戏曲娱人乐神。这一时期,童子艺人的酬神戏十分活跃。
可以说,这时的童子戏演出已不再是祈神祭规的一种仪式了,而是一种戏剧艺术。但是其中又明显留有与戏剧无关的宗教祭祀意义的活动,与纯正的戏剧有别。因为其中具有祭神祀鬼的功能,常常在家中出事时,请来童子戏演出,演出游离于戏剧之外,鲜明的宗教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童子戏的戏剧形式所具有的观赏娱乐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地方对戏剧化的祭祀仪式进行改造,把它纳入地方戏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其中仍然非完整地保留了不属于戏剧范畴的祭祀活动内容,使具有戏剧形式的祭祀仪式变为含有祭祀内容的戏剧。
1957年春,南通骑岸业余剧团在上海红霞歌舞团的帮助下,整理了童子戏十几个腔调,对传统声腔进行比较全面地梳理,并首次用于剧团创作演出现代小戏《三看亲》《水稻大王》。其时,南通市郊区文化站组织童子戏老艺人成立南通市童子业余剧团,演出传统剧目《李兆廷·写退婚书》《秦香莲》,从乡间的草台走上剧场。自此,童子戏开始向新的地方戏曲嬗变。为了摆脱其巫觋的社会功能和迷信色彩,易名为“侗子戏”,并于1958年成立了南通市侗子实验剧团,后又更名为僮子戏实验剧团。僮子戏对传统童子戏的声腔和伴奏进行改革,引入民间山歌、小调、号子,并借鉴吕剧等地方戏曲音乐素材。在创作手法上,吸收京剧板腔体的规律,形成板腔体、曲牌体、小调联缀合一的趋向,出现了多种板式和适合行当表演的唱腔。此外,演员开始适应定腔定调的规范,脚色行当明朗化,有了小生、花旦、老生、小丑、彩旦、恶旦和花脸之分。演员也不再是单一的童子艺人,业余剧团青年演员也加入进来,剧目以现代戏为主,整理改编传统戏为辅。1960年5月,僮子戏实验剧团易名为南通市实验通剧团,开始了南通地方新型剧种实验全面启动的新阶段。实验通剧在继承传统童子戏老腔调的基础上,加强声腔改革,通过现代戏《白毛女》、传统戏《陈英卖水》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借鉴,糅合了京剧、歌剧、话剧的表演手法,开始注重形体动作和内部心理体验的有机结合,以探索新型地方戏为途径。实验通剧剥离宗教祭祀仪式,脱离了巫术的社会功能,不存在与个人目的相关的功利诉求,俗称看人戏。基本在剧场镜框式舞台、四堵墙环境中演出,台上演戏,观众买票台下看戏,观众与演员是定位清晰的审美主客体对应关系。1964年9月,南通市实验通剧团撤销,实验通剧的探索活动至此中断了。
“文革”以后,童子艺人自由组合成立松散的民间演出队,演出伴奏仍用锣鼓,男女同腔,音调随意,场所以村台为主,在剧目的呈示形态上,基本是回归到童子戏传统的老路上去了,但已经带上了鲜明的实验通剧的印记。
如今,童子戏更多是娱人的地方戏剧,但是在此前它确实有着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严重的祭祀仪式的巫术含义。童子戏作为娱乐的形式,人们从中获得的不仅仅是愉悦感,更多的是复杂的观念及神灵保佑的意义。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童子戏的巫仪性内容逐渐淡化,世俗化的娱人形式在加强,但是巫仪性的内容已积淀于世俗化的形式之中,在娱人形式中蕴含着观念积淀下来的情感。(责任编辑:徐智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