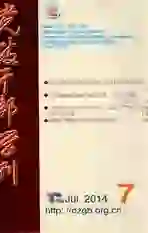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政体制度的偶然任意性
2014-09-01王海明
王海明
[摘要]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论原理,一个国家究竟实行何种经济制度,亦即何种经济形态占据统治地位,说到底,皆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究竟如何,因而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和不可自由选择的。相反地,任何政体制度,不论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却都曾出现于生产力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都曾出现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因为,任何政体制度都不是被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必然决定的,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不是必然的、不可选择的、不可避免的;而是充满各种可能,是偶然任意、可以自由选择的。
[关键词]经济制度;经济形态;政体制度;生产力;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B03;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7-0004-08
上篇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毋庸赘言,生产关系与经济、经济基础或经济活动是同一概念,都是关于物质财富的活动,亦即生产与交换以及分配与消费之和。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或经济、经济形态固然并不相同,却也相去不远。因为所谓制度,正如罗尔斯所言,无非是一定的行为规范体系:“我将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1]因此,所谓经济制度,就是经济、经济形态或生产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系。这样一来,生产关系或经济活动虽然不是经济制度;但是,一个社会实行、选择何种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与经济制度却是同一概念:实行何种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属于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的行为规范体系范畴。
最重要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恐怕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揭示的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亦即一个社会实行何种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的历史必然性。这一规律可名之为“生产关系高低与生产力高低正比例规律”。首先,马克思发现,生产关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2]
确实,一个社会实行何种生产关系、经济形态或经济制度,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如果某种生产关系或经济形态、经济制度适合生产力,就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就会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那么,即使人们讨厌和不想实行这种生产关系,或迟或早也必定实行这种生产关系。相反地,如果某种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就会给人们带来巨大损失,那么,即使人们喜欢与渴望实行这种生产关系,或迟或早也必定改变和抛弃这种生产关系,而代之以与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3]
生产关系所具有的适合或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是生产关系的独自具有的属性,不是生产关系的固有属性,而是生产关系被生产力发展变化所决定的属性,是生产关系的关系属性。因此,任何生产关系、经济形态或经济制度,即使是惨绝人寰的奴隶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限度——亦即没有变成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力的限度——内,都是适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但是,当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一定限度,从而成为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力的时候,原来的生产关系便由适合、促进生产力发展,变成不适合与阻碍生产力发展了。这样,或迟或早,必定发生生产关系革命,转化为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从而能够适合、促进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力: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
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只能适合且产生于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力,而不适合或不可能产生于比较低级的生产力。奴隶制或封建制比原始共产主义更高级,因而只能适合比原始社会更高级的生产力,如金属工具生产力,而不适合原始社会生产力,不适合石器生产力。如果在生产力还处于石器水平因而没有剩余产品的时代,就实行奴隶制或封建制,奴隶或农奴必定饿死无疑。因此,不但比较低级的生产关系只能适合比较低级的生产力,不能适合比较高级的生产力,而且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也只能适合比较高级的生产力,而不能适合或不可能产生于比较低级的生产力。
因此,任何生产关系都只能适合一定的生产力,而不能适合一切生产力,它对于生产力的适合或不适合都是暂时的、历史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3]
这样一来,一个社会究竟实行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还是比较低级的生产关系,便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因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比较高级的生产力,必定产生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如果仍然是比较低级的不发达的生产关系,或迟或早,必定会发生生产关系的革命,从而产生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4]因为只有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合、促进比较高级的生产力,给人们以巨大利益;而比较低级的生产关系则不适合、阻碍比较高级的生产力,给人们以巨大损害。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断言,比较低级的生产力,必定产生比较低级的生产关系。如果产生了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或迟或早,必定又回到比较低级的生产关系:“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2]因为只有比较低级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合与促进比较低级的生产力的发展,给人们以巨大利益;而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必定阻碍或不适合比较低级的生产力,给人们以巨大损害。于是,无论哪一种生产关系,只要生产力还没有成为新的、比较高级的生产力,因而还适合生产力发展,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是决不会产生的。在新的比较高级的生产力还没有获得以前,如果比较低级的生产关系灭亡了,新的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产生了,那么,或迟或早,必定会发生生产关系的复辟,又回到原来比较低级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
生产力产生和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较高,生产关系必较高;生产力较低,生产关系必较低:生产关系高低与生产力高低正比。倘若微观言之,则因为生产关系高低与生产力高低成正比,所以,较高与较低生产力的高低差异程度,必定与它们所产生的较高级与较低级生产关系重要属性的差异程度成正比:较高级与较低级生产关系重要属性差异越多越大,它们所适合的较高与较低生产力的高低差异就越大越显著;较高级与较低级生产关系的重要属性差异越少越小,它们所适合的较高与较低生产力的高低差异就越小越不显著;较高级与较低级生产关系的重要属性接近完全相同,它们所适合的较高与较低生产力的高低差异就接近消失而归于零,它们就能够同样适合同一水平的生产力。
这就是生产关系高低与生产力高低微观正比例定律,它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而越来越彰显昭著。举例说,奴隶制或封建制生产关系与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相同点极少,似乎只有自然经济;而不同属性较多且重要,如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别、无阶级无剥削与有阶级有剥削之别等等。因此,奴隶制或封建制生产关系所适合的生产力,高于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力,二者截然不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奴隶制或封建制生产关系,共同点极少,似乎只有私有制;而不同点较多且重要,如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之别,经济强制与超经济强制之别等等。因此,资本主义所适合的生产力,远远高于奴隶制或封建制所适合的生产力,二者极为不同。
相反地,奴隶制与封建制生产关系虽有高低之分,但就其重要属性来说,几乎完全相同:都是私有制、都是自然经济、都是超经济强制。二者的不同点,只不过在于,奴隶制的超经济强制是人身占有,而封建制的超经济强制是人身依附罢了。封建制与奴隶制生产关系重要属性几乎完全相同,意味着,封建制与奴隶制生产关系所适合的生产力之间的高低差异极其微小,接近于零,因而能够与奴隶制一样适合同样低级的生产力,亦即一样适合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铜器生产力。试想,奴隶与农奴,岂不同样能够使用铜器生产工具?岂不同样能够进行以铜器生产工具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劳动?这就是为什么,封建制生产关系虽然比奴隶制生产关系高级,但封建制生产力却未必高于奴隶制生产力。
封建制生产力未必高于奴隶制生产力,不是别的,恰恰是“生产关系高低与生产力高低微观正比例定律”所能够解释的典型事实,完全符合这一定律,因而并没有否定“生产关系较高生产力必定较高、生产关系较低生产力必定较低”,并没有否定“生产关系高低与生产力高低成正比例定律”。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普遍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否定了这一定律吗?也没有。
诚然,按照这一定律,社会主义生产力必定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二者不同属性多且重要,如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别、有经济强制和经济权力垄断与没有经济权力垄断和经济强制之别、无阶级和剥削与有阶级和剥削之别等等。更何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虽然跟原始共产主义与奴隶制或封建制的不同,极为相似;但是,一方面,原始共产主义与奴隶制或封建制是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无疑需要远为高级且复杂的条件;另一方面,原始共产主义与奴隶制或封建制是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因而二者生产力的高低差异必定更为巨大。
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适合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适合的生产力之间的差异必定极大:社会主义生产力必定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力是发达的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生产力必定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然而,事实却是,当今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都低于资本主义生产力。这一事实岂不否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必定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理论?岂不否定了生产关系较高、生产力必定较高的论断?岂不否定了生产关系高低与生产力高低正比例定律?不!决没有否定。
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力低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事实,充其量,不过意味着对“生产关系高低与生产力高低正比例定律”的违背;而任何规律或必然性都决不会因其被违背而不成其为规律或必然性。违背规律或必然性的自由活动必定受到规律或必然性的惩罚,必定达不到目的而失败;只有遵循和利用规律或必然性的自由活动,才能够达到目的获得成功。
如果违背这一定律和历史必然性,强行在不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必定要受到这一定律和历史必然性的惩罚,遭受极大苦难。结果,或迟或早必定改正错误,抛弃较高的生产关系,抛弃社会主义,而回到较低的生产关系,复辟资本主义:或者是完全复辟,或者是不完全复辟。苏东九国违背这一定律和历史必然性,在不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尽管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结果终因遭受这一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严重惩罚,而无不改正错误,复辟资本主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以恢复私有制和市场调节为主要特征。这岂不足以证明:生产力产生和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较高生产关系必较高、生产力较低生产关系必较低?岂不足以证明:生产关系高低与生产力高低正比?
综上可知,一个国家究竟实行何种经济制度,亦即何种经济形态占据统治地位,说到底,六种经济形态——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的何种经济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皆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究竟如何,因而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和不可自由选择的。这就是为什么,以经济形态为划分根据的六种国家制度——原始国家、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缘故。
下篇政体制度的偶然任意性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原理,无疑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然而,人们却往往将其绝对化,以为任何国家制度都必然决定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都具有历史必然性,都是历史的、时代的,都仅仅适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的社会和一定的时代,而不能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时代,因而不具有普世性。殊不知,只有以经济形态性质为划分根据的六种国家——原始公有制国家、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制度,才必然决定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才具有历史必然性,才都是历史的、时代的,都仅仅适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的社会和一定的时代,而不能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时代,因而不具有普世性;以经济形态性质为划分根据的六种国家制度之所以都仅仅适用于一定历史时代而不具有普世价值,只是因为一个国家实行何种经济形态具有历史必然性,是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必然决定的。
倘若不是以经济形态,而是以政体的根本性质——亦即执掌最高权力的公民人数——为划分根据,那么,所划分的民主制与非民主制国家制度,便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便与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没有必然联系,便是超经济、超阶级、超历史、超时代的,因而都不具有普世性和普世价值。因为一个国家究竟实行何种政体,究竟实行民主制还是君主专制等非民主制国家制度,完全取决于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数,完全取决于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数究竟是一个人(君主制)还是少数人(寡头制)抑或是多数人(民主制),因而完全是偶然的、可以自由选择的,而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不是必然的、不可选择的、不可避免的。
确实,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数——究竟是一个人还是少数人抑或是多数人——怎么可能与经济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必然联系?怎么可能被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必然决定?怎么会具有历史必然性?怎么可能不是偶然的呢?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最高权力岂不都既可能独掌于一个人,也可能执掌于少数人,还可能执掌于多数人?显然,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数的多少的本性就是偶然性和普世性。因此,政体——政体就是以执掌最高权力的人数的多少为根据的政治分类——的根本的特征就是偶然性和普世性。任何一种政体,不论民主制还是专制等非民主制,都具有普世性,都超经济超历史超社会超阶级超时代而能够普遍实行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政体,不论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都既可能实行于原始社会,也可能实行于奴隶社会,还可能实行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首先,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原始社会按其历史发展的一般顺序,呈现三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形态:游群、部落和酋邦。游群是人类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四处游动的自主的血缘社会,大约出现于二三百万年前,终结于一万年前,历时约二三百万年:人类的游群时代也就是旧石器时代。部落——氏族为其基础和中心——是人类处于农耕和畜牧阶段因而趋向定居的社会,只有到新石器时代,亦即距今约八九千年,才广泛地散布于世界各地。酋邦是处于平等的部落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等级社会。
队群和部落虽然也有实行非民主制的可能性,但一般说来,都实行民主制。因此,哈维兰说:“群队一般说来是相当民主的:任何群队成员都不会告诉别的人去干什么、怎么狩猎、跟谁结婚。”[6]恩伯说:“具有部落政治组织的社会与队群社会相似,都是平等的社会。”[7]酋邦虽然是一种等级社会,特别是正式的官僚管理机构使酋长的权力极大提高,甚至可能使他独掌最高权力而成为专制君主,但也可能未必如此:“处于酋长领地政治发展阶段的社会可能在政治上完全统一于酋长的统治之下,但也可能不完全是这样。”[8]
可见,在原始社会,民主制固然是主流,但是,不管怎样与人心背道而驰,还是出现过专制等非民主制:“不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不论在低级、中级或高级野蛮社会,都不可能从氏族制度自然生出一个王国来……君主政体与氏族制度是矛盾的,它发生于文明社会比较晚近的时期。处于高级野蛮社会的希腊部落曾出现过几次专制政体的事例,但那都是靠篡夺建立起来的,被人民视为非法,实际上与氏族社会的观念也是背道而驰的。”[9]59
奴隶社会可能实行任何政体——民主共和制与寡头共和制以及君主专制和有限君主制——已经是事实。古巴比伦、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和古印度孔雀帝国,无疑都是典型的君主专制。相反地,古希腊和古罗马则实行共和制。斯巴达是寡头共和制。雅典初期也是寡头制,梭伦改革使雅典由寡头制转变为民主制,到伯利克里时代,雅典民主制臻于全盛。公元前509年至27年的古罗马,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执掌于原本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堪称贵族共和制——贵族共和属于寡头共和范畴——的典范。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476年,罗马实行帝制,一人独掌国家最高权力,是典型的君主专制。奴隶社会还存在有限君主制,特别是贵族君主制,如公元前2369年至2314年,阿卡德城的国王萨尔贡一世建立的统一的阿卡德国家,实行的就是贵族君主制,亦即以君主为主而与贵族元老院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政体。
封建社会大都实行君主专制制与有限君主制。有限君主制又分为贵族君主制与等级君主制。贵族君主制是以君主为主而与贵族元老院或地方割据势力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有限君主制,如封建割据时期的法兰西、德意志和俄国中的一些大公国,国王虽然执掌最高权力,却不可独自行使,而必须得到某种形式的贵族会议的同意。等级君主制是以君主为主而与等级会议——亦即教会贵族、世俗贵族和市民组成的三级会议——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有限君主制,如俄国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的大贵族杜马和缙绅会议的等级君主制;法国腓力四世“三级会议”的等级君主制;英国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的议会君主制等等。诚然,封建社会更为盛行的政体还是君主专制,如英国威廉一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以及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专制;俄国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君主专制;法国路易十三、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君主专制;德国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的君主专制。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最为漫长,自大禹开创家天下的专制政体,直至清朝,实行君主专制竟然四千余年。
封建社会虽然盛行君主制,但也曾存在过共和政体。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便属于封建社会的寡头共和制:最高权力掌握在少数公民(贵族和富商)选举的大议会、元老院和共和国元首(总督或执政)手中。从12世纪开始,威尼斯设立大议会,拥有国家最高立法和监察权力。议员480人,皆从姓名列入“黄金簿”的少数贵族和富商中选出。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则执掌于大议会所选出的40人委员会(元老院)。佛罗伦萨则堪称民主共和政体:国家最高权力执掌于庶民——亦即“肥民”和“瘦民”——的代表所组成的议会。所谓肥民,主要是企业主、银行家、大商人、律师和医生;所谓瘦民,主要是小行东和手工业者,如鞋匠、成衣匠、铁匠和泥瓦匠等等。肥民结成7个行会,叫做“大行会”,包括丝绸商行会、毛皮商行会、羊毛商行会、银行家行会、律师行会和医生行会等。瘦民则结成14个行会,叫做“小行会”。佛罗伦萨国家最高权力执掌于这些行会会员所选出的议会。最高管理机关叫做执政团或长老会议,由每个大行会选出一个代表和两个小行会代表组成。长老会议的主席叫做旗手,由行业议会推选,任期2个月,可以连选连任;其他8人叫做“首长”,协助旗手管理国家内政和外交等事务。
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最普遍最典型的政体无疑是民主制,以致今天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几乎统统实行民主制。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曾存在过君主制: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封建社会君主专制,1791年通过新宪法,确立君主立宪制。该宪法规定,法国实行按分权原则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政府是君主制,行政权委托给国王……但在法国,没有比法律的权力更高的权力;国王只能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1799年拿破仑发动政变,独掌国家最高权力,1804年加冕为皇帝,建立了资本主义君主专制政体。20世纪意大利和德国出现的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独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法西斯独裁政体,则是资本主义君主专制的另一种类型。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一种民主制与君主制的混合政体:名义君主立宪制而实为民主共和制。这种政体的典型,如所周知,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1714年乔治一世以后的英国。一些国家也都实行民主制与君主制的混合政体,只不过与英国和日本“名为君主立宪而实为民主共和”恰恰相反,乃是“名为民主而实为专制”。
可见,一方面,所有政体——民主共和与寡头共和以及有限君主制与君主专制及其混合政体——几乎都曾经出现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几乎都曾出现于以经济形态性质为划分根据历代社会,几乎都曾出现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意味着,任何政体,不论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都不是被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必然决定的,都不具有历史必然性,都是超经济超历史超社会超阶级超时代的,都能够普遍实行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普世性。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封建社会都实行君主制和绝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都实行民主制的事实,特别是,人类迄今在99%以上的时间——亦即原始社会二三百万年的队群和部落时代——都生活在民主制社会的事实,显然又意味着,政体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个社会实行何种政体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但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政体类型的决定作用,并不具有必然性,并不是必然的决定作用,并不必然决定政体类型,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制或非民主制。否则,全部封建社会岂不统统都只能实行君主制?只要有一个封建社会实行共和制,岂不就意味着:封建社会并不必然实行君主制?因此,只要有一个封建社会实行共和制,就意味着,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君主制的决定作用不是必然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实行君主制。
确实,无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政体类型的决定作用是多么巨大,即使巨大到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不是必然的,也不可能必然导致某一种政体。因此,亨廷顿说:“经济因素虽然对民主化有重大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有一种全面的相关性。然而,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模式,就其自身来说,是造成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10]王绍光则援引雪瓦斯基的话说:“经济发展不一定能导致民主,民主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随机出现。换句话说,在经济发展的任何水平都可以出现民主。在一些被人们认为最不太可能实现民主的国家或地区,也出现过民主政权。”[11]
那么,是否有其他因素能够必然导致某一种政体?许多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他们看来,可以必然导致某一种政体的因素,除了生产力和经济,还有政治状况,亦即国内外的某种政治局势和政治需要,如革命、战争、分裂、无序、武力征服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等等必然需要集权和独裁,因而必然导致独掌最高权力的伟大人物的出现:专制具有历史必然性。恩格斯也曾这样写道:
“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也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12]
诚然,在国家发生革命、战争、分裂、无序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等非常时期,需要集权和强有力的伟大领袖,因而极易导致专制,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等等就是如此。但是,这种非常政治局势只是极易导致专制,却非必然导致专制。否则,我们如何解释美国独立战争为什么没有导致华盛顿的专制?难道还有比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国内外政治局势更需要集权、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伟大的铁腕人物吗?显然,政治局势、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一样,对政体类型的决定作用可能极其巨大,甚至大势所趋,但也不是必然的,也不可能必然导致某一种政体。
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都是偶然因素,其他因素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亨廷顿认为民主化是多种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原因相结合的结果:“寻找一个可以在解释这些不同国家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共同的普遍的自变项,几乎注定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同义语反复的话。民主化的原因因时因地而异。理论的多重性和经验的多样性意味着下述命题可能成立:(1)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所有国家或一个国家的民主的发展。(2)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是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3)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复合结果。(4)这些产生民主的原因之复合因国家不同而不同。(5)通常导致一波民主化的复合原因不同于导致其他各波民主化的复合原因。(6)在民主化波浪中最初政权变化的原因可能不同于这一波中后来政权变化的原因。”[9]
确实,任何一种政体——不论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的实行都是当时社会的地理环境、生产力、经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意识形态、阶级结构、争夺最高权力者的斗争、国民的人格、传统习俗、国内外形势和思想家们的理论等等多种因素的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情况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对于导致某种政体虽然有根本与非根本、内因与外因以及主因与次因之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状况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但无论是哪一种因素都不足以必然导致某种政体,因而都是某种政体产生的偶然性原因。在这些偶然的具体的特殊的多种因素作用下,人们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便既可能使最高权力无限制地被一个人所掌握(君主专制);也可能使最高权力受限制地被一个人所掌握(有限君主制);还可能使最高权力被少数公民所掌握(寡头共和);亦可能使最高权力被多数或全体公民所掌握(民主共和)。
因此,任何社会实行何种政体便都是偶然的、可能的、可以自由选择的和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而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不是必然的、不可选择的、不可避免的和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这意味着,任何社会在任何条件下实行任何一种政体,不论是民主制还是专制等非民主制,都不具有历史必然性,都是可能的、偶然的、可以自由选择的和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实行何种政体绝对不具有历史必然性,是绝对偶然的、绝对可能的、绝对可以自由选择的和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否则,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实行民主政体,那就无异于说,在不具备这种历史条件的时候,只可能实行非民主政体:非民主制具有历史必然性。因此,实行何种政体的偶然性如果不是绝对的,就等于说实行何种政体具有历史必然性。所以,一个社会实行何种政体,不仅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绝对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不仅是偶然的、可能的和可以自由选择的,且是绝对偶然的、绝对可能的、绝对可以自由选择的。
诚然,任何偶然都表现着某种必然性,没有纯粹的、不表现必然性的偶然性。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实行何种政体的本性是一种纯粹的绝对的偶然性。因为“纯粹的绝对的偶然性”与“不表现必然性的纯粹的绝对的偶然性”根本不同。纯粹的绝对的偶然性,无论如何,也总是表现着某种必然性。一个人究竟如何死亡,是纯粹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偶然性。但是这种纯粹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偶然性也总是表现着某种必然性:他必有一死。他必有一死,是纯粹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必然性。同理,实行何种政体是一种纯粹的绝对的偶然性,也并没有否定这种纯粹的偶然性表现着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政体。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政体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任何社会都存在政体具有绝对必然性。相反地,任何社会存在何种政体则绝对地无条件地是偶然的:任何社会存在何种政体具有绝对的偶然性和绝对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政体,不论是民主制还是专制等非民主制,都绝对可能实行于任何社会。这仅仅是说,民主制或非民主制的实现的可能性是无条件的,而不是说民主制或非民主制的实现是无条件的。任何政体都具有绝对的无条件的可能性,但是,任何政体的实现却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换言之,任何政体都是绝对可能的,任何社会都绝对可能实行任何政体。但是,可能变成现实,却是有条件的。一个社会要将实行某种政体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是有条件的。就拿民主来说。任何社会都绝对可能实行民主。但是,要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亦即实现民主,是有条件的。毋庸置疑,一些社会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另一些社会则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社会不论是否具有实现民主的条件,民主都是可能的,而不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对于具备民主实现条件的社会,民主具有所谓“现实的可能性”或“实在可能性”,亦即经过人们的活动现在就可以实现的可能性;而对于不具有民主实现条件的社会,民主则具有“抽象的可能性”或“形式可能性”,亦即只有将来才可以实现——而现在则不会实现——的可能性,是需要经过人们的活动到将来才会实现的可能性。试想,秦皇汉武时代,确实不具有实现民主的条件。今日的中国则具有实现民主的条件。但是,即使对于秦皇汉武时代,能否实现民主也同样完全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因而也是偶然的、可能的、可以自由选择的。假设当时人们都想实行民主,或者想实行民主的人的力量占据上风,那么,民主就会实现。因此,秦皇汉武时代,专制也不具有历史必然性,民主也不是不可能的。那时民主也具有可能性;只不过不是实在可能性,而是抽象可能性,是要经过努力奋斗才会在将来实现的抽象可能性。
抽象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根本不同:抽象可能性的本性是偶然性,因而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而不可能性的本性是必然性,因而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想当年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仙丹,无疑是荒唐的。因为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相反,如果他寻求长寿,立志活到100岁,则并不荒唐。因为他活到100岁,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可能的,是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只要他经过漫长的养生年月在遥远的将来就可能实现,因而属于抽象可能性范畴。这种可能性概率极小,几乎是不可能。但可能性概率不论如何小,仍然属于可能性和偶然性范畴,是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而不属于不可能范畴,不属于必然性范畴,不是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秦皇汉武时代民主的可能性就属于这种抽象可能性范畴,这种可能性概率极小,接近于零,因而几乎是不可能。但是,即使可能性接近于零,也仍然是可能性,仍然是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而不是不可能性,不是必然性,不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因为,说到底,民主实现条件与民主实现可能根本不同。任何社会,不论是否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都具有实行民主的可能性:民主可能或能够实行于任何社会。
因此,任何一种政体,不论是民主制还是专制等非民主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不论是否具备实现的条件,都具有实行的可能性,都是绝对可能的、绝对偶然的、绝对可以自由选择的和绝对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都是绝对超经济超历史超社会超阶级超时代的,都绝对能够实行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绝对的普世性.
综上可知,任何政体,不论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事实上都曾出现于生产力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都曾出现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意味着,任何政体都不是被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必然决定的,都不具有历史必然性。究其原因,可知任何一种政体的实行,都是当时社会的地理环境、生产力、经济、政治、文化、社团、法律、道德、意识形态、阶级结构、争夺最高权力者的斗争、领袖们的人格、才能和贡献以及国民的人格、传统习俗、国内外形势和思想家们的理论等等多种因素的具体的特殊的偶然的情况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对于导致某种政体虽然有根本原因与非根本原因以及主因与次因之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状况无疑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但无论哪一种因素都不足以必然导致某种政体,皆非必然产生某种政体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而都只是某种政体产生的偶然性原因,都只是产生某种政体的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在这些偶然的特殊的有利或不利的多种因素作用下,人们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便既可能使最高权力无限制地被一个人所掌握(君主专制),也可能使最高权力受限制地被一个人所掌握(有限君主制),还可能使最高权力被少数公民所掌握(寡头共和),亦可能使最高权力被全体公民所掌握(民主共和)。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实行何种政体,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不是必然的、不可选择的、不可避免的,而是充满各种可能,是偶然任意、可以自由选择的。这就是为什么,以政体为划分根据的国家制度——民主制与专制等非民主制——是偶然任意而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缘故。
参考文献:
[1]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穴Revised Edition?雪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熏Massachusetts?熏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1.
[5]哈维兰.当代人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468.
[6]Carol R.Ember?熏Mevin Ember[M].Cultural Anthropology?熏Ninth Edition?熏Prentice Hall?熏Inc.1999:224.
[7]恩伯.文化的变异[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406.
[8]Lewis H.Morgan:Ancient Society[M].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熏1964?熏P110?觸111.
[9]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押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Universityof Oklahoma Press?熏Norman?熏1991?押59.
[10]王绍光.民主四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87.
责任编辑姚黎君彭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