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文武台
2014-08-29陈敏
陈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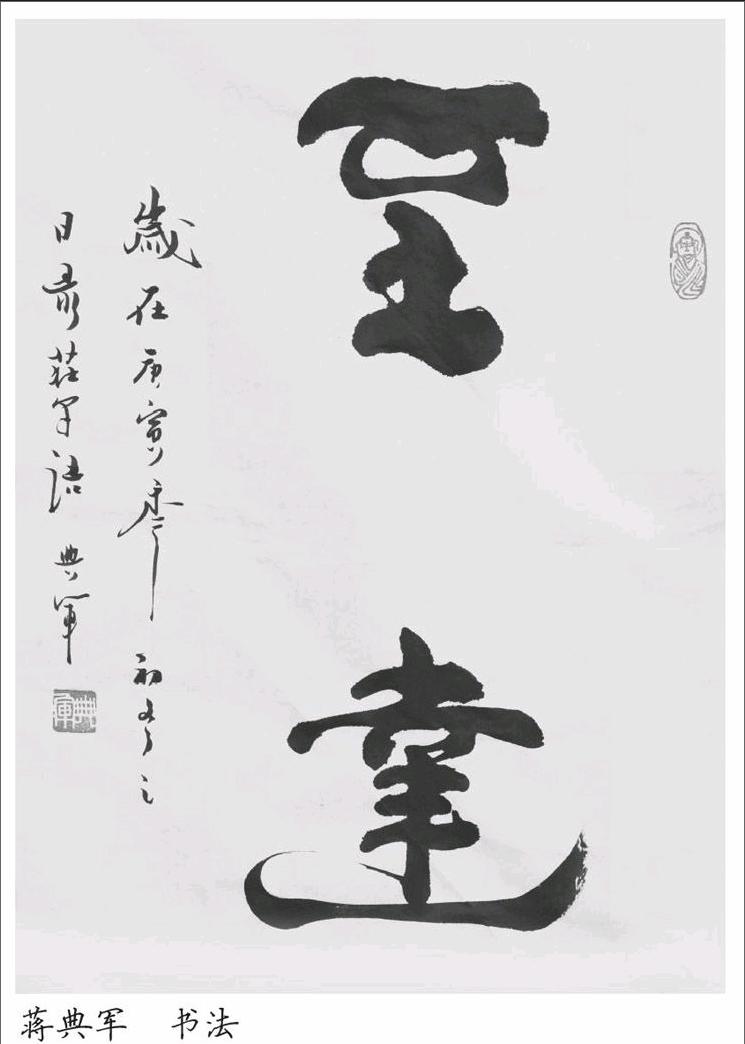
1
人对祖先故乡的怀恋,有时是莫名其妙的。
我在莫名其妙地问及父亲关于故乡的人事时,父亲总是沉默不语,或者将话题转向一边,而母亲就像讲童话般地告诉我:老家在一个无比高的山嘴子上,我们都爬不上去。至此,老家这个词成了一个隐秘在我心底的哑谜,扣着我的心弦,我渴望解开它,却一直解不开。
我第一次去父亲的“文武台”是祖母去世后的第四天。去那里的路途正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遥远而艰辛。先要搭车去一个叫板岩的小镇,然后再步行50里石峡路、穿越一条长达百米的颤巍巍的吊桥之后开始翻山越岭,向“只堪图画不堪行”的山尖攀爬,去那个被人称作文武台的地方。疯长的野草淹没了原有的崎岖山径,找不见路时,就得另辟蹊径。多亏一个老乡带路,才使我们顺利抵达。
父亲曾说“土改”时,家里分了一头牛,由于山路过于险峻,牛无法自己踏上去,只得把它绑在一个巨大的担架上,雇了二十多个壮劳力花了一天半的功夫才抬了上去。至于父亲曾居住的那个“文武台”也是后来被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叫出来的。因为那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山嘴子上就出了两个人物,一文一武。文的是我父亲,武的是我父亲的本家叔叔,名叫陈长命,一个天生的猎杀者。十六岁参军,后来提升为侦察连长,他百发百中,最难打的位置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击倒对手准确无误,可惜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一年光荣就义。他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了一个英名,那个英名像深山里的回音,一直盘旋在老家山寨的上空,它比我父亲文化局长的头衔响亮。
至于父亲和老家亲人之间的过结,多年来我是从母亲口中一点点得知的,而父亲却只字未提过。
父亲四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他和不满七岁的姑姑。祖母是个足不出户的小脚女人,不能下田耕作不说,就连到沟底弄半桶水回来也十分艰难。在那个陡峭的山寨,除了缺衣少食,水是他们过日子的第一难。正当祖母和两个孩子步履维艰时,一个小她5岁的男人主动找上门,帮祖母挑回了一担水,站在烈日炎炎的门口说:“你洗个澡吧,以后我会常来给你挑水。”祖母心头一热,当天就用小男人挑的水痛痛快快的洗了她生命中的第一次澡。男人隔三差五来为祖母挑水,半年后,他理直气壮地成了祖母的新任丈夫——父亲和姑姑的继父。
父亲的继父年轻、力大,挑水、劈柴、干活都是一把手,没人能与他抗衡。他的强势同样表现在他极高的生育能力上,六年时间里,他就让我祖母生了五个孩子,一男四女。个个瘦得像猴子。
面对着一大堆嗷嗷待哺的嘴巴,他不得不起早贪黑。也顺理成章地把他的爆脾气像泼脏水一样泼在和他没有亲缘关系却要靠他养活的父亲以及姑姑身上。他强迫不满十岁的父亲天不亮就起床去潭涧抢水,父亲起不来,他就将他提出被窝,扔进猪圈。他力大过人,一口气能把岩缝里渗出来的、积攒了一夜的潭水舀干。他为烧炭,常在夜间偷偷摸摸地去“顺”别人的树木。他霸道的举动引来了众人的白眼。某一天晚上,全寨子人倾巢出动,明晃晃的松油亮子火把他小偷小摸的手脚照了个正着。他们在坡上排成一行,先是咒骂,后又大打出手,扁担棍棒一起向他劈头盖脑袭来,宣称要将那个野杂种撵下山去。但,他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众多男女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们全被击退了。
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动手,但他也有选择地站错了方向;他也加入了诅咒继父的行列,他跳得比任何人都高,也学着别人的样子骂他的继父。他这么一骂,迎来了他一生中最惨烈的惩罚和最后的悲剧。当晚,他继父就把他倒挂在一棵榔树上吊打了一顿,并连夜将他逐出了家门。父亲那年才13岁。他求亲生母亲为他做主,不料,他母亲不仅没同情他,反而咒他是个吃里扒外的不孝之子,迟早会遭天打五雷轰。那天夜里他的母亲没有让他进门,只从门缝里塞出了一块牛粪砣一样的红薯面馒头,说:“你淘米要饭自谋生路吧,以后再不要进这个家了!”然后在他面前关上了家门。
2
父亲带着一身伤痕连夜摸下山,在一个炭窑里凑活了几宿。上苍没有将他赶上绝路,他碰上办丧事的大户人家,死者有个大权在手的儿子,在县委宣传部当部长,被乡里人称“一面官”。他用翠绿的松柏枝叶为他逝去的母亲搭建了一个戏台子式的灵堂。于是死者的身份就和一般人或一切穷人显示出差异来;每晚沾亲带故的、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前来守灵,他们吹吹打打、围着棺材唱着孝歌。穿着长孝衫的女人们呜呜咽咽地哭。
山里习俗,谁家老人去世了,四邻八乡的人都会在夜里赶来唱孝歌,至少要唱7个夜晚,遇到个更富裕人家的,人会更多,时间会更长。人们从擦黑唱到天亮从不间断。
父亲为讨碗热汤也加入了唱孝歌行列。他少年丧家,悲从心起,围着棺材边唱边哭。那些唱了一辈又一辈的孝歌歌词被识文断句的父亲唱着唱着就唱变了。父亲把孝歌的歌词给唱改了。他改后的歌词听上去尤为悲切,围坐在棺材边的男女孝子顿时哭声震天,把那个漆黑的夜晚感染得更加悲戚。身服重孝的部长也感动于眼前这个陌生的小男孩,为他把歌词改得这么恰到悲处而无比动容,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他眼光独具,一眼认准父亲是个非同寻常的孩子。
部长在办完他父亲的丧事后,就把我父亲带进了县城,推荐给县长做了通讯员。父亲自知自己交了好运,当县长问他能做什么时,他非常聪明地说他能在晚上为县长捂脚,打仗时为县长挡棍子。县长想笑却没笑,只用卷着的报纸温柔地敲了敲父亲的头。三年后,父亲做了县长的文秘。
父亲就那样侥幸地活了下来,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像山里飞出来的一只鹰越飞越高。那个把他驱逐出来的家永远停留在他生命中的第13年里。时空的阻隔与他素养的提高使最初的怨愤慢慢演变为生疏、隔阂、冷漠。他的性情由于童年亲情的戛然终止而一点点变得孤僻,随之而来的是冷峻与孤傲的与日俱增。
3
父亲的胞姐,我的姑姑十四岁时,就被继父逼嫁了。没出嫁前,她总是跟继父又吵又闹,可新婚之夜,她却出奇地乖巧,没吵,也没闹,而是用一条很结实的腰带把自己的裤子牢牢扎住。那条守卫她纯真的带子被她勒得死死的,让她呼吸都有点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