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两国历史上的天文学交往(一)
2014-08-23石云里
石云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中朝两国历史上的天文学交往(一)
石云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从很早开始,统治朝鲜的王朝就仿照中国设立官方天文机构,负责天象占侯与历法制定.为满足本国在这些方面的知识需求,朝鲜统治者们曾非常努力地从中国学习和引进天文学.中国政府往往把向朝鲜颁送历法作为显示宗主国地位的手段,而朝鲜王朝却把能够制定本国历法作为政治上独立的象征.因此,两国之间的天文学交往总是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天文学;外交;中国与朝鲜;科学与政治
中国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交通便利,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自古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至少从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等王朝的出现开始,朝鲜古代王朝在政治制度方面都借鉴和模仿中国制度,天文学在其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体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朝鲜历代统治者都注重向中国学习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而另一方面,最迟从元朝开始,中国统历朝治者也把对附属国颁发历书等看作是显示宗主国地位和权威的象征.因此,尽管古代朝鲜天文学家不乏自己的创造,但中国的天文历法,从基本学科制度到知识内容,都被他们几乎全盘照搬.这就使他们的天文学始终是处在中国天文学的影响之下,与中国天文学属于同一系统.由于中、朝各王朝之间的天文学交往主要都是在官方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也成为两国针对对方的外交活动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与两国的政治关系之间显示出明显的相互影响.所以,这种交往既体现了中国发达的天文历法知识对邻国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这种知识在两国政治关系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两国间在外交背景下的这种天文学交往在中国元朝时期初具规模,明朝得到较大发展,而到清朝则变得十分频繁.其结果使得中国在这些皇朝中取得的天文学成果系统地传入朝鲜半岛,极大的提升了那里的天文学发展水平.
1 漫长的起步
《高丽史·历志》称:“夫治历明时,历代帝王莫不重之.周衰,历官失纪,散在诸国,于是我国自有历.”[1]这段话虽非信史,却也道出了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在天文学上的渊源关系.
从公元前57年前后开始,朝鲜半岛上先后出现了新罗(公元前57-公元902)、高勾丽(公元前37-公元668)和百济(公元前31-公元660)三个独立国家.三个国家都先后开始与中国各个王朝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交往.受中国政体的影响,三个国家也先后在自己的政府中设立了负责天文历法工作的机构.例如,公元6世纪,百济就已设有“日官部”[2].7世纪中期,“新罗国王德曼圣造瞻星台”[3],8世纪“始造漏刻”,并始立“漏刻典……置博士六人、史一人”.后又“置天文博士一员、漏刻博士六员”,其中“天文博士后改为司天博士”[4].高勾丽官方天文机构建立的时间史无明徵,但一般都认为,该国也应该有“日者”一类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员[5].
1145年朝鲜史家修成的《三国史记》中记载有大量的天象记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三国天文学家的独立观测[6].从这些观测记录来看,三国天文学家在进行异常天象观测时所选的观测对象(包括交食、月掩星、五星凌犯、客星、彗星和流星等等)、所用的术语和星官名称等也都与中国所选所用的相同,说明三国天文机构在这些方面也基本采用的是中国系统.
至于历法方面,当时百济曾“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2]卷49)高勾丽于619年“遣使如唐,请颁历”([4]卷20),所引进的应该是当时唐朝正在使用的傅仁均《戊寅历》.而674年,新罗“入唐宿卫大奈麻德福传学历术还,用新历法”([4]卷7),这里学回的应当就是《麟德历》.
在恒星系统方面,从高勾丽古墓星图(共有二十多处,时间分布在公元357年至公元6世纪之间,均属于中国风格,包括有三足乌、四象、北斗七星、南斗七星和二十八宿[7])来看,中国恒星知识当时在朝鲜半岛已经非常普及.629年,新罗“高僧道证自唐回,上天文图” ([4]卷7),就属于对中国星座知识的引进.
公元918年王建统一朝鲜半岛,建立高丽朝,很快设立了太卜监和太史局,负责天文星占、历法守时等事务.后太卜监先后改称司天台、司天监、观候署等,最后又正式合司天监、太史局为书云观([1]卷76).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高丽朝天文机构与唐、宋天文机构在体制基本上相仿,只不过规模略小.
高丽最初曾先后采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和辽的年号,表明他们采用过这些中国王朝的历书([1]卷1-3).最后,唐朝徐昂编定的《宣明历》被该朝历官所掌握,并长期被用作官方历法,用于本国民用历书的编算和日月食预报.对于其五星计算部分,高丽历官则未能掌握.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高丽很快成为其属国,并受到其严厉的控制.不过,两国间在天文学上的交往却因此变得比以前更具规模.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元朝政府经常把本国历书作为礼品送给高丽国王,仅元世祖统治时期赠历举动就达到十五次之多[8]*对元朝政府的赠历事件,《高丽史》卷26和29也有记载:元宗5年(1264年),“韩就还自蒙古,帝赐西锦一段,历日一本”.“(元宗9年2月壬寅)安庆公 还自蒙古,帝赐王西锦一匹,历日一道”.忠烈王22年(1296)2月己卯,“金光就还自元……太后赐葡萄酒二器,并赐历日.”.此外,元朝政府可能还经常向高丽政府发布交食预报,例如,据《高丽史·天文志》记载,“忠肃王七年(1320)正月辛巳朔,元来告日当食”;“恭愍王元年(1351)四月癸卯朔,元史告日食,不果食……二年九月乙丑朔,元告日食,不果食”,等等([4]卷47).
1281年,《授时历》被元朝政府正式采纳.同年,忽必烈就遣使将新历书颁发到了高丽.前去颁历的王通等人也是天文学家,他们在高丽期间“昼测日影,夜察天文”,并“求观我国地图”([4]卷29).他们所做的工作无疑是郭守敬大地天文测量(即所谓“四海测验”)项目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次测量的范围就是“东极高丽,西至滇池”([8]卷48).《元史·天文志》等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高丽北极出地度(三十八度少)应该就是王通等人在高丽的测量结果.将之换算成现代单位,相当于北极出地37°42′,与高丽都城开城的地理纬度基本相同. 授时历书传入后,高丽政府开始设法学习其编算方法.与此前的唐、宋等王朝一样,元朝也禁止私习天文.因此,作为一个藩属国,要想从元朝学到天文历法必定不太容易.然而,元朝对高丽的一项政策却为高丽政府提供了便利.
为了加强对高丽的控制,元朝初期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对于高丽王位的继承者,必须从小送到元大都,在元朝以蒙古人的方式长大成人、并同蒙族女子成婚后,方可回到高丽.这一制度为高丽学习授时历提供了便利.1278年,被封为太子的高丽忠宣王王璋(1275-1325)被送到大都,并在那里长大成人.1298年,他回国登基王位不成,再次回到大都,而且在1308年再次登基后还一直留在那里,直到1313年退位后才再次短暂回到过高丽一次.
正是在1298回到大都后,王璋“见太史院官之精于此术,欲以其学流传我帮.越大德癸卯、甲辰年间(1303-1304年),命光阳君崔公诚之捐内币金百斤,求师而受业,具得其不传之妙.”[9]从此,《授时历》便为高丽天文学家初步掌握,并据以编制自己的历书,于中宣王时期(1309-1313)正式颁行国内.
后来,崔诚之把自己所学传授给姜保,姜保也因精通授时历而被任命为书云观司历,最后还被提升为书云观观正.姜保根据自己所学,编写了《授时历捷法立成》两卷,并得以流传至今[10].不过,由于高丽天文学家没有学会《授时历》的开方之术,所以“交食一节尚循《宣明历》”([4]卷50).另外,高丽历法家门显然也未学到《授时历》行星推算部分的知识.
明王朝建立之后,高丽很快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1369年,明朝政府派遣使臣前往高丽,所带礼品中就有“《大统历》一册”[11],这标志着明朝与朝鲜天文学交往的开始.同年,高丽政府又派成准德前往明朝,希望能学到《大统历》编算方法([4]卷42).成氏回国时,朱元璋送给他《大统历》一本([11]卷46).
除了《授时历》外,高丽时期传入朝鲜的另外一部重要的中国天文学著作是《步天歌》.此后,书中以歌诀形式描述的以三垣二十八宿为框架的中国星座系统也成为朝鲜官方天文学家接受的系统[12].
2 大见成效的发展
1392年,李成桂建立李朝,很快即与明朝建立了外交关系.明朝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把向李朝颁送历书作为一种制度,长期保持,每年颁送“朝鲜国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13].另一方面,李朝的前几位国王对天文历法都显示出了较大的关注,因而也重视对它们的发展.例如,李成桂就命人刻制了著名的《天象列次分野之图》.这幅石刻星图目前仍然留存于世.按照其铭文所言,该图的前身“旧藏平壤城,因兵乱沉于江而失之”.李成桂即位后,有人进献了一个藏本.李成桂对它非常重视,于是命人将它重刻于石,从此成为朝鲜的标准星图,知道17世纪欧洲星图通过中国传入为止.
李朝初期仍然沿用不完整的《授时历》和《宣明历》,尽管1402年“明帝赐《元史》”给李朝第二任国王李芳远[14],但李朝历官对其“历志”所载的完整《授时历经》也未能加以利用.直到第三任李即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419年,领书云观事臣柳廷显献议,请求世宗令手下儒臣厘正历法.李采纳了他的建议,“以为帝王之政,莫大于此”.于是“命艺文馆直提学臣郑钦之等考究《授时》之法,稍求其术.复命艺文馆大提学臣郑招等更加讲究,俱得其术”[15].
(1)《大统历法通轨》,包括《太阳通轨》、《太阴通轨》、《交食通轨》、《五星通轨》、《历日通轨》以及《四余通轨》等几部分.明钦天监监正元统于1384年前后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编成,并成为明朝《大统历》的官方版本,用于钦天监的历法与天象计算工作[17].
(2)《回回历法》(亦称《回回历经》),为中国官员与回回历法家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在1382到1384年之间合作译编的一部阿拉伯天文学著作,现存明南京钦天监监副贝琳1477年重编本共分“回回历法释例”,“回回历法”,“经度立成”和“纬度立成”.可用于回回年历、日月五星黄道经纬度、日月食以及月亮和五星凌犯现象(也就是这些天体相互之间、或者与恒星之间的角距离小到一个范围内是的状况)的计算.
(3)《纬度太阳通径》,元统在1396年奉朱元璋之命完成的一部试图对回回历法与大统历法的太阳计算部分进行会通的著作,书名中的“纬度”所指的就是回回历法*该书的唯一存本收藏于韩国奎章阁档案馆.有关这部著作的内容与重要性,见[16]..
(4)《西域历法通径》,明钦天监夏官正刘信(?-1449年)所作,是明初关于回回历法的另外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16]).
可以说,明代初期中国天文学家所完成的几部最重要的著作已经被李朝天文学家悉数获得,基本上无一遗漏.明朝对私习天文和私造、私印历书厉行禁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藩属国的朝鲜,能够如此迅速和全面地获得明朝官方天文学家撰写的这些重要著作,这不能不令人感到莫大的惊奇.以朱元璋以及明初其他皇帝对各路藩王的那种忌惮与防范心态,肯定不可能在关乎“天命所在”的天文历法问题上对朝鲜国王网开一面,为其搜罗相关著作和学习相关知识提供官方便利.李朝官员之所异能获得成功,必定另有蹊径,而且能直通明朝的钦天监内部.关于这一点还可以找到另外两条证据,也就是李朝官员从明朝获得的另外两部著作:
(1)《各年交食》一卷,附于《大统历法通轨》中《交食通轨》之后,卷首写有“授时历各年交食,中朝书来”,内容为用《交食通轨》中的方法对宣德和正统年间的日月食进行计算的具体算例.
(2)《宣德十年月五星凌犯》一卷,为用回回历法对宣德十年月亮和五星之间、以及它们同恒星之间凌犯现象的逐日详细计算[18].
在明朝,能够用官方历法系统对每年的交食进行计算的只有钦天监,而对月亮和五星凌犯的计算也是明钦天监回回历法家的常规性工作之一;因为,明末孙能传在1602年编成的《内阁藏书目录》中就登录有“《洪武二十四年月及五星凌犯》一册”[19].由于凌犯是中国传统星占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很显然,计算这些项目的目的没有别的,主要就是为官方星占家关注的凌犯占服务.事实表明,朱元璋之所以命令翻译回回历法,主要原因就是它能满足这一需要.而且有史料显示,他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初就曾用钦天监对凌犯的计算及其星占意义来为其处理周、齐、潭、鲁四路藩王寻找“天意”的依据([13]).
所以,上述两份文件,尤其是第二份文件,在明朝当属于高度的国家机密.对于这样的机密文件,李朝官员都能从“中朝书来”,没有十分特殊途径肯定不行.当然,他们完全可以像崔诚之学《授时历》是那样,通过重金达到向钦天监官员“求师而受业”的目的.但是,在李朝和明朝之间,当时是否有像忠宣王王璋那样长期居住中国都城、熟悉中国朝廷的“推手”呢?
不管怎么说,这些著作的输入为李朝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于是,在1442年,李便命奉常寺臣李纯之、奉常注簿臣金淡对《授时历》同《大统历法通轨》的异同进行甄别,去粗取精,编成《七政算内篇》三卷.又对《回回历经》和《西域历法通径》等书进行了认真消化,编成《七政算外篇》三卷*书中解决了中国现存《回回历法》版本中所未能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回回阴历同中国阳历之间的日期换算问题.这一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回回历法》中的算法都是按照阳历给出的,而天文表确实根据阴历计算的,二者的历元和年月日安排都不相同,没有正确的日期换算方法,则根本无法正确使用《回回历法》.[20].同时,又根据李朝都城的地理纬度,重新计算了每天日出、日落以及昼夜长短的时刻表,附录于上述两部自撰著作之中,“永为定式”.到此为止,从而第一次拥有了真正从形式上属于自己的官方历法系统,被用于书云观的历书和日月食计算之中.作为对具体计算过程的具体指导,李朝天文学家又编出了《七政算内篇丁卯年交食假令》和《七政算外篇丁卯年交食假令》两部著作,以丁卯年(1447)的交食为例,给出了利用两个官方系统进行具体日月运动和交食计算的详细示例.
除这些著作外,李朝天文学家还注意从其他中国文献中吸收天文学知识.1445,李纯之又奉命“搜索其天文历法、仪象晷漏书杂出于传记者,删其重复,取其切要,分门类聚”,编成《诸家历象集》一书[21],分天文、历法、仪象和晷漏等4卷,广泛搜录了中国文献中国各种书籍中的天文学知识.
不仅如此,王璋甚至还亲自出手,编写成《交食推步法》两卷,同样以正统丁卯年(1447)的日月食为例,讨论了日食(上卷)和月食(下卷)的推步方法.此外,书前另有“算学发蒙”一篇,介绍了历法计算中使用的筹算法则,其中包括开平方.李纯之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则则明确指出,包括算学部分在内的这部著作“皆我世宗大王所作也”[22].鉴于《七政算内篇》和《授时历立成》等著作中“立成诸数浩繁不便于观览”的问题,书中推出了计算太阳盈缩差、月亮迟疾差和加减差的一般推求公式.这样,在实际计算中就不必取查立成表,而只需按照公式直接计算即可,更加简便易行.从实质上来讲,这项工作就是总结出了《授时历立成》中各项内容的推求公式,而这些算法在明朝却是传了很长时间,直到明末才被天文学家们逐步弄清.
在大量引进中国天文学著作并对之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同时,李朝政府还把中国天文学知识用于天文历法人才的培养之中.1429年,李朝政府在确定“诸学取才经书、诸艺数目”时就规定:“阴阳学:《天文步天歌》,《宣明历》步气朔、步交会,《授时(历)》步气朔、步交会、太阳、太阴、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四暗星、步中星……”[23].这些科目一直到17世纪“西法”传入半岛后才有所调整,从人才培训方面为朝鲜天文学沿着中国传统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总之,与明朝之间的天文学交往在李朝初期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也因此初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其结果甚至使朝鲜天文学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明朝天文学的水平,成为朝鲜科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到此为止,李朝政府已经拥有了一个人员、仪器和知识都十分完备的天文机构,形成了系统的取才考试、培训绩效以及日常工作的稳定制度[26],有能力像明朝钦天监一样进行观象、星占、授时、日月食预报以及本国历书的编算颁行工作.不用说,李朝早期君主的知识与政治抱负可以说完全得到了实现.而李朝在天文历法方面也开始实行“双轨制”:一方面他们继续接受中国颁发来的历书(他们称之为“唐历”),并行用明朝年号,以尽藩属国之义;另一方面他们则用《七政内篇》计算、并向国内颁行自己的历书(他们称之为“乡历”).而对于日月食预报以及有关每年日月五星动态的《七政历》,他们也都能完全自行计算.只不过对于日月食,他们在预报中都会同时使用《大统历》、《七政算内篇》和《七政算外篇》三种系统进行计算和比较;而对于《七政历》,他们最初每年只为国王提供一本,而“不准印出”,直到1466年,观象监(即原来的书云观)才以“星经相考时,凭考无据”为由,“请自今令典校署印二件,一件进上,一件藏于本监”,得到批准[27].
但是,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如果发现一个藩属国在天文历法活动上居然达到这样的规模,那绝对是难以容忍的.关于这一点,李朝权贵们其实心知肚明,并且有所提防.例如,1469年新春,有明朝使臣即将来访.朝鲜国王即命承政院传令沿途地方官,“明使若欲见历日,辞以唐历未来,勿见乡历”[28].当然,要对少数几个使团成员封锁消息肯定不是很难,难的是当有更多中国官员长期停留在朝鲜境内时,再想保密恐怕就有风险了. 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朝派遣军队援朝抗日.起初倒也无事,但到1598年,明朝经略杨镐在岛山之战中因进攻受挫而撤军.明兵部主事丁应泰前往勘战.他先弹劾杨镐,致使杨镐被罢.后竟然又对为杨镐鸣不平的朝鲜国王李日公提出弹劾,并列出三条罪状:第一,朝鲜认为辽河以东为其故土,为了恢复故土,故意“诱倭入犯”;第二,朝鲜所编关于日本国情的《海东纪略》一书不遵明朝正朔,僭称皇号,有违藩国礼仪;第三,李日公“暴虐臣民,沈湎酒色”,与杨镐结党,欺骗天子*《海东纪略》一书主要介绍的是日本国情,所介绍的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交往也较多,因为被丁应泰作为李日公通倭、诱倭的罪证.此外,他还指控该书“从日本康正、宽正、文明等年号,而大书之,且小字分书永乐、宣德、景泰、成化纪年于日本纪年之下,则是尊奉日本加于天朝甚远.而书又僭称太祖、世祖,列祖、圣上,敢与天朝之称祖、尊上等.彼二百年恭顺之义谓何,而皇上试以此责问朝鲜,彼君臣将何说之辞?”这就是他第二条指控所指.[29].
丁应泰的弹劾再次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而他的第二条指控则引发了李朝对本国“私造”历法问题的担心,并有官员提出,不应该继续颁行本国历书:
中朝颁正朔于八荒,八荒之内岂有二历书乎?我国之私自作历,极是非常之事.中朝知之,诘问而加罪,则无辞可对.凡中朝之历,有踏印,其无印信者,皆私造.私造者,于律当斩;其捕告者,赏银五十两.今用唐历印出,则虽有诘之者,可以国内不能遍观,势不得已印出为辞.于理顺,吾何畏彼哉?若印出我国所作之历,则是不用中朝之历,而自行其正朔于域中也.观象监所称,欲洗补而仍颁者,假托之辞耳.我国人心,素慢不谨.累千部历书,其谁一一洗补?况昼夜时刻,仍存不改,人之见之者,必以为私作之历也无疑.自古天下地方,东西远近,各自不同,岂皆随其国,而必改其刻数乎?仍颁之令一下,或相取去,或相转卖,传布国中,无处不到.丁应泰方在国内,彼既与我有隙,吹毛觅疵,狺然而旁伺.万一得此历,而上奏参之曰:“朝鲜自谓奉天朝正朔,历用大明历云,而有此私作之历,臣欺皇上乎?朝鲜欺天朝乎?愿陛下,下此历于朝鲜,试问而诘之”云,则未审此时观象监提调当其责而应之乎.观象监久任者,赴京师而辨之乎?予实不敢知也.不但此也,深恐丁也,幸得往岁之历,以为自售陷人之地,予方凛然而寒心,其又益之以新历乎?历可废而祸不可测.予意我国所撰之历,决不可用也[30].
从这段文字来看,丁应泰在弹劾李日公的过程中,也许还直接利用过历书方面的证据(“幸得往岁之历……其又益之以新历乎?”).尽管李日公也拿这件事“问于大臣”,但显然李朝政府并没有就此停止颁行自己的历书.但这件事情表明,对这些行为在政治上的性质和后果,他们是有充分认识的.
不过,到了明朝晚期,随着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交往的加深,对明朝官员来说,朝鲜有自己的历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1625新春,就出现了时任明平辽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向李朝官员索要朝鲜新年历书的事情,对此,朝鲜史书中作了明确记载:
毛都督求新年历书,朝廷许之.诸侯之国,遵奉天王正朔,故不敢私造历书,而我国僻处海外,远隔中朝,若待钦天监所颁,则时月必晏,故自前私自造历,而不敢以闻于天朝例也.都督愿得我国小历,接伴使尹毅立以闻,上令礼曹及大臣议启.皆以为,若待皇朝颁降,则海路遥远,迟速难期,祭祀军旅吉凶推择等事,不可停废.故自前遵仿天朝,略成小历.以此措语而送之为便.上从之[31].
可见,此时的朝鲜国王和大臣也认为,没有必要向明朝官员隐瞒此事,因为他们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适的理由:中朝路途遥远,钦天监所颁历书不能及时到达,不难及时满足朝鲜在祭祀军旅、吉凶推择等方面对历书的需求.对于这样的解释,明朝官员看来也只能接受.况且,此时的当务之急是联合朝鲜,共御正在辽东崛起的后金势力.
3 大变革时期的艰难转折
李朝在天文历法上实行的这种“双轨制”最终并未导致他们所担心的那种后果,两种体系在朝鲜相安无事,而李朝最后也与明朝之间保持着良好的藩属国关系.但是,明朝末期发生的另外两件事情却开始对中、朝之间的天文学交往带来新的影响.第一件事是欧洲天文学的传入以及明朝试图借助它进行历法改革的举动,第二件事情则是满清在中国东北的崛起以及最后入主北京.
实际上,在欧洲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之后,朝鲜来华使臣已经对他们有所耳闻,并对他们所传播的欧洲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学知识,也有所了解和接触.例如,这一时期著名的李朝学者李晬光记载道:
万历癸卯(1603),余忝副提学时,赴京回还,使臣李光庭、权忄喜以欧罗巴国舆地图一件六幅送于本馆,盖得于京师者也.见其图甚精巧,于西域特详,以至中国地方暨我东八道,日本六十州,地理远近大小,纤悉无遗.所谓欧罗巴国在西域最绝远,去中国八万里,自古不通中朝,至大明始再入贡.地图乃其国使臣冯宝宝所为,而末端作序,文字记之,其文字雅驯,与我国之文不异,始信书同文,为可贵也.按其国人利玛窦、李应诚者亦俱有《山海舆地全图》,王沂《三才图会》等书颇采用其说.欧罗巴地界南至地中海,北至冰海,东至大乃河,西至大西洋,地中海者,乃是天地之中,故名云[32]
显然,“冯宝宝”很可能是“利玛窦”之讹传,因为二者的繁体字(“冯宝宝”“利玛窦”)非常相似.所以,所谓“冯宝宝”地图应该是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另一个刻本.当然,李晬光也提到了这幅图四周所附的欧洲天文学知识:
余尝见欧罗巴国人冯宝宝所画天形图,曰天有九层,最上为星行天,其次为日行天,最下为月行天,其说似亦有据.([32]下册:488)
很显然,李晬光是从那幅“冯宝宝”的世界地图上看到这些内容的.
当然,朝鲜之所以能对来华传教士及其科学知识有上述了解,主要还是通过赴华使臣这条渠道.李晬光提到“使臣李光庭、权忄喜以欧罗巴国舆地图一件六幅送于本馆,盖得于京师者也”,说明情况确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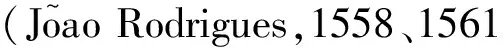
在这次会面中,陆若汉向郑、李二人们赠送了西洋器物和图书,其中包括望远镜、自鸣钟等天文仪器以及有关西方天文学的中文著作.郑斗源回国后将这些物品悉数上交,并在给承政院的“西洋国状启”中对与陆若汉的会面进行了详细报告:
西洋国去中原九万里,三年可达皇京.陆若汉即利玛窦之友,尝在其国制火石包以灭红夷、毛夷之作梗者,尤精于天文历法.到广东请以红夷石包讨虏师,帝嘉之,以为掌教官,送于登州军门,待以宾师.钦天监修历亦全用若汉之言. 一日若汉来见臣,时年九十七岁,精神秀丽,飘飘然若神仙中人.臣愿得一火石包归献,若汉即许之,并给其他书器,列录于后: 《治历缘起》一册、《天文略》一册、利玛窦《天文书》一册、《远镜说》一册、《千里镜说》一册,《职方外记》一册,《西洋国风俗记》一册,洋贡献《神威大镜疏》一册、《天文图南北极》两幅、《天文广数》两幅、《万里全图》五幅,《红夷石包题本》一. 千里镜一部,窥测天文,亦能于百里外看望敌阵中细微之物,直银三四百两云.日晷观一坐,定时刻,定四方,定日月之行.自鸣钟一部,每于十二时自鸣.火石包一部,不用火绳,以火石击之而火自发,我国鸟铳二放之间,可放四、五次,捷疾如神.焰火肖花即煮火肖之碱土者,紫木花即绵花之色紫者[34].
不过,此时的朝鲜国王李崑(1595-1649)和承政院官员们对郑斗源提到的西洋人精通天文历法、钦天监改历这些情况似乎没什么兴趣,对他带回来的天文仪器与书籍也表现默然.李崑虽然下令奖励郑斗源,但并不是因为他带回的天文仪器与图书:
陈慰使郑斗源处事明敏,其所觅来西石包精巧无比,实合战用,其留心杀贼,为国周旋之功,极为可嘉.特加一资,以表予意.一行员役中可赏者,亦令书启[35].
当时,朝鲜刚刚在1627年遭受了后金的入侵,被迫与之订立了城下之盟,并继续受到其强大的军事压力,所以,李崑的这番褒奖显然不是凭空而发.但是,承政院的官员们则似乎连这一点都漠不关心,反倒把郑斗源说得一无是处,并请求国王撤回嘉奖令:
陈慰使郑斗源状启殊极诞谩,其所上进之物,图为巧异,无所实用者多,而盛有所称引.其不识事理甚矣.此诚可罚而不可赏.而一小石包觅来之故,至加资级,物情皆以为非.请还收加资之命.([35],549)
李崑则再次强调:
郑斗源觅来火器制度精妙,我人学习,则必赖赖其力.数之多少不必论也.海行艰苦,且有其宫,一番酬慰,似无不可矣.([35],549)
承政院在随后三天中三次奏请撤销奖励,国王虽然三次驳回([35],549-550),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从之”[36],可见当时朝鲜文官势力之大.
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此时承政院的官员对郑斗源所介绍的那些事和所带回的那些物品的意义基本上毫无了解,因此自然不会有兴趣进一步追踪了解.但是,满清的进一步扩张及其最终入主中原注定会彻底改变这种局面.
1636年,刚刚称帝的皇太极(1592-1543)统兵亲征朝鲜,迫使其去除明朝年号,缴纳明朝所赐诰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时贡献,并送质子二人,由此正式成为清朝藩属国.从这时起,李朝开始接受清国颁发的历书.但是事实表明,李朝上下对清国的历法工作既没有信任,更谈不上敬意.例如,1639年,观象监在得到清国历书后,发现它与本国历书之间存在不同之处.经过重新推算后,他们认为本国历书没有错误.同时,他们还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拿明朝人出版的《时用通书》进行了比对,发现该书在大小月的安排上与清国历书一致.但是,在将以前许多年中的本国历书、明朝历书和《时用通书》进行比较后,他们发现前两者毫无差异,而后两者则差异颇大,于是他们得出结论:
意者,钦天监所刊之历,乃历年推算,宜益精审无差.至于《时用通书》,不但大小月多不同,闰朔亦异,此则出于冒禁私撰,而将前头各年预先推算,其势易于差误,有不足取信.而清国未必真得钦天推算之法,或就《时用通书》中已成之法刊成此书,以致违误.今当一以钦天监所颁旧历为准.([36],卷38)
观象监的这一建议得到国王的李崑的采纳.由此看来,李朝君臣最后宁愿相信明朝钦天监颁发的旧历书,也不相信清国的新历书,并且还说清国历书是按照明朝民间“冒禁私撰”、“不足取信”的通书刊成的,这完全表示了对清国历书和清国历官的蔑视.显然,在李朝历法官的心目中,明朝仍然是正统,明朝钦天监的历书才是权威性的,但可惜清国“未必真得钦天推算之法”.

顺治元年(1644年),朝鲜国王李倧之世子, 质于京,闻汤若望名,时来天主堂,考问天文等学.若望亦屡诣世子馆舍谈叙.久之, 深相契合.若望频讲天主教正道,世子颇喜闻详询[37].
及世子回国,若望赠以所译天文、算学、圣教正道书籍多种,并舆地球一架,天主像一幅.世子敬领,手书致谢.([37])

我国不是没有类似的这些东西[指地球仪与天文书],但数百年来推算天行常有误.所以我得到这些珍品怎能不高兴.我想如果回国,不仅要在宫廷中使用,而且要出版,将它们普及到知识层.相信它们将来不仅在学术殿堂成为受宠之物,而且将帮助朝鲜人民完全学到西方科学.([33])

经过对韩兴一带回著作的数月研究,1646年2月初,观象监提调金堉正式上疏支持改历.他提出的改历理由主要有两条:首先,中国自古历法有差必改,而《授时历》行用已久,积差日多,到了应改之时;“而西洋之历出于此时,诚改历之机会也”.其次,“中国自丙子、丁丑间已改历法*这里指的应该是明朝政府在1639年前后尝试用西洋新法编算各年历书.,则明年新历必与我国之历大有所迳庭”,因此“新历之中若有妙合处,则当舍旧图新”.第一条理由与韩兴一的说法基本相同,而第二条理由则是出于对两国历书异同问题的现实关注.鉴于“韩兴一持来之册有议论而无立成”,只有“能作此书者然后能知此书”,同时“外国作历乃中原之所禁”,所以他建议,“虽不可送人请学,今此使行之时,带同日官一、二人,令译官探问于钦天监,若得近岁作历缕子,推考其法解其疑难处而来,则庶可推测而知之矣”([36],卷46).
几乎于此同时,奏请使金自点等人从北京带回《时宪历》一册,经过研究,观象监发现其与本国历书在时刻制度和节气安排上存在重大差异.鉴于朝鲜历官“不可以《时宪历》所载之文究其神妙之处,必得诸率立成,各年缕子,然后可以知作历之法”,所以他们再次建议:“使能算之之人入学于北京,似不可已.”李倧决定,“极择术业高明者以遣之.”([36],卷46)
于是,李朝政府趁李景奭以谢恩使身份入清之机,让他带天文官前去学习新法,并“密买”《时宪历》.但李景奭到北京后却传回消息:“臣等又以《时宪历》密买之事广求于人,而得之甚难.所谓汤若望者又无路可见.”既未购得《时宪历》,又未见到汤若望.但“适逢本国日官李应林之子奇英被掳在彼,其人颇通算术,且惯华语”,所以李景奭“使之学习历法于汤若望,以为他日取来之计”.([36],卷47)
1648年旧历2月,“谢恩使洪柱元回自北京,清人移咨送历书,所谓《时宪历》也”([36],卷49),这标志着清朝政府正式向李朝颁发《时宪历》.但是,直到此时,朝鲜天文学家在编算本国历书时使用的还是《七政算内篇》,因此,如果在这个时候行用《时宪历》,势必会引起混乱.果然,就在洪柱元带回清政府所颁发的《时宪历》后两个多月的时候,礼曹给李倧上了一道启文:
丙子以后,中原与我国,历书无不相同,而独于今年,闰法相错,此必日官推算错误之所致.若闰在四月*依《大统历》当年闰三月,《时宪历》则闰四月.为是,则今月祭享、国忌,并皆失时,殊极未安.请推治日官.([36],卷49)
由于李曹掌管国家的大典和礼制,历书的这种混乱自然令他们难以容忍,但他们却错误地将其责任归咎于观象监.好在此前朝中大臣对《时宪历》的来龙去脉已经有所了解,所以领相金自点、右相李行远便出面为历法官员解围:
清国则时用汤若望新法,我国则仍用旧法,今以日月食验之,未尝差违,我国算法,未可谓全然错误矣.取考丁丑历书,乃是丙子印出大明所颁降者,而其法无异于我国之历.清国在沈时所送历日,大概相同.及其移入北京之后,始有依西洋新法,印造颁行天下之文,此乃大明时所未有之法,而我国日官未及学者也.([36],卷49)
不过,二人明显还是在为本国历法辩护,不但认为“以日月食验之,未尝差违,我国算法,未可谓全然错误矣”,而且还搬出明朝的其他历法著作来为本国历法辩护:
且考大明《时用通书》及《三台历法通书》,则今年闰朔之在三月,并皆昭载.三月非闰,未可的知也.([36],卷49)
新旧历书之间的这场冲突虽然暂时得到平息,但从中可以看出,面对清朝新颁的历法,当时李朝大部分官员还是宁愿坚守自己已有的系统.但是也有例外,就是那位第一个将《时宪历》的消息带回国内、并第一个提出改历建议的吏曹参判韩兴一.只有他“独以清历为是,凡其家祭祀之日,皆用清历”, 结果却遭到了众人的责怪(“人皆病其无识”).而编纂《仁祖实录》的史臣竟然专门对此留下了一段批语,其中充满批评和讥讽之意: “兴一本非通晓天文者,何知清历之果为是,而断而用之乎?其诸异乎用汉‘祖腊’之陈咸矣.甚哉,其无谓也!” ([36],卷49)

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清朝不但在中原站住了脚跟,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在历法上与它保持一致,这是政治上无法回避的选择.所以,就在接到清朝政府第一次正式颁发的《时宪历》后不到一个月,李朝政府马上就“遣天文学正宋仁龙学西洋历法于清国”([36],卷49)*《仁祖实录》到当年九月有提到“遣日官宋仁龙, 学时宪历算法于清国”.可能宋仁龙到九月份才真正成行..但据宋仁龙自称,由于清朝当时对“历书私学,防禁至严”,所以“仅得一见汤若望”,得其“略加口授,仍赠缕子草册十五卷,星图十丈,使之归究其理”[38].
尽管这一结果已经来不易,但观象监官对这次学习结果还是有两点不满意:首先,由于语言不通,所以这次学习只能是“画字质问, 辞不达意”;其次,从内容上来讲,这次“只学日躔行度之法,不啻一班之窥”.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西洋之法……其合于定理,亦未可知”,因此提出,在决定是否改历之前继续派人前去学习.而为了避免“辞不达意”现象的重演,他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别择日官中聪敏者,令治新历之法,日加程督,待其开悟,然后资送北京,质正其疑处”[39].

然而,《时宪历》在李朝的行用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1660年,有前观象监直长、安东道居进士宋亨久上疏,认为《时宪历》“种种差谬处不一而足”.对此,观象监也有人认为“宁存旧法,以俟知者为当”.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决定,在正式采用《时宪历》的同时,观象监每年仍按《大统历》推算历书,并“缮写二件,一以藏置,一以进上”([38],3874-3876).到次年,宋氏再次上疏,“请废《时宪历》,还用《大统历》”,遭到反对[40].
到此,围绕《时宪历》采纳的问题在朝鲜应该说是大局已定.但问题是,此时的清朝在历法问题上仍然局面未定.1666年,由于杨光先告到了汤若望,清政府中止《时宪历》,复用《大统历》.这年年底,当清朝历书颁到朝鲜时,而此时朝鲜按西洋新法所计算的历书早已颁发下去,于是又引现了一番混乱:
上谓郑太和曰:“今来清历,与前异者,何故耶?” 对曰:“中原历法,论议多岐.明朝时人亦陈疏论《时宪历》之失,故汤若望历法不得印行.此所以与前异者也.” 上曰:“然则用何历为是耶?” 太和曰:“清人亦于祭祀时,皆以《大统历》用之矣.” 上曰:“《时宪历》将废不行乎?” 大和曰:“似当不行矣.”上曰:“士夫家亦用今来新历乎?” 太和曰:“既颁旧历,未及印出新历,京外大小祭享,则当以新历推择,而闾阎,则必仍用旧历矣.” 承旨金万基进曰:“一国之内,岂有二历乎.新历宜速印颁于八路.” 太和曰:“言非不是,势有难及.” 上曰:“单历一张,急先印出,斯速颁布,而前用《时宪历》,今虽不用,亦宜年年印置,以凭日后推步之差错,如前《大统历》印出之为也.”([40],卷13)
用印单张历书的方法来救急,总算解决了“一国二历”的尴尬和不便.但面对情况多变的中朝,朝鲜政府不得不想出一个以策万全的办法,这就是既复用《大统历》,同时对《时宪历》也“年年印置”.
康熙历狱结束后,《时宪历》在中国恢复使用,李朝也于“庚戌岁(1669)还用《时宪历》”[41].自然,这样的改变还是难免带来各种麻烦.例如,在这年年底,宋亨久再次上疏“论《时宪历》之差”,明显是对恢复该历法不满.对此,观象监派历官宋以颖与他公开辨难,结果宋氏又遭失败([41]).直到《时宪历》恢复两年后,观象监还不得不继续完成一些收拾残局的事情:
观象监启曰:“王世子诞日,乃辛丑(1661)八月十五日,而至丁未年(1666),改用《大统历》法,则辛丑闰月,非七月,乃十月也.以此推之,八月当为九月,故世子诞日,议大臣定以九月矣.自庚戌(1669)年,还用《时宪历》,世子诞日,亦当还定于八月.而事体重大,令礼官就议于诸大臣.”上可其启.大臣议以为,当依启辞施行,上从之.
当然,从此之后,《时宪历》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直到1894年李朝采用太阳历后,才降到“参用”的地位,仅“忌辰、诞节及择吉用《时宪历》”([14],卷1).
从以上的追述中可以发现,尽管朝鲜朝野了解《时宪历》的欧洲背景,尽管他们在其采纳的问题上也出现过一些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在本质上不同于明清之际围绕历法改革而出现在中国的那些争论.因为,中国的争论虽然也涉及许多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但最终焦点却主要是集中于采用西方天文学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涵义上;而朝鲜的争论则围绕的是纯技术性的问题,较少涉及到《时宪历》西方背景及其政治涵义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接受的并不是什么政治上存在问题的西方天文学系统,而只是一个作为宗主国“正朔”象征的历法系统而已[42].因此,不管内心是否愿意,他们的选择只有一个:接受.这是由清朝和李朝之间这种“宗主-藩属”的外交关系所决定了的. (未完待续)
2013-12-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117022).
石云里(1963-),男,安徽省黄山市人,安徽范大学物理系1981级校友,教授、博士.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兼执行主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与韩国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国际东亚科学史学会副主席,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历史仪器工作组主席,Annals of Science、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和《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期刊编委.
石云里.中朝两国历史上的天文学交往(一)[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7(1):6-15.
P1-09
A
1001-2443(2014)01-0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