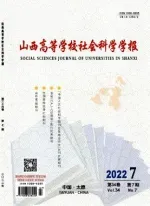意境概念的历史生成与禅境意蕴
2014-08-15陈元龙董卓然
陈元龙,董卓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71)
一、意境概念的历史生成
意境,是中国传统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可以说是中国美学史上关于艺术美的最高审美境界。意境自诞生就受到众多诗人、诗论家的关注和研究。从字形上看,“意”是由“音”“心”组成的,表现了人内心的情感活动,是外物反映到主体,主体有感而发而表现的一种状态。就像孔颖达所说“感物而动,乃呼为志。”而关于“境”,《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竟,乐曲尽为竟,从音从人。”[1]本义是指乐曲尽了。段玉裁注曰:“曲之所止也,引申凡事之所止、土地之所止皆曰竟。”[2]可见,境被引申为事物的终止、土地的疆界,具有时间范围和相对空间的含义。我国古代文论在谈意境时,总是把情和景作为构成意境的两大要素,并和具体形象的特征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意的规定性是指思想内容,那么,境则是指艺术形象和画面,二者不可分割、互为表里而有机统一。是无意识与意识、感性心理与理性心理相交融的结果,它和客观事物相结合,体现在文艺作品中,成为具体形象的画面就是意境。
在历史上,意境一词作为一个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来的是唐代的王昌龄,他在《诗格》中这样说道:“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3]在这里,意境是与情境、物境相并列的一个概念,三者共同强调了“境”在美学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后来,唐代的诗僧皎然,在《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扬上人房论涅磐经义》一诗中说:“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流露出诗境和禅境相通合一的审美主张,强调了诗情要借助意境来表达和发挥。在《诗式》中皎然明确地将诗歌构思作为“立意”和“取境”的过程。他说:“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4]130他认为诗歌的境界超越于文字和诗人形象之上,决定着作品水平的高低。他还认为诗歌的意境要“采奇于象外”,要有含蕴不尽的言外之意,同时他还主张意境要自然不落人工痕迹。“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4]126可见,皎然特别重视诗歌的意境要自然真实,浑然天成,认为这是意境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此后,司空图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他在《二十四诗品》中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美学范畴,“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5]而这个“味”应是“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即“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认为诗达于此可为诗的最高境界。司空图认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应该作为诗境的内在精神。其中,第一个“象”是实境,第二个“象”就是由这个实境所产生的象外之境,意境就是由实境引出虚境从而引发读者的想象,它是有限与无限、个别与一般的统一。诗歌要想有好的意境,必须“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也就是说,诗歌要超越表面的物象把握内心的精神。意境不在象内,而在象外。意境虽然是情景交融,但它却不能止于情景两因素,情景交融形成的艺术形象能够产生象外之象才能形成意境。
南宋的文学批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诗歌的“兴趣说”。他说:“盛唐诗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6]这里的“兴趣”可以理解为一种“情趣”,表现了主体沉浸在物我合一、身世两忘境界之中的一种情感活动,纯感性地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而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韵味无穷、深远含蓄、余味深厚的意境。受南禅“顿悟”说的影响,严羽认为:“其所重者只在诗歌中的感发作用与禅悟相近似,而并不是要求诗歌中一定要表现出什么清静幽微的禅理。”[7]246因此,他还用“妙悟”说来界定诗歌的特性,在佛学的认识论中妙悟是认识的最高阶段。悟者,觉也,有了解、领会等义。就认识论来说,对事物由现象到本质、由感性到理性认识,才称得上了解和领会。但佛家用这一“悟”字,并不是强调用逻辑推理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是用一种不言之喻、无言之辩,往往通过一种事物或一个比喻,一句微言妙谛而获得启示,心领神会,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便是如此,具有真实性、直观性和偶然性的特点。
明清之际,王夫之通过“情景关系”来对意境的审美特性进行阐发。他认为,意境并非单纯是审美景象或审美情思,而是在主客体的相互交融之中。同时,意境也不是静态的空间,而是不断生成着的时空同一体。经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而达到“情不虚景,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的境地。在情景无迹妙然天成之中,也就诞生了诗的意境。
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境界说”,可以说是意境论创生以来的一次总结。他首先明确用“境界”概念论词,他在《人间词话》一开始就写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把境界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最高美学范畴,在这里,“境界”的含义可以说就等同于“意境”了。“《人间词话》所标举的‘境界’,其含义应该乃是说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者,如此才是有境界之作品。”[7]162表明了意境是主体对自我情感、人生际遇、自然变化的体悟和思索等等,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概念。王国维的“境界说”拓展了意境的内涵,经典地总结了意境“情景交融”“意与境浑”的审美特质。
意境理论的形成显然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作为一种古老的东方智慧,禅宗精神在中国绵延不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中的“境界”一词引入中国,主要表示主体独特的心理感受和艺术体验。唐朝以后,禅宗对意境理论的影响逐步深入,特别在文人士大夫的诗歌创作方面。
二、禅宗思想的审美境界
(一)“境”“心”一体
“境”及“境界”一词最早出现在翻译的佛教经典著作中。佛教典籍中的“境”或“境界”,来源于梵语,原意是指人眼所见之物。后来,这个含义又从眼观实境扩展到了耳闻鼻嗅的虚境,直至指代一切天上人间之景象。佛经中大量使用“非汝境界”“非公境界”“何人境界”等意义,则多指主体的心理空间或是心灵境界,它反映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人格高低。因此,关于“境”的概念,佛教里的含义不仅限于疆界地域的含义,如丁福保在《佛学大辞典》中说:“心之所游履攀缘者,谓之境。如色为眼识所游履,谓之色境;乃至法为意识所游履,谓之法境。”可见,“境”主要是用于描述人的心理世界。佛教认为“界”有三种:欲界、色界、无色界三个层次。《佛学大辞典》对“境界”的界定:“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又,我得之果报界域,谓之境界。”可见,“境界”一词在佛教里指的是佛弟子修持所经受的心理阶段和所达到的修持程度。《华严梵品行》中说:“了知境界,如幻如梦。”《景德传灯录》所言:“一切境界,本自空寂。”“境”指的是主体的精神世界、内心活动,和诗人对意境的领悟和把握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昌龄在《诗论》中首次引用意境一词时,显然就是受到佛教中“境”的内涵的启示。由此可见,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的境或境界的提出,及其一整套理论话语的建构如意境理论的生成,与禅宗渊源极深、息息相关。
禅宗关注的是当下的心性,当下的现实生活,心性是第一位的,在哲学上是典型的形而上的唯心主义思想。禅宗认为“境由心生”“境心一体”,要离开一切矛盾和分别之心,超然于外,不执著一切的表象,而实现圆融无碍洒脱自在的境界。“外无一物而能自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坛经·付嘱品第十》),一切都是由心所生发出来的。心性就是山河大地,就是世界宇宙。“佛者,觉也”(《坛经·忏悔品第六》),“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坛经·般若品第二》),强调了要重视自身心性,心性第一,身外之物都是由心而出的。古人云:“风月无今古,情怀各相异”,风与月永远都是那样,但由于人们心境的不同,所产生的感觉往往大异其趣。禅宗把心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是绝对化和本体化了,世界万物都来自于“心”的观照。从美学的角度思考,强调了认识的主观性,风吹幡动,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强调的就是主观的感受、主观的心性。
(二)“境心之悟”
禅境意蕴作为佛教思想与本土文化的结晶,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深刻的精神内涵。魏晋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玄学思想盛行,谈玄论道成风,二者的思想很快相结合。唐朝时期,北禅思想盛行,后经六祖慧能的改革,提倡“人人都有佛性”“顿悟”“见性成佛”等等,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上层士大夫的欢迎,风靡大江南北,直至现在仍是中国佛教信徒中人数最多的一派。禅宗思想主张一种自由的审美生活,随缘任运、随遇而安,以自由的心境来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审美境界可以说是人生境界的极致,道家的物我合一的人生境界就是一种审美境界,道法自然,以自身与天地合一,以万物为须臾,以自身涵盖宇宙乾坤。禅宗的审美境界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种非理性、非逻辑性的思维方式,“一落言诠,即失其旨”,其修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悟”,可以说“无悟即无禅”。特别是南禅思想大力倡导顿悟思想,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重视当下的自我体验和开悟。禅宗的主要特点是主张“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不立文字,顿悟见性”。超脱于善恶之外,体悟与自然人生、宇宙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
禅宗认为要想达到成佛境界,要明心见性,不滞留于境更不要为其所染,这样才能超凡入圣而成佛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靠直觉和顿悟,达到与宇宙合一、明心见性的目的。禅宗思想本身就体现为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人生理想和人生境界。“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禅”,修行不在于脱离尘世、遁入空门,有心事佛的在家也可以修行,“搬柴运水,无非妙谛”,可以说“处处是道场”,关键在于心的开悟。“明心见性”即是找到自性,真正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觉悟到自身具有的佛性。在此基础上,进而认为看待万物要没有分别之心。“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在禅宗看来,“万法唯心”,万物皆由心造,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所以要用智慧的审美的眼光来观照外物。“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坛经·般若品第二》)用自己如如不动的真心,无分别之心,清净之心来观照一切现象。黑格尔说:“从一方面看,美与真是一回事。”[8]美感是超脱了任何利害关系于对象无所欲求的精神愉悦。美学里认为审美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无功利性的眼光看待外界的一切,是对周围事物真挚的热爱。禅宗追求的是主体心性的自由,是对现实人生深深的热爱却又是超脱其外的,其中蕴含的审美精神和审美观照都是很浓厚的。
三、结论
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重要范畴,意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宗白华先生就曾说过:“就中国艺术方面——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9]不管是研究国人的审美心理与审美理想,还是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审美内涵都绕不开意境范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与禅结合得最紧密且取得成就最大的艺术门类首推诗词,其与意境的关系可谓水乳交融。以《诗经》为例,它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其艺术价值很高,而清人潘德舆曾这样评价:“《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王国维也说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0]从古至今,研究意境的学者之多、作品之多可以说是无法精确统计。虽众说纷纭,但都不否认禅宗思想是意境理论生成的一个重要的源流,禅宗美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作品与意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许 慎.说文解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58.
[2]洪成玉.古今字[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34.
[3]陈应行.吟窗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 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杜黎均. 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189.
[6]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6.
[7]叶嘉莹. 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M].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黑格尔.美学:第1 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42.
[9]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
[10]王国维.人间词话[M].济南:齐鲁书社,198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