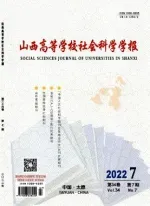马克思人学思想被误读折射出中国学人的“文化人格缺陷”*
2014-08-15唐善梅
唐善梅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1815;南京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从马克思主义诞生那天起就蕴含在其丰富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却一直被我们误读。一开始我们可以归结为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误导,斯大林专制集权和个人迷信对我们思想造成的束缚,当然文革那场浩劫也算是重要因素,当时流行的语录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误读到了怎样一种地步。在20 世纪3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兴起了被胡克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的“早期著作热”,发掘马克思学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半个世纪后我国学界才开始了“第二次启蒙”(邓晓芒),开始讨论人性等问题,一批先知先觉的学者开始着手研究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总算开拓出了一片疆土,为我们这些后辈学人奠定了继续研究的基础。在对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进行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时而会产生一种“冲突”的感觉,马克思的思想总是时不时对内心中原有的一些东西造成了颠覆。学习了邓晓芒老师的“新文化批判主义”和“自否定哲学”的思想后,找到了这种冲突的来源。作为中国学人,尤其是具有一定传统文化基础的学人,在接受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时有着一定的“文化人格缺陷”,同样的语言、词汇,我们所理解的和马克思所表达的不是一个意思。在我们的文化人格结构中,缺少和马克思共同的东西——建立在个人人格独立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
一、关于人道主义精神
马克思是西方人,出生在德国,那是一个以理性思维发达著称的国度,出现过康德、黑格尔等人类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哲学家。马克思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最初几年,是在德国政治生活相对平静的时期度过的,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离法国很近,又由于它曾受过法国统辖,所以受着法国革命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1]59。当时,领导德国进步自由主义运动的是知识阶层,尤其是律师、作家等。马克思的父亲也是一位律师,虽然他没有参加运动,但毫无疑问,他一定受到这种思想和政治气氛的感染,尤其是他广泛阅读了18 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泰、狄太罗和达兰贝尔等人的著作,无限敬仰启蒙思想。父亲对启蒙思想的崇拜和进步自由主义的思想,都深深感染着马克思。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人和理性的崇拜,文中并提出人类幸福和个人自我完善一致的人道主义理想目标。他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这里的人类是具有“类”意识上的人类,是西方哲学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人的理解,是建立在独立的个体人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类的共同性或共同的“人性”,就是活动的自由自觉性。他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征、它的类的特征,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征[3]。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述中,曾认为自由是人的类特性。他在回答女儿的提问时,说自己最喜欢的格言就是:凡人所具有的,我都应该具有[1]125。这句格言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口号。人道主义不仅是马克思继承前辈的思想,更构成他深厚的人文底蕴。
对这一点,我们“五四”时期的启蒙学者们都有过误解。在他们看来,人道主义就是群体主义,它可以扩张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于世界主义,但无论如何,要求牺牲个人以成全群体、牺牲一己而成全多数是最基本的信条[4]。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只有群体,没有个人。尽管孟子有过“民本”思想,但这从来没有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鲍鹏山老师在《商君书》的讲座中提到过商鞅的统治思想(也就是用来统一六国的秦国的统治思想),老百姓只需要做“耕战之民”,战时上战场打仗,非战时农耕,为国家提供粮食。老百姓是不需要有什么思想的。有思想的被当做“强民”是要被除掉的,难怪秦始皇和李斯要焚书坑儒。我个人认为,中华文脉的第一次断裂就在那个时候,春秋时期儒家“士的精神”被摧毁殆尽。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心目中,“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百姓都是他的子民,他们对自己的最高要求也不过是“爱民如子”,像父亲对待儿子似的,而且是封建家长式的父亲,“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里的“子”是没有人格和价值可言的。事实上“爱民如子”的帝王并不多,视民如草芥的到比比皆是。我们搞不清楚在战争期间死去的老百姓身份很正常,即使那些为抗战牺牲的士兵又有多少能被历史记录下来?我们的历史只记载英雄人物,对马克思看重的“人民群众”没有兴趣。人民群众只是一个个封建帝王利用的工具,在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的时候,人民群众是发挥重大作用的,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的白骨应该都是人民群众的。人民群众从来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逻辑是“胜者为王败者寇”,为了为王是可以不择手段的,牺牲人民群众算什么?对此抨击最尖锐的当属鲁迅了,他说几千年来我们是一个“吃人”的民族,我们不仅在肉体上惯于吃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总是将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吞噬无遗、化归乌有[5]。
马克思用“人的本质异化”敲响了“人性危机”的警钟,想运用一种比以往都更加严密的科学来指出一条人性解放的道路,并展示未来自由社会的前景。他的目的是一种实践行动,是用哲学来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他并不把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看作是永恒的价值尺度,“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才是最高的价值,这就是哲学上的价值。这种价值按照我们传统文化的思维是理解不了的。我们在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中,曾一度轻视或排斥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凡是讲到人道主义和人性都要加上否定性修饰词语,基本上是政治意义的定性,缺乏学理上的探究。这是有着“文化人格基因”的。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对个人价值的肯定。
二、关于理性精神
马克思是西方知识分子,西方知识分子一向把批判当作自己的天职,这种批判是立足于有理性的人的人性或人的本质之上的。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是思想者,正如自我意识就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一样,真正的思想就在于不断地反思,即“对思想的思想”。批判就是一个理性存在者的自我实现,是建立人的理性的必由之路[6]。这一点从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等的批判就可以看出来。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普鲁士政府的封建专制进行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进行批判,这些批判都是建立在他自己的理性思考和学理研究的基础上的。德国政府曾经三次派人劝说马克思进政府任职,但是,都被马克思拒绝了。他说: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就是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善其身是为了济天下,穷独时向往济天下,向往而不达则发牢骚,或隐居,或成为狂士。这都不是主流。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是“货与帝王家”,成为“帝王师”,最好的也就是成为名垂青史的“谏臣”,如唐代的魏征,那也是遇到“明君”才行,很多谏臣还是落得个杀头或者流配的命运。谏臣在向君王进谏的时候也是依“天道”“祖制”等现成的规矩,与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无关,更别说批判的。“往圣的绝学”是只能用来“继”的,不能用来批判的。即使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等口号,希望直接拿回来开启“民智”,或者被统治者使用避免“亡国灭种”,他们自己也并不都是理解了这些口号背后蕴含的关于人的理解的抽象理念,他们只是拿来用作救国的政治实用工具,更谈不上理性批判了。20 世纪90 年代讨论的“人文精神失落”,说知识分子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堕落了,所以我们的人文精神失落了。这是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政治理想后的一种无所适从,他们已经不再是老百姓的精神领袖,只是靠脑力劳动谋生的劳动者而已。我们的思维观念中就没有关注现实这样一种人文精神传统,我们只有学而优则仕的文人传统。理性批判在我们传统文化基因中是缺乏的。
三、关于自由精神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和西方个体人格的独立。西方近代建立起来的这一套法权哲学,特别是权力制衡理论,标志着西方自由意识已经进入到了实行期和成熟期,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叫做“天赋人权”,也就是人人生来自由的意识。政治自由就是着眼于建立保障每个人平等地自由的社会制度而提出来的,这是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由放在政治的层面上考虑过,它顶多被看作个人的一种心情或境界。例如道家主张回归自然自由。政治自由为其他自由奠定了基础,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拥有财产的自由、贸易自由、迁徙自由,还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这些自由没有一种是儒家或道家关心过的。24岁的马克思在担任《菜因报》主编期间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就是为人民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马克思当时批判过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权,马克思指出:“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7]82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8]440。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时,资产阶级就“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9]622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的批判就想当然地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很糟糕,资本主义人权是虚伪的,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在马克思对他的祖国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祖国的人们还没有现代人权的概念呢。我们到现在都缺乏法治精神。我们传统中的法是“刑法”,是封建统治者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和西方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契约概念不一样。我们常常把公意理解成众意,少数服从多数。真正的公意是建立在每个人同意的基础上,比如对立法的需要。有学者根据《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描述指出我们误读了这一概念。除去故意误读之可能,从文化人格角度看,我们根本不具备马克思所讲的那种建立在法治意识基础上的民主和专政的概念,只能依靠我们头脑中旧有的观念去执行了。
马克思曾经描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不自由,这个社会就不自由。马克思、恩格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是一种具有超越精神的概念。所谓的自由王国,是一个理想,人类的理想就是自由王国。这个理想康德已经提出来了,就是“目的国”。在这个目的王国里面每个人都是目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人类社会是从阶级社会走来的,一切阶级社会都是必然王国,《资本论》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有它的“铁的规律”,但是这种铁的规律必然要被扬弃,过渡到自由王国。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只是一个逻辑推论;但是作为一个理想的终极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不可缺少的,可以用它来衡量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看它的自由度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这个尺度是不可少的,不然我们就没有努力的方向了[10]。这里谈的必然王国、自由王国都建立在西方人意识中的彼岸概念上。西方人有自己的一个办法解决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内在矛盾,这就是诉之于上帝或任何一种彼岸世界的信仰。因此在西方,当人们给予个人以人格独立性时,往往把由此带来的犯罪意识引向来世救赎的方向,以避免由于希图在此岸得救而终致放弃个人的独立性,而当人们为了过协调的社会生活而以“社会契约”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时,却使这种契约建立在一个超越一切现实的先验前提之上,这就是“每个人生来自由”,它是一个契约社会中每个自由人的一种彼岸信仰,即康德所谓“实践理性的悬设”[4]。我们传统文化中缺乏彼岸的意识,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总是盯着政治和官场,不是争宠揽权,就是愤世嫉俗,少有对自然知识和客观真理的探索和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以各种方式从政、佐政、“报效国家”,对知识学问的一切探讨、对真理和美的一切追求,最终无不是为了这一政治目标、服从这一目标。我们只有对政治生命的看重,没有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为艺术而追求艺术等超越价值的追求。中世纪教育在人心中确立一个彼岸的精神世界,使西方人的自我意识在个体灵魂和上帝之间拉开一个无限的距离,这正是近代大学理念得以发展起来的前提。近代大学即使在世俗知识的教育上,也强调这些知识本身的超世俗的价值,强调其作为永恒真理的独立不倚和提升人的精神素质的作用。近代大学决不是传授技能的场所,而是养成科学精神和探讨宇宙奥秘的祭坛[11]。我们近代因为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但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已,我们只看到了西方技术的实用,没有看到科学的先进,科学精神是一种对于超越的追求。我们学习西方大学可以学习他们的知识体系,组织架构,就是学习不来背后蕴含的那种追求真理的超越精神。我们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启蒙,没有上帝这样一个彼岸的信仰,我们很难理解西方人的那种超越精神。所以我们很难理解马克思心中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们只能把全面发展理解成德智体美劳等人的能力素质的综合发展,我们很难把握这当中蕴含的人的类本质的概念。至于自由我们即使消除了以往的那种对自由“无法无天”的理解,加入权利义务的概念,但我们仍然无法理解其中蕴含的彼岸意识,那是西方人文化基因中蕴含的信仰意识。
由于我们传统文化基因中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理性批判精神和彼岸超越精神,我们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时候就很难真正“回到马克思”。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也是现代化的时代,在中西文明的碰撞过程中我们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无所适从,传统的文脉断裂了,不管是因为秦朝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还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总之易中天老师讲的春秋时期士的精神在当今是很难找到了。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我们由于自身的“文化人格缺陷”也不是那么的游刃有余。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19 世纪的产物,我们理解起来都有这样那样的距离感。我们在学习外来文明的过程中喜欢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的逻辑,实际就像邓晓芒老师所说的那样,精华糟粕是相对的,不是西方人抛弃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糟粕。人类文明前进的过程貌似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就像西方为了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走到极致让上帝死了,结果他们也出现了信仰危机,后现代又开始对这些问题重新进行反思。我们当前要做的应该就像邓晓芒老师说的那样,先来一个自否定吧,弥补一下我们文化人格当中的缺陷,没有具有自由人格的现代人的出现,哪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韩庆祥.马克思的人学理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4]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J]. 科学·经济·社会,1999(12).
[5]邓晓芒.人论三题[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序言.
[6]邓晓芒,欣 文. 成人的哲学——邓晓芒教授访谈[J]. 学术月刊,2005(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0.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2.
[10]邓晓芒.什么是自由[J].哲学研究,2012(7).
[11]邓晓芒.教育的理念.中国教育改革的哲学思索(笔谈)[J].高等教育研究,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