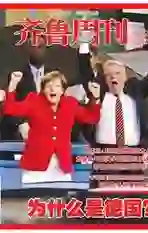孤独的年轻人
2014-08-12老四
1
美国作家耶茨写过一本书《十一种孤独》,描写了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普通纽约人的生活,写了十一种孤独的人生,那些孤独的年轻人,成为一个时代独特的注脚。于是,我想起了那个小屋,以及曾经属于我们的孤独。
我有一个院子,有野葡萄挂满窗棂
黄鼠狼时常破门而入,有蛐蛐
奏响《命运交响曲》在床头
有蚊虫亲吻爱抚,麻雀唱诗
在高楼和沥青的缝隙里
我有30平米的孤独和得意
有令人艳羡的田园往事
隔壁的巡抚大院、泉城路、贵和银座
隔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是我的附属国
……
——《寿佛楼后街28号》
写这首诗是在四年前,去青岛的火车上。老六夫妇为了排遣我一个人生活的孤独,计划了国庆节的海滨之旅。最终,他们的蜜月,演变成我和老六的喝酒之旅。
本文不是要说青岛,而是寿佛楼后街28号,我在这里住了两年。之前,为了体验一个人的孤独,我决定搬离兄弟们群居的房子,找一辆三轮车,把床铺和几百本书搬到老城区的这个大杂院。
2009年,我24岁,那是一个怎样的年纪?同样是24岁,博尔赫斯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46年后,这位双目近乎失明的老人在诗集再版序言中写道:“我发觉1923年写下这些东西的那位青年本质上已经就是今天或认可或修改这些东西的先生。我们是同一个人。我们俩全都不相信失败或成功……”而我在24岁那年,似乎也已经奠定了此生的方向,不甘寂寞地活着,孤独而又充满决绝。
“痛并快乐”——回忆小房生活,总会首先想起这句话。雨季来临,地板上冒出几股泉眼,房间里成了泉池。被子、衣服全都潮了,只好买来箱子,把所有易潮物全都密封起来。而冬天,水龙头被冻住了,就去买了纯净水往家扛,洗刷、饮用全都靠这些水。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一个小小的电暖器,成为我唯一的依靠。没有卫生间,公厕在大街上,有三四百米远,若有内急,只能骑上自行车飞奔。拉稀就没办法了,只能一次次飞奔,一整夜都被消耗在两点一线之间。
我扯了网线,老城最核心的巷子的这处小院,第一次有了网络,邻居们纷纷来参观。但他们不会上网,要搜索什么东西,只好我来帮他们百度。一个大姐,要我帮她查查网店是怎么回事,她是开花店的,电脑上怎么能开店呢,她一头雾水。
去大明湖挖了点儿土,在窗台底下整出一平方米的“菜地”来,种上空心菜、韭菜,做面条时偶尔过来掐几把青菜。
周末我就骑上自行车,在附近的城中村转悠,老东门、柳行、花园庄,荷尔蒙分泌极度旺盛的男女,分不清是恋人关系还是炮友关系,从性用品店里出来,闪入街边的出租屋。他们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在我的小说里,我看到了他们在餐桌前、厨房里、床上的情景。
深秋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我敲完了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一个字。这是一群人大学毕业后漂泊的故事,绝望、乱性、背叛成为人生的标签。后来无数人问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主人公后来怎样了,我都无可奉告,小说的荒谬和现实的荒谬结合,亦真亦假,至于他的命运,你看看现在的我,正在以庸常的姿势步入中年人的行列,会得到答案吗?
小屋离大明湖很近,经常窜进去,在夜里无所事事,看一群老年人唱歌。他们唱《我的祖国》、《英雄赞歌》,他们活在曾经的那个时代,仿佛时光倒流,在暮年,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英雄主义。那些英雄之歌,一直流传到现在,我跟着哼几声,然后跑去看人钓鱼,大明湖里的鱼很多,尤其夏天,有佛教人士定期来做放生活动,就有更多的人带着渔具前来收获。
而我正年轻,需要暴走。走着走着,就到了超然楼,当年蒲松龄在这里寓居,而今的超然楼一派豪华,已不是当年的样子。蒲松龄曾在大明湖畔生火做饭,烟熏得睁不开眼,吃饱了就走进贡院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终其一生,这个外乡人一直在往济南跑,最后一次,63岁的老头,喝了酒,醉醺醺骑马回家,哀叹“我亦头白叹沦落,心颓对此如死灰”。
我也在湖畔生火做饭,却厨艺惨淡,而又时常过于自信,做一次失败一次,只好自食恶果,把一锅残废的饭菜艰难咽下。有一次炒了一锅苦瓜,难以下咽,却又全部吞下,幸好有酒,最终在痛苦中进入醉态。
2
小屋虽简陋,却不时有人来访,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在这里住过的,有诗人、写小说的小导演、非著名记者、乡村教师、流浪的背包客。小屋成为他们经过济南的中转站。几乎没有例外,先是喝酒,醉了后痛骂对自己失礼的时代,然后各自抱着一张床进入梦乡。
“著名”记者小刀,真名隐去,忘记了是小屋的第几位客人,我找出他的被子让他在里面回忆大学时光——毕业后,很多人将被子、褥子抛给我,离开济南去流浪。那时候我还有他们的被子,以备他们回来时享用,后来一股脑儿全扔了。
不用打电话发短信,只要打开各大门户网站,浏览最热门的新闻,十有八九会得到小刀最新的讯息。他总是一个人,背着硕大的行军包,出现在任何一处新闻现场,寻找被遮蔽的真相。小说家村上春树来到耶路撒冷,面对人类的命运,说出内心的实话:“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在权力和寻租的夹缝中,还有多少人,试图打破这个时代的疮疤?小刀孤独的身影,就成了一枚冲向高墙的鸡蛋。
征地事件、女生被性侵事件、水污染事件……小刀的足迹和笔触,深入这个社会的细枝末节,他的孤独,没人在意。他说自己是“一个自卑的怂货,一个颓废的失败者,一个躲在角落里人人随便踹一脚的矮挫丑……”对抗的勇气,似乎就在自卑的牢笼里发芽。
3
一个夏天,山村教师郎古叩开我的房门,带来了他的画作和以我的诗作为内容的书法作品。他在一个远离城镇的山村当老师,住在学校里,除了做留守儿童的孩子王,整座山都是他的画室。endprint
接下来的冬天,我去找郎古。那是沂蒙山区腹地的一个小镇,以生产水果罐头著称,镇中心广场上,竖立着抗日名将左宝贵的雕像,而这一带最著名的是刘黑七,一个罪恶滔天的土匪。正值寒假,我没有去他任教的学校,而是被他带到了敬老院。
当老师之前,郎古作为当地的村官,和一帮年轻人被安排住进敬老院的宿舍。他考上教师之后,还有一帮朋友在敬老院里等待命运的分配。我们找到一家营业的餐馆,炒了几个菜,买了两瓶白酒,四五个人聚在敬老院简陋的宿舍里举杯痛饮。我观察宿舍的每一张床头,无一例外摞满了公务员考试书籍。
那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刚大学毕业,离开校园,被赶到另一个陌生的乡村世界。村官严格来说并不算一种职业,甚至连临时工都不算,只不过是在就业压力面前,大学生通往社会的一个缓冲。每个人负责一个村子,却又距离村庄很远,整天聚集在镇政府里无所事事。未来,除了进入体制内,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郎古考上了教师,脱离苦海,却走进了深山。他所在的学校是个地道的穷山沟,山民主要栽种山楂、苹果。为谋生计,一多半孩子的家长在外地打工,主要的活计是卖冰糖葫芦。
郎古每天早晨从学校出发,爬到山顶,对着酸枣树和山楂树朗诵古诗。他开始写作,书写一座山的寂寞,写他的学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的孩子们。他还利用学校的关系,订了一份《人民文学》,以便接通与外界的联系。
郎古偶尔回到敬老院——这里残留的欢笑足以抵消他被大山封闭的孤独。在这个院子里,除了几个孤独的老人,就是这些年轻人。未经历社会的年轻人和被社会舍弃的老人们,成了相依为命的伙伴。作为摆设的篮球架,终于被年轻人占领了,除了打篮球,他们也会在篮球架下摆上几张桌子,自己炒菜喝酒。
郎古给我看他拍的照片,寂静的夏夜,篮球场上一盏昏暗的灯泡,十几个男女围坐在桌子旁,喝酒吃菜,他们脸上散发着与小镇类似的清纯。那天晚上,我走到寂静的篮球场,清新的空气把我包围,天上是密布的星辰,这里是世外桃源,也是命运的分水岭。
爱情就此滋生,类似大学的群居生活,加上遍地而起的孤独,很容易把两颗心编织到一起,有的人突然就住到了一张床上,然后一起用功,一起考上公务员。如果其中一个没考上,没几天便分手了;即使都考上了,一个在天南,一个在海北,分手也成为必然。
后来敬老院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最后剩了几个,考试对于他们来说已绝了希望,也离开了这里,消失在远方的工地上。
由于搀和进了一场高利贷骗局,郎古被迫离开学校,到临沂谋生。有一次路过临沂,我去找他,喝醉了酒,我狂抽烟,而郎古则铺开许多张宣纸,疯狂地写字,字里透露出一股愤懑。事件平息后,他又回来教书,却是另一个更偏僻的山村小学,只有他一个老师,他既做校长又做语文数学体育美术老师。临沂之旅的最大收获是,一个大学生爱上了他。女友经常赶山路去看他,简陋的小学校留下他足迹的地方,后来又有了女友的足迹。
4
26岁,我搬离小屋。“想当年多么年轻”——这首苏联电影《我的爱在第三班》插曲,把无数人带回到记忆的深渊。当我步入老年,或许也会发出同样的感慨。可惜,时间左右了一切,我年轻过,也会苍老,命运没有过分打击我,也没有刻意疼爱我。
刚搬走没几天,那个小说出版了,一箱样书从北京寄来。我搬着书,穿过老城区稀疏的人群,穿过护城河,穿过一个菜市场,顺便买几个土豆,割半斤肉,艰难地爬上新居的六楼,“对于人类,它的分量是如此之轻,可以忽略,而它本身的重量,却把我压垮”。压垮我的,并不只是这些劣质的纸张,还有那些破碎的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的命运。
我把一本本书签上潦草的赠语,分寄给两年前的那些小屋来客。又过了几年,我试图找出一本来,以做回忆之用,翻遍书房里的所有角落,却再也没有找到。
(老四,即吴永强,《齐鲁周刊》首席编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