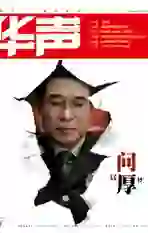遵养时贼事件是怎样造成的
2014-07-24陶短房
陶短房

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和四至五年(公元329-329年),在东晋辖下的江州(包括今天江西、浙江、福建各一部,治所在今天九江),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政治事件。
首先是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相当于行政长官兼军区司令)温峤病逝,他的助手刘胤被任命为继任者。朝中许多重臣都对这项任命不满,他们指出,刘胤性格疏懒,贪图享乐,又生性迷恋财富,可以出任幕僚或朝官,但绝不适合担任需要理政、理财的地方行政主官,否则必然误人误己。对此,朝廷方面似乎并不否认——但也不打算收回成命,而是以“刘胤系温峤推荐人选”为由,轻飘飘地回绝了众人的劝诫。
紧接着,这位被公认不会胜任、一旦出任地方主官必定贪腐的刘胤果然贪腐,在任上不仅懈怠政务,纵酒逸乐,更想方设法经商敛财,成了东晋这个流浪王朝首屈一指的官商和豪富,最终导致他被东晋官方明令革职,然而这位“撤职干部”居然以“正在上诉”的理由赖在任上不走,朝廷居然也就无可奈何。
再往下的戏份就更好看了:名义上已被撤职查办,但实际上仍然当着江州军政一把手的刘胤,某日接待了一位名叫郭默的“军队上访干部”,原来郭默收到一份去首都建康任职的调令,他在地方上野惯了,不愿去中央坐冷板凳,希望顶头上司刘胤能帮忙说情。
转职干部找撤职干部走门子疏通人事问题,本身就已经够离奇了,更离奇的是这个请求居然被刘胤以“既然朝廷这样安排,做臣子的就应该服从”之类大道理,义正辞严地搪塞拒绝了——他难道忘了,自己是怎么死赖在江州任上不走的么?
事情到这里非但没完,反倒进入高潮部分:愤愤不平的郭默打着“奉旨讨伐贪官”的旗号杀进官署,杀死刘胤,不仅把刘胤贪污渔利所得的资产如数据为己有,甚至还霸占了刘胤的女儿,而朝廷居然忙不迭地给郭默补发了讨伐刘胤的诏书,还差点将任命郭默接替刘胤一切职务(严格说是“免职前的一切职务”)的诏令也一并送了过去。
一出闹剧演到高潮却戛然而止,是因为杀出一位叫陶侃的,这位当时都督七州军事、驻节荆州的名臣听闻如此荒唐之事,愤愤不平地致书朝廷,质问总理朝政的丞相王导“杀死刺史就任命为刺史,以后谁杀了丞相,是不是就该任命当丞相了”;那位被已故的温峤誉为“管夷吾(管仲)再世”的王大丞相居然也不动怒,用“遵养时晦,等待您这样的能人出手”来搪塞,哭笑不得的陶侃一面起兵讨伐郭默,一面辛辣地将王导的做法讽刺为“遵养时贼”。
这起历时不到一年,却跌宕起伏、戏剧性十足的“大场面”——姑且称之为“遵养时贼事件”,可谓从头一路错到尾:朝廷明知道刘胤不适合当地方军政主官,却莫名其妙地下达了委任状;刘胤果然“不负众望”贪腐误事,撤职查办却硬是撤不下来;朝廷拿赖着职位不走的刘胤没办法,可一个接到调令的军官却能轻而易举地把他拿下;假冒圣旨搞假“肃贪”的军官不仅抄家、杀人,而且抢男霸女,怎么看都该算做造反或兵变,但“肃贪”者自己立即变成大贪不说,“假圣旨”也堪堪变作真圣旨……而让闹剧变成“正剧”的雷霆一击看似大气磅礴、替天行道,实则不过是为整出闹剧添上画龙点睛的最后一笔——原来看似庄严神圣的体制、秩序、法令、条文,从“时晦”到“时贼”,所相差者,不过是身任七州大兵马统帅的陶侃那几万雄兵罢了。
东晋之所以弄到“遵养时贼”的地步,并非中枢或皇室成心如此,而是情势使然。
东晋的第一代皇帝司马睿,在西晋皇族中,本属于和皇帝血缘关系疏远、社会声望也平平无奇的二三流人物,只因皇室先遭逢“八王之乱”,继而北方“五胡”肆虐,刀兵四起,前后两任皇帝和大多数皇族精英,都在内乱、混战中同归于尽,因被排斥、外放,阴差阳错躲过浩劫的他,才侥幸当上东南半壁残破之国的君主,这样一位君王名不正、言不顺,起家的实力也相当有限:初到建康时只有镇东将军、扬州刺史的头衔,这个名义上归自己领导的扬州,还是王氏家族勉强让给他的,而扬州以外的江、湘、荆、广、交等诸州,地方军政长官许多都是受命于西晋皇室的名门望族,对原本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威望还不如自己的司马睿竟然称孤道寡、发号施令,也是或阳奉阴违,或消极对抗。司马睿掌权之初,江州刺史华轶、湘州刺史甘卓等就曾立异,仅仅依靠王氏兄弟宗族的势力才勉强弹压下去。正因如此,西晋皇室对王氏宗族只能绥靖,无法发号施令,后来的王敦之乱,也让皇家颜面尽失,因为皇家根本没有“严肃法纪”的实力。皇家立不了王氏家族的规矩,王氏家族也拿各路诸侯、门阀和骄兵悍将无可奈何。
如此一来,“遵养时贼”现象就丝毫不难解释了:正因为不敢轻举妄动,朝廷和王氏家族才既不敢拿贪腐怠政于前、拒不接受处分于后的刘胤开刀,又不敢理直气壮地讨伐有明显反叛行迹,且贪腐甚于刘胤的郭默;正因为朝廷和王氏家族骨子里其实不相信刘胤、郭默甚至陶侃中的任何一方,才会心照不宣地任由他们自相吞并残杀,并毫不为难地承认一切胜利者所创造的既成事实。
事实上,朝廷之所以下狠心撤刘胤的职,主要并非因为他豪奢、贪腐、荒废政务——当时的地方官有如此毛病的比比皆是,但很少受到处分,而是因为他任职江州后倚仗权势大搞买办商业,遮断了下游朝廷赖以为生的长江商道、财路,据说情况最严重时,到了朝廷发不出文武百官俸禄的地步。正因如此,当桀骜不驯的郭默杀死了拒不就范、建康方面却鞭长莫及的刘胤,并随即上表贡献以求“补票”时,朝廷会顺水推舟:郭默再跋扈,就冲恢复朝廷财路这点,也比想撤撤不下来的刘胤可爱得多;也正因如此,当陶侃站出来号召讨伐时,朝廷和王氏家族便顾不得计较这位寒门出身方面大员的不恭不敬、夹枪带棒,转过头来把大义名分拱手奉送,因为陶侃的讨伐不仅更名正言顺一些,而且相对叵测凶险的郭默,“久经考验”的陶侃又显得安全得多了。
很显然,纲纪、体制、反腐、肃贪,在这种弱干强枝的畸形政治体系下,都不得不服从于“生存”这个天下第一大局。在这个大局约束下,号称“勇敢果毅”的晋明帝司马绍不敢替被王氏活活气死的父亲司马睿报仇,而要捏着鼻子给明明对王敦事件负有严重责任的王导加官晋爵;经历王敦之变后惊险保住禄位的王导,非但不敢给先打开城门放王敦进入首都、后起兵造反兵败身亡的江东豪族周札,反倒要给他平反昭雪、追授官职,以免激怒了人人自危的江南各世家。
更要命的是,如此烂透了的“大局”,还要受“小局”的干扰,这个“小局”,就是各级领导人的私心。因为“小局”,原本仰人鼻息、靠王氏吃饭的司马睿,即位后变着花样地试图从王氏兄弟手中收回扬州地盘;也因为“小局”,王敦要设计从陶侃手里硬抢下江州,交给和自己同族、为人傲慢不恭的王廙,而丢掉江州的陶侃又照猫画虎,连蒙带拐地抢下了广州地盘。王导明知刘胤不胜任,却硬要任命他任职江州,究其原因,也是对占据上游形胜、和自己家族曾有过节的陶侃心存顾忌,想在陶侃和自己势力范围间弄出个缓冲地带来。
整个东晋朝廷并非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一级级“空降”形成,“遵养时贼”也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摘编自新浪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