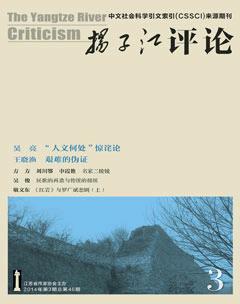民歌的再造与传统的接续
——关于当代中国文学资源的合法性问题刍议
2014-07-22吴俊
吴俊
民歌的再造与传统的接续
——关于当代中国文学资源的合法性问题刍议
吴俊
主持人的话:
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设计特征,产生了许多规定性的标准。其中既有政治上的是非,也有艺术方面的高低,但前者的重要性显然高于后者。标准之下的是非高低,其实也就是一种等级,即价值地位。长期以来,题材就有此区分,至今仍有重大与否之分,还有革命与否的不同待遇。概而论之,制度设计下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资源本身就是有是非和等级之分的。所以为什么是民歌会形成运动?为什么是现代戏剧能改造成革命样板戏?为什么如此设计文学奖项的评选?这些都有追根溯源的制度道理。有时制度也会考验人的常识,因为政治常常会和常识打架,一味死认常识会被视为政治上的不成熟。有时一桩公案已然成了谜案,后人再怎么翻腾也找不到谜底,无奈文字只能再次消失在历史的幽暗迷宫之中。但我们毕竟主要靠常识在生活,否则我们的生活就异化了;而抛弃生活的常识就很可能不再会是正常人了。这也是写作的人想要纠结真相的原因吧。
新中国的新民歌运动是当代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现象。以国家力量、国家权威进行社会动员甚至是全民动员的方式来展开的写作运动,最著名的莫过于新民歌运动和大批判运动,其他类似的还有各种“写史”(比如一度提倡大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及军史、校史等)运动。①比较而言,写史之类只是一种阶段性政治的写作运动,延续时间不算很长,范围也受限,而大批判运动(包括相关的大字报)主要源于当下明确的政治动机,有实际的政治目标指向,且并不以文学性为大批判的写作前提;作为一种写作运动,文学性最强烈、最鲜明的不能不首推新民歌运动。新民歌也由此才能够堂皇地进入后世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序列。那么,新民歌运动为什么能够获得国家权力的支配而成为一种大规模、较长期的文学写作运动呢?新民歌拥有何种特殊的文学价值地位呢?
1949年,共和国文学伊始就已运用国家权力构建新的文学秩序和国家文学制度②。可以说国家文学制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政治上的一个区别性的时代特征(历史特征)。其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规定就是毛泽东《讲话》的原则,工农兵方向、政治标准第一、以普及为基础等成为新文艺政治正确性的主要指标③。而最重要的操作性规定就是区分、明确各种文学资源的价值地位,即《讲话》所谓如何继承中外文学遗产的立场和方法问题,由此建构正确的新文艺系谱。——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在不断清除政治不正确的文学资源,并削弱直至剥夺其存在的合法性。
新中国文学的合法性资源主要限制在特定的政治范畴内:苏联的社会主义资源、有所选择的“五四”资源(特别是重新阐释的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传统)、中国古代的传统遗产(即民族文化中的精华/糟粕关系里的精华)、西方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如所谓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之类),最重要的则当然是解放区文艺④。
共和国文学的正统来源主要是解放区文艺。解放区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周扬的文代会报告标题即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也就是所谓工农兵文艺的另一种表述,当时的范例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⑤。
解放区文艺的大宗是由民歌为代表的民间文艺。在政治划分上,所谓劳动人民创造的民歌即为传统遗产中的精华所在。文艺遗产的合法资源主要就包括民歌及广义的民间文艺。民歌的“阶级”出生和身份获得新国家意识形态观念的保护与推崇,其政治地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更高于传统的古典文学。一般古典文学的封建主义烙印往往会被特意指出而加以批判。相关的显例就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收录的诗歌作品,几乎都是民歌(体)——《王贵与李香香》(李季)、《赶车传》(田间)、《圈套》(阮章竞等)、《佃户林》(王希坚等)、《东方红》(诗选)、《赵巧儿》(李冰)、《漳河水》(阮章竞)。民歌体现、代表了优良的文学传统,并且具有现实性,集传统精华与现实政治功用于一身。而古典文学的命运就有点风雨飘渺,时有不测之危的风险。如郭沫若对于李白、杜甫的研究,就用了后世所谓的阶级性政治观念而进行了刻意褒贬。⑥
但问题随之产生:共和国文艺、工农兵文艺的政治将如何对待民歌里最大量的情诗情歌呢?如何处理合法性资源中所含的先天歧义,即那些糟粕的成分或嫌疑,不能不成为国家权力主导的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挑战,必须对此做出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回应。这与民歌的政治合法性认定及价值地位有直接关联。
本文通过一个案例——何其芳、张松如在延安合编过一部《陕北民歌选》,1950年因重印出版,何其芳再写了一篇代序,并以《论民歌》为题先行发表⑦——的分析,探讨当代文学如何通过民歌的改造,包括1950年代新民歌运动等,一方面完成接续文学传统的使命,另一方面建立主导性的文学资源的合法性身份和地位,最重要的是由此建立新中国文艺的唯一正确系谱。由此而言,对于文艺资源的价值地位的认定,实际上支配和决定了当代文学的面貌构建。这也可视为权力之手的文学史书写。
《论民歌》里要解决的一个实质问题,就是民歌/情歌对当下政治观念的一种严峻挑战,具体就是如何解释情歌之“情”(情、色、性)和掩藏在情歌背后的政治——生活审美,日常意识形态,无意识的政治等。社会主义文艺提出的是“新的民歌”概念,新旧两者区别的性质就是“情的质变”,即情的政治性归属。——按照《讲话》的思路,思想和立场决定了情感的(政治或阶级)性质。“情的质变”意味着封建主义的文学传统脱胎换骨质变到了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新民歌改造、取代、发展、超越中国的传统民歌,实际上就是一个再造全社会情感表达合法性的政治操控及文学方式的过程。何其芳所编的“民歌选”,连同后来周扬主持编选的新民歌集等⑧,可以视如行使当代采诗官的职责。借用近年的一个时髦的学术术语叫做规训。民歌的采诗官们其实就是在行使民歌-诗歌-文学的规训职责。1958年周扬发表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⑨,标题的宗旨就已然彰明显豁。当代文学的正确道路就是新民歌代表的道路。经由民歌再造的新民歌,既以“精华”传承的方式完成了优秀传统的接续,更是以新的政治身份(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艺)获得并标志了当代文学的崇高合法性地位。这是其他文艺形式很难比肩的一个特例。
《论民歌》开篇即谈古代统治者总以端正风化风俗之名对民间歌唱艺术进行各种压制。从阶级论的立场讨论民歌的价值地位,但凡说到民歌的缺陷、不足或问题,后来总不外强调两点,一是受到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是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受到“历史局限性”影响。以此说明民歌的阶级属性和历史地位,并作为评价民歌的基本出发点。因此,《论民歌》主张对民间艺术要有阶级分析:民间艺术多杂有封建意识毒素,但也表达了底层人民的生活情感;而且相比较而言,民歌则更具有劳动者的思想情感特点。然后,文章便从题材内容思想主题等方面分析肯定民歌价值;还专门提到妇女题材(女性痛苦、婚姻、家庭、感情等)民歌的重要地位及独特性。接着就必须谈及民歌中最大量的“情歌”了。
谈情歌向来是研究、评价民歌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者就已开此先例。⑩同样,如何对待情色、色情乃至下流恶俗的民歌?也总是一种挑战和两难。新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新中国文艺在评价旧文化、旧传统和历史遗产时,往往陷于两难:既不能完全否定历代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又必须合理解释其中与新意识形态相抵触和冲突的内容;完全的政治正确实为理论乌托邦,却不能不是新意识形态必须坚持或信奉的理论/政治出发点。因此,阶级分析的方法,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就成为百战不殆、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论民歌》的主旨和方法即不能脱此窠臼。
文章指出唱民歌的动机是解疲乏、去愁闷、谈恋爱;既分析民歌情歌中的消极因素,但更多肯定其积极面。对于先天正确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民歌,作者当然主要须持正面评价的立场。立场问题也是历史评价和政治正确的首要问题。这正是《讲话》所强调的精髓所在。⑪因此,文章的核心观点概括而言便是,民歌主要为农民的诗歌,主要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及其反抗;但长久的封建统治也使民歌打上了封建主义的烙印。这是中国民间文学的共同特点。从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新中国才产生出了“新的民歌”。民歌从控诉、反抗发展成为革命战歌和新生活的颂歌。革命也就成为新民歌中情歌的内容主题。——在这一强大的分析逻辑中,民歌/情歌的缺陷由封建主义承担,民歌/情歌的成就是劳动人民的功绩,民歌/情歌的出路则在新中国的“新民歌”。民歌发展的这一历史逻辑也同样昭示了,情歌之情已然发生了性质的改变:不仅否定了情色和色情,也批判了非阶级性的个人情和一般人情,只有政治情、阶级情、革命情才是情歌尤其是新民歌中应该提倡、也是唯一正确的情感内容。⑫这已经从理论上直接开启了1950年代“大跃进”新民歌运动的先声,为民歌的革命性再造奠定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古代情歌里虽然不会有后来所谓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但这并不妨碍民歌/情歌在阶级理论中依然获得了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并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可以也需要借鉴的一种历史资源。既然民歌具有了这样一个现实政治定位,那么很必然的,古代的反动统治者想必也肯定是要压制民歌的——这种必然性无疑就是由阶级性所决定了的,而压制的名义往往用了所谓道德风化的理由。道德风化掩盖的则是阶级立场的对立。如果透过表象看实质,道德云云只是表面的理由,实质是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一种文化压制,正通过民歌的历史遭遇而表现了出来。
从对于正统思想的批判角度来看,何其芳所说的统治者对于民歌的压制,应该有其普遍性。事实上情歌往往成为历代禁而不止的“淫声”。不仅统治者本身会沉迷其中,而且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吧。⑬不过,后世的阶级理论好像难以完全解释古代“采诗之官”对于民歌的作用,而且在具体的历史评价上也会陷入某种不自觉的矛盾纠结中,⑭甚至还会因当下的政治功利需要而不惜刻意曲解历史。正可谓立场决定理论,立场决定知识和理论的运用,立场决定价值和是非的判断。更困难的是,必须按照现实政治来处理、解决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遗产中的糟粕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论困难性,有点类似在左翼政治框架内如何处理、评价鲁迅与左联政党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只能借助政治正确的权威力量来克服、跨越理论的阐释障碍。如果政治的边界太过明确,越雷池又太过危险,理论就失去了自由的空间和弹性。最后的解决方案只能是“瞒和骗”地走向乌托邦。
情歌不能言情,情歌就消亡了;情歌被驱逐了,民歌又焉能成立。因此,新的社会主义文艺提出了“新的民歌”概念。新的民歌里也有情歌,新情歌的内容主题则变成革命了。——民歌再造和传统接续,实质便是新旧民歌的更替和新旧传统的置换。新民歌、新情歌与传统民歌、情歌实际上已经成为分道扬镳的两种类型了——两者区别的性质就是前述所谓“情的质变”。
共和国文学运用国家权力构建文学言情、抒情的新形式。言情、抒情的性质和主题必须是革命,革命也就成为文学人情的合法性保证。革命情获得了唯一性的文学地位。与革命情地位确立的同时,非革命(更不要说反革命)之情逐渐被剥夺了文学表达的资格和权利,也逐渐被剔出、驱逐出了文学表达的基本领域。从革命情的逻辑来看,非革命之情的主体及实质就是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和非共产主义的思想感情;或者也可以说就是与阶级观念相对的各种抽象化、多样化、体现多元价值取向的个人情或曰个人主义,个人情或个人主义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意识范畴,与革命情的政治意识及表达方式格格不入,严重的、极端的个人情和个人主义甚至就走向了反革命。⑮因此,文学情的表达有其内在的必然的政治逻辑性。
当代国家权力对于文学(生产)的直接操控,不仅深刻影响了文学的基本观念和表现形式,而且广泛涉及到文学的日常存在、制作与传播过程及社会评价等所有重要方面。一方面文学能够将国家权力的操控内容及目标具体落实在日常阅读、日常审美之中,将国家意志落实、内化为全民社会意志。这很有点文学“移情”的效用。由此,特定的文学教化就渐成全民的意识形态。——从国家政治角度看,共和国文学具有着全社会动员的功能和力量。这也是我将当代中国文学视为国家文学的一种重要的相关因素。另一方面,政治合法性以外的“文学走私”不仅是对文学政治性的伤害,更要紧的是会伤及权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认识,无形中动摇权力意识形态的地位。因此需要经常性展开文艺批判和思想批判运动,在全社会范围内清洁、打击非革命的乃至反动的文学。主张并信赖用政治理性的阀门来增强文学发展的可控性,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情感)控制的任务总须交由政治手段实施的思想控制来担当。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国家文学特性也是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载道教化的历史传统,但具体的运用手法和实施途径则迥然异趣。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1950年代流行至今的名言⑯,对指导利用中外古今的文化遗产资源仍具理论影响力。历来对此的解释,一般都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列哲学立场及所谓批判继承的方法论上论证其学术正确性,而非单纯强调其政治正确性。但在具体实践中,更为显著的源于现实政治功利主义的非学术性倾向,或是尤其需要警惕并特别予以质疑的。因为这一方面有可能使传统成为一种暧昧的乃至似是而非的存在,另一方面,本土传统和域外资源一旦遭遇一元论、一体化的国家意识形态时,如何实现价值有效转换的问题至今仍没解决。其实这不仅是关涉当代中国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在学术层面也难以理论实践的难题。⑰由此最可见出中国国情中传统接续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所在。也即历史资源在当代的合法性认定,本身含有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双重困难。传统当然是一种资源,但也是一种负担,甚至,更像是一种现实遭遇的困难挑战。
本文的宗旨既在通过民歌的再造理论讨论传统接续的现实形态、方式及特征,更在彰显中国当代文学处理传统资源时所面对的挑战、困境及经验。我们现在面对的只能是一种历史的现实,如果对于既往历史一味秉持批判的姿态,实际无从解决真实的问题,而且无形中也就陷入了批判对象的思维逻辑中了。正视历史的积极效果在于使我们能够更易获得历史的经验。对于正经历着时代大转型的当今中国社会而言,许多情境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有根深蒂固的东西依然不变,而且似乎也不会改变。比如,从宏观政治的角度看,国家文学的基本制度特征及其保障,至今并无改变的迹象。只是文学多样性、多元化取向的实际合法性已经基本建立,全社会的多元文化空间和意识形态表达已经成为基本共识,这使得各种权利的博弈可能性变得更加公开和重要了,而结果也不再一成不变。这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公共社会的一种成长。因此,在文学资源问题上,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拥有了博弈的可能,那么更需要建立的是妥协性地对话而非极端性地对抗的策略,由此获得特定文学资源的实际合法性,并促使形成一种社会性的觉悟和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技术手段有时是必须的甚而是更重要的。
以一个最近的相关例子结尾: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归来》,涉及“文革”题材。从政治角度来说,“文革”早已被国家权力所全面否定,⑱但政治的诡异却在于,被否定了的“文革”实际上又渐渐成为一种禁忌,特别是文艺表现题材上的一种禁忌。就是如此敏感的禁忌题材,张艺谋却终于能够成功通过审查而获得公映。虽然他为此遭遇诟病,许多人至少对他的“文革”处理方式评价不一,甚而指其将“文革”的残酷血腥处理成了廉价平庸的情感戏,置换了重要的主题,而且也没有体现出新的电影思考。但从中国电影的当下可能性来说,《归来》告诉并鼓励了我们,今天的电影还是能够触碰并表达“文革”题材及对于“文革”的思考。就是因为种种相关的努力,才使得“文革”终于没有完全成为博物馆里几乎淹没和遗忘的陈列物,而且成为时时激活我们的记忆也显示其自身存在的一种现实的历史。这在客观上便含有建立并拓展文学(电影)资源合法性的博弈策略,而导演的实际目的如何对此已不是太重要了。
中国当代的文学资源确乎存在着合法性与否的现实问题,明白了“文革”的题材位置和处置方式,也就能够多少理解有关民歌的价值地位了。虽然两者从国家文学的立场看起来,可利用的价值效果并不一致,这也就有了不一样甚至相反的处理方式和实际命运。中国当代文艺就处在如此构成的资源生态中,当然因此也影响到了文艺的整体性面貌。
【注释】
①在1960年代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过全国规模的所谓“四史”运动,即大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四史运动直接源于最高领袖毛泽东1963年5月10日的批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一说“四史”运动实肇始于1958年“大跃进”中文学界首倡兴起的编写工厂史、公社史运动;亦有“三史”(家史、村史、社史)、“五史”(厂史、街史、社史、村史、家史;或指村史、社史、厂史、老工人和老贫下中农家史)之谓。因毛泽东的批示,“四史”之名影响最广。直到1980年代(1985)还有过全国性的写史活动。参见赵庆云《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⑵国家文学是作者近年来从政治角度宏观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特征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受制于国家制度权力支配的文学。参见《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吴俊、郭战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及近年发表的一系列相关文章,部分也收录于作者的论文集《向着无穷之远》(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
③1940年代中后期开始正式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1951年出版《毛选》第一卷。在《毛选》的编辑过程中,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的毛泽东著作均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讲话》的修改尤显突出和重要——《讲话》的政治地位由此最终获得理论的确立而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最高经典。肖进的《从〈毛选〉编辑到文艺整风》(手稿,即将发表)一文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④参见1949年7月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原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
⑤该丛书选编出版了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优秀作品,代表了“新中国文艺前途”,1949、1950年分批出版。其编辑方针标榜“这是解放区近年来文艺作品的选集”,“这是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结果”。丛书篇目原载《文艺报》1949年9月第1卷第1期、1950年8月第2卷第10期。
⑥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作家出版社1971年)运用阶级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人物,褒贬鲜明地进行了“扬李抑杜”,指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的诗和文。”而对李白则作了高度的评价。李杜的古典地位在郭沫若看来就有了悬殊的差别。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显然也将民歌置于古典之上。
⑦《陕北民歌选》,晋察冀新华书店1945年第1版;何其芳《论民歌》发表于《人民文学》1950年11月第3卷第1期,同载《陕北民歌选》,海燕书店1951年版。
⑧最著名的当属1959年红旗杂志社出版的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
⑨周扬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该文发表于《红旗》杂志创刊号。
⑩标志性的就是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1918年2月由北京大学发起歌谣征集活动,同年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1920年成立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北大创刊《歌谣》周刊,周作人、常惠主编,沈兼士撰写《歌谣周刊缘起》,沈尹默题写刊名。后来何其芳在编订陕北民歌及撰写序言(即《论民歌》)时,也曾查阅过北大歌谣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歌谣》周刊,并论及了情歌。
⑪关于《讲话》的权威阐释,参见周扬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要求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而共产党员作家,就更‘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些要求是无条件地必须遵从的。”更早时期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周扬编纂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1944年),并撰写了该书序言,由此开始奠定了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阐释权威地位。
⑫参见《情为何物情何以堪——共和国文学之初的情感政治》(吴俊,《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该文探讨文学情感的表达内容和方式,其中论及何其芳的《论民歌》,本文即脱胎于该文的这一部分,主题则在讨论民歌的价值地位。国家文学的政治规定性对新中国文艺的生长都有着共同的统摄作用。
⑬古以雅乐为正声,以俗乐为淫声。据说孔子就有“恶郑声”,“郑多淫声”之语。《周礼·春官·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阮籍《乐论》:“夫正乐者,所以屏淫声也,故乐废则淫声作。”朱熹《诗集传》称《诗经·郑风》“郑风淫”,将《郑风》中的15首定为淫诗,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乃淫诗之最。鲁迅《故事新编·采薇》:“(殷纣)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淫声既为俗乐,其中更多男女情歌也。
⑭从阶级理论看,采诗官当属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有着压迫劳动人民的阶级属性。从古代文化遗产的保存来看,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又因采诗官而得以保存流传。采诗官因有压迫和保护的双重性,使得教条主义对此往往陷于两难,而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则以公允之貌自设一不败立场,实则理论上难免暧昧,立论更难脱功利的动机。
⑮共和国文学早期的诸多文学批评和批判活动中,此类案例甚多。参见吴俊《情为何物情何以堪——共和国文学之初的情感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其实在新时期文学中仍不乏同类现象,诸如“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之类的诘问,常常就像是句暗示性的政治咒语,充满了威胁性。
⑯因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中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语,遂成最高原则。后世论及毛泽东思想在文化上的建树功绩,多引证此说。⑰如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就有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说,他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1980年代在大陆出版后,多次再版,2011年三联书店又出了增订本。
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其第五部分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本文获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科研项目资助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