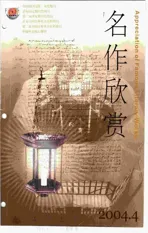姚奠中先生的学术与人生
2014-07-12山西刘毓庆
山西 刘毓庆
作 者:刘毓庆,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国学讲堂的新老朋友们,我们今天又见面了。因种种原因,我好长时间没登这个讲堂了。说实在,还有点想念大家。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姚奠中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姚奠中先生是我们身边一位备受大家敬仰的前辈学者。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姚先生是一个谜,因为用现代人的评价标准,无法准确地评价他。现代人评价一个学者,往往要看他有多少著述,有多少经费的项目,获得过什么大奖,是否入了什么人才计划,有什么学术贡献,等等。但让人不解的是,现在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以著作等身而著称的学者,能够获得像姚先生这样广泛社会声誉的。有的学者确实成果不少,成绩不小,但出了学术圈子便没有人知道了。而姚先生在圈内圈外都有很高的声誉,这该如何解释呢?你能用著作、项目、获奖、头衔来衡量吗?不能!姚先生不专注于著述,但是有一百七十多万字的著作摆在那里;他不是搞绘画专业的,也不是搞书法专业的,不过是游艺而已,结果却获得了中国书法的最高成就奖;他不是搞篆刻的,但是篆刻界的人却感到,他的篆刻是极品,而且有人评价,近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他不是诗人,但是,他写了几百首诗歌,可以称得上是诗史,有一些广泛流传。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社会效应?他合乎现在评价标准的哪一条?既然不合,为什么会得到普遍认可?
许多人什么都想争,最后争到了这个,却失去了那个。而姚先生呢,一生什么都不争,但最后他得到的却要比别人多得多,这是为什么?
姚先生百岁了,百岁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梦想,意味着羡慕。但对一般人来说,“百岁难,难于上青天”。而姚先生却可以说:“百岁易,易于履平地。”姚先生不但年寿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高峰,同时学术地位、社会声望,也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成就姚先生百岁鸿儒绝高地位的灵丹妙药是什么?是他的学问,是他的艺术,是他坦荡的人生。
学术是怎么成就姚先生的人生的呢?可能对我们当代人来说,这是一个难题,很难解答。因为我们现在把学术与人生已经剥离开了,不知道二者之间应该有联系。但姚先生是融为一体的。剥离开的结果是什么呢?顾了做学问,忘记了做人。如在当下社会,适当考虑经济收入,无可厚非,但如果只为赚钱而去研究学问、艺术,那就不是学者,而成了商人。
学问、艺术,携带着一种生命活力,留在自己身上,就会成就自己,作为一种营养,一种补品,可以使自己身心健康,获得长寿。犹如把五谷菜肴吃到肚里,变成能量运于全身一样。但你如果要拿它去赚钱,那么得到的是钱,丢掉的可能是生命活力。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人做学问做得很苦,学问做大了,钱也赚多了,名利也有了,但人品没了,命也没了。姚先生百岁华诞时,冯其庸先生画了一幅梅花,上面题诗道:“雄才博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一人! 我敬寿翁千盏酒,梅花愈老愈精神。”最近霍松林先生为姚先生写的千字文长卷写了序言,说:“姚老奠中先生雄才博学,其人品学问书艺均为当代典范。”确实是这样,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你去捋一下,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想找一个专家并不难,但像姚先生这样学问、诗、书、画、印全面的却是很难找到的。因为专家是搞生产的,如果专家不把学术与人生修养联系起来,一味把学术外化,拿它去换名利,他的人生境界永远不会高,想获得社会声誉自然就很难了。今天我讲姚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就是希望说明学术与人生的实在联系,从姚先生身上获得的启示。
守护中国学术的正脉
我们先谈姚先生的学术。
著名学者吴相洲先生评价姚先生说:姚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我非常赞成他的这个评价,当代能够守护学术正脉的人太少了,这个正脉是什么?就是中华学术传统。姚先生是如何守护这个传统的呢?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秉持“内圣外王”的治学理念。
所谓“内圣外王”,就是“修己治人”。“内圣”是修己,提升自己;“外王”是治人,是要用于世。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治学理念,但我们现在把这种传统丢掉了。比如说,我们大学生上学,要干什么,多数人首先考虑的是哪个专业好分配,哪个专业赚钱多,有几个人考虑过提升自己素养的问题呢?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教育。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失落了。而姚先生在坚持着。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就是提升自己。我学不是为别人学,而是为了提升我的境界,开阔我的眼界,充实我的知识,开启我的智慧,把学问变成一种眼光和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用它来处理周围的事务。“为人”是要拿着学问向别人炫耀,卖弄,获取名利,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姚先生坚持的则是“为己”的方向。他给学生立的教条,其中第一条就是“以正己为本”。一个学者,如果把正己放在首位,他所考虑的问题一定会脱离低级趣味。而现在的大学校园里,我们的学者考虑的是著述,是论文,是职称,是津贴。古人读一本书,要反复读,为什么?“以心会道”,用心去理解“道”,去领会其中的精神,所以叫“学而时习之”啊!但在现在的社会里,不用说“学而时习之”了,有几个人能把一本书读三遍呢(当然自己的研究对象要除外)?可能一般书一遍都读不了,因为只是要在里面获取信息,要搞生产,要快出成果,多出成果。清朝有位叫李容的人,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著述一事,大抵古圣贤不得已而后作,非以立名也。”又批评他的朋友说:“比见足下以其所著诸书,辄出以示人,人之服我者固多,而议我者亦复不少。其服我者,不过服我之闻见精博,能汇集而成书也。其议我者,直谓我躬行未懋,舍本趋末,欲速立名,适滋多事也。”意思是说他专事著述,拿著作向人炫耀,是一条舍本逐末的路。当前的学术界就是这样的,学者们以著述为能事,学校及科研单位考核,成果档次和多少,就是一项评价指标。不是所有的论文都算数,还指定要在CSSCI刊物上发表的才行。因为全国高校排名,这是一项评价指标。具体到老师个人,一般是三年大考核,决定是不是继续聘任你,或者是延聘、低聘和解聘。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多数研究者都变成了生产文章的机器。新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如电脑,我们很多材料都不需要翻书了,电脑就可以解决,输入一个关键词,就可以搜索出好多东西来。电脑是我们很好的工具,但电脑同时把我们变成了工具,因为坐到电脑前,我们修身读书的那种理念几乎没有了,唯一的目的就是生产文章。现在学术界出现了种种怪象,有的人焦虑:因为国家、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项目、成果、人才等考核指标,你要上职称,要进入什么人才工程,都要拥有国家、省级项目,所以大家都争着申报项目。有了项目,国家、省里就给你钱,那么你研究的方向就必须在许可的范围内选择,而且你三年或两年必须出成果。也就是说,我把钱给了你,给你职位,给你特聘,你就得给我生产。生产不出来怎么办?那就会焦虑、不安,压力太大,承受不起,长期失眠,甚至自杀。有的人抑郁: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总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有的人功利:出现了商人化的学者,做报告要出场费,少了多少钱我不出场。有的人人格分裂:学术水平上升了,人格下滑了,或剽窃,或欺诈,或利用学术地位索取贿赂。姚先生桌子上长期放着《庄子》《老子》,你问他什么,他能随口给你背出来。他能反复地去读这些东西,我们能吗?不能。我们在读《老子》的时候,只想着在里面找问题,找论文的题目,怎么能领会它的精神呢!
所以要坚持走读书“以正己为本”的路,得有定力才行。姚先生完全超越了世俗的追求,他把学问变成了人生修养的一门课程,变成了观察、认识现实的一种眼光和智慧。比如,他已是百岁高龄的老人了,读书看报一样也少不了。往常他的生活,主旋律就是读书写字、思考问题。读书累了怎么办?累了就写写字,或是篆刻呀绘画呀。他干这些首先是兴趣所在,同时从中领悟人生,培养自己健全的人格,进身于更高的人生境界。因而他的书法、绘画中,渗透着他的学问、智慧和人生。我从来没见过他打牌,抽烟喝酒更没有,也很少跟朋友一起热闹,也从没见过他在别人面前夸夸其谈过,但讨论问题则是常有的。他把学术当作了修身的阶梯,当作了提升自己的手段。
正己、修身,这追述的是“内圣”,而“外王”则是要“用世”,要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所以姚先生在给学生的教条中,有“以用世为归”一条。这里体现出的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从根子上说,章太炎先生推崇的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就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的学术是以“明道”“救世”为目的的。这是怎样的一种胸怀、一种境界呀!章太炎先生本名炳麟,字枚叔,之所以要叫太炎,就是出于对顾炎武先生崇敬的缘故。他说:“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这是说上天把承传文化的使命交给了自己,如果在自己手里中断了,这就是自己的罪过。不难看出太炎先生那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来。而姚先生则给我们说:在现在的大学分科里,历史系讲授的是世界史、中国史,把历史分成两半;哲学系主要讲授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变成了附庸。唯有中文系是以“中”字打头的,因此承传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落在了中文系的头上。这个话的力量很重呀!他是要我们肩负起承传文化的担子来的。从顾炎武到姚先生,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种一脉相传的精神,一种摧不垮、打不倒的文化承传使命。这种使命,姚先生始终坚持着,坚守着,从而影响了他的学术价值取向。他是在这种理念之下做学问的,因而在他早期的论文中,便频繁提到“民族之精神”“固有文化”的问题,频繁提到中国学术特色的问题。这从他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发表的一些言论中都可以体现出来。
第二,坚守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
“学以正己”“学以用世”,这是治学的精神,而坚守传统学术的路径,则是一个治学方法问题。姚先生在这方面,有两点特别值得学习。
一是“坚持文史融通,反对学科分割过细”。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很不相同。传统学术观念是文史哲不分。现在有些学者主张文史哲合一,以为这样就是国学了。其实文史哲“不分”不等于“合”,分开再合起来,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性质了,因为分的概念已形成了。现在大学里主要的倾向是“分”,学科越分越细。到目前为止,“国学”在大学校园里落不了户口,还属于“私生子”,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符合现行的学科分科规则。许多人认为,如果国学要作为一个学科,那么二级学科怎么分?一分,不又是文史哲了吗?那设立“国学”学科还有什么意义?这是在用西方人的观念来对待中国传统学术。现在学科划割分界,使原本相互联系的东西,变得互不搭界了。互不搭界是小事,最可怕的是画地为牢,封建诸侯。这种情况层次越高越明显。比如看到一个陌生的作者发表了一篇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文章,人们就要问,这是不是我们圈子里的人?其实这是一种最没出息的表现,画圈就是画地为牢,认为自己的领地,别人不能侵犯,但同时也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有一年,在临汾开尧文化的研讨会,我写了一篇关于考古年代与历史年代对接的文章。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他对前面的发言都一一赞扬,轮到我发言,他却变了一个人似的。主要是他觉得我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竟然闯到了他们的领地,他觉得不舒服。中午吃饭时,他跟我坐到一个饭桌上,便开始教训我了。他说:“你以为先秦史是好搞的?你必须懂文字学,必须懂音韵学,必须懂训诂学,必须懂历史地理学,必须懂考古学……”一口气说了若干个“学”,最后又反问了一句:“你以为先秦史是好搞的?”我只能说“您说得对”,还能说什么呢!他自认为先秦史就是他的领地,不允许侵犯。这也反映了目前学术界的一种现象。后来我把那篇文章发表在《晋阳学刊》上,不多久,我们学校历史系的一位青年老师告诉我,他的导师北京大学的赵世瑜教授把我在《晋阳学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在他的博客上向学术界推荐。这说明历史圈子内还是有学者能接受我的。再比如在晋东南高平召开的一次炎帝研讨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我旁边坐着的两位先生,拿着我的文章说:“这是会议上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结果后来总结会议的人,对我的东西不予理睬。过了几年,我的书出来了,有人才给我写信说,当时在会上,就看到了我的文章,觉得写得很好,后来打听到我是搞文学研究的,于是就没跟我联系。这就是画地为界。有些人在自己地界上夜郎自大,觉得自己是大腕。社会上也有不少人,把“专家”当作了“大家”。我们现在打听一个学者,就必须问他是搞什么的,好像只有能说出是搞什么的来,才叫有学问;说不出来,就什么也不是了。
但姚先生你说他是搞什么的?你看他的著作,历史、哲学、文学、小学等都有。他是文史哲融通的,他非常反对学科越划越细的作风。所以在指导我们时,就要求我们从小学入手,由小学入经学、文史,最后回归于诸子。要走他这条路是很艰难的,因为这要有很大的知识储备。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打造一根针,这是很容易的,有一点铁就够了,但要打造一个锤子,需要多少铁呢?显然几百根针的铁也打造不了一个锤子。而且针能扎得很深,锤子却不行,没有深度。这在一般人看来,就是锤子不如针了。正是由于针“投入少,产出多”,所以学术界人们都争着去做“针”,在自己专业那一亩三分地上,做上几年,就成专家了,立起一面旗帜,建立一个高地,自己便称起老大来。但要知道,锤子砸下去,那震撼力,是一千根一万根针也做不到的,你那根针才有多大震撼力呀!现在我们大学校园里培养人才,多是在制造针,而不是制造锤子。比如全国许多学校都在成立国学院,国学院的人多是从文史哲各科抽出来,拼合在一起的。合了怎么办?搞历史的仍然搞历史,搞哲学的仍然搞哲学,搞文学的仍然搞文学。各搞各的,跟原来并没有多大差别。有的学者除了搞自己的专业外,有了兴趣再搞一点别的,就夸夸其谈,认为自己搞的面太广了,了不得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大多数学者国学基础没打好,给了这些人夸夸其谈的资本。没有锤子,针便可以炫耀自己分量重了。北京有位朋友给我说:“姚先生不是搞历史的,可没想到他写的《通鉴校补》的序言,还有《曾国藩家书全译》的序言,话说得那么到位!”其实这就是文史哲融通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要文而得文,要史而得史。比如说一个锤子的铁,你要造针吗,拿出一小块来就可以造很多针;要造茶杯吗,再拿出一小块来,就可造好几个茶杯;再拿出一块来,还可以打造一个茶壶,等等。但你要只是一根针的话,那只能是针,再打造什么都不成了,就是这道理。
再一点是“坚持秉要执本,反对以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百年来,中国人从社会大众到学术界,都做着一件蠢事,就是以西方人的概念规范中国人的行为。在学术界最先是胡适、冯友兰,他们把西方的概念拿来,大谈方法论、本体论、宇宙论等,把中国哲学中的精神给撕裂了。许多人只感到这样的观点很新,却不考虑这样做问题抓得准不准,是否抓住了要害。而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表文章谈这个问题。姚先生说:像他们这样做学问,把中国的学术按西方概念来划分,把要害的东西都丢掉了(当然这不影响姚先生对冯友兰先生的肯定,他曾说,20世纪只有冯先生能称得上是一位哲学家)。其实他们所说的方法论、本体论、宇宙论都可以在中国学术中找到,在诸子里面都有,但它是不是中国学术的本质呢?不是!比如先秦诸子,姚先生只用了四个字概括:“修己治人”。很简单,就这四个字非常得要领,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而胡适、冯友兰等所归纳出的方法论、本体论之类的东西,其实都是中国哲学的皮毛。我们再返回来看看诸子谈什么,如孔子谈的不就是做人,老子谈的不就是做事吗?这不很简单吗!再看看我们现在研究宋明理学的文章、著作有多少,实在太多了!但是宋明理学究竟是要干啥呢?你问他,他问你,很少有人作回答。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修复世道人心。你把这个东西给丢掉了,而谈什么本体呀、宇宙呀,还有多少用处呢?目前就是这样,整个中国学术走的就是这条路。这不是在研究中国学术,而是在肢解中国学术,迎合西方理论。从文学到史学到哲学,都是这样。
今天我们谈姚先生的学术,就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来考虑问题。要考虑怎样才能把各种文化最精髓的东西提取出来,为人类未来发展服务。中国传统学术是在不断汲取新的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人类积累了五千年的智慧之果,这种文化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气概,它面对的是全天下,而不是某个个人、民族和国家,追求的是万世太平,而不是眼下的利益。这种文化蕴含的智慧和价值体系,只有通过中国传统学术的路径才能发现、提取,如果用西方的一套观念和概念来分析它、归纳它,这种文化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同时,也只有打破文化本位主义,才能对这种文化作出正确的认识、分析和取舍。
第三,践履“回真向俗”的学术思想。
这是一种理念,一种学术选择,也涉及了研究对象的问题。我们前面讲了姚先生“以用世为归”的思想,怎么用世?用世自然要面对社会,要思考现实中的难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现在高校中一些学者,热衷于研究高深的学术,似乎自己研究的问题懂的人越少,就表示自己的水平越高,人们关注越多的问题,反而被认为是最普及的,缺少学术含量。如果研究的问题只有三个人知道,你即使排名老三,也可以自夸是世界前三位。这样许多研究变成了少数人的高级娱乐活动,只要学术圈子里有几个人说好,自己便洋洋得意起来。但你的社会角色是什么?你对社会承担着什么义务?你研究的东西对社会有多少意义?这些问题便不去考虑了。至于说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则是一片茫然,社会责任感几乎完全失去了。这也是西方学术带来的问题,只考虑到要“求真”,却失去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失去了“求善”“求美”的责任,以致文史研究的意义频繁遭到学生与业外人士的质疑。姚先生则不然,他不以解决学术难题为高,而以解决普及性中存在的问题为要。他觉得自己是教书的,首先研究的应该是与教学相关的问题,应该是大众在知识上遇到的难题或误解。用他的话来说,越是普及性的东西,越需要大学者去研究。为什么?因为普及性读物面对的是社会大众,一点小错误就会误一大片人;而高深的学问,错上一个问题,只会影响圈里的几个人。因此普及性问题比高深学术更有必要投入力量去解决。我们再看姚先生的文集,他面对最多的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问题。他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讲习文集”,就表示集中所谈多为讲习中遇到的问题。姚先生的文章适合两种人看。第一种是一般的民众,因为他的文章能把复杂的问题用三言两语说清,便于把握。以往不明白的现在一看便明白了,接受了,所以说好。第二种是有一定研究深度的学者,因为他能把握住问题的要害,别人思考了好长时间,用了好长的文章觉得还是说不清楚的问题,他却能用几个字精辟地概括出来,因此觉得妙。至于自认为不含糊而实际只是半瓶子醋的人,是万万读不得的。我曾在饭桌上遇见过一个做资料员的人,明明知道我是姚先生的学生,却在我面前反复说姚先生的文章写得没有水平,没引了几条资料,等等。因为他不懂,他不明白姚先生虽没有旁征博引,但每一句话的后面都有一大堆资料作支撑。他认为引资料多才叫有学问,却不知道资料是为观点服务的,是为了说明观点才出现的。我们在集会的场合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有学问、有水平的人是听人说,没有水平、没有学问的人却夸夸其谈,旁若无人,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
我们再看看姚先生是怎么解决问题的。举个例子,比如说,王昌龄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这首诗大家都知道,看来很简单,大家似乎都读懂了。但问题出来了,作者是在哪个方位看黄河呢?是往上看,还是往下看呢?往上游看,黄河是“来”;往下游看,黄河是“去”,怎么能上呢?是不是问题?还有,作者是站在什么地方看黄河呢?玉门关吗?玉门关离黄河一两千里地,你能看见吗?看不见,这就是问题。姚先生根据《乐府诗集》的版本,认为这首诗不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而是“黄沙直上白云间”。我们看“沙”字的草书与“河”字的草书,几乎难以区别,所以很容易相误。再说玉门关,那里是一片沙漠,突然起风,在死寂的旷野一股黄沙直起,冲向云端,那个荒凉的气氛一下子就突显出来了。王昌龄诗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里把玉门关与黄沙联系起来,可以作“黄沙直上”的旁证。很简单的问题,大家忽略了。
再如柳宗元的《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有人据此绘了《寒江钓雪图》,元、明以降很多人分析这首诗,都把重点放在了渔翁上,有人说渔翁是高士,有人说是隐士,后来还有人说是穷苦老百姓,认为这首诗的主题重在写渔翁。而姚先生抓的是什么?是诗的题目“江雪”二字。题目是“江雪”,说明它重在写雪,写寒冷的环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漫漫天地间看不到一个人影,自己就在那个寒冷的环境下生活,表现出了冷酷的环境对作者心灵造成的压力。诗的重点不是写渔翁,只是通过渔翁体现出了作者在严酷的环境中,坚持奋斗的精神。白居易的《长恨歌》,许多人认为是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如何如何的,姚先生抓的则是标题的“恨”字,恨什么?谁在恨?想一想,大难临头,唐明皇为了保全自己,让杨贵妃去送死,杨贵妃难道不恨吗?《长恨歌》里写杨贵妃没有死,她不愿意见唐明皇,因为她恨死他了。这样的问题在大学者看来太小了,不去思考,但却影响了对诗篇的准确理解。
再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这也是一首妇孺皆知的诗。但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人们并不甚清楚,故而也影响了对诗整体意义的理解和体悟。我们先看看别人怎么说。李汉超解释说:在一个寒雨的夜晚,诗人陪着即将分手的友人同舟进入吴地。这意思是,“入吴”的是诗人和他的朋友。社科院编的《唐诗选》也说:诗是写寒雨之夜,诗人陪客进入吴地。次日清晨客去后,只见一片楚山孤影而已。这里有三个疑问:王昌龄当时做江宁丞,芙蓉楼在镇江城西北,江宁和镇江都在吴地,怎能从吴地“入吴”呢?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诗清楚地表明送客的地点在“芙蓉楼”,怎能又把地点移到船上,而且竟送了一夜?第三个是,既然是送客“夜入吴”,为何又说是“平明送客”?这不相互矛盾吗?姚先生的特点就是善于在别人都认为没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许多人面对这首诗,都没看出问题来,姚先生看出来了,这就是水平。研究别人都在研究的东西,而且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让人信服,这就是水平。我们再来看姚先生的解释。他说这首诗中,“入吴”的不是人,而是“雨”。夜来寒雨,降落吴地,弥漫江上。“平明”是“送客”的时间,主语是诗人。“送客”地点在“芙蓉楼”。由于在楼上,因此举目遥望,就见到了雨霁后的楚山孤影,增人惆怅。这不很清楚了吗?如果依前人的解释,把时间和地点都搞乱了,只剩下“一片冰心在玉壶”最后两句可让人明白了。
我们再看孟尝君与冯谖的故事,这是所有文学史上都在写的一个故事,也是中学课本、大学课本都反复选的文章。一般人都认为这篇文章是写冯谖如何机智、如何有远见的,对于孟尝君则说他是如何地不理解冯谖,他收纳冯谖只是为了表现他贵公子的好客而已,等等。但姚先生不这么认为。他用“知遇之感”四个字来概括文章的主题,为什么是“知遇之感”呢?他抓住了文章中孟尝君的一句话:“客果有能也。”认为从冯谖提出非正常要求的那一刻起,孟尝君已意识到这个客人不同寻常了,所以后面才有“客果有能也”的赞美。大家想“客果有能也”是啥意思?说明冯谖有才能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了。冯谖三次弹铗而歌,是对孟尝君的试探,他不轻易拿出自己的本事。孟尝君是很有涵养、很有气量、很难得的贵族,而且能识人、能用贤。这样理解,全文便非常通畅了,但大多数人在阅读时都把这些忽略了。
这就是“回真向俗”的问题。“真”,是探索学术之真;“俗”,是面对社会大众说话,解决大众遇到的常见的问题。对社会大众来说,这看来很容易,但对学者来说,做起来很难。也就是说,一个学者,“转俗成真”容易,“回真向俗”很难,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生境界的问题和学术眼光的问题。从学术眼光来说,你能不能发现这些问题?能不能把知识变成智慧,变成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眼光?这是很难的。从人生境界来说,你愿不愿把这些通俗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这也是很难的。我们说圈子,姑且用“圈子”这个词,在圈子以外的人不能理解,好像这个很容易做到,但圈子以内的人都知道,因为你写这些东西,近于通俗,用现代学术的眼光看,不算真学术,高校科研考核系统中,也不给记工分。要摆脱现在这个学术评价体系,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社会需求来安排自己思考的方向,这需要有一种超越世俗名利的精神,为社会大局着想,为人类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精神的承传着想,才有可能去做。因此像姚先生“回真向俗”的学术思想,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他的胸襟、胆量和境界。
不忧不惧的人生境界
以上我们谈的是姚先生的学术。下面我们谈姚先生的人生。
正是前面谈到的这种学术路径和思想,成就了姚先生的人格,也成就了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很难概括,我想,是不是可以用“不忧不惧的人生境界”来提领?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又说:“仁者不忧”,“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什么不忧?因为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一般人之所以“忧”,是因为患得患失,把个人利益看得过重。“惧”呢?往往是因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惧”。“愠”呢?是因为自己觉得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利益而“愠”。实际上都是一个“私”字在作怪。只要摆脱名利的困扰,人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也就是“君子坦荡荡”的境界。关于姚先生的境界,在这里我想讲三点,即“开局以大”“用世以仁”“行事以道”。
第一点,“开局以大”。
所谓“开局以大”,主要是指姚先生的胸怀,指他的那种大格局、大气象。这是他广博的学识养就的一种大气象。他广阔的胸怀之中,没有私利存在的空间,他注视的不是眼下利益,而是从大局出发,看到事物的变化,处处以民族社会国家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有人给姚先生祝寿,以为先生之乐在抱孙子外孙、享受天伦之乐上,其实不是。他对那些东西看得很淡,当然自己的孙子嘛,能不亲吗?但他不是跟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陶醉在天伦之乐中,而是在不断学习中“乐以忘忧”。他每天的功课是读书、看报。读书是为了修己,提高自己;看报是为了了解世界、国家大事。一百岁的人啦,你跟他对话,感觉不到他的陈旧、落后、保守,而是与时代同步前进。他随时都在关注着国家和世界大事,关注着人类的命运。每一次当国家遇到灾难捐款时,他总是山西大学捐款最多的一位。他不考虑别人捐多少,他只考虑实际情况看自己能捐多少。周围的人遇到丧事,他年纪大了不能去,便托别人捎礼,往往也是上礼最多的,两千、三千、五千,都有。前几年,李星元老师把姚先生20世纪40年代写的两份契约的复印件给我看,我很震惊。那是民国时的事,他把老家的地产和房产送给了一户邻居,但他又怕自己的后人去找人家要回,所以就立了契约,说明已经是人家的了,永不索回。这是给,不是卖!这事以前我们都不知道,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提到过。直到前几年,这一家的后人看到这个契约,才拿来感谢姚先生。还有姚先生把自己价值上千万的字画捐给学校,把自己的稿费拿出来设立国学教育基金,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把钱留给儿孙,或给儿孙买房买车。这类问题他几乎不考虑。这种大胸怀,有几个人能比?有人说,“姚先生有钱,当然可以这样做,他的字在市场上卖得很贵”,等等。但是大家要知道,姚先生为多少人写了多少不收钱的字!同时,在人民公仆的人群中,在知识群体中,比姚先生钱多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又有几人肯拿出来捐给社会呢?
正是因为姚先生有这样的胸怀,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乐观的。比如解放后,他受极“左”路线迫害,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在反右中,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住牛棚,扫厕所,烧锅炉。一次次涨工资,他却从刚解放时的三级教授,被降至六级副教授!一些跟他有同样遭遇的人,有多少因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而内心纠结痛苦,甚至有人自杀,但是姚先生不是,他看到了这只是一个过程,不好的事情总会过去的。大家要知道,姚先生肚子里装着几千年的历史,类似的事情历史上有多少,结果会怎样,他都很清楚。所以他说历史上这种情况多着哩,我这算啥呀,还有比我冤的呢!而且从历史上看,这个过程不会长久。所以让他烧锅炉时,他研究如何用铁锹把煤撒开,既省煤又能把火烧得很旺,甚至感受到了其中的乐趣,他就是这样面对生活的。他曾经因为一位同学对国家前景失去信心写过一首词,其中有几句说:“革命前途海样宽,为何轻易便悲观。”“种田是要辨禾草,哪能草多不种田!”这很能体现他的胸怀。
有一种情况需要特别提一下。多少年来,包括“文革”期间,姚先生始终与国家、政府保持一致。有些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姚先生是有个人利益方面的考虑,讨好领导。我在姚先生身边生活了四十年,从没有听姚先生说过任何奉承话、虚话、讨好领导的话。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看大局。他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目睹了那个时代政权的腐败和国家的衰落。他看一个党派一个政府,首先是看其对国家发展、对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另一个就是从工作出发。即使是他不喜欢的人,只要是跟他说工作,他都积极配合。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不辨是非,恰恰相反,他的是非观很强,只是“和而不同”罢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对一种做法不满意,有意见,一定会当面提出,在会上提出,或者是写出来给上级领导。而且,他不但不会因为有看法便影响到工作,而且还要配合组织把工作搞好。这一点有不少人理解不了。在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好像与上级领导对着干,就是有骨气的表现,动不动就跟人叫板,把这当作有个性,并以此为高。其实这样做是很成问题的,既不利于工作,又会影响情绪,还会伤害自己的身体。这原因便在于不懂得“和而不同”的道理,也没有大的气量。姚先生能学问做到令人佩服的地步,政治上做到令人羡慕的官级,书法上成就了海内大家的地位,年龄上超越了期颐的高寿,最重要的就在于他有与众不同的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量。
第二个,“用世以仁”。
韩愈说:“博爱之为仁。”仁就是爱心,是宽容的人,仁厚的心。“仁”从二人,通俗点说,就是“心中有人”,每办一件事,都要考虑到别人的存在,要考虑到会不会伤害到他人。比如停车,你从外面来,啪,把车停在了楼前。你是方便了,但却把里面车的出路给挡了,想出也出不来,这就不是“仁”。如果你在停车时考虑一下,是不是会挡了别人的路,你再决定往什么位置上停,这就是“心中有人”了,这也就近于“仁道”了。“用世以仁”就是用仁爱的心面对社会人群,要爱人、容人、理解人,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姚先生做任何一件事都是用仁人之心来筹划和安排的,用仁心面对身边的人和事,所以心无芥蒂。举几个例子,如他在省里多少年管职称,有一次评职称,在审查他一位学生的材料时,他觉得不错。有人说:“你这学生在背地里还骂你呢,你不值得为他说话。”学生背地里说老师的坏话,老师知道了肯定生气。一般人可能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不吭气;另一种会推辞说,这个材料嘛,还欠缺一点,让他继续努力吧。但姚先生却出人意料地说:“政策没有规定说,学生骂老师就不能评职称的呀。”看看姚先生的胸怀,能不让人敬佩吗?还有1986年评职称时,基本上是论资排辈,因为“文革”期间多年没评职称,所以积压了很多人。当时教过我的老师,不是一个,而是一大批,同时都要上副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自然就是论资排辈了。可是当时人才紧缺,名额有限,虽然老的需要照顾,但更需要年轻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怎么办?于是姚先生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在高评委会上带头向领导反映现状,为山西大学等一批老校争取了更多的指标,在照顾到一大批二十年未评职称的中老年教师后,还力主打破陈规,破格提拔一批青年后进。姚先生的几个研究生,虽然资历浅,但明显地成果要突出一些。当时有人议论说,姚先生徇私情,照顾他的学生,但姚先生不管这些,他是为了未来学术的发展考虑,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谁不服气,可以把材料拿出来,大家比。当时他的压力很大,从一些上级领导,到下面争评职称的教师,都给他施压,但他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并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希望得到社会和上级领导的关注、支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按说这样对他自己没有一点好处,还会惹来很多麻烦,但他不忍心看到经过十年“文革”破坏的山西高校教育继续向下滑坡。同时他要为有作为的年轻人的成长,尽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仁心”的表现。历史证明,姚先生的举措对山西大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孟子说:“仁者无敌。”所谓“无敌”,就是没有敌人。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因为仁者为人心所归,所以无敌;二是心中无敌,用友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姚先生就是这样,不愉快的事,伤害过自己的人,他从来不往心里记。有人问,姚先生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就是秘诀。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南开大学有位老师给他寄来了一本新编的讲义,是复印的。一看这个讲义上的署名,我认识,因为这个老师教过我,是从山西大学调到南开大学的。姚先生说:“你看看,这个讲义编得很不错。”后来我跟一位老师提到了这本讲义,这位老师就告诉我:“这个人很坏,‘文革’期间,他把姚先生私下跟他谈的话,拿到大会上批判,辱骂、批斗姚先生。”但姚先生从来没提过这些事。还有一个学生,多少次有关姚先生的活动他都没来参加,但姚先生的书法展览他却参加了。我不理解,后来才有人告诉我:“‘文革’时他斗先生斗得可厉害啦!”但姚先生也从没提过。
最典型的是:一位同事,不知什么原因对姚先生很不满,背地里有机会便诽谤姚先生,曾鼓动姚先生的一位在校研究生,告姚先生的状。在别人看来,他好像与姚先生不共戴天。后来学校有意提拔这位同事到主要领导岗位上,征求老师们的意见。老师们反对的很多,同一个教研室的老师几乎没有一个支持的。学校领导征求姚先生的意见,姚先生首先肯定这位同事的业务能力和水平,然后又分析了他的优缺点,最后的结论是可以先试用一年。学校领导采纳了姚先生的意见,这位同事走上了领导岗位。老师们很不理解,姚先生为什么要为他的敌人说话呢?可他们哪里知道姚先生心中没有敌人呢?
姚先生从来是对事不对人,不与人为敌,但对事要讲理。他看人是从大的方向看,好的方向看。你要具体问到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他一般是说他的长处,不说短处。对于人们公认的品质不好的人,姚先生也是对他做的事抱批评态度。“没出息”,就是姚先生说得最重的话了。
第三点,“行事以道”。
“以仁”是儒家的心肠,是用仁心对待事物。“以道”是道家的智慧,凡事都顺其自然,量力而行,不要勉强自己。“顺其自然”说起来容易,要做起来却很难。比如现在好多人为争名利,晋升职位,到处托人找关系,送大礼,有时明明知道很渺茫,但还是要去争,似乎是欲罢不能。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搏”。“人生能有几回搏”一度曾成为许多人的口号。姚先生则绝不这样。如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要分析、称量。自己能出多大的力就出多大的力,从不勉强自己。这表现在方方面面。举一个例子。1978年1月,姚先生六十五岁了,我们在泰山参加会议,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校教材会议,要编写适应新形势的新教材,有十四所高校参加。当时开会的老先生比姚先生年龄大的有好几个。会议中间组织爬泰山。这些老先生经过长期的压抑,终于有机会释放了,每个人都朝气蓬勃,爬泰山时为了表明自己还能为革命工作,他们都使劲往上爬,有的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稍作休息还是要爬。而姚先生呢,爬了不多远就说:“你们走吧,我不上了,我在这里看看就行了。”我体会姚先生一是阅过无数大山,故乡山西不必说了,大别山,他生活过,云贵川的崇山峻岭,他也长途跋涉过;二是顺其自然,量力而行。他没有想过要表现自己的身体和力量。从这一件小事都能看出他的为人来。
他处理任何事情,都能把握一个度,掌握以和为贵的原则,同时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摩擦。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工作上遇到种种不愉快,与我一同上副教授的人大多都晋升了教授,甚至有些比我晚评的副教授,也上了教授,而我却在副教授职称上停留了整整十年。当时一方面是人事关系没有处理好,一方面是在情绪的影响下不愿参加外语考试。有点与领导、与政策顶牛的意思。我说:我搞的是先秦文学,外语对我来说没有一点用。我宁愿放弃职称,也不想耽误那么多时间作无谓劳动。姚先生则教诲我说:“只能船靠岸,不能岸靠船。你不能让政策迁就你。”又说:“要学会对事不对人,不能与政策作对。要尽量减少摩擦。”这使我很受启发,因为加大摩擦只能伤害自己。我想:姚先生在“文革”中不比其他教授少受冲击,但是他懂得顺道而行、减少摩擦的道理。他曾说过一次开批斗会,会一开始他没等着喊叫名字,就主动站到了台前。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那个时代的惯例,只要一开批斗会,他就必然会站在台前挨批。与其让人拉出来,不如自己走出来,少受些侮辱。结果这次批的不是他,而是一个一直积极批斗别人的人。过后回想起来他觉得很好玩。在这样的时代,如果你觉得自己冤屈,与那些积极分子辩论,或者对着干,只能吃大亏、受大辱,不如顺着来。世界上有棱角的东西,终是容易受损的,而且也难运转,而圆的东西与外界的摩擦就很少,所以有圆转、圆通、圆融之说。世界上凡是有生命的东西、能够运动的东西,都离不开圆,这就是道。当然姚先生这样做不是耍圆滑,而是识时务。因为这个时候你要与所谓的不合理现象作斗争,不但会激化矛盾,让事情恶化,还会使自己受到更大的伤害。只有在不违背道德原则的前提下先保护好自己,才能谈将来的作为。这是一种智慧。
姚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难进易退”。“难进”就是慎于进取,这里的“难”是谨慎的意思。为什么“难进”呢?比如领导给你个官,你高高兴兴地做了,但是你得考虑:一是你这个官是怎么当上的,合不合于道义?二是做上了,能不能做好?名利就在你面前,你努力伸长手就可以得到,但这是否符合道义?这都是要认真思考、谨慎对待的,所以说“难进”。但退却是很容易的,把官让给别人,把名利让给别人,这是举手就可以做到的。这看起来是一种品德,其实有个道在里面。遵循这个道,既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也可使事物处于和谐状态。比如姚先生做中文系主任时,有位领导跟他谈话,话中透露出对他年纪的看法。姚先生一听就明白了,于是主动辞职。可是在学校,比他年龄大的几个系主任都没有退,一直在干着。他原来身上兼的职务,好多都是他主动辞掉的。他希望由年轻力壮的人来干,这样事业才能发展。
我从来没有见过姚先生跟人辩论过,争得面红耳赤的情况更谈不上,对有争议的事情,他觉得能说的,便说出自己的观点来,否则便一笑了之,反正不跟你争。这也是“道在其中”的。因为一争就可能发生摩擦,一摩擦就会伤感情,也伤害自己,何必呢?有一次,北京的一位学者来拜访他,一见姚先生就说:“姚先生,我来向您请教来啦。”然后那位学者就大谈山西文化,大谈晋商,谈得海阔天空、云山雾罩。最后这位学者走时还说:“姚先生,我走啦,耽误您的时间啦,过后有时间我再来向您请教。”姚先生听了,只是笑笑。这位学者走了,姚先生才问身边的人:“他来干什么呢?”身边人说:“人家向您请教来啦!”先生说:“那他得到什么了吗?”身边的人笑着说:“他这张车票白买啦!”大家哈哈一笑完事。要一般的人,可能会教训这位学者几句,但姚先生不,他知道没有用。
别人让他指导书法,他觉得适合指导的人,就指导,比如说这一笔可以长一点,那一笔可以短一点,等等。如果觉得这人其实不是来请教,不适合指导,这时他只是点点头而已,或鼓励几句。在这里,有个度的问题,如何掌握好分寸的问题,这就是一种人生智慧。他这种智慧从学问中来,又成就了他的人格。他用这种智慧来用世,来处理周围的事务,自然游刃有余,如鱼在水,故而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完美人格的高峰。
董仲舒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心静,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姚先生就是这样,他从不贪求外在的东西。荀子的“虚一而静”这句话他写过好多次,这表现了他的一种认识和追求。心静不为外物所扰,心平不为事物倾斜,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取天地之气以养成其身,这能不长寿吗?所以姚先生从不因个人得失而忧愁,从不因欲望未得而哀伤,他的心永远是向上的、乐观的,永远看到的是光明,在他心里没有过不去的坎。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太难了,比如我的工作做多了一些,领导不知道,这次评奖把别人评了没评我,你怨吗?肯定怨。提拔干部,都是一起来的,人家都提了,你没能提上,怨吗?肯定怨。能做到不愠,这是一种境界。他“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成功地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家庭和工作氛围,使周围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邪气不入于外,正气充溢于内,身心健康,不寿而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