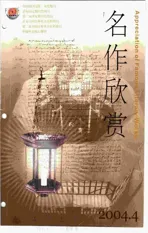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前否定——读屠格涅夫散文诗《对话》
2014-07-12天津曾思艺
天津 曾思艺
作 者:曾思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话》这首简短而深刻的散文诗是屠格涅夫的名作之一,通过两座山峰——少女峰和黑鹰峰的对话,简洁、含蓄地表达了作家颇具超前意识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
散文诗正文前的题词“无论是少女峰还是黑鹰峰,都还没有印上人类的足迹”,既点出了少女峰和黑鹰峰这两座山峰,又概括地表明了作品的主题:自然是永恒与伟大的,人类则是短暂与渺小的。少女峰和黑鹰峰是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两座著名高峰。少女峰海拔4158米,在瑞士南部伯尔尼州和瓦莱州交界处,如白衣少女亭亭玉立于云雾中,故名。黑鹰峰海拔4274米,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山上有冰川。关于这句题词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一说,源于拜伦的著名诗剧曼弗雷德》,第一幕第一场写到黑鹰峰,称它为“群山之王”,“坐在岩石的宝座上,穿着云袍,戴一顶白雪的王冠”;第一幕第二场、第二幕第三场的故事都发生在少女峰上,并提到“在凡人的脚从来没有践踏过的白雪上”。一说,源于俄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的《俄国旅行家书简》,在1789年8月29日的书简里有这样的描写:“银灿灿的月光照耀在少女峰的峰顶,它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之一,千百年来都是雪盖冰封。两座白雪皑皑的山峰,就像少女的乳房,这是它的王冠。任何凡人的东西都不曾触及过它们,就连风暴也无法搅扰它们的宁静,只有明媚的阳光和柔丽的月光亲吻着它们温柔的圆顶;永恒的静谧笼罩着它们的四周——这里是凡俗之人的止境。”一说,这个题词还受到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争辩》、法国作家塞南古的小说《奥贝曼》、缪塞的诗《致少女峰》、意大利作家莱奥帕尔迪的对话体散文《赫拉克勒斯与阿特拉斯》《宅神与守护神》等的影响。
首先,这首散文诗极力渲染大自然的宁静、纯净和庞大、冷漠,并通过时间的无始无终,表现了大自然的永恒。作品的题词就特别强调了少女峰和黑鹰峰“都还没有印上人类的足迹”,从而定下了作品的基调。接着,散文诗从天空到地面,一再描绘两座山峰所处的环境安宁、纯洁:“绵绵群山上面,是蓝云云、亮晶晶、静凝凝的天空。”地面的山峰和峭崖,只有“硬邦邦的积雪闪闪发光”,放眼远望,只见“一块块险峻威严的巨石破冰而出,直插云霄”。在此基础上,通过黑鹰峰的话——“无论是你,还是我,他们都还没有一次能亵渎咱们的身体呢”,呼应题词,说明两座山峰迄今远离人世喧嚣,没有受到人迹的污染。进而,通过黑鹰峰的回答,展示了一个永恒的场景:到处是皑皑白雪,是万古不变的冰天雪地,是清清爽爽的白茫茫的一片。结尾,更是真正的宁静与纯净:“两座极天际地的大山睡着了;亮悠悠、绿汪汪的天空,在永远沉寂的大地上空,也睡着了。”与此同时,作品还写出了大自然的庞大与冷漠。两座山峰庞大无比——“两座极天际地的大山,两位摩天巨人,巍然耸立在天宇的两旁”,他们置身于重峦叠嶂、崇山峻岭之中,对人世的变幻全然无动于衷。不管人们把世界搞得“五光十色,支离破碎”,或是使水面变得极窄,使森林锐减,还是人类最终灭绝,他们几乎都漠然置之,甚至为人类的消亡感到轻快:“现在好了,安安静静了。”作品一开始就写阿尔卑斯山的群峰不知存在了多少年,然后是一连五个“几千年过去了”,写出了时间的无穷无尽,从而很好地表现了大自然的永恒。
其次,通过两座山峰的对话,写出了人类的渺小、短暂,及其对大自然的破坏。少女峰和黑鹰峰对话的中心议题,实际上就是人类,他们称之为“两足动物”。在这两个庞然大物眼里,人类非常渺小,像“许多小虫子在蠕动不休”,像“什么东西在爬来爬去”。对两座山峰来说,几千年只是“俯仰之间”而已,而人类在几千年之间,早已逝去无数代了。而且,绵绵无尽的时光残酷无情,两座山峰几千年又复几千年,却风采依旧,人类则越来越少,最后终于从大地上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万古不变的冰天雪地。在两座山峰眼里,人类对于大自然毫无贡献,有的只是破坏:把大地弄得“五光四色,支离破碎”,让“水面变得窄溜溜的”,“森林也变得稀疏疏的”,搞得山谷里到处是“斑斑点点”,亵渎了山峰,亵渎了河流,亵渎了整个大自然……
《对话》不以人为主人公,而以少女峰和黑鹰峰为主人公,并且通过他们的对话,明确向世界宣布:自然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人类不过是匆匆过客!这是一种相当鲜明的反人类中心的思想,在当时具有较强的超前意识,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突出的现代意识。此外,作者出色地运用了拟人、反复、对比等突出的艺术手法,使作品更加生动、深刻。
众所周知,“二希”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整个古希腊文化的核心就是个体性。这种重视个体性的思想随着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必然表现出来。普罗泰戈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①这种思想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强化了主客二分(主体——客体)的传统,把自然当作苦苦探究的客体对象。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进一步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由于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物肯定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②而古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旧约》更是强调人类中心、人与自然的对立,甚至人对自然的征服,如《创世记》中上帝就公开宣布,让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并明确指示,“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因此,美国学者怀特指出:“与古代异教及亚洲各种宗教(也许拜火教除外)绝对不同,基督教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而且还主张为了其自身的目的开发自然是上帝的意志。”③因此,自“二希”文化合流的文艺复兴以后,人们普遍盲目自大地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形成了突出的人类中心观念,进而把古希腊开始的对自然的穷究发展为征服自然、主宰自然。弗兰西斯·培根就公开宣称:“如果我们考虑终极因的话,人可以被视为世界的中心……万事万物似乎都为人做事,而不是为它们自己做事。”④此后的文学作品也一再表现这一主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部作品。一部是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主要就是流落荒岛的鲁滨逊不怕艰难,凭借自己顽强的劳动来征服自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取之于自然的新天地,极端肯定了人对大自然的征服。另一部是歌德的《浮士德》,它更是高度赞扬了人对大自然的征服。浮士德一生五个阶段的探寻,前四个阶段均以悲剧而告终,但最终他却找到了正确的途径——发动群众,移山填海,并且得出了最后的断案:“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而这种开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大自然的开拓与征服,是指人迫使大自然献出更多的空间、资源乃至财富供其占有,从而使人获得生活的享受,活得更加自由。
正是在上述一系列观念的影响下,19世纪乃至当今的人们都比较普遍地认为,自然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资源宝库,是人征服的客体,而人是自然的主人,主宰着并能随心所欲地享用自然的一切。但屠格涅夫却逆当时的社会主流而动,宣称人只是宇宙的匆匆过客,大自然才是真正的主人,人在短短的生存期间,对大自然只有破坏。这是一种相当超前的观念,与现代生态思想的某些观念吻合,因而具有一定的现代特色。
当今生态伦理学否定古典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倡人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深层生态学更是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一系统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这一系统也即自然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在自然之中。美国学者弗·卡特、汤姆·戴尔详细分析了世界上数十种古代文明的兴衰,他们发现:“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文明人跨越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因而,人类中心主义只会遭致人类自身的灭亡。
《对话》是屠格涅夫晚年的作品,在艺术上相当成熟。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表现了作家的某些消极情绪,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的确具有颇为突出的超前意识和现代色彩,表达了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警醒了至今仍陶醉在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神话中并不断掠夺大自然、尽情消费的某些现代人……
①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3页。
②④转引自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第279页。
③转引自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