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体窥视下《蚀》的男权建构
2014-07-12赖金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杭州310018
⊙赖金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杭州310018]
女体窥视下《蚀》的男权建构
⊙赖金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杭州310018]
擅长塑造女性形象的茅盾,在对传统性别场域的革新过程中,对新女性进行了合理想象。但作家鲜明的男性立场和男性主观视角,使《蚀》中被冠以时代女性的人物,最终还是成为男性思维甚至是作者自身的消费对象。
女体窥视男性思维
茅盾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为了更好地传承茅盾研究、培养茅盾研究新人,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与浙江省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举办了“走近茅盾”征文。现选发三篇。赖金鑫从性别视角剖析了茅盾显现于《蚀》中男性立场;杨帆分析了《林家铺子》中小资产阶级的性格核心与悲剧命运;徐雨霁则选取并不太受重视的茅盾前期作品《野蔷薇》进行全面分析。三位新秀显示出初生牛犊的学术敏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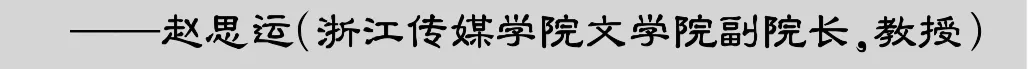
在《蚀》海量的人物景观当中,“男性话语”无疑成为了角色造型的一个重要场域。忠于无意识表达与心理外化的茅盾,让小说内容带有悲观基底的同时,也让小说文本附上了深厚的男性思维烙印。
尽管试图在“时代女性”上大下笔墨,但囿于男权藩篱中难以自拔的“作家思维”终于只能借由异性者的想象进行不合情理的女性勾描,这造成《蚀》中女性角色的塑造局限于狭小的男性视角。呈现在“偷窥镜头”下的女性角色无一例外地站立于由茅盾搭就的男性立场,是经由男性意淫催生的“易性想象”,因而大多带有作为男性主体的茅盾投射在这些女性角色身上的颓废与骚动感以及“阿尼玛”柔软的感伤。本文希望通过对《蚀》中以“女体窥视”为代表的“身体话语”的探讨,实现对茅盾作品中男权立场以及男性思维的解构。
一、“乳房”塑型下的男性话语。《蚀》中的女体造型大多经由男性的主观视角,在不无肉感的身体话语中,女性的体态身姿逐一显示,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乳房”塑型方式。在陈建华对茅盾早期小说视觉性语言的研究文章《“乳房”的都市与乌托邦狂想》当中就曾指出:“在茅盾的早期小说《蚀》三部曲里,对‘乳房’的描绘,就其质量与频率而言,在新文学里均冠绝一时。”这种造型方式在尽情展现女性体态美的同时,也在无形当中默许了男性话语的强行进入,让小说带有了强烈的男权烙印。虽然“时代女性”已然成为《蚀》的文化坐标,“寻求感官刺激与生存价值”的果敢女性在作品俯拾皆是,但她们的出现却始终不能对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形成反超,因而流于浅薄。在对传统性别场域的革新过程中,茅盾对新女性进行了合理想象,但作为男性作家,他在本质上是在男权维护,这不同于女性文学的自发性变革,不是“自选动作”,而是“规定动作”。就像《创造》中君实对娴娴的改造,大多属于一种男性的主观意淫,其目的是两性关系中男性主导地位的保全,但结果却让“被改造者”出离了“改造者”的原始预判,成为一种虚无的“性幻想”。
《追求》中把章秋柳视为一头猫而戏弄的曹志方,在章的愤怒中看到的却是后者“两颗樱桃一般的小乳头和肥白的椎形的座儿,随着那身体的转移而轻轻地颤动”。可见在身体游戏中周游自得的章秋柳,也依旧有被曹志方以“解放女性”的名义倍加嘲弄的时候,她习惯于用身体去还击“下半身”的思维逻辑,却也不幸被贴上了“浪荡与狂放”的标语,当被老曹用“身体戏弄”还击之时,也只能“像是一头猫”一样把身体“平伏在床”。而惨遭男性羞辱的当口,茅盾也就只能让她用这种“香艳淋漓”的方式加以回应。躲在这种肉欲十足的画面背后的不仅是老曹的“忽然爱你”,更有茅盾脑海中作祟的男性思维逻辑——表现为男性在女性肉体前的软弱无力以及女性理所应当地“出卖身体”,身体成为了女性用来自我抗争的唯一途径,因果必然,直截了当,偏离于女性的真实思想。类似的人物还有月下以吻戏弄了抱素又不告而别的惠女士,“共妻”暴动下也开始玩起束胸把戏的孙舞阳,皆是“身体当先”的典型反映。而抱素眼中的慧和静:“慧的美丽是可以描写的,静的美丽是不能描写的”;看上去很平凡的静一旦成为抱素眼中的“静女士”,她的美不仅是神奇的,还是“不可分析的整个的美”。显而易见,惠和静的人物构型正是通过抱素之眼一步步完成的。在午夜观影的思考里头,也在小屋子中的交谈当中。茅盾在这里显然借由抱素之口开始了自己的择偶选择,相互衬托的人物塑造法本无可厚非,但此处的描写却惊现了一种“挑拣”的色彩,让人略感不快。
作为“现代现象”的“身体话语”,从来便是个体感性欲求层面现代主体的觉醒,指的是意的身体,而非物质的身体。而在《蚀》的文学语境当中,男性却在“女体窥视”的过程中,以观看者的身份获得了自我主体性的身份确证,女性则成为了男性话语欲望化想象的客体。时代女性在自我抗争以及两性角力中,实际上满足的正是男性参与者的自我虚妄。看似在身体的行使权上获得了自由的“时代女性”,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男性角色以及男性读者甚至是作者自身的消费对象。因而“窥视镜头”虽然为女性带来了视线聚焦,但这种聚焦却注定了必然的“浅薄”,因而只能让“身体话语”代替“经验世界”出席。在这里放弃心理勾描看似是一种自废武功,却也显示出了这些女性的不可捉摸。精神的神秘性反倒让人物更加出彩。因此,这种写法倒也讨巧。
二、革命恋爱场域中的两性角力。两性角力场的催情作用在《蚀》中展露无遗。大革命背景下由《幻灭》《动摇》《追求》搭就的叙事楼厦在多重恋爱关系的撞击中愈发显得深沉而厚重。葛天逸《双重土壤滋养出的奇葩》一文对《蚀》的典型恋爱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闺阁少女的恋爱幻想;2.女党人的变态恋爱;3.诱惑者与家庭中被诱惑者的畸恋。静女士显然就是“闺阁少女”的代表,在静先后和抱素及强的恋爱段落当中,迁移着静情感走向的一直是男性角色的作为。抱素和强始终把控着情感的发力点,而女性人物只能在其中承当着无关痛痒的情感受力,在读者眼中成为了一个弱者。
就连茅盾精心打造的“时代女性”其实也在“女党人的变态恋爱模式”里面渐渐丧失了爱的能动性,在“自由”的呼声中成为一种为性趋势的奴隶。在用“性”代替“爱”,用“肉体”把玩男性的过程中,这些女性角色在某种程度中生成了一种情感缺失。在慧对过去情感经历的回顾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个女性的行为动机其实是经受感情挫折之后的“自暴自弃”,这种看似洒脱的追求刺激,大抵只是一种流俗的疗伤方式,是两性角逐溃败的消极心理。同样的,章秋柳和曼青的往事亦是她在歌舞场里寻欢作乐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失败者,赵赤珠算是一个。怀孕后被迫失足的王诗陶同样也是一个。再看由方罗兰和孙舞阳这一对建构的畸恋恋情。在诱惑者与被诱惑者的情感角逐当中,看似是方罗兰终于成为孙舞阳的又一个俘虏,婚姻关系濒临破灭,方罗兰对孙舞阳倒是也动了情的,但再一次成为被“看”客体的孙舞阳显然成为了更加被动的一个,因为这种“情”里头“性”的成分远远多于“爱”。
总之,在这几种不同形式的恋爱纠葛当中,无论是新女性还是传统女性,全都沦为了两性角逐中的被动角色,是男性话语下发了“声”却在心理上被万般压制的失败者。
三、“迷茫一代”的“阿尼玛”心理。《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茅盾对《蚀》的创作过程做了自我剖析:“我很抱歉,我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我是越说越不成话了。但是请恕我,我实在排遣不开。我只能让它这样写下来,作一个纪念。”《蚀》三部曲中浓厚的凄凉基调是茅盾创作心境的真实映射,社会活动家以及文学创作者的身份矛盾始终未曾淡出作者的内心。对革命出路的质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让他始终陷入了苦闷的情绪里。大革命的失败让茅盾这一代文学作品的颓废情绪挥之不去,《蚀》三部曲正是如此。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的情绪,早已成为了大革命中“迷茫一代”的真实写照。
而《蚀》的“女体窥视”不仅是茅盾主观视角下的产物,同样也是那个矛盾时代孕育出的结果。小说文本非常有趣的一点在于男性角色在女性肉体面前的软弱无力,这种无力感显然带有茅盾本人的影子,是“阿尼玛”在男性身体中过分分泌的不良果实。对女性诱惑毫无招架之力的男性反应,正体现了作者本身的女性化倾向以及本能的女性认同感。这注定了作者对女性心理抒写的独特偏好,也为他把玩女性情感的乐此不疲提供了依据。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女性认同是带有根深蒂固的男权基底的,说到底是裹挟了男性因子的“杂交品牌”。男性的阴柔气质在《幻灭》里头成了抱素胸前的红领带,也成了慧女士离开时他的内心密语。到了《动摇》里头,那是方罗兰应对“罢工运动”以及“共妻”暴动的迷茫无措。而对于《追求》里头的曼青,那是看不清未来的乏力、被现实伤透了心的失落。
弗洛伊德把文艺作品当成作家的无意识表达,而茅盾在其中表述的正是自己的情感创伤和作为“迷茫一代”的颓废心理。多重创伤让众声喧哗中的茅盾显得愈发沉默无语,成为一个了曼青式的落寞派,“颓然靠在”自己的书桌上,“再没有话了”。长期陷于虚无、幻灭、颓废等非理性创伤体验状态而不能自拔的茅盾,在这种情绪之中不断激发出艺术创造力,建构出整个作品的颓废基调,也折射出茅盾自身“阿尼玛”式的男性人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尽管茅盾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大下笔墨,但鲜明的男性立场让这种女体构型带有了深刻的男性思维烙印,字里行间其实是十足的男性话语,这不仅体现在“女体窥视”的描写之中与两性恋爱的角力里头,也呈现在身体话语的表述当中。
[1]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作者:赖金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2012级汉语言专业学生,浙江传媒学院未来作家班学员。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本文系浙江传媒学院“凤凰行动计划”科研项目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