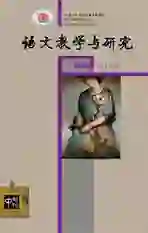话剧《我系香港人》中的象征手法
2014-07-10胡读书
《我系香港人》是杜国威和蔡锡昌合编的话剧,于1985年首演。它以“戏中戏”的形式简洁而生动展现了香港自1841年沦为殖民地以后直至“中英谈判”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及其间各阶段香港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剧作透过民间的视角来反应香港普通民众的“心声”,表达的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97回归背景下香港历史命运的忧虑,对香港和香港人的本土身份与主体意识的思考。剧作段落式的结构非常有助于片段式的故事情节的表达。剧中七个演员并没有固定的角色,除个别角色外也基本没有固定角色的台词,即不求塑造特定的人物性格。因此,剧作的重点不在描写某个具体的香港人,而在于表现作为群体的、普遍的香港人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身份的转变和各异的心声,“以片段式的叙事方法呈现和阐述香港百年的殖民历史,是对香港文化身份从质疑到确定的过程”。 (梁燕丽:《试论香港话剧本土化的特征》)全剧十五场场戏就在历史的前进中徐徐展开。
《我系香港人》在语言上,国语、英文和粤语方言相混杂,形式上,融入考试竞猜、流行歌曲等娱乐文化要素,使剧作显得港味浓郁。而剧作对香港历史沧桑的形象回顾及对现状与未来的思考,借象征手法得到了独特而有效的表达。
一.辫子与领带
《我系香港人》从第二场开始,随着人物C的叙述进入戏中戏,剧作通过C的太公太婆的生活经历,揭开了香港殖民的历史。太公太婆作为渔夫渔妇因偶然的原因来到香港,成为了香港居民。与我们在许多其他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类似,大清国的老百姓在主动或被动接受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之前都要被剪掉自己脑后的一根辫子。然而在这部戏中意味深长的是,“鬼佬”军官在割去渔夫那根辫子的同时,“作为补偿”,军官送给了他一条领带,而渔夫在接受领带之后,又“将领带翻到颈后,当作辫子用”。
在这场辫子与领带的较量中,渔夫为了护住这根“pigtail”曾与军官拼命:“你想割我的辫子,我还有脸吗?我跟你拼了!”辫子曾是一些中国人心中的命根子,是受之于父母的东西,割了辫子就是要了他的命。但在辫子真正失去之后,渔夫和被割掉辫子的其他人们一样,也并没有像丢了魂一样哭天喊地。当军官给他那根代表西方文化的领带的时候,渔夫也是坦然接受,并接受了军官为他在码头找到的差事。有意思的是,渔夫竟然将这条领带当作了自己的新辫子,这说明对渔夫这一类大清国子民而言,无论他们在哪里,受谁统治,生活方式有何变化,学了多少外语,但从前的伦理纲常依旧,“鬼佬”还是“鬼佬”,对“鬼佬”的态度永远都是憎恨的。这样的认知系统和意识形态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迅速改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了成功的“诀窍”——“适应环境,把握机会”,将戴在脑后的领带慢慢转到身前,装扮好自己,跻身所谓的上流社会,成为了有名誉、有地位的香港绅士。从此,一些有着中国人面孔的人,抛弃了以辫子为身份象征的中国人的名头,逐渐变为了以领带为代表的与其宗主国意识形态相同的香港人。但身份无论如何转变,都无法改变他们的血统和面孔。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虽然这些香港人能获得个人利益和地位,但他们必须以服从殖民统治为前提。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仍旧是异己的低等级的人,尽管他们用的是Rank Xerox的器具,穿的是Pringle或者Burberry的衣服,用着MaryQuan的化妆品,有着与英国人一样的洋名字。但只要殖民者还在香港,香港人就不能与他们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香港在经济上贡献再大,它仍旧还是个殖民地,自己的主权不在自己手中。因为,香港人的“领带”是英国人给的,他们的权利、荣誉与地位也都是来自于英国人。请看剧中英国官员的一番话:
“They want money? Ill give them the chance to make money, as long as they never earn more than I do. Who else can help them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They want power? Ill give them the chance to gain power, as long as they remain obedient and realize that I continue to maintain control. Anyway, where can they use their power? They want fame? Ill bestow on them honours and titles as long as they never forget that the honours, the titles, the power and the money all come from me.”
事实正是如此,香港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有“世界金融中心”、“购物天堂”的称誉,与英国对这块弹丸之地的充分利用大有关系。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在殖民地受到残酷剥削和羞辱的同时也客观上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在屈辱中繁荣,是殖民地发展历史中的重要特征。在割掉辫子让人羞辱不堪后,逐渐成为本地香港人的华人戴起英国人给的领带,在为大英帝国出力办事的同时,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金钱、地位和荣誉,也逐渐迎来了香港的繁荣。
二.气球与“船”
香港在二战后得到相对的社会稳定,文明政治制度相继出台,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发展,香港人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为香港的建设担当起重要角色,投身各项事业。有人潜心经营,获利良多;有人利欲熏心,把属于自己的“气球”吹到极限,最终以破产告终;有人贪得无厌,把众多产业拿在手中,结果一个都没有成功;有人联合,也有人从中破坏,也有人一事无成……剧作第五场以气球做比,堪称绝妙,舞台上以肢体默剧表演的形式将以上种种经济现象予以表现,看似游戏化的场面,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众人吹起来的气球越来越多,甚至有人拿起气筒打气,但最终,气球拼凑起来形成的只是一只小艇。小艇象征着香港这种文明发达的体制,这个稳定昌盛的社会,这个繁荣富裕的发展模式。英国政府放任香港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来吹气球,谁吹得多吹得大,谁就得到褒奖。只要不打翻这条船,你就可以在经济上为所欲为。然而其他方面呢?政治、教育等方面则都是政府“全面据守的险要阵地”,对于港人来说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这让我们联想到东南亚华人在当地的处境,他们可以为当地贡献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无论他们如何优秀,都不能受到最高等的教育。而在香港这样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则有更滑稽的现象,这就是第七场中的“社会分层制度表”。一个人的社会等级看起来似乎是很“公平”地分出来的,但是当一个DA型的人贴着金章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钱能使鬼推磨”;当一个人能够将气球吹得又多又大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文化程度都会受到社会、尤其是政府的青睐。而当麦理浩出场的时候,身无金章,却受到一群身上有金章的人的极力奉承,原因就在“他是‘鬼佬”!金钱至上的社会中尽管腐烂与肮脏丛生,但毕竟还有阶级对流的微弱可能,而在以人种来区分等级层次的香港,对于港人来说,则有一堵永远无法跨越的围墙。他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从前的“边缘化”的身份,走向主流社会,试图更进一步探究自己的主体位置所在,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走出过边缘的境地,不论蓝领还是金领,他们一直都只是为“鬼佬”吹气球、“做船”的打工仔。
在毫无出路的社会分层制度下,一部分香港人只能卑躬屈膝或屈意顺从地陪着“鬼佬”玩着已知结局的游戏;而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反抗,他们罢工,他们暴动,他们要争取自己应该得到的待遇和权利。在寻求自己的真正身份和地位的同时,香港人也开始寻找自己的根和源。他们找到的,是祖国母亲。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和商业社会中生活的香港人如何适应这个新的体制?他们感到有些惶恐和不知所措。对于97回归,有人鼓掌称庆,有人仰天哀号,有人临渴掘井,有人未雨绸缪,有人掷笔兴叹,辞归故里,有人风云际会,夜赶科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他们有人对现有社会深恶痛绝,有人则对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的一切满怀感激。但社会骤变在即,一部分人心怀恐惧,想移民出国,“逃到”加拿大、澳洲、美国等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地方去,然而他们的子女,作为第二代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却哪里都不要去,只想留在香港,因为他对这里才有归属感。而被逼着出国留学的孩子,“以香港人的身份”去参加International Student Evening“这个神圣的聚会”的时候,他想大声唱出能够充分代表香港、代表香港人特色的一首歌,结果,他选择不是潘迪华那首流行大街小巷的《Kowloon,HongKong》,
而是一首流传甚广的中国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正是这样一首民歌,道出了香港人的乡土情结、故国情怀。他们的成长依旧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哪怕是在全盘西化的殖民统治之下,他们的情感依然联系着“遥远地方”的大陆,在一个国际化的聚会上,他们寻到了根。
《我系香港人》创作于香港回归之前的中英谈判之际,非常敏感地写出了对97回归的前瞻,表达了自尊自信的香港人的心声。剧本最后,角色从戏中戏走到戏外,通过参加选民登记显示出他们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相信自己才是香港的真正主人,“港人治港”才是他们真正搭上的崭新的“船”,从此唱响他们新的《香港之歌》。
胡读书,复旦大学中文系2011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