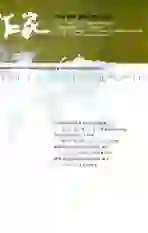《哈姆雷特》中奥菲利娅的歇斯底里式疯癫
2014-06-30武娟玲
摘要 疯癫意象是莎剧独特的文化向度,歇斯底里式疯癫是莎翁悲剧《哈姆雷特》中奥菲利娅所展示的疯癫符号。她的疯癫是一个标本,不仅体现在她谵妄的语言中,更包含在她疯癫的行为中。花、情歌和水是她疯癫的象征,在歇斯底里中,她最终对要求自己失语和盲目顺从的传统唱出自己的不满。通过死亡,她被社会接纳,因为社会包容了她,并且静默地赞成她的死亡。一方面,她是男权社会中无声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她的疯癫及静默的死亡是宣战的、胜利的,是横亘于男权秩序间永恒的创伤。
关键词:疯癫象征 男权 歇斯底里式疯癫
《哈姆雷特》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它的价值已然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历代学者们研究的典范。然而,评论者对《哈姆雷特》的研究主要以哈姆雷特为主,女性在哈评史中一直处于“弱者”地位。国内学者黄立丰从肖瓦尔特提出的女性主义批评重新梳理被忽略的女性哈评史并评价其历史价值,他指出女性哈评史依然禁锢于男权价值体系之中。但事实上,这种评价体系正冲击并瓦解着男性评价的权威。
奥菲利娅的疯癫是哈评史上不可回避的案例。A·C·布雷德利在20世纪初期总结到:“两个世纪来的评论和奥菲利娅的疯癫形象带给我们是漂亮、甜美、惹人爱的、伤感的和被遗忘的。”近些年,女性主义评论家从心理学、舞台表现、女权主义等角度把她的疯癫解读为失语、顺从,或是男权压迫的受害者。尼利认为莎翁是以一种特殊的疯癫语言而不是心理特征来展示奥菲利娅的疯癫。事实上,她的疯癫不仅体现在谵妄的语言中,更包含在疯癫的行为中:她采撷花朵、唱着忧郁的情歌,最终溺水而亡。花、情歌和水成为她疯癫的象征。歇斯底里的奥菲利娅最终对要求她失语和盲目顺从的传统喊出自己的不满,通过死亡,她被社会接纳,因为社会包容了她而且把对她的记忆变成了静默的赞成。因此,一方面,奥菲利娅的疯癫是窒息的、顺从的、静默的,是男权社会中无声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她的疯癫是宣战的、胜利的,是横亘于男权体制中无声的挑战。
一 花语·疯癫
哈剧中,奥菲利娅曾经是一个“幸福女孩”。她出身高贵,父兄对她呵护备至,最重要的是她得到了哈姆雷特的爱情。但现实无情,她爱的人突然发疯,紧接着她父亲被复仇的哈姆雷特误杀,爱恋的伤痛加上亲情的消逝使她无法承重,双重打击下,她只好借助花语来倾述她的心声:“这是表示记忆的迷迭香;爱人,请你记着吧,这是表示思想的三色堇……”
奥菲利娅变得疯癫,她悲哀的歌声传递出扰人心魂的忧伤。这绝不是一颗哀婉忧郁飘荡的心随意的绝唱,而是有着疯癫真理的因果,是顺从、是放弃。她采撷花朵,通过花语,奥菲利娅诉说失去的贞操,她甚至警告她的哥哥雷欧提斯即将到来的更大的灾难。在古典文学中,花总是和一个人的某种品质相对应的,在维多利亚时代,阐释花语更是一种时尚。奥菲利娅采撷的花朵表达出她对性、爱欲和生育的渴望及迷惘。
在《花语:历史》一书中,贝弗莉·西顿指出由于社會限制和性压抑,当时的人们常常用花来传达他们不敢说的话。哈罗德·詹金斯在雅顿版的《哈姆雷特》中提到,大多数花都有性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样解释非常符合奥菲利娅,评论者们却刻意去忽视。迷迭香经常被认为是情人之间记忆的象征,而不仅仅是对死者的纪念。三色堇也称“三色紫罗兰”,代表纯爱,初恋的少女喜爱这种倾斜着盛开的花。它看起来就像是在思考的样子,据说它的英文名字是从法文“思考”而来。因此这里奥菲利娅提到的思想是性爱的。茴香不仅指奉承,而且表示轻浮的爱,通常和女性欲望相联系。漏斗花因其蜜腺的特殊形状,被认为是与他人通奸的象征;芸香代表悲伤和懊悔,也被认为是减少欲望。雏菊代表对爱的牺牲,同时也代表掩饰爱情和轻信爱情的愚蠢等。
伊丽莎白时代这些花同时都是知名的避孕、堕胎或调经类的药物。一些权威医学人物如希波克拉底、老普林尼、盖伦等中世纪最有名的草药专家的著作中都有描述。在西方,基督教对性冷酷的限制加上严格的医生理论的训练,使得中草药知识只是在妇女中口口相传。
这种知识之所以隐秘,是因为女性总是羞于谈及这样的话题。女性是避孕的执行者,只有她们知道这些植物的秘密,知道什么时候采摘什么样的植物、使用植物的哪个部分、如何萃取和准备药物,也知道适宜的剂量和在经期使用的最佳时间。换句话说,莎翁时代中草药避孕知识只是停留在民间口传之中。莎翁来自于乡村又酷爱植物,不可能忽视这些植物的作用。奥菲利娅提到的五、六种植物中,在早期避孕药中是被经常提及的。
哈姆雷特抛弃神圣的奥菲利娅,在歇斯底里的伤痛中,她采撷堕胎药花。手捧花束,她唱着骇荡的歌声,渴望被引诱、被抛弃,在疯癫的花语中,她彻底地表达了她渴望爱、渴望欲、渴望生育又拒绝生育。她成为矛盾的集合体,哈姆雷特求死的愿望使他不能再接受奥菲利娅,对爱欲的失望使她在采撷的花朵中找到了倾诉的借口,借助花语,她说出了自己的声音。
二 疯癫·水
父兄及哈姆雷特所构成的男权秩序使奥菲利娅遭受了心理上的缺失,引起了她的疯癫。手捧花束的她对爱毫无反抗,最终选择了淹死在水中。遭受了内心欲望的斗争,她不得不服从专横的父亲。她的疯癫源于对异性错位的身体之爱和无法满足的欲望,因为被所谓的合法文化阻止,只能以死来赢得男权限制的胜利。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指出,“水域给这种做法添加上它本身隐秘的价值。”它不仅将人带走,而且还有另外的作用——净化。弥漫的水气浸透了人体的脉络,使之变得松垮从而导致人发疯,疯癫是人身上晦暗的水质表征。
奥菲利娅遭受的是歇斯底里症状,一种癔病,伯顿在《忧郁的剖析》中提到,这是一种上层社会女性经常有的疾病,她们在自己的父亲家中等待时机,在等待自己变成社会所赋予她们的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完成。文艺复兴时期的内科医生乔登定义癔症为“母亲的窒息”,这是由子宫运动引起的,“它有时候朝上有时候朝侧面翻,压迫了周围部分,因此相互影响,然后就会开始窒息和无言的癔病症状。”
奥菲利娅窒息的症状和文化上的失语源于她对于哈姆雷特纯洁的欲望,是她涌动的子宫的病症。“游走的子宫”正是指由于性的缺失而导致的月经的停止。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相信经期的流动是性的副产品,缺乏性就会导致身体这种血液的停止。治疗的药方便是结婚,结婚能使狂乱的子宫能处在丈夫的控制之下,这也“宣布了男性对于狂热的女性的控制”。婚姻和性的副产品都不是奥菲利娅的选择,因为她父亲认为求婚者不合适,她无路可走。再者,医生对这种癔症所产生的潜在的狂躁的治疗便是“快速结婚,否则,只能变得疯癫和急躁,(年轻的女孩)将会自己逃走,不是淹死便是吊死”。奥菲利娅溺水结局直接的原因是父亲禁止她结婚。
这种叫做“母亲的窒息”疾病是各种身体和精神疾病掩盖性的名称。这样的症状表现为非理性、谵妄、忧郁或者狂躁,根据身体不同部分引起的不同行为“通过爱、害怕、忧伤、兴奋、生气、憎恨等”表达,有的则会笑、哭、唠叨、威胁、责骂或是唱歌等。奥菲利娅的癔症一方面源于她得不到哈姆雷特的爱,另一方面父亲的死亡带来的悲伤恶化了乔登描述的症状。她歌唱、像孩子一样喃喃呓语,“她一边呻吟,一边捶着她的心,有时眨眼,有时点头,做着种种的手势”,变成了“疯癫的典型”,这正是乔登对疯癫定义的最好的版本。劳伦斯·巴布指出,“相爱的人总是会遭受一些精神上的狂热;他们是爱情的奴隶,除却他们自己,他们是爱情的苦工”,奥菲利娅就是典型,她“因为伤心失去了她的正常的理智”。
不同于查德·纳皮尔医生用忧郁当做不同疯癫形式的代名词,乔登使用“窒息的母亲”暗示出性别差异,指出女性癔症的症状更为普遍。他证明女性和癔症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尼利认为:“奥菲利娅的疾病,被称作癔症,是性阻碍,是无助,也是女性身体被限制。”男权文化制度严格控制女性的激情与激动,同时也控制女性“疯癫”的本质。男权要读懂女性疯癫从而更严格地限制女性并继续充当男性保护伞这个文化角色。
因为要服从她的父亲,奥菲利娅猛然跌入了自我毁灭的绝境,也使她被挤出社会秩序之外。她再也没有办法完成女儿—妻子—母亲这样的循环。由于被哈姆雷特强硬拒绝,她只能把她的性和感情的萌芽投射在自己父亲身上。当父亲活着的时候,她还能顺从社会秩序,尚能拒绝她唯一的求婚者。一旦他死去,她只能吟唱悲哀的情歌,呻吟忧郁的叹息。她疯癫的语言和歌曲从对哈姆雷特的爱欲转向对自己父亲的哀悼。对父亲的悲痛融合了孝顺的职责和浪漫的爱情,她用忧伤的谣曲和伤感的情歌轮番歌唱。
她用忧郁的情歌悼念失去的爱人。“张三李四满街走,谁是你情郎?……姑娘,姑娘他死了,一去不复来。”父亲代表了这位死去的爱人,因为他的死最终移除了社会限制对他女儿的控制。她的“行为挑战了男权所规定的社会规范、父亲的权威和亲情。”没有了父亲作为她子宫的锚,瘋癫接管了她。她用花和情歌破坏了男权秩序,通过强调爱欲来为自己寻找声音,这正是父亲要无情遏制的。
失去了所有,奥菲利娅走入水中。肖瓦尔特说道:“淹死,成为一种美丽的女性之死,这是一种优雅的沉浸。水是女性深邃的身体器官的代名词”。她的死是有意的、悲剧的、美丽的,更是沉默的、反抗的。
她是混乱社会的存在,她呼吁变化,然而这个世界根本倾听不到她的声音,因为这是一个畏惧变化的时代,奥菲利娅在这个社会力根本没有发言权,只能求助疯癫来逃避男权的控制。她的母亲只是逻辑上的存在,她完全听命于父亲。父亲和哈姆雷特双双成为她疯癫的罪魁祸首。当“被剥夺了思想、爱欲和语言,奥菲利娅的故事变成了‘哦,——什么也没有,变成个空壳、变成女性爱欲的缺失”。水淹没了她的躯体,她变得沉默。
尽管水淹没了她的权利,消逝了她的声音,然而溺水却使她的生命再次变得完整。通过死亡,她被社会接纳,因为社会包容了她,并把对她的记忆变成了静默的赞成。疯癫时她极力批评“爱情的谬误,宗教的虚伪,男性的背叛”,歇斯底里中她最终对要求她失语和盲目顺从的传统发出了自己的不满。这种自我表现的疯癫,无论多么优雅的死,都使曾经拥抱她的社会把她推到了边缘。溺水净化了她颠覆性的疯癫,仪式化的基督葬礼最终使她重新回归社会。回归在这里变成胜利者的嘲讽,也变为终极的胜利。
花、水和情歌象征并演绎了奥菲利娅的疯癫,留给观众无尽的阐释。她的疯癫是女性疯癫的标本,这疯癫及她的死亡远远超越了甜美、顺从,变成了无言的控诉和声讨。溺水死亡淹没了社会秩序的公正性,赤裸裸地展示了男权的凌驾与霸道,静默中酝酿了胜利,苍白中启迪了灵感,那是奥菲利娅恬静的微笑,是她散开在水上漂浮的白色身体之花,是飘荡在男权秩序间永恒的创伤。
参考文献:
[1] 莎士比亚,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Bradley,A.C.Shakespearean Tragedy,Fourth Edi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3] Beverly Seaton.The Language of Flowers:A History.Virginia: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95.
[4] 米歇尔·福柯,刘北成等译:《疯癫与文明》,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5] Burton,Robert.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Ed.A.R.Shilleto.3 vols.London:Bell,1927.
(武娟玲,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