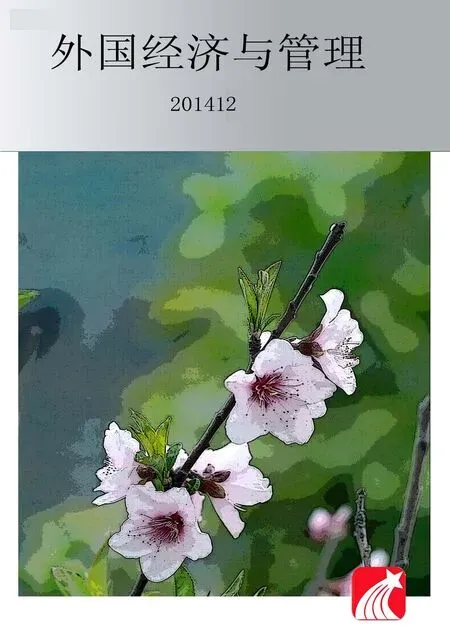职业生涯幸福感概念介绍、理论框架构建与未来展望
2014-06-26翁清雄陈银龄
翁清雄,陈银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一、引 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职业的追求已不仅仅满足于解决基本的生活需要,从职业中获得成就感、实现个人价值、达成职业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等逐步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这种转变的一个最直接体现是人们越来越重视职业生涯幸福感(career well-being),并将能否获得职业生涯幸福作为个人职业选择与职业成功的重要标准(Arthur等,2005)。与此同时,日益激烈的竞争所带来的职场压力,也使人们更易陷入职业倦怠。因此,改善个人职业状态、提升职业生涯幸福感,被认为是新时期组织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方向(Kidd,2008)。
本文首先通过对职业生涯幸福感及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剖析了职业生涯幸福感的内涵和测量方法;其次,结合工作幸福感研究以及相关理论,构建了职业生涯幸福感研究的理论框架,深入探析了职业生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及结果变量,以期深化对职业生涯幸福感形成机理及作用机制的理解;最后,从测量工具、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研究设想,以期为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及相关管理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二、职业生涯幸福感概念
(一)概念内涵
自古以来,幸福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状态。正因为如此,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开始得很早,并且引起了各个领域学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主题包括幸福感、工作幸福感、职业生涯幸福感等。
1.幸福感。一开始,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主要以金钱和物质为目标,通过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来提高个人的幸福水平。而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幸福与财富的关系减弱,幸福更多地取决于内心的主观感受,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也因此得到人们的重视。Wilson(1967)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幸福感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人们对人生的主观评价和感受。之后,学者们对幸福感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认为它包括对生活的多维评价,涉及对生活令人满意程度的认知判断,以及对情感和情绪的评价等(Diener,1984)。研究发现,幸福感不一定是由日常生活中的外在条件所引起的,它也可能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态度、自尊、价值观和个人信仰等内在因素(Hergenroeder和Blank,2009)。
2.工作幸福感。在现代社会,由于工作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工作中的幸福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Kooij等,2013)。与工作中的幸福感相关的概念包括员工幸福感、与工作相关的幸福感、职业幸福感等,可统称为工作幸福感。Horn等人(2004)将工作幸福感定义为个体对自身所从事工作各个方面的积极评价,包含情感、动机、行为、认知和身心五个方面的内容。工作幸福感目前主要通过工作中的情绪或工作满意度来测量(Makikangas等,2007;Diener,2009)。国内学者认为工作幸福感是指员工对工作的积极情感和认知评价(王佳艺和胡安安,2006),可以通过个体在工作中的满意度、离职意愿、积极和消极情感来反映(吴伟炯等,2012)。
3.职业生涯幸福感。职业生涯幸福感概念直到2008年才被提出。最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学者Kidd,她将幸福感研究扩展到人们对整个职业生涯的情感体验。Kidd(2008)指出,职业生涯幸福感不同于工作幸福感,后者体现的是个人对当前所从事工作的主观体验;而前者体现的是个人对职业生涯经历和职业生涯发展过程的主观感受,不仅包括当前工作中的情感体验,还包括人们对整个职业生涯的总体感受。
Kidd(2008)还对职业生涯幸福感与工作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她认为,职业生涯幸福感具有一些独有的特点,是人们对所经历的职业事件、职业过程、职业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总体情绪体验。她的进一步质性研究表明,职业生涯幸福感是个人受到自身职业流动机会、职场人际关系、工作自主性与权力、工作绩效、目标价值、职业技能发展、工作—生活平衡等方面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综合情感体验。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职业生涯幸福感是人们以职业生涯发展为核心,针对自身职业经历、职业现状以及职业前景的一种主观评价和情绪体验。
(二)概念的测量
由于职业生涯幸福感这一概念提出较晚,因此相关研究还非常少,对职业生涯幸福感测量方法的讨论和研究更加少见。目前,只有Creed和Blume(2013)在其最近的研究中通过测量职业满意度和职业困扰来评价职业生涯幸福感。
由于职业生涯幸福感也包含了工作中的情感体验,因此,有关工作幸福感的维度划分和测量工具,为更好地测量职业生涯幸福感提供了借鉴。首先,对幸福感的测量主要还是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这是因为幸福感主要反映的是个人内在的主观感受。其次,对工作幸福感一般都是从多个侧面进行测量的,使用较为频繁的指标有倦怠、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投入(参见表1),这三者分别从态度、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反映个体对当前工作的主观感受。有鉴于此,对职业生涯幸福感的测量也可以分别从职业倦怠、职业满意度、职业投入等方面来进行,通过比较严谨的心理学量表编制方法,在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一套较好的测量工具。

表1职业生涯幸福感及相关变量维度划分与量表
三、职业生涯幸福感研究的理论框架构建
在无边界职业生涯时期,人们经历的职业转换越来越多,因此,仅仅关注当前的工作幸福感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整个职业生涯的幸福感。因此,在已有关于工作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职业生涯幸福感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关于职业生涯幸福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为此,本文结合工作幸福感相关研究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职业生涯幸福感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在下文对职业生涯幸福感的前因和结果进行了深入讨论。

图1 职业生涯幸福感研究的理论框架
(一)职业生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职业生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体、职业、组织和岗位等多个方面。
1.个体特征。影响职业生涯幸福感的个体层面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人格、情绪和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等。
第一,性别、年龄。一般来说,男性在家庭和工作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承载的社会和家庭期望更高,比女性更容易在职场竞争中赢得优势。女性则由于受传统观念、性别歧视以及生育所带来的职业发展间断等的影响,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很难晋升到较高的职位。因此,男性职业生涯幸福感的平均水平很可能高于女性(Siltaloppi等,2009)。但是,对于某些职业,比如医务人员和教师,性别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谭贤政等,2009),女性甚至可能占有优势,职业生涯幸福感的性别差异则可能不太显著。
职业生涯幸福感也很可能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产生波动。在职业生涯早期,人们普遍对自我和职场认识不足,容易在职业发展上受挫,这时职业生涯幸福感整体较低;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人会在中年期达到职业发展的顶峰,个人的职业理想得到实现;而到职业生涯后期,很多人会遭遇职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等问题。当然,也有一些人,尤其是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到退休前才达到最高点(Fisher等,2002)。因此,不同职业的人群在不同的年龄段所体会到的职业生涯幸福感存在差异。
第二,学历、收入。学历不仅被认为是获得一份好工作的敲门砖,而且会影响个人的整体职业发展潜力。高学历的员工更容易获得领导的重视,在工作中容易获得更多的支持,晋升机会更大,职业发展更为迅速,职业满意程度也相对更高(翁清雄和席酉民,2010),因此,学历对职业生涯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根据马斯洛(1954)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处于人类需求的最低层次,生理需求的满足主要依靠人们的收入,收入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对所从事的职业产生了更加积极的情感,所以,收入水平对于总体幸福感和职业生涯幸福感的提升也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人格特质。研究普遍认为,在人格因素中,外向性往往能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和满意度,与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反,工作中存在神经质倾向的个体满意度很低,往往会产生消极情感(Christensen等,1998),这将降低其幸福感。就职业生涯幸福感而言,神经质的员工一般难以承受工作变动带来的压力,较难适应不同的组织或工作岗位,在职业生涯历程中会体验到更多的挫折和消极情绪(Barrick和Mount,1991),职业生涯幸福感整体较低。尽责性高的员工在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较容易得到上级和同事的认可,尤其是容易获得上级的信任,因此,其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会更加顺利(Barrick和Mount,1991),职业生涯幸福感也会更高。
第四,情绪智力。情绪智力反映了个体在面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时对自己的行为以及情绪和情感加以管理的能力,会影响甚至部分决定个体的情绪体验(Brunetto等,2012)。情绪智力应与职业生涯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可以从人际关系、职业承诺和情绪调节三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情绪智力较高的个体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Schutte等,2001),并获得有益的结果,如较高的职业满意度和愉快的体验,所以情绪智力与职业生涯幸福感正相关。其次,情绪智力水平高的个体,能够更加明确地感知到工作中的积极和消极情绪,并形成比较清晰的职业倾向,产生较高的职业承诺(Brown等,2003),因此更容易体验到所从事工作给个人带来的乐趣。再次,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面临工作转换或职业发展受挫时,可以更好地调节自身的消极情绪,积极应对可能存在的问题(Zeidner等,2004),较少地经历消极情绪,因此会产生更高水平的职业生涯幸福感。
第五,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在无边界职业生涯时期,员工通常需要通过组织间工作流动来获得职业发展,因此,个人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作用更加凸显。有研究表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有助于个体明确职业目标和职业自我概念;制定有效的职业管理策略有助于个体在职业选择中实现人岗匹配(翁清雄,2010),也有助于个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也有研究发现,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可以提升个体对当前职业状况的满意度,增强个体在职业生涯中的自信(Claes和Ruiz,1998),使得个体在长期的职业发展中,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由此可见,自我职业生涯管理能够促进个体整个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提升个体的职业生涯幸福感。
2.职业因素。职业生涯幸福感来源于个体对职业生涯中所从事工作的长期感受,这与个人的职业压力、职业稳定性、职业决策和职业成长相关。
首先,职业压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少企业为赢得竞争优势选择了以绩效为导向的薪酬制度,员工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有的职业要面对人身安全、个人健康等方面的威胁,有的职业则要每天投入很长的工作时间,这些都增大了员工的职业压力。实证研究表明,职业生涯中的持续压力容易增强员工的焦虑感和挫败感,使员工体验到较多的负面情绪(Liang和Hsieh,2005),因此与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长期性、持续性的职业压力不仅会带来负面情绪,而且容易损害员工的健康,一些员工可能会因为这种压力而产生讨厌工作、逃离工作的消极状态(Liang和Hsieh,2005)。可以推断,职业压力与个体的职业生涯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职业压力的持续时间会影响这种负向关系。
其次,职业稳定性。职业稳定性反映了个体当前的职业和工作岗位是否连续和稳定。职业稳定是个体收入可持续的基础,也可以给个体带来舒适、积极的内心体验。在职业发展早期,个体需要通过一些工作转换来进行职业探索,此时,职业稳定与否并不是个体关注的重点,工作转换有利于个体确立良好的职业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个体的职业发展,因此在这一阶段职业稳定性与职业生涯幸福感关系较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职业生涯后期,个人职业竞争力降低,职业不稳定会对人们的职业生涯发展产生潜在的威胁(Mäkikangas等,2011),容易使人陷入紧张和焦虑的状态,产生负面情感,此时职业稳定性与职业生涯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
再者,职业决策。较高的职业决策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职业发展道路的稳定,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是对个体所从事职业的一种肯定(Arnold,1989),因此能带来高水平的职业生涯幸福感。类似的,Creed和Blume(2013)研究发现,职业决策中的妥协行为与职业生涯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在进行职业决策时,妥协会给人带来挫败感,也容易导致个体对妥协后所选职业的不满,使得个体很难有较高的工作投入,甚至产生工作倦怠,从而使得个体的职业生涯幸福感降低。
最后,职业成长。职业成长反映了个体当前的职业进展状况,当职业成长顺利时,个体不仅在工作中接近了职业目标、发展了职业能力,而且其努力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因此,职业成长顺利会使个体对整个职业生涯更满意(翁清雄和席酉民,2011),从而产生较高的职业生涯幸福感;反之,当个人的职业目标在特定企业内很难实现,个体的职业成长受限时,个体往往会对工作产生不满甚至倦怠的情绪,并且更倾向于选择离职(翁清雄和席酉民,2010)。工作不满意、工作倦怠以及存在离职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正说明职业生涯幸福感不高。另外,根据公平理论,当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时,个体易产生挫败感和消极情绪(Weng等,2010),导致幸福感较低。相反,当个体获得的回报等于甚至高于其付出的努力时,他会对当前的职业发展状况产生积极的情感,从而产生高水平的职业生涯幸福感。因此,我们认为,职业成长与职业生涯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3.组织情境。员工的职业生涯幸福感不仅受到个人和职业因素的影响,也与组织情境因素有关,相关的组织情境因素主要包括组织文化、组织支持、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等。
首先,组织文化。不同组织文化中的个体在生活满意感、情感体验、价值观等方面均存在差异(Sheldon和Kasser,2001)。据此我们认为,组织文化与员工的职业生涯幸福感之间存在联系。良好的组织文化能够得到员工的认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绩效,并使员工长期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具体来说,创新型组织文化能够为员工提供充分施展才能的组织氛围;团队型组织文化可以使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到同事和上级的支持,产生心理归属感(Ogbonna和Harris,2000)。这两种组织文化都有利于员工职业生涯幸福感的提升。而结果导向型组织文化只注重硬性的结果考核,不注重员工的个人发展,缺乏人性关怀(Ogbonna和Harris,2000),容易降低员工的职业生涯幸福感。
其次,组织支持。组织支持理论认为,组织支持不仅有利于提高工作绩效,而且有利于满足员工的情感要求(徐晓锋等,2004)。当员工感受到来自组织的支持时,一方面,他们会对组织产生感激之情,并通过努力工作和创造更高的绩效来回报组织,从而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他们会感到自己的能力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和尊重(Hutchison等,1986),从而对当前的组织和职业产生积极情感,进而体验到较高的职业生涯幸福感。当员工在工作或生活上遇到困难、职业发展受挫、职场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时,组织的及时支持可以降低消极事件对员工的影响,帮助员工确立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员工的长期发展,从而提高他们的职业生涯幸福感。
最后,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组织实施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比如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不仅能够满足组织发展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满足员工的自我实现需要(刘晓燕等,2007)。比如,组织采取有效的职业生涯管理手段和措施可以帮助员工更加清晰地确立目标,让他们感受到组织对自己发展的重视和支持,提高他们对本职工作的认识与认同,从而对他们的职业心理和行为(如职业满意度、职业承诺、工作卷入等)产生积极的影响(周文霞和李博,2006)。实证研究表明,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性的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职业生涯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快速、稳定的职业发展又能够使员工对职业生涯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Kooij等,2013)。因此,我们认为,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有助于员工获得高水平的职业生涯幸福感。
4.岗位特点。工作岗位的特点与个体的工作情绪息息相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职业生涯幸福感。
首先,工作角色。随着职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由角色压力引发的员工身心健康问题逐渐增多。工作中的角色压力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源于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两个方面。当面临不同而又存在矛盾或者不确定的角色期望,并无法进行调适和有效应对时,个体的精神就会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导致情绪资源被耗尽(Kahn等,1964),这种情况日积月累将降低员工的幸福感。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长期处于角色压力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水平会显著降低,员工甚至会产生职业倦怠和离职倾向等不良反应(Moore,1998)。因此,我们认为,过高的角色压力会降低人们的职业生涯幸福感。
其次,工作控制权。当一项工作提供较多的控制权和较大的自由度时,员工就能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和展示自己的才能,这在长期的职业生涯发展中,有利于增强员工的自信和积极情绪(Siltaloppi,2009),从而提高员工的职业生涯幸福感。相反,如果个体对自身工作的任务分配、时间安排、工作程序等缺乏控制权,就容易对工作感到厌烦,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主动性也会降低。久而久之,个体容易因在工作上的被支配而产生不满和消极情绪体验。此外,研究也表明,工作控制能够缓解工作压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Carmen等,2011)。所以,可以推断,工作控制权与职业生涯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职业生涯幸福感的影响结果
职业生涯幸福感对个体的职业态度、职业结果、工作—家庭关系以及生活幸福感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1.职业承诺。个体对职业生涯发展的主观体验和评估决定了他对当前的工作和职业的反应(Chao,1990)。根据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2004),职业生涯幸福感作为职业生涯发展中持续的积极体验,不仅具有短暂的拓展功能,还具有长期的建构功能。也就是说,较高的幸福感不仅能增加个体当前的工作投入,提升个体短期的工作绩效,而且能够使个体对当前的职业产生更强烈、更持久的认同和情感依赖。而这种对职业的认同和情感依赖正反映了个体对职业所具有的高水平承诺(Meyer等,1993)。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个体在对当前的职业或工作拥有较高的满意度和积极的情绪体验时,会对其职业产生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高水平的承诺(Goulet和Singh,2002)。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职业生涯幸福感能够提高个体的职业承诺水平。
2.职业转换。随着组织结构的日益扁平化,员工在一家企业终身就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当他们在一个组织和职业内得不到较好的发展时,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离职或进行职业转换(翁清雄和席酉民,2010)。根据Rhodes和Doering(1983)提出的职业转换整合模型,人们在体会到工作不满意和职业不满意时会产生有关离开所从事工作和职业的思考,进而产生离职和职业转换意愿。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工作满意度、职业满意度能解释离职倾向和职业转换倾向的大部分方差(Rhodes和Doering,1983)。由此,我们认为,职业生涯幸福感可以预测个体的职业转换意愿和行为。可以设想,如果人们在当前的职业中无法获得快乐,总是感到不满和烦恼,体验到的职业生涯幸福感较低,他们就很可能对当前所从事的职业产生情感排斥,产生离开当前职业的想法和行为,以便选择一个自认为可以获得更高幸福感的职业领域。因此,我们推测,职业生涯幸福感与职业转换意愿和行为负相关。
3.工作—家庭关系。工作—家庭关系是指工作因素对个体家庭的影响,主要分为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消极的冲突反应。工作—家庭促进是指个体的工作角色经历能提升其家庭角色表现,而工作—家庭冲突是指来自家庭和工作生活领域的角色压力是不相容的,工作中的角色压力妨碍了员工在家庭中的正常表现(Voydanoff,2004)。当整体职业生涯幸福感较高时,个体能够从工作中获得较高的满意度和良好的情绪体验,根据工作—家庭溢出理论(Kinnunen等,2006),工作上的这种良好的状态可以转移到生活之中,提升个体在家庭中的角色表现;而且工作上的良好进展也可以减少个体对工作角色的担忧,使个体有更多的时间来解决家庭中的问题(Voydanoff,2004),从而降低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推测,职业生涯幸福感能够增强工作—家庭促进关系,减少工作—家庭冲突。
4.生活幸福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家庭和工作中的角色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也引起了个体工作和生活质量的变化。人们一方面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努力,以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另一方面又更加注重生活幸福感的提升。根据Blauner(1964)的研究,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个体在工作和职业中的情绪感受通常也会影响到其在生活中的体验,如家庭关系、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等。关于工作与生活之间的渗透,Near等(1980)从工作与生活环境相互依赖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工作中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很容易延伸到家庭生活中。Dolan和White(2007)的溢出模型也表明,人们在工作和职业中的感受能够通过溢出效应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幸福感,更高水平的工作满意度和职业满意度能够带来更高水平的生活幸福感。这是因为,当个体在工作中体会到较高水平的满意度时,其积极情感会增加而消极情感会减少,生活意义感会增强,因此生活幸福感将得以提升(Diener等,1999)。因而,我们推测,个体的职业生涯幸福感越强,其生活幸福感就越强。
四、未来研究展望
职业生涯幸福感作为个体对其整体职业生涯经历的积极体验,对于个人成长和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关职业生涯幸福感的研究在管理实践中也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对职业生涯幸福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综合而言,关于职业生涯幸福感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应开发一套专门测量职业生涯幸福感的量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专门根据职业生涯幸福感的概念属性开发出相应的测量工具。职业生涯幸福感与工作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不应简单地将工作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应用于职业生涯幸福感的测量,否则相关研究之间可能缺乏承续性,研究结果难以进行比较和综合,不利于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Kidd(2008)对职业生涯幸福感的概念进行了很好的阐释和分析,也将其与工作中的幸福感区分开来,建议未来的研究在这一概念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开发出一套信度、效度较高的职业生涯幸福感量表。
第二,应多采用纵向研究方法。职业生涯幸福感研究更加侧重于个体不同职业经历的影响,因此横截面数据难以奏效,无法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在研究职业发展与职业生涯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时,由于两者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横截面数据无法验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要求我们采取纵向追踪的方法来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此外,职业生涯幸福感并不稳定,容易受到每天的工作与生活经历的影响并产生波动,因此,建议未来的研究采用多波次观测,以探析个体心理的短期波动及其原因。例如,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分析个体的工作压力变化、人际冲突状况对其职业生涯幸福感波动的影响。
第三,应拓展职业生涯幸福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职业生涯幸福是个体的重要追求,研究如何帮助个体通过构建积极的职业行为来充分实现职业生涯幸福,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虽然已有的工作幸福感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研究职业生涯幸福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未来关于职业生涯幸福感的研究应更加突出特殊性,更多地从个体纵向职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尤其要考察个体的工作经历、职业态度和行为等与其职业生涯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在结果变量上,除了前文关于四个结果变量的假设外,应进一步区分工作幸福感和职业生涯幸福感对个体工作态度、职业发展行为、组织绩效等的预测作用差异。此外,除了个体、岗位、职业和组织等层面因素之外,对于社会层面的因素是否也会对个体的职业生涯幸福感产生影响,如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所从事的职业在社会中所拥有的声望、地位的改变是否会引起个体职业生涯幸福感的波动等,未来的研究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同时,由于职业生涯幸福感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分别从社会、组织、职业以及个人层面出发,阐明不同层面因素对职业生涯幸福感的影响。
[1]Arnold J. Career decidedne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two-cohortlongitudinal stud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recent gra-duates[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1989, 62(2): 163-176.
[2]Arthur M B, Khapova S N and Wildercom C M. Career success in a boundaryless career world[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5, 26(2): 177-202.
[3]Brown C, George-Curran R and Smith M L. The rol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the career commitment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J].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003, 11(4): 379-392.
[4]Brunetto Y, Teo S T, Shacklock K and Farr-Wharton 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job satisfaction, well-being and engagement: Explaining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in policing[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22(4): 428-441.
[5]Carmen B and Sarah C W. What makes a creative day? A diary study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affect, job stressors, and job control[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1, 32(4): 589-607.
[6]Chao G T.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areer plateau:A comparative analysi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0, 16(1): 181-193.
[7]Christensen K A, Stephens M A P and Townsend A L. Mastery in women’s multiple roles and well-being: Adult daughters providing care to impaired parents[J]. Health Psychology, 1998, 17(2): 163-171.
[8]Claes R and Ruiz-Quintanilla S A. Influences of early career experiences, occupational group, and national culture on proactive career behavior[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98, 52(3): 357-378.
[9]Creed P A and Blume K. Compromise, well-being, and action behaviors in young adults in career transition[J].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013, 21(1): 3-19.
[10]Dolan P and White M. How can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be used to inform public policy[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 2(1): 71-85.
[11]Fisher J W, Francis L J and Johnson P.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correlates of spiritual well-being among primary school teachers[J]. Pastoral Psychology, 2002, 51(1): 3-11.
[12]Goulet L R and Singh P. Career commitment: A reexamination and an extension[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2, 61(1): 73-91.
[13]Hergenroeder H and Blank 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 adults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A pilot study of a randomized sample[J]. Developmental Medicine & Child Neurology, 2009, 51(5): 389-396.
[14]Horn J E, Taris T W, Schaufeli W B and Schreurs P J. The structure of occupational well-being: A study among Dutch teachers[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4, 77(3):365-375.
[15]Kidd J M. Exploring the components of career well-being and the emotion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career experiences[J]. 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 2008, 35(2):166-186.
[16]Kinnunen U, Feldt T, Geurts S and Pulkkinen L. Types of work-family interface:Well-being correlates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spillover between work and family[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6, 47(2): 149-162.
[17]Kooij D T, Guest D E, Clinton M, Knight T, Jansen P G and Dikkers J S. How the impact of HR practices on employee well-being and performance changes with age[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23(1): 18-35.
[18]Liang S C and Hsieh A T.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career development and job burnout among flight attendants in Taiw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viation Psychology, 2005, 15(2): 119-134.
[19]Mäkikangas A, Feldt T and Kinnunen U. Warr’s scale of job-related affective well-being: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its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s with work characteristics[J]. Work & Stress, 2007, 21(3): 197-219.
[20]Mäkikangas A, Hyvönen K, Leskinen E, Kinnunen U and Feldt T. A person-centred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of job-related affective well-being: A 10-year follow-up study[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1, 84(2): 327-346.
[21]Schaufeli W B and Bakker A B. Job demands, job resour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burnout and engagement: A multi-sample study[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4, 25(3): 293-315.
[22]Siltaloppi M, Kinnunen U and Feldt T. Recovery experiences as moderators between psychosocial 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occupational well-being[J]. Work & Stress, 2009, 23(4): 330-348.
[23]Weng Q, McElroy J C, Morrow P C and Liu 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growth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0, 77(3): 391-400.
[24]Wilson W R.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7, 67(4): 294-306.
[25]Zeidner M, Matthews G and Roberts R 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the workplace:A critical review[J]. Applied Psychology, 2004, 53(3): 371-399.
[26]谭贤政, 卢家楣, 张敏等. 教师职业活动幸福感的调查研究[J]. 心理科学, 2009, 32(2): 288-292.
[27]王佳艺, 胡安安. 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6, 28(8): 49-55.
[28]翁清雄.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对职业决策质量的作用机制[J]. 管理评论, 2010, 22(1): 82-93.
[29]翁清雄, 席酉民. 动态职业环境下职业成长与组织承诺的关系[J]. 管理科学学报, 2011, 14(3): 48-59.
[30]吴伟炯, 刘毅, 路红等. 本土心理资本与职业幸福感的关系[J]. 心理学报, 2012, 44(10): 1349-1370.
[31]周文霞, 李博.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与工作卷入关系的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06, 9(2): 6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