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立德·莱得访谈
2014-06-10
ARTTIME:正如您刚才解释的,您穿插了一些事实和虚构的东西,这在不少作品和The Atlas Group (1989-2004)中也是为众人所知,而往往也有不少人对此提出异议。您是怎么想到要把真实的找来的物件和虚构的物件,图片和文字放在一起?您又是怎样看待纪实和虚构的关系呢?
WR:对于 The Atlas Group(1989-2004),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混淆”事实和虚构的成分。我只是在处理不同的事实而已。有些事实存在于史实中,另外一些存在于虚构的故事中。也可以说在这个项目中,不少事實是从虚构中浮现出来了。在我脑子里,当我开始着手做对于汽车爆炸历史的整理工作时,我希望不管花多长时间也要仔细研究每一次汽车爆炸,一共有3641起。我从未想过我只研究一起爆炸案就罢手了。所以,这意味着我的工作将花去我整个人生。我和Tony Chakar还有Bilal Khbeiz 一起花了两年时间研究第一起汽车爆炸案。按照这样的速度,我们需要7282年时间来完成对所有这些车爆案对研究。从某种角度,我也就可以想像人们如何在余下的7000多年被此问题困扰。那么这些汽车爆炸事件是否真的可以缠绕某些人心绪长达7000多年之久?或许不会,至少历史上没有实现,只是虚拟的呈现而已。但是我可以想像其它的事件可以困扰人们以致几百年之久,比如对于某个圣人或预言者的杀害。不管怎样我是在想像某种可以拉长到7000年之久的事件。但是我相当怀疑或者几乎肯定我研究的汽车爆炸事件并非这样的事件。
ARTTIME:从2004年后,The Atlas Group 似乎销声匿迹,什么事件让你结束了这个项目?您是否从此由集体项目转而专注于自己的个人创作和项目?
WR:我不会说The Atlas Group (1989-2004)项目已经结束。我只是不再主动生产这些构成这个项目的前提设想,比如暴力,艺术和文献等。我仍然不断的组织文献,而后也放入The Atlas Group(1989-2004)项目中。但这些文献通常是发生在1989年和2004年之间的,也算是这个项目的开始和结束。我不再感兴趣于通过心理创伤来思考暴力这样的概念,所以就不再感兴趣于组建这个构成The Atlas Group 项目的核心。在某个时期,我开始考虑这个艺术实践是否可以通过反复的函数和电脑程序进行编制。程序员们可以通过对于大量的数据库的分析,从而研究出某种函数公式把这些数据从繁杂的组合变为清晰的画面;从没有关联的数据变得有规律和轨迹可循。对我来说,似乎如今很多艺术实践活动都是和这种对于大量数据的研究和整合有关的方式进行的,也是电脑科学的方式。我开始觉得The Atlas Group 就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或许是不太寻常的数据库,但仍然只是数据,而整个项目的结构是在这个“黎巴嫩内战”的巨大数据库当中找到某种形态并归纳一些动向。现在我不再觉得这种方式可以产生更多新的东西,虽然所掌握的数据可能比以前更繁复更具体也更多元化,但这已不是我感兴趣的工作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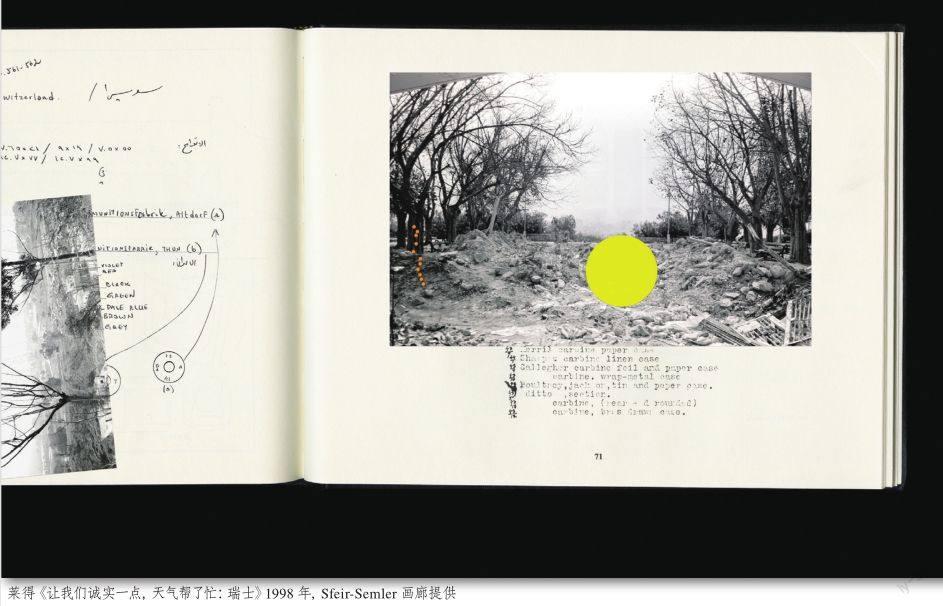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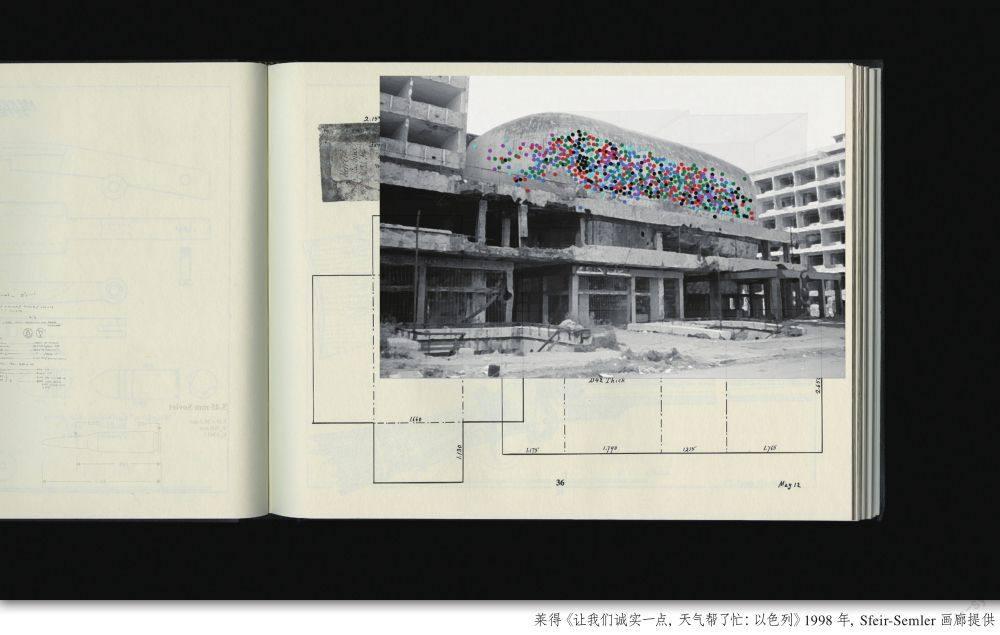

ARTTIME:我想你的作品被公认为有不少政治倾向和敏感性,您有否成功的在黎巴嫩或中东其它地方展示过您的作品呢?
WR:至于 The Atlas Group 在贝鲁特,我是通过讲座的形式展示这个项目的。我也曾在一个群展上展示一个系列,叫做 The Sweet Talk: The Hilwe Commissions。但我还没有以完整的方式在黎巴嫩展出这个项目。我曾在墨西哥城、柏林、里斯本、伦敦、巴黎等地全面完整的展示这个项目,但没有在贝鲁特。而其实也曾有过机会可以在贝鲁特展出,只是我没有办法去做。总觉得一些事会发生,而且会很糟糕,完全,但是也无法预知是什么。我害怕的是展览可能完全没有办法被看到。我可以想像有一些人走进展厅,“我还以为这里有个艺术展览”。然后我回答,“是啊,这就是。你看不到?”“不,看不到。”
ARTTIME:在一次采访中您提到曾经拒绝了一个在贝鲁特 Andree Sfeir画廊新落成的空间的一个展览,您说的就是这个完整展示The Atlas Group 的机会吗?
WR:是的。我觉得所有构成这个项目的图片,视频,文字和雕塑都会奇怪的受到影响,所以如果在这个空间展示这些东西,它们只能起到1/100的效果。我觉得作品一旦出现在贝鲁特,将会完全被压缩。同时,我又觉得,或许这会显得和刚才说的完全相反,我需要把这些展示的东西压缩到1/100的比例。这两种自相矛盾的想法,让我比较疑惑,但这种感觉可以说非常强烈,以至于我拒绝了这个2005年在黎巴嫩展示的机会。
几年前,我觉得我的艺术作品更多的被非物质的东西影响。我也觉得另外的黎巴嫩艺术家似乎也有这样的倾向。这种感觉,和在工作室完成的一些形式上的尝试让我开始了现在这个和阿拉伯艺术史有关的项目,这个项目叫做Scratching on things I could disavow (《擦去那些可以让我抵赖的事情》)。
ARTTIME:您可以说说近期卢浮宫项目的来由吗?和您对于完成这个项目的一些感受?我知道这包括了一系列的展览,现在这些展览进行得怎样了?
WR:这次合作其实来得比较自然。我曾和Marcella Lista 有过合作。她邀请我去和Jalal Toufic 聊一下,那是2011年,作为卢浮宫的一个公共项目,她当时和Dominique Cordellier一同筹划的展览Revenants并行的一个项目。当时我已经开始我的新作品/项目-《擦去那些可以让我抵赖的事情》(Scratching on things I could disavow),而这中间一部分就是关于伊斯兰当代艺术崛起和建构的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对于法国政府在阿布扎比的卢浮宫计划很是感兴趣。而且我听说法国政府和阿布扎比达成协议,作为这次项目的一部分,巴黎卢浮宫中的伊斯兰艺术品中的一些物件会去阿布扎比展出。我一开始只是想去对这些物件做一个拍摄记录,哪怕只是放在箱子里。我问Marcella是否能让我去看看。然后,事情就一件接一件,从一次简单拍摄到了一个展览,一本书,还有录像。
ARTTIME:你是否感觉到当今西方国家忽然对于阿拉伯国家艺术品有了浓厚的兴趣,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比如卢浮宫和古根海姆先后在阿拉伯地区建立美术馆分馆,更多的阿拉伯国家的当代艺术家也受到瞩目。
WR:我觉得西方国家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兴趣对我来说并非很吃惊,是阿拉伯国家自身对于阿拉伯,古典、当代、伊斯兰等等艺术品的兴趣让我比较激动。这些年阿布扎比,卡塔尔和贝鲁特在这方面的发展和变化都让人吃惊。比如说在阿布扎比和萨帝亚特岛同时将建成新的卢浮宫,古根海姆美术馆,国家美术馆,表演中心,海洋博物馆,还有纽约大学分校。而这些都由当今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来负责设计,面对这一切,你会想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酋长国的酋长和领袖们(Emirati Sheikhs and Sheikhas)突然间对视觉艺术感兴趣了?对美术馆画廊着了迷?还喜欢上了基金会、艺术学院、艺术收藏、杂志、报纸、各种奖项甚至艺术家驻地计划。(而这整套对艺术界的基础建设是伴随其它行业的基础建设的,包括制造业、医疗、金融等其它行业)。当你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想像着面对的是两个具有特色的脸孔。第一,是这些统治者并非真正热爱艺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和他们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如果他们需要另一个卢浮宫来帮助他们和法国政府的关系以获得更多的军事支持,花个几百万又算得了什么?这样想似乎太愤青了。那么另一种可能的脸孔,却不是那么愤世嫉俗。所有的这些对于文化和艺术的投资是真心想要学习西方社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民主,而在走到这一步之前让他们的子民们品尝西方社会的滋味。所以这一代的阿拉伯国家统治者是在用30年时间实现西方社会用了100年时间来建构的文明社会。当年是谁建立了大都会博物馆?不正是19世纪末掠夺和控制美国经济和政治的一群社会有权势的贵族吗?那么当年的美国式酋长通过建成大都会把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纽约,为什么今日的阿拉伯酋长就不能一试?
ARTTIME:您可以简单谈一下Gulf Labor 组织都成立吗?您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吗?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一个艺术家自发的组织?它是否会演变成如The Atlas Group 类似的艺术项目?
WR: Gulf Labor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集体项目和艺术家组织,在不同时期加入和参与的有不少知名艺术家:Emily Jacir, Sam Durant, Hans Haacke, Ashok Sukumaran, Shaina Anand, Andrew Ross, Beth Stryker, Haig Aivazian, Naeem Mohaiemen, Doug Ashford, Mariam Ghani, Rene Gabri, Ayreen Anastas, Tania Bruguera, Guy Mannes-Abbott 還有很多其它成员。关于组织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在网站上找到更多的信息 http://gulflabor. wordpress.com/
ARTTIME:更具体一点,2011年3月Gulf Labor 组织了艺术家联合抗议,针对阿布扎比古根海姆美术馆的一些人权问题,曾一度引起轩然大波。而在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艺术家们也不断加入和发起类似的抗议和社会性活动,很多时候这些社会活动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行为艺术作品。您是怎么看这一趋势的?而这是否会成为这个艺术家组织或者您创作的一个方向?
WR:我想说到目前为止,Gulf Labor 还不是一件艺术作品或艺术项目。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能会找到契合的时机、概念和事件,并且和我们参与者的作品有关联性的时候。但是迄今为止,它的存在和运作都还不能被认为是艺术创作或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