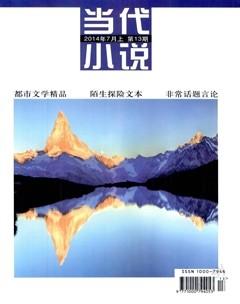柳棺
2014-05-30项中立
项中立
多年前的那个黄昏,我奶奶忧伤地为我伯父打点着远行的行囊——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包裹,包裹着一双纳帮千层底的布鞋。我奶奶打算把包裹的带子系成活扣,这样我伯父解起来的时候要容易些。但是她总是出错,她颤抖着手,把包裹的带子一次又一次地系成死扣。我奶奶觉得,这是件不祥的事情。
村口老柳树底下,又响了两声卡车喇叭。
我奶奶终于系好了包裹。她把包裹挂在我伯父孱弱的肩膀头,然后,她说:儿啊,动身吧,人家又在催了。
我伯父趴在炕沿上一动也不动。他的水淋淋的小脸,深深埋在他的掌心里。
我奶奶又说:儿啊,去跟他们挣口饱饭吃吧,好歹强过在家里挨饿……
我伯父突然就跪在我奶奶面前:娘,你别逼我去。我情愿在家里饿着……
我奶奶好像无话可说了。她的眼泪,在瞬间弥漫了瘦削的脸颊。
这时候。我爷爷终于站了起来——整个黄昏,他都像一只浑浑噩噩的老猫一样,蹲在门口抽烟袋。他的烟袋杆有一尺半长。粗粗的紫铜管,岫玉的烟锅,像一把精致的小榔头。那时候,我爷爷这杆烟袋可以从南边农场换5斤薯干,或十斤稻糠。家里的东西,几乎都拿去换了吃的,惟有这杆烟袋,我爷爷舍不得——我爷爷提着他的烟袋杆,在堂屋里转了一圈,又不紧不慢地走进里屋来。他的样子让人看起来是在找什么东西。他甚至查看了屋门后面。然后,我爷爷极其从容地站到了我伯父身后,冷不防举起烟袋杆,照我伯父的后背抽下去……
我小姑一直是靠着门框的。我爷爷的沉稳叫她起了疑心。她在机警地观察着我爷爷的同时,心中做着某种不得已的打算。所以,当她看到我爷爷举起他的烟袋杆时,我小姑像一只绝望的小鹿,用她单薄的身体,毫不留情地撞向我爷爷。我爷爷猝不及防,趔趄了一下,歪倚在炕沿上……但这一切都晚了半拍,在我小姑撞倒我爷爷之前,那根烟袋杆,已经在我伯父背上,奏出了沉闷的不动听的音乐。我伯父凄厉地叫了一嗓子,夺门而逃……
我奶奶后来说,她清楚地看到我伯父背上,隆起了血紫血紫的一条。
我奶奶尾随我伯父冲了出去。但她的脚力怎么比得上我伯父呢?当她赶到老柳树底下时,载着我伯父他们的卡车,已绝尘而去。
我奶奶从村口回来,做得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爷爷的烟袋杆丢进石头井里,害得我爷爷不得不潜到井里打捞。我爷爷素来水性不好,险些淹死在井里。
但是,六年之后,当我爷爷得知我伯父已经成了国家在册的筑路工人的时候,我爷爷简直得意忘形。我爷爷说,是他果断地一抽,把我伯父抽成了全村惟一一个吃国家粮的人!我爷爷愈加爱惜他的烟袋。那时我爷爷的肺病已相当严重。早戒了烟,只是那根烟袋,我爷爷从不离身。相比之下。我爷爷更热衷于跟别人讲述他抽我伯父那个片段。我爷爷说他本来想找根棍子的,他甚至找过门后边,没有,他才临时决定改用烟袋杆(我得说一下,我爷爷是个杀猪匠。古老的杀猪方法,是先用棍子把猪抽成半死,然后,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锻炼了我爷爷过人的膂力。即使在饥饿的困扰下,我爷爷的膂力仍然厉害)。我爷爷说,他当时只用了七成力气。这恰到好处的叫我伯父既感到了疼痛难忍,又不至于废掉。我爷爷说,倘若拿捏不好,误加一成力气,我可怜的伯父,怕当时就废了……
只是。我爷爷到死都没有想到,他那一烟袋杆子,也抽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遗憾——我爷爷在弥留之际,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小姑,还有很多家族里的晚辈,都守在他床前,但是我爷爷迟迟不肯咽下最后那口气。他的浑浊呆滞的目光,一次次地挤过人们之间的缝隙,迎候在空寂的门口。大家都知道他在等我伯父。那年月。一封信走到遥远的筑路队,至少得个把月。我爷爷最终没有见上我伯父一眼,他遗憾地走了。
我伯父赶回家来时,我爷爷坟头已是荒草萋萋。我伯父长跪不起。他采了很多安魂草插在我爷爷坟头。那种淡蓝色的小花朵,在清风中娇憨地摇曳不止,我伯父积在心间多年的怨恨,也被它慢慢地摇成了一缕清风。
我伯父最终原谅了我爷爷当年的暴戾。
我伯父他们离乡远行之后,拐木匠的闺女阿秀总是喜欢在黄昏时站在村口老柳树底下,向着那条路上遥望。没有人清楚阿秀从哪一天,开始了这样辛苦的守望,也没有人知道阿秀究竟为谁而守望。支离破碎的残阳。叫阿秀的脸色看上去憔悴不堪。她的头发干枯凌乱,晚风吹拂着,有一绺遮住了眺望的眼睛,她也不去拂一下。她的样子,像一尊哀怨的塑像,任谁看了,都不免心生凄凉。
我奶奶在无意间看过一回阿秀守望的样子,便固执地拒绝在黄昏时候走近村口的老柳树。
“那样子好可怜呢!”我奶奶跟我小姑说。那时候,我小姑正准备嫁到南边农场去,我奶奶正一针一线地为她缝制着嫁衣。“秀丫头应该比你大两岁吧?我记得她和你哥同岁。要不是这样魔怔,秀丫头也该嫁人了……”我奶奶性格柔弱,她这样说着的时候,就为可怜的阿秀淌下了眼泪。
阿秀每天要守候到那条路在暮色里模糊不清的时候,才默默回家。然后,她点着灶火,给拐木匠煮饭。拐木匠只做棺材。他每天都辛苦地工作着,但是,他的院里通常只有一口棺材。他不停地把这口棺材拆卸掉,然后,再安装好;再拆卸掉,再安装好,直到这口棺材卖出去。棺材不是好卖的东西,所以,拐木匠和他闺女阿秀的日子,总是过得清贫。
拐木匠小心翼翼地吸溜着稀饭。告诉阿秀,花媒婆刚走,提得是前村王家的老二。
阿秀不响。拐木匠就变得胆怯起来。他知道,倘若他再说下去,阿秀一准会躲到屋外面去。因此,拐木匠便专心致志地吸溜着稀饭。他的闺女阿秀,目光呆滞地凝望着他搭在碗沿上夸张地嘟着的嘴唇。沉默的夜晚,就这样一如既往的开始。
拐木匠终于缓缓地喝完了稀饭。接下来,他响亮地咂着牙花子,同时,他的目光,小心翼翼地搭在默默收拾着碗筷的阿秀脸上。唉!这孩子日见消瘦了,她的尖尖的颧骨凸出来,眼窝深深凹下去。她的面容。酷似她娘临死时的面容……拐木匠的心头,突然掠过一阵不祥的惊慌。拐木匠开始埋怨自己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他死去的女人。
拐木匠愈发害怕黄昏这个时候了。他在辛苦地拆装着棺材的时候,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抬起来。望下天上的日头。那日头每往下落一寸,他的心就跟着沉一截儿。当他手上的木板被涂上一层淡淡的橘黄色时。夏房的门就会轻轻地响一下,跟着响起阿秀有些拖沓的脚步声,嚓嚓地。每一下都如同粗粝的砂纸打磨在拐木匠心上,疼了一下又一下。拐木匠停下手里的活计,他说秀啊,再这样下去。你会垮掉呀!阿秀没有停下,她甚至都没有缓一缓脚步。她像一个梦游者那样,毫无反应地自顾从拐木匠面前走过去,走向暮色中的村口……
直到有一天,村口的老柳树被一记炸雷劈成两截,阿秀才结束了她的孤独而辛苦的守望。这件事发生在我伯父他们离乡之后的两年多。这一年,粮食丰收,饥饿远离了人们。当年远行的人已经陆续还乡。死在外头的人,国家也发放了抚恤金。惟独我的伯父,既没有活着回乡,也没有抚恤金。活着回来的人说,我伯父一个人在另一个更遥远的筑路队。筑路队开山筑路。环境险恶。每天都有人死掉,而搞不清死者籍贯的事是常有的事。我们全家都认为我伯父早已成了漂泊他乡的孤魂野鬼。我奶奶一边哭,一边毫不留情地指责我爷爷当年的狠毒;我爷爷像当年一样,蹲在堂屋有一搭没一搭地抽他的烟袋。那时候,我爷爷抽的不是干花生叶儿或干倭瓜叶儿了。他抽的是地地道道的关东大烟叶,刺鼻的烟味在屋里萦绕,叫人横生一种难以压抑的急躁:我的小姑靠着门框,她的目光充满恶意。在我爷爷的铜烟袋杆上钩来钩去。我小姑后来说,她很想冲过去夺下那杆抽走了我伯父的烟袋杆,然后折断,再扔到石头井里。但我小姑发现我爷爷的后背像瓢虫一样弓着,一下一下地抽动不止,我小姑觉得,那也是一种叫人揪心的可怜相。
我奶奶选了一个晴好的黄昏,到村口老柳树底下给我伯父烧纸。那儿是我伯父当年离乡远行的地方。我奶奶固执地认为,在那个地方烧纸,我伯父漂泊的亡灵便能够听见亲人的呼唤。我奶奶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凄凉地呼唤着我伯父的乳名:根子。我的儿啊,快回家吧,娘在老柳树底下等着你呢……那天。我奶奶的手抖得厉害,划了大半盒火柴,才点着了纸钱。顷刻间,有无数只哀怨的黑蝴蝶从火堆里飞出来,低低地徘徊在老柳树底下。
一直麻木地站在老柳树底下的阿秀,突然地撕心裂肺地嚎哭起来。她一边疯狂地扑打着那些黑蝴蝶,一边怒斥我奶奶:你是在咒他死吗?根子哥他没有死啊!大柳树还好好地活着,根子哥怎么会死呢……我奶奶劝不住阿秀,只好抹着眼泪独自回到了村里。
那场大雨,在我奶奶回到村里不久,突然地铺天盖地而来。毫无征兆的暴雨,叫很多人猝不及防,心惊肉跳。跟着,一记炸雷,同着一道亮闪,凌然劈下。之后,天和地瞬间跌进一片寂静和空茫之中。我奶奶在迷糊了几秒钟之后,突然拽了我爷爷,朝村口狂奔而去……
老远。他们就看见村口的老柳树不见了庞大的树冠,半截光秃秃的树桩,像具无头尸,恐怖地站在雨幕里。
数分钟之后,我奶奶怕见的情景真真切切地呈现在她眼前:阿秀栽倒在地,她脸上焦糊一片……
但是,阿秀没死。她只是被雷火灼伤了面孔。伤愈之后,阿秀脸上留下厚厚实实的疤痕。曾经美丽的阿秀,变得丑陋不堪。从此,拐木匠家的门槛,再没有媒婆踏过。这叫拐木匠伤心至极,每天他的院里除了拆卸棺材的琐碎的响动,还多了拐木匠沉重的叹息。
邻村的瞎小,是在一天的午后摸索进拐木匠家的。老柳树被雷劈死之后,丑陋的阿秀和我奶奶一样,相信我伯父已不在人世。她已是很多天没有出过夏房的门。夏房门被她从里面反锁,连拐木匠都进不去,瞎小只能站在窗前,说话给她听。
瞎小说,美丽的阿秀,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见你,是四年前,在村外面的一片荒草地里。那时候,我已被饥饿折磨得站不起来。我匍匐在草地里。我手里攥着一束开得艳丽的打碗花。我正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把它吞下去充饥。你知道,打碗花是有毒的,尤其能够致人瞎掉眼睛。满地的野菜都被人挖绝了,只有一簇簇的打碗花茂盛地开着。
我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你。你和另一个男孩子挽着手——或许,你们那更应该叫做互相搀扶,步履蹒跚的,由远处走近了我。你们当然不会发现我。我被饿得瘫伏在打碗花丛中,打碗花严密地隐藏了我。
你们在我面前不远处,突然发现了一棵被众多目光漏掉的野菜根。你们欣喜若狂。小心翼翼地扒开土壤,尽可能地保留住它的完整和长度。你们把它捧在阳光下,久久地端详。那根肥硕的野菜根足有半尺多长,像条白生生的人参,令人眼馋。我伏在打碗花丛中,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后来,那个男孩子小心翼翼地撸掉了野菜根上的土渣,把它十分庄重地捧到你面前。你笑着把它又推给了男孩子。你们这样推来推去地重复了很久。最终,男孩子把菜根分成了一大截和一小截。他自己嚼掉了一小截,那一大截给了你。你在津津有味地嚼掉那一大截之后,幸福地把头靠在他肩上。你的脸在阳光里美丽而恬静。后来,我打消了嚼掉那束打碗花的念头。我怕我的眼睛一旦瞎掉,再也看不到你的美丽了!
再后来,我参加了远方的筑路队,在一次放炮开山中,被一块炸飞的石头击中眼睛。我的眼睛还是瞎掉了。
现在,人们都说你被雷火烧得丑陋不堪,但是我想象不出你变丑的模样。在我的心目中,你永远都是那个美丽的阿秀!
阿秀,美丽的阿秀。我想娶你!
……
拐木匠听得泪流满面。
瞎小总共来过七次,每次都把话这样说一遍。瞎小说完第七次,夏房里有了阿秀低低的哭声。
拐木匠说:秀啊,嫁了吧,瞎小是诚心的。
阿秀说:嫁了可以,爹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拐木匠说:嫁妆吗?秀啊。你是要绸呢缎呢?
阿秀说:我不要绸,也不要缎。我只要爹把村口那半截柳树桩。做成口棺材。
这叫拐木匠犯了难。棺材,拐木匠是有本事做的,但是嫁闺女赔口棺材,是件不吉利的事啊!好在瞎小不在乎,瞎小说棺材是镇宅之宝。既然瞎小不在乎,拐木匠也就乐得这样做了。他把村口的半截柳树桩锯回家。又破成寸半厚的板子。花上四天工夫,做成了一口漂亮的柳棺。他把柳棺漆成庄重的枣红色。还罩上了一层亮晶晶的清油。阿秀出嫁那天,拐木匠借了一套马车,把阿秀和那口柳棺。一同送到了邻村瞎小家。
我伯父在离乡六年之后。突然还乡。
那个冬天的雪,像是疯掉了。从初一飘到了十五。雪深处,齐腰;地上没有了路,人要出门,需用铁锹临时开道。那时候,我才出生三四个月大。我每天安静地伏在我娘怀里,吃奶,睡觉。但是在某一个雪天,我突然反常地大哭不止。我哭得声嘶力竭,从早晨一直哭到黄昏。身子都哭青了。一家人都被我哭得心惊胆战,预感到将有什么大事发生。我爷爷说我“搅灾”。我爹则坚持认为是我身体的某个部位不自在。我的哭声,终于在那个雪人“滚”进屋的同时,戛然而止。所以,我爹的眼睛才愿意从他儿子身上离开,去注视那个狼狈的雪人。我爹头一眼居然没有认出那个雪人就是我的伯父。我爹愣愣地问:你是谁?雪人抖抖身上的雪,脱了皮帽,亮出个黝黑的伤痕累累的头脸,说,兄弟,我是你哥根子呀!我爹又愣愣地瞅了一会儿,才确信雪人没有撒谎。
我爹和我伯父紧紧抱做一团,失声痛哭。赤裸的放纵的男人的哭声。像沉闷的雷,在屋子里滚撞,终于撞开了窗户,奔荡在空寂的雪原上。
我爹说:哥你还活着?
我伯父说:死过几次,但最后都缓了过来。
我爹说:娘都给你烧过纸钱了。
我伯父说:我一次也没有收到呀。嘿嘿。
那天晚上,哥俩盘着热炕头,喝光了一坛包谷酒。包谷酒是我爷爷自酿的。我爷爷从不喝酒,却有个酿酒的习惯——我爷爷做杀猪匠的时候,每次给猪开膛破肚之前,必含一口酒,喷在下刀的地方。我爷爷至今搞不明白这样做的益处,但师傅是这样教他的,同时。师傅还捎带教了他酿酒的方法。后来,我爷爷不杀猪了。酿酒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那天晚上,我爹和我伯父喝到鸡叫二遍,他们都醉得不浅。我伯父像个放赖的孩子。四脚八叉地仰在炕上,泪流满面。我伯父说,六年来,我做过多少次回家的梦啊!梦见自己这样躺在家里的炕头上,暖烘烘的。兄弟,这不是梦吧?我爹使劲拧了一把自己的腮,发觉疼着,就说,哥,不是梦,是真的!我伯父沉默了一会儿。喃喃地说,不是梦吗?哦,这一次好像不是……回家的梦,我都搞不清是真是假了。有时候,我在梦里都提醒自己,是在梦里,可我还是赖着梦境不愿醒过来……醒过来,就什么也没有了……爹,娘,兄弟,小妹,大柳树,还有……还有……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寒冷的工棚。像刮骨刀一样凌厉的山风……兄弟,你根本想象不到荒山野岭上的冬天有多冷。我们在半山腰凿炮眼,抡锤和掌钳要轮换着来的。抡锤的费力气,还要不停地运动,抗寒一些;而掌钳的姿势固定,不能动弹,时间久了,血就冻凝了……王小开。那个英俊的河南小伙子。才十六岁,抡不动十八磅的大锤,更多的时候是掌钳,那年冬天,山上出奇的冷,十六岁的王小开,在掌着钳的时候,不动声色的就冻死了——“死”这个字,在筑路队是犯忌的,我们不说“死”,说“成”。王小开“成”的时候,始终是一种蹲着的姿势。他脸上漾着很受用的笑意。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柄钢钎。我们从他手里拿下钢钎的时候。他的手指。齐刷刷地散落……王小开是我们队上“成”掉的最年轻的一个。前年冬天,我们四十三个人被派上了一座叫“腰带山”的山。我们的工作是凿出四万多个炮眼。我们两年半没有下过山。我们四十三个人最后只剩下十七个,有二十六个人“成”在了腰带山。我们把他们葬在了山坡上,紧挨着我们的工棚。每天收工回来,我看见他们长满荒草的坟堆,就想象他们孤独的灵魂在荒山野岭游弋……我自己也差点“成”在腰带山……兄弟你看我这腿,折过两次,我的头,被炸飞的石块击中,落下的疤痕……有一次我昏迷了三天三夜,我是被隆隆的炮声震醒了的。我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
“哥,你怎么没早点回家呢?”
我爹早已泣不成声。
我伯父说:“我生爹的气。我发过誓。到死都不见他。”
那天夜里,我爹和我伯父躺在炕上,说一阵,又哭一阵。我爹后来告诉我,天快亮的时候,我伯父才睡着了。我伯父在睡着的时候,他眼里还在不断地涌着眼泪。
按照我伯父的计划,他要住上一段时间才回筑路队。但是第二天。我伯父在拜望过族里的长者之后,突然决定次日就赶回筑路队。那个下午,我伯父蹲在炕沿上一言不发,他只是接连不断地抽着他从筑路队带来的香烟。屋地上躺满了他胡乱扔掉的长长短短的烟蒂。
那天晚上。我伯父突然失踪。我爹找遍村里他能去的地方。终于在村口曾经生长过大柳树的地方,找到了我伯父。那儿是他当年离乡远行的地方。
我伯父孤独地坐在雪地里。他已经吸完了他带来的所有的香烟。我伯父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面对我爹的出现,没有丝毫反应。我爹陪我伯父坐了大半夜。他们相对无言。其实,我爹已经感觉到我伯父选择这个地方独坐别有隐情。我爹只是不敢细问,他怕触动我伯父藏在心底的隐痛。
天亮之后,我伯父再次离开家乡,回到筑路队。像当年一样,我伯父仍是在村口上车。我爹和我娘,还有我小姑和我爷爷,把他拥送到村口。我爹说,哥你不回筑路队不行吗?眼下家里也不挨饿了。我伯父笑了笑(他居然笑了笑),说,我现在是国家在册的筑路工人了,怎好说不去就不去呢?我小姑一直是泪眼汪汪的。但她的目光偶尔碰到我爷爷时。立刻变得犀利和充满恶意。对此,我爷爷却浑然不觉。他夸张地挥舞着他的烟袋杆,大声地呼叫着我伯父的乳名,根子,记着过两年就回家看看啊……
这以后。我伯父每隔两年探一次家。伯父来时,捎回许多域外的新鲜物件,伯父去时,带走很多家乡的土特产,塞满大大小小的包裹,似乎连家乡的沙土,也想带些走。
我七岁那年,因为伤腿的缘故,伯父在家乡住了整整一个暑期。这是伯父在远行之后的大半生中,住家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七岁的记性相当不错。所以我能够牢牢记住那个暑期,我与伯父朝夕相处的情景。或许因我是家里惟一的男孩,我在伯父面前较我的两个妹妹明显受宠。伯父嗜酒。伯父喝酒时总要倒一小杯给我,然后,慈爱地欣赏我屏住呼吸,一千而尽的架势。被烈酒呛出眼泪的我,会得到伯父的赞许:好样的!就是比你妹妹们厉害!我的两个年幼的妹妹因此对伯父很有意见,曾经噘着嘴,撵伯父快回他的筑路队……
那个暑期,伯父几乎每到黄昏时,都要带我去村口那个生长大柳树的地方坐一坐。我出生时。大柳树已不存在,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一棵柳树,是伯父把我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我。
“是这里,你看——”
伯父用手指挖走厚厚的沙土,一个枯朽的柳根就露出来。伯父说这就是那棵柳树的树根。伯父的目光突然凝重起来,嘴角浮着浅浅的笑纹。伯父的心神,一定是回到了有柳树存在的年月。伯父说,那棵柳树很是粗壮,要两个人手牵手才能合抱过来。那时候,村里的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常常在黄昏的时候。相约柳树底下。他们喜欢手牵着手,合抱那棵柳树。粗大的柳树阻隔了他们的目光,谁也看不见谁,但他们的手紧紧牵着,相互感觉到对方的体温和心跳。男孩子在树这面说。大柳树作证,女孩子在树那面说,大柳树作证……
阿秀嫁给瞎小的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瞎小欣喜若狂。满街游走,不慎掉进石井,溺水而死。出人意料的是。阿秀没有用柳棺成殓瞎小,她请拐木匠另打了一口松木棺材。松棺比柳棺好,有人说,阿秀对得起瞎小。也有人摇着头说。也未必。阿秀不用柳棺成殓瞎小的背后,一定另有隐情。阿秀不去分辨,她只是一如既往地每天将柳棺擦拭一遍,每年罩一层上等的清油,红亮红亮的柳棺。就那样沉沉稳稳地卧在堂屋,许多年。
阿秀的儿子叫成柱。成柱和我是中学同学,我们一块儿念了三年书。他是个寡言少语的学生,成绩也一般,也不热衷班里的事情,若不是因了他娘常年侍弄一口棺材这件奇事,我压根儿注意不到他。在我的意识里,棺材是个不祥的物件,它不应该跟活着的人有任何关联。因此,我对这件事充满好奇,有意无意地接近成柱。后来,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中学三年,我是成柱惟一的朋友。
某一个星期天。我终于受到成柱的邀请(他从不邀请任何同学),去他家玩。成柱的家,算得上那个时代比较清贫的家庭。房子是土坯垒成的,草灰墙皮,脱落得斑驳陆离,像懒汉光头上的疤瘌疮。小格子的窗户,窗纸糊了一层又一层,将多半天光挡在了外面,屋内便黑暗得如同深深的洞穴。堂屋里,稳稳当当地停放了一口红亮红亮的棺材。有一个干瘦的女人,不紧不慢地,拿一块干净布片,仔细擦拭着它,棺面净得纤尘不染。那个女人,满脸的栗皮色的疤痕,丑陋而恐怖。我乍一见,吓得一跳,我想,这样丑的人,应该躺在棺材里面更合适一些。
在我看女人的同时,女人也瞥了我一眼,只一眼。她的手,不自主地停了一下。跟着,她回复了慢吞吞的擦拭。
“你是柳村人?”她问我。她的声音阴森可怖,像是从棺材里飘出来的气息。
“我是柳村人。”
“那你一定是柳根子的侄儿了。”
“你怎么知道?”
“你长得很像你伯父。”
后来,我把这事讲给我娘。我娘说,那个丑女人叫阿秀。阿秀是个苦命的人。或许是因了对苦命的阿秀的怜悯,我愈加频繁地往阿秀家跑。我甚至捏着一块干净布片,跟着阿秀慢吞吞地擦拭着柳棺。渐渐地,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话题——有关我伯父的。阿秀说,你伯父还是两年回家一次吗?我说,我伯父的伤腿疼得厉害,他有六年没回家了。阿秀说,你伯父,他也是老了。我说,我伯父来信说,他很想家……我们的谈论,往往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毫无情趣的沉静之中,耳朵里只有单调而细微的擦拭之声。这时候,阿秀会莫名其妙地摇摇头。轻轻叹一声。
中学毕业之后,成柱考上了一所中等专业院校,而我,鬼使神差地做起了服装生意。我在城里租了门市,生意还算凑合。后来,成柱中专毕业分配在城里的税务衙门,我们经常凑到一起,聊聊天,喝喝酒。
几年以后,成柱在城里买了商品楼。但阿秀拒绝搬到城里和儿子同住。成柱为此很是郁闷,约我到一家新开张的火锅店吃火锅。
“她是舍不得那口柳棺呢!”成柱说。
那天的酒。成柱喝得亢奋,全然没有他自称的“郁闷”的意思。我猜想,他一定是碰上了什么好事。果然,在灌下几杯“白牛二”之后,成柱神采飞扬地告诉我,他刚被提了财务科长。他刚刚上任,工作累人。他请求我有空多上他家跑跑,代他望下老娘。
“她日见老了!”成柱又灌下一杯酒,说。
我因此每隔三五天,就往阿秀家跑一趟。我像从前一样,捏一块干净布片,帮她擦拭柳棺。我们谈论的话题。仍然是我的伯父。
“你伯父最近有信来么?”
“有。”我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他来信说,打算提前退休。”
“他总算要叶落归根了……唉。”
我们的谈话,又在不知不觉中打住。我不经意地瞄了阿秀一眼。我发现她的目光呆滞,她头上的白发,居然那么稠了。阿秀真是老了。
但是有一天,阿秀破例地没有跟我谈论我伯父。她神色慌张地告诉我,昨天夜里,成柱来过了。“他问我,娘,这柳棺是镇宅之宝?我说你爹说的。他就给柳棺烧了很多炷香。然后,跪下给柳棺磕头。他划火柴点香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划了十几次火柴都没有划着——他心里一定藏着大事,我问,他又不肯说。”
阿秀的目光,充满了乞怜地望着我。我清楚我必须帮她弄清楚她儿子究竟摊上了什么为难事。对于这件事,我是有点信心的。成柱和我无话不谈,我相信,这件事,他不会瞒我。
我把成柱约在那家火锅店。我们都喜欢那里的“状元猪蹄”。
“出了什么事?”我开门见山。
成柱对我的询问置若罔闻。他好像只是为酒而来,一口一口地喝着“白牛二”,但我看得出,他喝得心猿意马。我慢吞吞地陪他喝着。我有足够的耐心,等他回答我。
我们的酒很快喝到了兴趣索然的地步。我买了单。在我们走出火锅店的时候,成柱突然跟我说,上面在查我,挪用税款,买楼。
“你信吗?”他问我。他的目光毫无温度地盯着我。说实话,我有点信。不久前,我因纳税的事,找成柱帮忙。事后,我拿出两千块钱酬谢他。我原本只想做做样子,不想,他真就“笑纳”了。
这算我“有点信”的理据么?
我抬头看着火锅店招牌上的那个“火”字。火上面的那两点,被书者画成了两团火焰,画得很有水平,像两团真的火苗,突突地在跳。
我对象是我服装店的员工,四川巫山人。我伯父说,他曾在四川巫山筑过路,那里的女人,个个漂亮恬静,招人喜爱。我伯父因此十分赞成我的婚事,一再写信来,询问婚礼的日子定好没有。他说无论如何都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
眼见我的婚期日渐临近,我伯父又写信来,说工程吃紧,怕是不能赶回来参加我的婚礼了,喜酒改在以后补喝;他还在信上说,他退休的报告已经批下来了。等到这段工程结束。他就可以解甲归田了。
我们一家,在兴奋中盼望着我伯父在某一个黄昏(城里开到乡下的班车。只有每天黄昏,在柳村村口出现一次),踏进我们的家门。我娘炸了满满一篮的排叉(我伯父最喜欢吃),我爹每天都把院子清扫一遍,然后,溜达到村口,朝那条路上遥望。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盼来盼去,盼来的是一封加急电报。电报大意是,我伯父在一次施工中,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希望他的直系亲属,速往筑路队探望。
筑路队距离柳村,迢迢数千里。我爹身体素来不好,很难承受旅途辛苦。伯父的直系亲属,就只有我和我的两个妹妹了。我们坐了四天四夜火车。赶到筑路队时,伯父已经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骨灰。
筑路队的人说,我伯父在一次开山作业时。被塌方的石头砸折了肋骨,骨茬子刺伤了心肺。但我伯父坚持着不咽下最后那口气。他的目光,执着地望着门口。大家知道,他是盼着和家里的亲人见最后一面,所以,才拍了那封加急电报。但是,我伯父最终也没能和我们见上一面。他遗憾地走了。
我伯父留下了一封遗书,只有简短的两个字:柳棺。
筑路队的人说,柳根子同志没文化,不会写字,他平时的家书,都是大家代写的,这封遗书也不例外。他说。他的亲人会看懂这两个字。
柳棺。
柳棺。
我在回来的路上,反复默念着这两个字。我眼前,出现了阿秀擦拭柳棺的情景。伯父遗书上的柳棺,指的是阿秀家那口柳棺吗?伯父为什么单单要那口柳棺呢?是因为他曾讲过的大柳树吗?
我决定,用阿秀那口柳棺,来成殓我伯父的骨灰。
回到柳村,我在一条布袋里塞满钞票。然后。我拎着布袋来见阿秀。阿秀根本不拿正眼看我。她只是轻轻地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柳根子。我就知道你忘不了大柳树……你怎么会忘了大柳树呢……”
阿秀用一块干净布片,将柳棺重新擦拭了一遍。她擦得异常细心,直到确认棺面上没有一星灰尘,才跟我说,你把它弄走吧。
阿秀说完,进了里屋,再也不肯出来见我。
我悻悻地拎着布袋。我突然发觉,自己做了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
成柱被警察带走那天,我恰好有事去找他。我在税务局办公楼前的小广场上,目睹了他被警察推上警车的情景。
我第一个担心的人是阿秀。
我赶到阿秀家时,阿秀已将自己反锁在屋里,任凭我怎样哀求,她始终不肯打开房门。
我说,你儿子他只是借了公家一点钱。我帮他把钱还上,他就没事了。
我说,成柱他是去外地上学了。过两年毕业回来,他仍然可以当他的科长。
屋里始终没有一点阿秀的声息。我每隔一两天就来阿秀家一次。我每次都隔着门,跟阿秀讲一阵话,屋里一如既往地毫无声息。但我确信,阿秀没死,她还活着。因为我每次放到门前的新鲜食物和纯净水,都不见了。这说明阿秀坚持进食。阿秀进食就不会死掉。
我第六次来阿秀家时,发现我上次放在门前的食物和水,原封未动。我预感到不妙。找了几个阿秀的邻居,一同拆开了房门,发现阿秀早已经死了。她的尸体旁边,堆放着我带给她的食物和水——她一点都没有吃。阿秀成功地骗过了我。
我没有把阿秀死掉的事告诉成柱。后来我去劳改队探望他时,觉得他的心情蛮不错,他说,两年,一眨眼就挨过去了……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