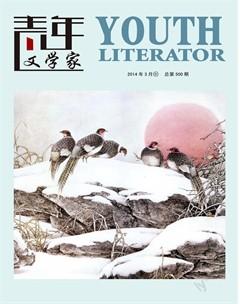《包法利夫人》中的现实与虚化
2014-05-30陈小可
摘 要:《包法利夫人》是一部根植于批判现实主义土壤的小说,它的出现提醒人们关注自身存在,直面现实;同时,这也是一部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小说,在注重描写现实的同时,虚化了背景,强调人物内心独白,对于小说形式以及未来文学发展都有着重要贡献。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 ;现实主义;虚化
作者简介:陈小可(1993-),女,汉族,江苏盐城人,本科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8-0-01
一、提醒现实
1848年法国的革命风暴之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趋于稳定,一群资产阶级的凡俗之辈,却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制约,这处境便使人们越来越变得人人相似。人人相似着,有着相似的脸、喉舌、头脑,相似多了,便容易忽视了日常的生活存在,变得庸庸碌碌,或如木偶般行动,安于可怕的平庸。
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如《包法利夫人》的出现,“探索着直至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探索具体的人类本身的生活,帮助人们审视身边的生活,防止逐渐遗忘却了存在。“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反映生活”,这是《包法利夫人》一类的作品的价值,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到现实,直面客观的生活。
小说中艾玛年轻时受到的修道院里禁欲主义的刻板说教、消极浪漫主义小说的侵蚀,其心灵早已被这个社会所腐蚀,灵魂深处被播下了靡乱的种子。艾玛的幻想被激发越发不可收拾的转折点是那次沃比萨尔的舞会。在舞会上,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侈,让她终于亲眼见到了书里所写的上流生活。当曾经的幻想被以这样一种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艾玛的时候,她的心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不满足于平庸的家庭生活。那次舞会之后,与其是说激发了艾玛的浪漫情怀,不如说是给了冒险天性一个出口。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看不到冒险,而对于刺激和冒险的渴望却是根植于人类印象记忆之中的:当生活沉淀下来,露出苍白无聊的景象,冒险而产生的快感便会呼唤着人们,这份源自古老时空的呼唤会愈发清晰与诱人,正如伊甸园里的欲望之果。
出于冒险带来的快感,包法利夫人用一次次的行动(偷情),希望走出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世界,通过行动,与他人区分开来,成为个体。她自以为那晚的豪华舞会能开启她通往奢华的大门,她以为和莱昂、罗多尔夫的偷情可以让她脱胎成贵妇人,实际上,包法利夫人却在离上流社会生活越近的同时走向毁灭。她在这行动之间,忘记了自我,无法辨认出自己。她期望通过行动展示自己不同于日常的形象,可悲的是这形象却并不与她自身相似,所以她做着梦,却坠入了现实的陷阱。
包法利夫人的悲剧不是特殊的案例,它符合那个时代“平庸”的特质,《包法利夫人》把我们所忽视了的现实和可能性,用小说的语言、陌生的手法展现给读者,让读者如饥似渴的阅读,哀叹讽刺,却又发现,那正是自己每天过着的生活呵,原来自己正是自己嘲笑的那类人中的一分子。自己和他人都相似着,以至于忘却了自己的存在和这个世界的荒诞。《包法利夫人》不仅在于提醒着现实生活的存在,还于“人人相似”的生活中展现不同,提供给读者更多生活的可能性,展示了真实生活下的另一个出口,提醒人们的反思。1856年12月,福楼拜在給彭郎芳的信中说,“这本小说,含有一种明显的教训,如果母亲不允许她的女儿读,我想丈夫拿给他们的夫人读,总该不坏吧” ,这正是《包法利夫人》一定程度上起着的警示作用。
二、虚化写作
作为具有现实意义和批判效果的作品,需要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美即真实,艺术来源于真实,如此倾向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共性,但《包法利夫人》另有了创新——虚化。
在大多数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人物身份都事无巨细交代清楚,作家致力于呈现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论是小说中的结构还是关系,都是有据可循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却像一个时代的断层,几乎没有对社会背景作出交代,也没有对人物家族作系统回顾,作品的一开头就是对夏尔上中学时情景的描写,紧接着就开始进入正题,叙述当下的境遇。作者就像一名能工巧匠,在时间的缎上只截取现实的,极工文辞叙述当下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存在。至于过去和背景,则是一片虚无,给人以绰约的想象。福楼拜自己说过,“我觉得美的,亦即我想写的,是一本建立在虚无之上的书。它仅仅靠自己,靠其文笔的内在力量来维持,就像地球没有任何支撑而维持在空中一样。这是一本没有主题,或者尽可能让主题隐而不露的书。”
这种对于背景的虚化,的确正如福楼拜所期望的一样,《包法利夫人》成功靠文字的内在力量完成了对现实生活和存在的展现,具有普适性,并且,正是由于背景虚化的写作,读者和小说自身的视线都被集中于小说叙事时间中“现实”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虚化的写作和后来的现代主义以及荒诞派有相似性: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在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中,在两个流浪汉等待戈多的过程中,读者却不知道这是哪个年代,不知道戈多是谁,也不知道戈多是否存在,然而,就在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退却成虚无,存在的荒诞和人生的痛苦,外界对人的威胁感、压迫感,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感、孤独感跳脱出来了。同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写的是现实,却又从未刻意彰显真实。将小说中的人物和心理独白摘出来细细感知,发现非理性的世界和存在的矛盾、人生的不如意,由小说语言可以让读者窥见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感受,领略梦呓般难以表达的流露。不需要背景的交代,只需关注内心特色,从阅读中,感受艾玛走向虚无的爱情陷阱、罗多尔夫的腐化堕落等等。
这样的虚化:关注内心世界,注重文本,为小说形式日后的发展起了重要贡献。福楼拜晚年用了7年的时间培养后来的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左拉和都德等作家,此后的小说发展多少有着福楼拜的印记——这位锐意创新的作家,为艺术做出了完美的尝试。
参考文献:
[1]昆德拉, Kundera M, 董强. 小说的艺术: L'art du roman[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2]汪火焰, 田传茂. 镜子与影子——略论福楼拜和他的《 包法利夫人》[J]. 外国文学研究, 2001, 1: 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