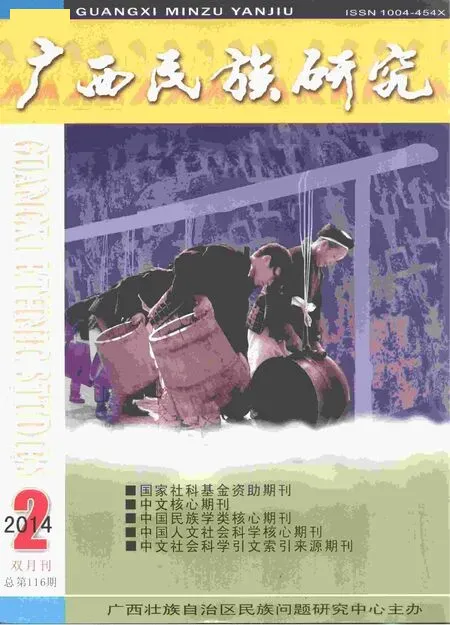民族和解的厘定和路径探究*
2014-05-09严庆胡芮
严庆胡芮
自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世界各国的重心都在倾力于发展,对于偶发的民族冲突的解决方式也从以往的“以暴制暴”转变为和平方式。“和解”一词自然地也被引入到民族政治研究中。在中国期刊网论文中标题或关键词含有“民族和解”的学术论文有202篇,内容含有该词的论文共有3591篇。①数据来自笔者对中国期刊网 (http://edu.cnki.net)相关文章的统计。“民族和解”虽被频繁使用,但学界却没有对其进行清晰且权威地界定。为了将“民族和解”从案例上升到系统的学理分析,本文在对已有的关于“民族和解”学术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着“集各家之所长”,厘定“民族和解”,并试图归纳总结出民族和解的基本路径。
一、“和解”与“民族和解”
在中国的文字中,“和解”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在《荀子·王制》中就有记载:“和解调通,……则姦言并至,尝试之说锋起。”[1]503-504在此句中,“和解”是指“宽和”的意思,具体来说就是为人要宽厚谦逊,心宽才能人和。而在之后的《史记·九三韩王信传》中,对于“和解”的解释使“和解”一词的外延显得更为宽泛。书中记载:“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结合语境可以很容易地知道“和解”在文中的意思是“平息纷争,重归于好”。在现在通用的权威词典中,对“和解”的解释也万变不离其宗。《辞海》中对“和解”的解释是:不再争执,归于和好。[2]413《现代汉语词典 (2002年增补本)》给出的解释也是极其相似的:不再争执或仇视,归于和好。[3]510
“和解”一词的英文为“reconciliation”。查阅相关英汉、汉英词典,对于“reconciliation”有如下的解释:
1.和好,复交,调解,调停,调和,一致。[4]1299
2.使和解,使和好;使听从,使顺从,使默许;调停,调解;使和谐,使一致,使符合。[5]1920
3.和解、顺从、调解、调停的行动;和解、顺从、服从的状态;和谐、协调的过程。[6]1889
“reconciliation”一词最早是由荷兰灵长类学家德瓦尔在分析灵长类动物时提出来的,指的是冲突结束后不久冲突双方出现的相互友好行为,比如相互冲突后短时间内出现的挨坐、抱对等行为。[7]之后,社会学、政治学逐步将该词引用到国际、国内群体关系的研究中来。
综合上述对于“和解”的解释,可以得知:“和解”作为一个频繁使用的词,其本身存在着一个清晰的逻辑因果关系和过程性,即在主客体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使彼此将来能拥有优于现在的境况,在不触及自身容忍底线的前提下达成的调和与妥协。和解是指相关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改善和优化。
“和解”虽然在中国语言文字使用上延续了几千年,但是“民族和解”作为一个复合词的出现却比较晚,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关于“民族和解”的确切的学术界定。在1984年版的《民族词典》、1986年版的《社会大百科全书 (民族卷)》以及《民族学译文集 (一,二)》里均未出现“民族和解”这个词及其解释。在社会学学界研究普遍使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2004年版)和《社会科学新词典》(1991年版)中也未出现对该词的解释。
第一篇将“和解”应用于民族问题研究的文章是《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和解的障碍》。[8]文章详细地阐述了斯里兰卡国内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矛盾,以及该国国内长期滋长的民族和宗教地方主义等方面因素,使得斯里兰卡在国家统一和两大部族和解的路上举步维艰。该文章在1981年被收录入《民族译丛》第3期。
中国学者研究“民族和解”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是徐植和新飞于1979年联合发表的《乍得:动乱与民族和解》。[9]文章透过1979年8月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召开的关于乍得全国和解的第四次会议回顾了自1965年动乱以来,乍得国内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以及在国际力量和国内民族领袖和爱好和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召开的四次和解会议,对乍得国内民族和解的条件、方法及前景进行了预期。但是通过该文章也可以清楚地发现,作者对于“民族和解”一词的应用还只限于简单的案例列举和事件描述,并没有从学理的角度对“民族和解”一词进行系统地定义和分析。不仅是该文章,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中以“民族和解”为关键词或者以“民族和解”为标题的202篇文章的收集和整理发现,这些文章都直接使用了“民族和解”的概念对国内外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却没有对“民族和解”进行理论界定和说明,而界定“民族和解”的概念是展开相关研究和构建民族和解理论的基础。
因此,笔者一方面结合“和解”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另一方面通过对收集到的关于“民族和解”使用情况的分析,对“民族和解”做出如下界定:民族和解是从各民族的利益出发,以建立多民族国家内部和多民族世界平等和睦、共同发展的机制为目的,通过和平谈判、协商和一定的妥协等方式,来解决民族冲突的政治手段。“民族和解”是化解族际冲突、族类群体与国家之间冲突的重要方略,其价值取向是:从物质、精神上弥补受到损害的一方,并以此实现民族和睦。“民族和解”在国家制度的表现形式即为民族和解政策。①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在周平的《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找到了关于“民族和解政策”的定义。书中说到:民族和解政策是一些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激烈的民族冲突并深受其苦的条件下,在痛感民族尖锐的对立和冲突所带来的破坏作用和消极影响的基础上,为缓和国内民族关系,减少民族冲突采取的民族政策。
二、民族冲突与民族和解
作为解决民族冲突的方法和手段之一,对“民族和解”的研究离不开对民族冲突的分析,探寻民族和解的路径必须了解引发民族冲突的原因。1996年,由波兰科学院与民族研究所编辑的《民族研究》丛书第一卷—— 《民族冲突》问世。全书收入的30篇文章为自1994年12月以来在该所的关于“民族冲突”讨论会上的论文。[10]全书引用的文章通过对族际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冲突的案例分析,较为系统全面地定义了民族冲突。因为研究的角度不同,因此具体的定义大不相同,但是其核心的内容却始终如一,即通过在民族问题研究中引入社会冲突理论,揭示族际之间、族类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态势。
引发民族冲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依据宁骚在《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一书中的观点,影响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冲突的基本原因表现为五个方面:国族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的矛盾、国民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权力垄断与权力分享之间的矛盾、国土开发与利益分配之间的矛盾、国家的现代化与族体发展之间的矛盾。[11]194-250有的学者对民族冲突发生的原因则分析得更为具体,并归结为三种解释:一是从民族心理视角出发,通过对相关民族所处的安全困境、具有的地位忧虑和民族统治欲的分析,总结出具有主观冲动性的民族心理路径解释;二是从资源竞争角度出发,通过研究族际间、国家与族裔群体间因资源 (包括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等)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而产生的竞争,归纳出民族竞争的路径解释;三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在极端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下催生的以“我族为中心”的民族冲突,而这种原因解释为族裔民族主义路径。[12]86-93
因为视角不同,对于民族冲突的分类研究同样也存在着差异。从冲突主体的角度划分,可使用如下的分类方式:
种族冲突是以种族特征为参照,由主观的种族优劣论引发的,种族屠杀、种族隔离迫害、种族歧视、种族社会地位分层等因素都可能成为种族冲突的原因。部族冲突发生在依旧以部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中,因为传统的部族、部落成分复杂,社会整合性较差,政治上的专制和独裁、部族之间的敌意等往往引发冲突。族群冲突则发生在移民群体和东道国的主体民族之间,这类冲突的产生常常是因为文化的碰撞、生计方面的竞争或者是东道国主体民族民粹主义情绪的增长等。
在族类群体与国家的冲突分类中,依据的是族类群体与国家间实力的对比和族类群体对于权力的要求程度。分裂运动是国家内部的族类群体通过民族自决来寻求拥有独立主权的政治行动;分离运动是族类群体逃离现存的国家体系与同族国家合并的政治行动;分立运动则相对比较温和,族类群体通常是为了寻求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社会地位,在主张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寻求承认和自治的过程。
伴随着“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的深化,越来越多民族冲突频发的国家认识到大规模冲突对于民众的伤害,也日益感受到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对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纷纷采取措施缓解民族矛盾,从联邦制 (如比利时)、民族区域自治 (如西班牙、加拿大)到地方议会 (英国和北欧国家),从欧盟在维也纳设立种族主义监控中心到澳大利亚开展社会和睦运动,都代表了寻求族际和平的政治取向。[13]“民族和解”以其非暴力、协商性的优势进入人们的视线。
实现民族和解并非易事。安德鲁·瑞格比就实现民族和解的条件分析到:想要实现真正的和解,有三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首先,新的政治领袖不能在政治目标制定上好高骛远,要将目标降低到和平共处和终止暴力冲突的层面上;其次,关键人物和舆论领袖们应重新确定价值的定义,要崇尚共存与合作;最后,引导人们认识到和解计划的完成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认识到实现和解的基本价值并非易事,认识到向前的唯一方式是分阶段地追求这些价值。[14]196安德鲁从政治领袖、民族领袖和人民大众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意在表达想要民族和解得以进行,必须依靠社会各个层面的联动。戴启秀在《和解外交:超越历史的欧洲一体化》一文中总结到欧洲实现一体化的目标是因为实现了下述条件:首先,超越历史,这方面是和解关键;其次,在政治框架内采取措施消除历史积怨,推动联合与合作;然后,建立信任,这是和解的基础;接下来,经济和政治上的互相需求;接着,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最后,以往民族冲突或族际冲突中主体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15]
回顾民族和解的历史,有的国家在民族和解的道路上虽经历波折,但是最终国家得到了统一,国内社会趋于稳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而有的国家民族和解过程历经千辛万苦,和解会议开了又开,却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是否抓住了民族和解的关键节点以及了解民族和解的精神要义。
民族和解的关键是利益的分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82利益作为政治行为的驱动力,决定了个体、团体甚至到国家的政治选择,在民族和解中也不例外。在民族和解过程中,已有利益和机会利益的分配往往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只要在利益分配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么民族和解就已经有一只脚迈进了成功的大门。但是,在民族冲突中,利益关系是十分复杂的,牵涉的主体也是十分复杂的,影响利益关系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双方的实力对比、国际力量的干预等。因此,在民族和解过程中,除了充分考虑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外,还应强调和解的精神要义。
和解的精神要义是一种妥协的艺术。从宏观和长远利益角度来看,民族和解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因为主客体的和解可以为国家带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美好的预期,但是就主客体自身来看,却是一个零和博弈,因为在和解过程中他们必定要有放弃和妥协。因此怎样把握和解过程中的让步与妥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民族冲突与民族和解有着清晰的因果逻辑关系,准确地理解民族冲突发生的原因、过程以及民族冲突的类型,有助于在实践中更加准确、科学地运用和解策略。在结合各国具体实际的前提下,通过分析民族冲突的原因可以准确地找出民族和解需要解决的核心要点;通过对民族冲突过程的充分认知可以更好地对民族和解过程进行预估,以避免在和解过程中出现懈怠或冒进的错误;通过对民族冲突类型的全面掌握,可以让民族和解的主体选取更具有效度的和解方案。
从过程来看,民族冲突的产生和发展极其复杂,宏观上看是从潜在的阶段到显性的阶段,具体来看是从民族边界的清晰化→利益分歧主客体闭合内聚→针对性的内部动员→必要资源和条件的准备→“导火索”的出现→冲突的爆发→冲突的持续→冲突的衰弱→冲突的结束。因此,可将民族和解分为过程中和解和冲突后医治冲突创伤的和解。从主体角度来看,可将民族和解分为民族国家间和解、国家与族类群体间和解、族类群体与族类群体间和解。
三、民族和解的路径
开展民族冲突主体、过程、原因以及类型的研究,是探寻民族和解路径的基础。因为民族冲突的主体不同、过程不同、原因不同、类型不同,民族和解的起点和路径也会有所不同。从现有的民族和解实践来看,通常依循以下路径:
1.以施害方正视历史、反思过去为先导的心理和解
回溯民族冲突的历史可以发现,导致冲突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冲突过程大多也是漫长的。现实中的相关民族作为历史的承接者,虽然更多面对的是现在与将来,但是以往的历史却是现在与将来的起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因此只有正视历史,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才能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发展。德国对纳粹统治的历史以及二战中的暴行采取了直视不讳、深刻反省的态度,为民族和解在正视历史方面树立了榜样。
1970年12月,在结束了对捷克和波兰的访问之后,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来到了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并双腿跪地祈祷忏悔,虔诚地为德国纳粹在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赎罪;1995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科尔在访问以色列时来到以色列犹太人受难纪念碑前再次下跪,重申了国家的歉意。这些场面至今仍令世人动容。二战以来,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17]“从德国视角来看,主要涉及怎样摆脱自我怜悯,正视本国历史的事实,这一视角转换的诠释就是试图用别人的眼睛去看待自己本国的历史”。[18]除了政府领导人的诚心悔过,德国还坚持自1953年《战争受害者赔偿法》施行以来,对在二战中受害的国家进行赔偿,对战犯进行彻底的审判,彻底清算纳粹的所有罪行,对受害者和受害国家皆予以满意的答复。除了在政策层面上的积极努力外,在教育方面,德国政府为了让子孙后代牢记奥斯维辛集中营无辜牺牲者曾经有过的不幸遭遇,将多处纳粹集中营遗址辟为纪念馆,供国民参观;政府还在教科书中增加揭露法西斯罪行的内容,以起到警钟长鸣的教育作用。[19]
施害方是族际关系创伤的制造者,其反思的态度有助于给予受害者精神慰藉与道义感的补偿,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关键起点。
和解是一种关系由敌意向谅解的转变,需要施害方和受害方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相互认可。施害方可以从正视历史的角度,忏悔过去对受害方的伤害;从现实补偿的角度,通过为受害方提供良好的政策和条件弥补创伤。但是从受害方的角度出发,宽恕施害方是一个漫长且不断变化的心理过程。宽恕的压力应对方式的核心有很多方面。宽恕的种类也有很多种,宽恕的治疗过程也是不同的,这是基于不同种类的人际关系所决定的。[20]17现实生活中,基于血缘和亲情,原谅自己的亲属或者信任的人是容易的。但是对于陌生人甚至是伤害过自身的人来说,宽恕则是不易的,它需要积极客观的正面情感将负面情感替代。宽恕不是一个行动而已,它是一连串的“正念”所累积出来的“心胸”,这不是听几次演讲或读几本书就能获得的经验,因它与个人的无知、恐慌、逃避、自责、封闭、抗拒等隐藏的心态有关,我们必须一个结一个结地化解掉那些内在的障碍,才可能体验出宽恕的真谛。[21]4
1948年,在只有白人参加的“全民选举”中,国民党中的右翼布尔人党派获胜,标志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建立。右翼党派在执政过程中,制定了许多被联合国形容为“对人类犯下的罪行”的恶劣条款,深深地伤害着南非黑人的尊严,同时进一步恶化了黑人与白人间的关系。1994年,南非实行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国大选,非国大党获胜,曼德拉当选总统,标志新南非诞生。[22]对于民族尊严共享的认识、将民族尊严融入国家尊严中的创新理念以及在种族矛盾激烈冲突中理性的妥协与让步都是曼德拉所具有的政治智慧。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大赛在南非举行,曼德拉决心利用这一赛事来争取到南非白人的认同,但由于黑人政府禁止橄榄球队使用带有白人种族主义象征的跳羚标志,黑白之争再次弥漫全国。考虑到橄榄球队对于白人群体的敏感性,曼德拉采取了妥协的策略。在比赛当天,曼德拉身穿南非橄榄球队队服亲临赛场,鼓励队员,南非队最终夺取了冠军。在为冠军球队颁奖后,曼德拉总统把手放在白人队长的肩上,然后握住他的手说:“非常感谢你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年轻的队长看着曼德拉的眼睛回答说:“不,总统先生,应该感谢您为我们的国家做出的一切。”真诚的对话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遍整个南非,当曼德拉举起绿色的球帽向全场挥舞致意时,全场的白人都亢奋不已。[23]一件简单的球衣,一段简单的对话,一个简单的挥手动作,对于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来说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又是至关重要的。这里面包含的是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是南非黑人心胸的体现。也许这次的事件并非是对南非白人的完全性的原谅,但却是向之后南非民族和解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谅解的过程中,关键人物的表态和引领作用至关紧要,因为在很多时候,群体性的谅解难以自发形成,需要积极地建构和引导。
2.通过权力分享实现政治和解
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是维持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资源的有限性和分配过程中的相对不公却为民族和解埋下了隐患。托马斯·霍默·狄克逊在对南非、卢旺达、巴基斯坦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之后提出了“环境匮乏观念”。他认为环境性匮乏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供给性匮乏、需求性匮乏和机构性匮乏,这些环境性匮乏导致了国家内部的冲突,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24]罗尼·利普希茨认为冲突的发生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的需求程度和分配的结果。[12]91围绕着资源与利益的分配,族际之间、族类群体与国家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利益和资源的获取与分配归根究底是需要权力来做保障的。马克斯·韦伯曾这样定义权力:“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25]595没有权力就没有支配权和地位,这种支配权和地位之于民族和解则是需要分享才能实现的。
1947年,当缅甸要求摆脱英国寻求独立时,现代缅甸建国之父昂山将军意识到民族团结和联合是独立的首要条件。他在著名的“彬龙协议”中对缅甸的民族政策作了调整,并此为基础,对独立后的国家体制作了设计,决定实行联邦制,从而为独立后缅甸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6]缅甸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民族自治邦享有自治权利,并允诺掸邦和克耶邦在十年后可以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留在联邦内。这是一部根据缅甸的历史和现实制定的、符合缅甸国情的、相当宽松和自由的民族联邦宪法。这样从法律的角度为不同民族的人民提供了根本性的永久保障。
同样,在津巴布韦的民族和解过程中,在排除种种困难之后,分裂了25年之久的津巴布韦非州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人民联盟终于在1997年12月12日签署了两党统一协定。自津巴布韦独立以来,历届两党联合政府始终坚持实现民族团结,始终不遗余力地坚持民族和解政策。[27]而在这方面,以库马拉通加夫人为首的斯里兰卡人民联盟政府执政之后,正式提出了一揽子放权方案。其主要内容有:废除总统制,改变国家政体,使其从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变为一个地区握有实权的“地区联合体”;全国划分为9个地区,中央向地区放权,地区将得到土地处置、颁布法令和命令等重要权力。[28]不得不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当权政府是做了很大妥协的,因为这是以放弃已有的完整的执政权为代价的。但是这种妥协同时也是十分值得的,一方面为国家的和平统一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政府的合法性。
1997年,南非制定了一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进步性宪法”之一的新宪法。新宪法对“平等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国家不得基于以下一项或数项内容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任何人不平等待遇:种族、性别、性、怀孕、婚姻状况、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性倾向、年龄、行动障碍、宗教、伦理、信仰、文化、语言及出生地。”[22]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南非政府从政党制度入手,主张“一党主导多党联合执政”的模式,各执政党在民族团结政府中基本上做到合作共事,协商解决争端,求同存异,没有因分歧而损害政府的正常运转。而在经济方面,南非政府放弃原先激进的国有化纲领,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现状,保持了国家经济生活的稳定。[29]
一个民族是否享有权力意味着是否享有资源和利益,而民族冲突的实质就在于权力之争,因而权力共享或分享是实现民族和解的根本所在。
3.以文化平等政策推进社会和解
政治上的权力分享和族类群体内部个人的权利保障,使得显性的民族平等得以实现。依据各国民族和解的历史来看,虽然在国家层面的民族和解以及政治改革如火如荼,但是在社会层面的民族和解却往往滞后,即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和解并非是同步的。在社会层面,还有隐性的、潜在的种族歧视、民族矛盾,这些是刚性的国家政治策略难以解决的,因此需要柔性的、富有弹性的文化去加以补充。“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30]694一方面,文化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发生选择性的改变;另一方面,文化之于社会又有其独特的作用,即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提供心理和精神上的动力。因此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着整个社会。在运用文化解决民族冲突的实践中,俄罗斯和加拿大可谓是成功的典范。这两个国家通过文化自治和多元文化政策,推行文化平等理念,旨在促进社会层面的文化理解、文化共存和文化互动。
作为民族构成十分复杂的国家,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可谓纷繁复杂,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发展也是历经坎坷。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告解体。事隔多年,回顾这段历史,不可否认苏联解体虽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可谓是其关键性因素之一。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苏联,一直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民族问题。[31]在吸取前苏联的经验教训之后,俄罗斯于1991年颁布《公民法》、1994年颁布《俄罗斯公民和睦协定》、1996年颁布《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和《俄罗斯民族文化自治法》、1999年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原住人数较少民族权益保障法》,确定采取民族文化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并行的做法。[32]
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具体实施工作主要表现在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方面。在民族语言保护方面,民间民族文化自治组织在征得联邦政府和地方自治机构的许可后,创立了专门的民族学校,开始民族语言学习课程,培养民族干部,特别注重师范人才的培养。据统计,在秋明州就约有197所民族学校,其中包括曼西人和汉蒂人的68所民族学校、鞑靼人的121所、巴什基尔人的4所、楚瓦什人的2所和高加索人的2所;在鄂木斯克州有29所日耳曼人学校、22所鞑靼人学校、17所哈萨克人学校。[33]在民族文化保护方面,民族文化自治组织热衷于参与到地方建设工作中,积极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此来弘扬民族文化,延续文化的多样性。总而言之,俄罗斯从联邦政府到地方自治机构再到民间自治组织都积极地参与到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行动中,大力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满足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需求,以此来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治,以文化权益保障降低政治分离的可能取向。
加拿大是一个由20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正如加拿大人所讲,世界有多少国家,加拿大就有多少民族。[34]1971年,加拿大政府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宣布实行多元文化政策,1988年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标志着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加拿大民族关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元文化政策推动了加拿大人对民族多样性的现实态度,它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一致的肯定。[35]正如《加拿大百科全书》中所写的那样:“多元文化”在加拿大至少有三种含义:其一是指一个具有种族或文化异质特征的社会;其二是指族裔或文化群体之间相互平等、尊重的观念;其三是指1971年以来加拿大联邦及各省推行的政府政策。[36]1401在少数民族人才吸纳方面,加拿大政府自1971年起开始设立高级文化官员职位,同时提高在全国范围内各机构的少数民族代表比例;在丰富民族文化活动方面,成立了文化协商委员会,鼓励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项目参与到全国性的重大活动中去;在文化基础建设方面,政府逐年提高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财政支出,提高了地方族裔语言的教育水平,兴修少数民族文化博物馆,支持和保护多元文化艺术和遗产。渥太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威尔·基姆利奇卡对加拿大政府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到:“关于加拿大成功原因的关键解释之一就在于它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使我们的人民保留或表达认同自豪感成为可能”。[37]社会学家诺曼·布基尼亚尼对于多元文化政策的价值做出了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已经在加拿大原住民自己建立的新社区里提升了他们的意识,而且有助于各种群体在保持各自的民族身份的同时确立国家的认同感。[37]
文化是民族以及各种族类群体的重要特征,文化存续、选择以及发展的自主性与族类群体的尊严、荣耀密切相关,文化理解和文化尊重是实现民族社会和解的重要途径。
四、结语
民族和解、民族和谐是族际关系发展的目标,而要消除民族敌意、医治民族冲突的所遗创伤,致力于族际关系优化与和谐,就离不开民族和解的态度与行动。在不同的时空组合中,影响族际关系变革的因素是不同的,实现民族和解的路径和施力点也是不同的。
1994年南非成为最后一个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伴随着族际政治格局的重组,南非政治家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创造性地践行民族和解模式。民族和解模式在南非的初步成功引发世界政坛的广泛关注,民族和解模式也迅速风靡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北美洲和欧洲。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和解委员会,但整体来看,这些和解委员会大多没有获得成功。尤其是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建立和解委员会的国家(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塞拉利昂、加纳、肯尼亚、缅甸、泰国等)大多刚刚经历从军人执政向民主的转型,这些国家国内政治整合度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民主意识刚刚启蒙,民族和解在这些国家遇到了困难与阻力。
民族和解模式的盛行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人类正在极力抑制民族冲突,消弭过去民族冲突造成的创伤。但不可否认,在族际交往中一些纠纷和矛盾难以避免,新的问题和冲突会不断出现。化解民族敌意,实现民族互信,需要人类长足的努力。正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要设计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圣公会首位非裔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所说的:“没有方便的和解路线图。也没有捷径或简单的处方用来医治持续暴力后的创伤和社会裂痕。在以前的敌人之间创立信任和理解是个极为困难的挑战。在建立持久和平的进程中,最需强调是的反思痛苦的过去,承认它、理解它,而且超越它的,最好方式是确保类似事情不再发生。”[38]1
[1]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中国书籍出版社编辑部.辞海:全新版[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
[3]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英汉大词典编委会.英汉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张柏然.新时代英汉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斯图尔特·B·弗莱克斯纳主编,《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编译组.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7]张剑.秦岭川金丝猴冲突及冲突后行为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9.
[8]迈克尔·罗伯茨.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和解的障碍[J].现代亚洲研究,1978(12).
[9]徐植,新飞.乍得:动乱与民族和解[J].世界知识,1979(20).
[10]王丽芝.波兰《民族研究》丛书第一卷——《民族冲突》介绍[J].世界民族,1993(7).
[11]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2]严庆.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3]郝时远.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1(1).
[14]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M].刘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5]戴启秀.和解外交:超越历史的欧洲一体化[J].国际观察,2007(4).
[16]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7]黄凤志,逄爱成.德法和解历史对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借鉴与思考[J].东北亚论坛,2010(5).
[18]乔格·卢尔.战后和解——以德法、德波关系中的德波关系为例[J].戴启秀,译.德国研究,2006(3).
[19]和春红.战后法德和解:从不可能到可能[J].学术论坛,2011(11).
[20]Worthington,E L.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Theory and Application[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6.
[21]保罗·费里尼.宽恕就是爱[M].周玲莹,若水,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
[22]夏吉生.新南非政党制度的特色和发展[J].西亚非洲,1999(5).
[23]言轻.尊严与宽恕:弥合族际关系的良药——归还民族尊严让新南非走上了民族和解之路[N].中国民族报,2012-02-17.
[24]Homer-Dixon T F.Envi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Evidence from Cases[J].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4,19(1).
[25]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中国问题研究所,南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6]石安达.缅甸新时期的民族和解政策[J].世界民族,1999(3).
[27]李克刚.津巴布韦穆加贝的民族和解政策[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88(2).
[28]王兰.斯里兰卡和平前景暗淡[J].当代亚太,2000(6).
[29]章毅君.评曼德拉的民族和解政策[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3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1]熊坤新,贺金瑞.现代国际冲突与民族和解案例分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6).
[32]韩刚.俄罗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转型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3).
[33]王莉.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自治政策[J].中国民族,2010(12).
[34]王英.民族和解与多元共建——《耕耘加拿大》的评介[J].民族论坛:学术版,2013(1).
[35]高鉴国.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评析[J].世界民族,1999(4).
[36]Marsh J H.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M].Hurtig:Edmonton,1988.
[37]韩家炳.加拿大和美国学者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评论[J].国外社会科学,2006(4).
[38]Sørensen B R,Bloomfield D,Barnes T,et al.Reconciliation after violent conflict:A handbook[M].Internat.Inst.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