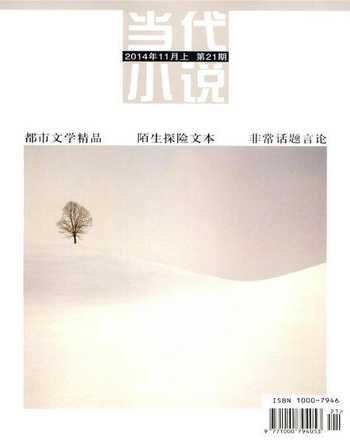理发店的夜晚
2014-04-29安庆
安庆
一
牟敏忽然觉得,自己被挟持了。
她无助地看着闯进理发店的这个人:胡子拉碴,头发蓬乱,像刚从什么地方里拱出来。男人打量着理发店,正面的大镜子里映出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意识到是自己时他慌乱地扭开。掩上门,那个人终于说话了,他拽了拽头发,吞吐着,是,是理发店吧?给我,给我理发。声音短促、沙哑、有些疲惫。
牟敏还没有完全地癔症过来,好像还在打盹,还沉在刚才的梦里。她想说太晚了,不干了,刚才都困得睡着了,要是往常早已经关门回家了。她没敢说,夜深了,整个街道上没一点动静。她无助地看着对方,身子还在抖着,双手交叉抠在膀子上,耷拉下来的头发遮住了一边的眼睛,站起来时,她下意识地去摸剪刀,摸一条毛巾,实际上,心乱得不知所以,乱了方寸。但还是说了那句憋在心口的话,太,太晚了,明,明天吧。
明天?那个人似乎没有听见她说什么,在心里嘀咕,明天,我明天来?我明天来他妈干什么?对方踌躇了一下,然后说,不行,给我理,马上!他把发干发灰的手指又往头上插,头发缝里落下一些东西,很细、凌乱的细粉,细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迅速窜遍理发店的角落。牟敏下意识挪了挪椅子,看见了搁在桌面上的一把刀,刀刃合在刀鞘里,刀脊上闪出一道银光。她想,如果有事,就用这把刀。她紧紧握住那把刀,刀却似一条不听话的鱼从手心里滑落,刀落下的声音里那个人抖动了一下。
给我理发!快点,还要赶路。那个人又在催促,盯着她,眼里闪出一股寒光。
赶路?
对!
去,去哪儿?
往前走!
往前?牟敏想那就是往南了,老塘南街的人出去往远一点的地方都是往南走的,即使去北京、东北也是先往南走,去县城里坐车,再坐车往北,车子再路过村庄的方向。她和丈夫就这样地坐过,眼瞅着自己的村庄被掠过去,那些鸟儿在村庄上飞,狗汪汪叫着跟着火车跑,像是着急火车把自己的亲人拉跑了。她想着火车,铁道线,要是自己的男人在家多好。泪水就是这时候悄然地滑落下来。
快点!
牟敏开始挪动着身子,炉上的水壶冒着热气,白气在房间里缭绕,和灯光缠绕在一起,房间里的光线更加模糊。这时候要来几个人多好。她抬起头,无助地望着窗外,小身子显得更小,窗外只有深秋满天的繁星。
洗头时她还一直听着街上,哪怕有一个人的脚步都会让她的胆壮起来,或者有一条狗过来都行,都会让她有一种依托。头上的味道冲鼻,手握住头发像握住了一把乱草,太干了,一见火就着。牟敏又把洗头膏打过去,往盆子里续水,水里又掺进了模糊的颜色,牟敏在想一个人的头怎么能脏成这样,这个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干什么的?牟敏越想越害怕起来,正常的人不会这样,不会把自己埋汰成这个样子。牟敏的身子一阵发紧:是逃犯吗?不然就是一个有神经病忘了家的人。牟敏从镜子里看对方的面目、神色,眼里有一种黯然,但不像神经病。这么说一定是一个逃犯了,牟敏越发紧张,手差不多愣在了杂乱的头上。停了有几秒钟,对方等得不耐烦了,说,洗呀,快给我洗完。牟敏拿起了梳子和剪刀,洗完头,那个人一字一顿,快给我剪头,快,太难受了。
理,理啥发型?
随便,想怎么剪怎么剪,还,还什么发型。
嚓嚓嚓……牟敏已经按寸头在给他剪了。牟敏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人的头发很短,青头皮都能看到,牟敏就是按电视上的板式开始做的。理了几分钟,那个人举了举手让牟敏停下来。牟敏停了,他把门又重闩了一次,又抬头看看头顶的灯,很亮,在转椅旁边还有一个小灯。他说,把灯关了!牟敏像是没有听见,那个人又说了一遍,把灯关了!不行,我理不好的。那人说,亮个小灯就行。
牟敏没有动。那个人自己起来,找到了开关,光线即刻暗了,还没有原来的一半亮。牟敏差不多是摸索着在给他理发了。第一次这样,没听说过这样理的。牟敏低着头,耳朵听着大路上的响动,一辆奔马车从远处响过来,突突突,渐渐地近了,就像开到了自己的眼前。牟敏的心跟着跳,想奔出去,发出一个信号,想着怎样才能发出去信号,身子朝窗口的方向扭,手停了一下。那人警觉起来,不要停!快剪!头埋下来,又开始剪头。奔马车就在她犹豫的瞬间嗵嗵嗵地开过去,村子里又静下来,一股眼泪终于不可阻挡地滚出来,她差一点就要啜泣出来。
辗过的奔马车让牟敏失望,她无法发出什么暗号,她也不能确定对方真的是个逃犯,单凭他的做法、头上的脏还不能成为证据。奔马车要是停下来多好。房东家里今天也没有一个人,本来就没有人,一家人长期在外,偶尔才有人回来,在家的女人前几天去了娘家奔丧,说一个本家的叔不在了,一直都没有回来。要是有一个手机就好了,男人说过给自己买手机的,春天走时还惦念着买手机的事。牟敏说不急,今年春节手里有一个手机就成。这时候显出手机的重要了。牟敏的手不敢停,一停那个人就催,说你快点,你快点行不行!牟敏的手在头发上又动起来,嚓嚓的剪刀在夜里回响,风吹在细沙上,头发茬儿像落地的细雪,剪过的头看上去有了精神。牟敏又习惯地看一下镜子,镜子里是一个模糊的头,模糊中显得更大。那个人突然把头扭了方向,转椅转了个九十度的弯,说,快,就这样理,不看镜子。牟敏愣怔着,想说服他,想对他说这是理发人的习惯,理发店不是剃头挑子,来理发的人统统遵守规矩,怎样理怎样剪是有程序的。可牟敏没有这样说,牟敏在运剪中似乎忘记了恐惧,从惊悚中慢慢镇静下来。她想找一个话题,想了想,牟敏说,大哥,你长得又不是丑,为啥要不对着镜子?对着镜子我已经习惯了,你这不是难为我吗?那个人低着头,张张口,但没有话出来。牟敏又追一句,大哥,这么晚从哪儿过来,怎么也没听见你搁车儿,是步行啊?遇着了啥事儿么?那个人在她的剪刀下有些疲惫,说,理吧,哪来的那么多话。又过了几秒钟,问牟敏,好了吗?牟敏说,没有。牟敏正吃力地理着他的耳根儿,这是通常比较讲究的地方,和脸颊在一个方向,要多下功夫。牟敏睁大眼,弯着腰,乳房从高处垂下来,鼓鼓地耸在客人额前,有一种挑逗。牟敏听见了咽唾沫声,对方的喉咙里咕噜一阵,简单点吧,不用太细。牟敏说,不行,快好了。牟敏完全进入了角色,剪刀换成了推子,电推子发出一阵嗡嗡嗞嗞的响,眼吃力地盯着他的头。
村外的大路上又传来了机动车声,这一次听着像一个小面包车。她想着村里都是谁家有面包车,是不是来这儿理过发。牟敏的手抖了一下,车声近了,她想着怎样跑出去,车灯的两柱光扫过窗户,窗户上一阵白。那人把围裙撩开,站起来挡在门口,盯着窗户上的光,好像在阻止牟敏。光在一瞬间又消逝了,车轮滑过路面,滑过老塘南街,渐行渐远。
灯全灭了,人在黑暗里抹身,这是他理完发又想起要做的事情。炉子上的水激发了他洗身的欲望,他让牟敏给他找一条抹身的毛巾,再把水倒进脸盆时,灯全灭了。他说,你坐下,扭过身。对不起,我得把身洗洗。说话声似乎变得委婉,有了礼貌,恢复了一个人的常态。
牟敏转过身,眼泪哗哗流下来,没想到在这个夜晚没了自由,被挟持了。她寻找想跑出去的机会,但都被他识破。那人说,你要稳当点,我不会伤你,不然…… 话没有说下去。牟敏蓦然想起自己的男人,男人也喜欢这样洗身的,不过,每一次都是堂堂地把身子亮给自己,把灯光打得大亮,旮旮旯旯儿都看得清楚,让自己面对一个男人健壮的身体,替他搓背,男人往往一转身会用湿淋淋的身体把自己裹住,甚至就那样湿淋淋地和自己做了。
但今晚在黑暗中抹身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水的响声就在身旁。大概因为陌生才暗了灯吧?这个男人还懂羞辱。
抹身。弯腰。洗毛巾。水珠。男人的粗气。她想象着盆子里的水,水的颜色。哈出一口气,很累又获得轻松的叹息,这一点像自己的男人。
男人抱住她,是在抹过身后。黑暗里,洗身的声音停下来,牟敏听见细碎的脚步声,从窗外射来的月光在墙上映出一个巨大的身影,在墙上挪动,慢慢地往她的身边靠拢,突然地冲过来抱她。牟敏躲着,绕着转椅,终于被抱住时镜子里模糊一团。在湿淋淋的头发拱过来时,牟敏听见,对不起,我以前就是这样,洗过了要抱自己的女人……牟敏使劲挣,大喊,我不是,我…… 嘴被严严实实地捂住了,就连鼻子也被捂上,她的气息只能从男人的指缝里勉强挤过。然后,牟敏感到一股难以抗拒的蛮力。
二
麦子敲门时,她还蒙头睡在床上。往常这时候门早开了,牟敏每天都准时地把门打开,把炉子燃旺,坐上一壶水,然后走出理发店,在村堤上往远处瞭,薄雾在地里妖娆,庄稼收割了,田埂间溢出一缕缕薄气,河边的树杈缠绕着更厚的岚。理发店里常聚着一堆女人,腾不出手的时候炉子上的水会有人替她拎下,续进暖壶,再帮着温上。还有人甘愿当她的助手,把客人的头发先替她洗了,一边调侃着,牟敏,你要给我工钱的。那种气氛,叽叽喳喳的打骂声,客人们也是喜欢的。女人们喜欢理发店,还因为理发店在南村口,每天能看见给她们带来好消息的投递员,等到她们的邮件或者汇款。麦子的信件和包裹是最多的,每次来了新包裹就呼呼啦啦打开,风把衣服的皱褶捋展了,来了新衣服就穿,甚至就在理发店把一件新衣服换上了,在女人们面前展示出来,不像有的女人藏到柜子里,逢年过节或串亲戚的时候才舍得穿上。麦子喜欢洗头,喜欢在头上变花样,好像一种款式的衣服要配一种发型,隔几天让牟敏把头发整一遍,牟敏呢也是乐意在麦子的头上变花样的。麦子呢不光在理发店帮她温水,打扫,还帮她做饭,顺便把自己的饭也做了,两人打了伙锅。渐渐地,麦子成了她最好的朋友。
当然,她们也喜欢说男人,说在外边的男人,对男人的惦念,说谁谁的男人给家寄得钱多,谁谁包了工程,揽下了一个工地的外架活儿。说牟敏,你如果专门去给工地上的男人理发说不定也行的,城里那么多工地,城里的发屋挺贵的。这些话,牟敏听过,男人们回来也在这儿说过。这一夜,她忽然想到了这个话题,要是真跟着男人去工地上开个小发屋,天天能跟自己的男人在一块儿,也不至于受这样的一次委屈。
她忘了自己怎么从理发店回家的,怎么倒头在家里哭睡的。幸亏丈夫不在家,幸亏没有惊动别人。这样一醒,她又回到了刚刚过去的夜晚,眼前是一个光身的男人。这个晚上真是太可怕了,被劫持了,不,被控制了,老塘南街竟没有一个人来救她,平常还不算太静的夜晚那一夜竟着了魔一样静,像一个村子一个村夜都被挟持了,就是要她来经受这样的一次挟持。不知道她是不是这个夜晚最倒霉的人,但一定是老塘南街被挟持的女人。有些事情好像是有预兆的,不然为什么偏偏这个晚上就睡过了头,往常是已经关门了,回到家里了。这个夜晚,满天的星星和月光看到了她的屈辱、她的委屈。那个人洗完身忽然狠狠地抱住了她,她感到了一个男人的硬、硬的身体、硬的骨骼、硬的胡茬,刚才忘了把胡子也给他刮了;还有在搂着她时背后紧贴她身体的一种硬,像一根钢筋。自己的男人经常这样抱她,那种硬,贴过来时让她有一种温存,有一种冲动。可是这个人让她害怕,让她畏惧,让她打颤、痉挛。她浑身筛动,泪水被一溜子一溜子地筛出来,像一条长河,她哽咽着,你,你别这样,你会遭报应的。那个人搂得更紧,喘着粗气,鼻息穿过脖颈,往耳廓里灌,仿佛要把另一个耳廓穿透,她听见说,我他妈的怕什么报应,我都成这样了,有什么让我再怕的,我迟早会被抓起来的,有青纱帐多好,我吃玉米烧玉米也饿不死我,可是玉米收了,所以说,我快,我快跑不动了。
那男人开始解她的衣裳。她抖成了一把糠,浑身骨架都散了,一股液体滑过裆部,细细的,蚯蚓样流过了地面。她大叫了一声,这一声是喊出来的,她的大叫引来了路边的一只狗叫,门外的招牌又一阵摇晃,她的嘴被及时地捂住,要窒息了。狗叫声停下来,她觉得非常的孤独,哪怕狗多叫上几声也可以为自己壮壮胆子。窗户也被窗帘遮住,星光和月光被挡在外边,竟然无力得穿不过一层软布。她被男人撂倒在床上,更大的畏惧攫住了她,她紧紧地护住了被角,浑身在被窝里打着抖,她知道接下来该有什么事情发生,男人就是这样对付女人的,不过自己的男人是一种表示爱的冲动,眼前的这个人是一个逃犯,一个肯定犯了罪又不知犯了什么罪的人。她的眼可怜地瞅着光膀子的人,她知道接下来身上就会被压上一个男人一个陌生的男人,山一样将她压住、压碎,她觉得自己即刻就要死了。她惊惧地忘了流泪,只是筛糠着,抖抖嗦嗦地说,你,你不要,你,你,你……她依然看到的是一双饥饿的眼睛,一个男人的欲望势不可挡,接下来的事情似乎就要来临。她尖叫一声,格外尖利,像一把刀子刺穿了某个内脏,她捂住头,浑身筛动,整个宇宙在经历一场地震。然而,是可怕的沉默,几分钟的漫长。几分钟后,她忽然听见一个男人的呜呜声,像一头老牛,闷闷的,男人的眼泪扑扑嗒嗒滚在地上。外边又有几声狗吠,有夜猫的叫声,夜更静,一层恐惧在深夜如翻卷的洪水,整个世界被淹没了。
她颤颤地掀开被头,愣住了,她的眼泪也在一刹那,在这个陌生人、逃犯面前倾泄而出:她的屈辱、她的忍受、她的理想、她的不开怀,她留守的孤独,对公婆白眼的忍耐,一下子全调动了……妈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就连这个夜晚也要让我遇到这个男人,她在刹那间,忘记了防线,想反抗,去拿剃须刀的念头松懈下来。不知从哪儿来的胆量,她劝起了面前的男人,你算什么男人,欺负我一个可怜的女人,我给你理发,给你洗头,我半夜守在这里就是等你的耻辱啊?自首吧,别再跑了,跑来跑去会跑不动的,你能跑到哪里?只能钻玉米地算什么男人?别觉得窝囊,别觉得屈,去吧,早些出来,你家里人还在等你,等你出来再洗你的耻辱吧。不要折磨自己……她的眼泪噼噼啪啪往地上掉,淌成了一条河。
静了一会儿。这个人摇了摇头,说,你不要说了,现在我告诉你,你不要怕,我不会再把你怎样,不会,就是因为女人我才动了别人,把别人动残了。那个人太不像话了,我回家的时候他竟然让我碰上了,老婆才告诉我,她被欺压好多天了。我咽不下这口气,谁能咽下?对不起,大妹子,我让你害怕了,把你吓着了,我对不起你,我,我不是要故意吓你,我躲了几个月了,玉米刷刷长时我就开始躲,现在玉米都收了,地光秃秃的,我还在躲,我天天吃生玉米都吃怕了,后半辈子我都不会吃一口烧玉米生玉米了。我今天就是想借你的水洗一洗,借你的手艺把头整整。其实我还算讲究的一个人,我不想浪荡,我的头上身上都痒,现在好了,我感谢你,将来我会来给你送理发钱,来谢你的。那个人说着还是近近地看着她,一双眼离她很近,眼泪落在了她的脸上。
牟敏松了一口气,说,不用了,不用了大哥,听我的劝告你去自首吧,迟早得走到那个地方,别拖了,逃不过的,政府不认你说的这个理,你终究是把人打残了。别拖,拖来拖去拖的都是自己,耽误更多……那个人好像太疲惫了,终于把眼挪开了。从地上站起来,他拨拉着刚理过的头,得寸进尺地说,大妹子,我,我有个想法,我想在床上困一觉,我,我不瞒你说,我好长时间都没睡过床了,我都不知道躺床的滋味了,真的,我就是想床了,在床上好好地困一宿。大妹子,怎么样啊?
牟敏想了想,牟敏想不让也是不行的。说,你来吧,今天我把床让给你,我本来很少在理发店睡的,今天打过了盹让你赶上了。牟敏起身往床下跳,那人一手拽住了,不行,你必须睡在床上,你不能离开我,这样我才能睡着。牟敏说,我不会告你,你安心睡吧,这个时候我到哪里去?那个人看看床,掀开被子看了看,被子软绵绵的,摸上去挺舒服,棉絮厚厚暖暖的,有一种新棉的味道。他打了个哈欠,眼里透出对床的渴望。可他没有钻被窝,眼在屋子里瞅着,最后他把眼落在一根用来搭毛巾、搭围裙的绳子上。他说,对不起,我想睡个安稳觉,你只好委屈了。牟敏就是这时候忽然想起了什么,说,你,你先别绑我,我这里有方便面,我给你泡,我知道你饿,你肚子都响了。那人耷着头,又打了哈欠,说,我急着理发,急着洗身都把肚忘了……
牟敏最后还是被绑上了,被迫坐在被子的边上,头倚着墙听着窗外的夜鸟声,后来听见了他的鼾声,牟敏的泪又扑扑簌簌地落下来。这个夜晚她注定是孤独的,无助的,她睡不着,她只有半闭着眼睛,瞅着窗外和挤进房间的夜色,她在迷蒙中看着躺在自己身边的人,一个陌生的男人的消瘦、苍白的脸色,她竟然有些心疼,甚至想着,要是自己的男人该怎么办?男人惊悸地醒过来几次,慌乱地坐起来,癔症着问,你是谁,我,我在哪里?她轻声着说,睡吧,想睡就好好地睡一觉吧。说,你放心,我都被你绑上了……
听见麦子的叫声,她赶忙洗把脸,泪痕、疲倦和惊惧都洗掉了。门吱呀一声打开,出了门,她在前边往理发店走,撇了麦子很远,实际上眼里噙了泪。看见站在门外的麦子时她真的想伏在麦子的肩头哭一场,最后使劲忍住了。胡同不长,很快就看见了胡同外的路,看到理发店时她还是又打了一个颤。那个人差一点就睡过去了,早起赶生意的奔马车把他震醒,他忽地坐起来,窗口已穿过一层鱼肚白,像一股细线,天拱破了黎明前的那层黑暗。他看一眼蹴在床头的牟敏,弯下腰鞠了个深躬,门哗啦打开,然后又折回身,呼呼啦啦把牟敏解开,再鞠个躬,从门外消逝了。
三
牟敏是3天、或者5天、或者10天以后出去的。老塘南街的女人为她的出走把日期都记糊涂了,对牟敏的不辞而别有些微词、有些尤怨、有些失落。这个牟敏想男人想疯了,怎么突然就消失了,连声招呼都不打,平常不大表达的牟敏,原来是老塘南街最风骚的娘儿们,可是风骚几年也没把自己的肚子骚大,她家的中药袋子快装一麻袋了。其实这几个女人是想牟敏,不想让牟敏走,怎么走也得打个招呼吧,疯疯癫癫风风火火地就走了。
理发店前还是一伙女人经常扎着堆儿,望着村外的路等着那个骑摩托的投递员来。理发店的关门打击了女人们的积极性,聚的人慢慢稀少了。女人中最抑郁的是麦子,她觉得生活中一下子就少了许多的寄托:她要盘头、洗面,要穿着新衣裳来理发店满足她的虚荣,让牟敏们看她的变化,甚至把衣裳和牟敏交换着穿,也随便送出去三件两件。可是,她搞不清牟敏的变化,牟敏说转变就是180度或者360度,一下子跑出去了,连个话头也没有留。这个狐狸精,准是又到了排卵期,找男人种孩子去了,说不定这一次就种上了。种上吧,有个孩子过得才有着落。她站在理发店前,没有温在火上的水壶,没有等在理发店的客人,没有旋到理发店的风、镜子里的小鸟儿;没有往常的打闹、讥诮,她感到的是一层孤单。麦子还来,还会来,还天天来,有时就自己独独地站在理发店前,带着几分的失落,有时就砰砰敲着理发店的门,一溜儿白牙咬着下颌,发泄似的,喊着,理发店,牟敏,我把你们砸了……接着转过身,麦子的目光怅惘起来、迷乱起来、无聊起来、孤独起来。有一天她从理发店门前出村,慢慢悠悠地顺着大路走,秋天已凉了的风吹着她蓝色的套裙,套裙的一个角儿在风中翘动,仿佛是要走很远很远去接牟敏回来。
四
怎么说呢,这一天,牟敏居然站到了一个叫槐树屯的村庄。槐树屯这三个字是那个男人不经意间说出来的,好像是说,我在槐屯……或说是槐树屯……鬼使神差,她竟然找来了,一路打听着找到了。看见槐树屯时她还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有时候,是自己也说不清、解释不清自己的。
本来是要去找男人朱马的,却突然改变了方向,在路上多走了两天。她是带着工具出来的,背了一个旅行包,旅行包扛在肩上,使她更显得瘦小。她想好了,如果能在工地上理发就住下了,也和自己男人守在一起。
远远地看见的那个大槐树,叶子里掺进了微黄,再强的树木原来也经不住秋后的几场霜气。牟敏有了目标,牟敏的目标就是坐在大槐树下,仰着头,看大槐树,有心无心地等待着什么。后来的几天里她又在理发店守过,衣兜里始终忘不了放一把剃头刀,有几次等到了深夜,凉风从门缝、从窗缝里挤进来,让她打一个冷颤。她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等待一个人吗?那个人伤害了你吗?到底还是伤害了他自己?对,反正他再来要不报警,要不就是掏出这把刀子,再好好地劝劝他,别再傻躲。她无数次这样想,又把自己否定。自首了吗?那个人!那天凌晨之后,他又去了哪里?怎么走的?往西走,几里地之外就是一条连接南北的公路,路上可以截到过路的客车,也许他就是从公路上随便坐上了一辆车,走了,在另一个地方战战兢兢的生活……
一天黄昏,她往很远很远的田野里走去。以前在理发店也有过这样,会忽然地想往地里去,站在麦地或秋田里。现在,庄稼都收了,地里长出的是又一季的麦苗儿,大地铺展着,麦苗间隙露出干燥的土地。她却看见的是满野的秋庄稼,浩浩荡荡的玉米,想象着一个人天天在庄稼地里吃住或者睡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都会使他惊悸,那几个月的日子到底是怎样度过的。她在地头坐得太久都忘了理发店,最后还是麦子在村路上喊,牟敏,牟敏……她才匆匆地跑回去。
她在大槐树下等到了一条狗。大槐树上残余的槐叶儿在秋风里晃动,那条狗蹲在槐树下,尾巴拖在地上,抬着头朝村外的路上望着,浑身的黄毛,有些邋遢,眼里有一种迷蒙;狗看了看牟敏,狗的眼角有一团眼屎,像一个肉瘤子滴溜着。狗也往大槐树上望,那个人那一天好像说了,他的女人差一点吊在大槐树上,槐树上的神把她救了。牟敏仰着头,久久地看着槐树,又回过头看着槐树下的黄狗。
来了一个老人,和狗一起望着村外的路,拐棍捣在地上溅起几星黄尘。狗往他的身边靠了靠,撒娇、尤怨、无奈,叽叽几声,也许还有别的意思,又低低地几声吠叫。老人说,别等了,伙计……老人低头看看狗,狗支着耳朵……老人和狗又望着远处、远处的路,狗的眼望得很远,站得比老人还直。
牟敏远远地看着,摸一下心口,有点疼,隐隐的。牟敏忍不住又奇怪地往村里走,好像有人在催她一样。老人和狗都扭过脸,看着她,有些狐疑。听到哒哒地小蹄子声,牟敏转过身,狗在她的身后撵过来,狗爪子下是一绺细细的黄土。狗跑到了她的前头,扭过头,汪汪叫几声,又往前走,像有些抵触又像在给她带路……她回过头,又看看那棵老槐树,好像已经知道了答案。她拎了拎肩上的包,回转身,朝公路上走。
有一天,牟敏终于找到了朱马——她的丈夫。似乎带着满身的风尘、疲倦,一见丈夫她就哭了,哭得很痛,酣畅淋漓,稀里哗啦,哭声里带着细细的哨音。她最终没有说出哭的理由,不知道该怎样说,想了想她把头扬起来,就不说了。丈夫把她领到了一家小旅馆,一进门就心急火燎地把她裹住,她先是筛糠着,像是过于激动,男人怎么也得不成,丈夫叹息着有些恼火。后来,像是终于被唤醒了,或者仿佛有过一次唤醒,牟敏的欲望特别的强烈,她一次次呼唤,紧紧地搂着丈夫,当丈夫真正排山倒海时她又泪雨哗哗起来。
五
牟敏回到老塘南街是一场雪后。一下车,就看见了理发店,打开门,一股潮气扑面而来,窗台上有挤过来的雪,镜子上蒙着灰尘。好像一直在等她回来,麦子随后就过来了,麦子的手里握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老塘南街理发店 收。麦子把牟敏搂在怀里,喃喃地说,牟敏,你可回来了!牟敏,快生火吧,我早该做头了。
牟敏把灯光打开,房间里一下子亮堂了。她开始收拾,开始生火,一有火,屋子里就暖和了。她抓了抓麦子的头,说麦子,我今天就把头给你做了。她从麦子手里接过了那封信,低下头,在生着的炉子上燃着了。灰烬在炉子上蜷曲,小飞蛾一样飞。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