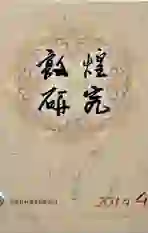永昌圣容寺的历史变迁探赜
2014-04-29党寿山
内容摘要:《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碑铭和西夏仁孝陵墓出土的西夏文残碑中都提到圣容寺,此圣容寺在哪里,它的变迁如何,对此史学界尚有不同的见解。本文除对圣容寺的位置、来历作了阐述外,还对番和县圣容寺与凉州大云寺的关系、西夏时期的圣容寺作了比较和考证,这对研究番和县圣容寺及与圣容寺有关的敦煌莫高窟艺术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凉州;番和县;圣容寺;大云寺;西夏;莫高窟
中图分类号:K928.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4-0101-08
以圣容像命名的圣容寺也有直呼圣容瑞像、圣容佛者,如敦煌莫高窟第231窟和第237窟等中唐石窟中就绘制有御山石佛瑞像,在“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的榜题中就出现了“圣容瑞像”的名称(见图1)。永昌县西夏千佛阁遗址中有“圣容佛 至千佛阁”的题记,这里的“圣容佛”指的就是圣容寺佛[1]。至于圣容寺,不仅西夏有,而且元代及其后也有。李逸友在《黑城出土文书》[2]一书中提到了元代亦集乃路境内的众多寺庙,其中就有圣容寺。就西夏而言,《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国境内有寺院中圣容一种者,当遣常住镇守者正副二提举,此外不许寺中多遣提举”[3]。这说明圣容提举司设置于各个圣容寺,因此西夏时期的圣容寺不只一座。
这里说的圣容寺是西夏时期的一座寺院。《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下文简称凉州西夏碑)的汉文碑铭记载:“庆寺监修都大勾当、行宫三司正兼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律晶赐绯僧药乜永铨。”西夏仁孝陵墓出土的西夏文残碑中也有“年中西隅,圣容众宫”之说。那么碑铭中所说的这座圣容寺究竟在哪里,多年来由于资料缺乏,学术界对此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笔者曾参与过永昌县西夏千佛阁遗址的清理和天宝元年杨播所记之《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下文简称杨播碑)的考释工作,因此试图对这座圣容寺的位置、来历,它与凉州大云寺的关系以及西夏时期的这座圣容寺进行探讨。
一 圣容寺的位置与来历
关于碑文所说的圣容寺究竟在什么地方,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圣容寺在凉州,因为凉州西夏碑出自凉州[4];另一种认为圣容寺在西夏王陵,因为出现圣容寺名称的西夏文残碑出自西夏王陵[5]。两种看法中,第一种看法的赞同者较多,特别是史金波先生还指出了圣容寺的具体位置在甘肃永昌县北10公里处的御山峡西端,凉州碑所记圣容寺与永昌圣容寺可能是同一寺庙[6]。2011年在武威召开的“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上,梁松涛、杨富学先生明确地指出:凉州西夏碑及西夏陵墓残碑中的圣容寺就是凉州番禾瑞像所在的圣容寺[7]。作者同意这种看法,并对圣容寺的来历稍加补正。
1. 永昌圣容寺,初为瑞像寺,是一座极具神秘色彩的早期皇家寺院。
永昌县古称番禾、番和、盘和,属凉州。早在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神僧刘萨诃西游路经此地,于御山谷中“授记”,预言“此山崖当有像出”[8]。如果灵相具足,则世道平安;如有残缺,则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经八十七载,至正光元年(520)”,一日,御谷山上“因大风雨,雷震山岩,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像端严,唯无有首”[8]。此时,北魏朝廷政道衰颓,世乱民苦,萨诃预言验矣!40年后,在200里外的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佛头,“奉安像身,宛然符合”[8],于是官民“悲欣千里”。从此,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图2)。御山谷中石佛瑞像的神异传说传到北周朝廷,于是保定元年(561)“敕使宇文俭检覆灵验不虚,便敕凉、甘、肃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至三年功毕,■僧七十人,置屯三”[9],“立为瑞像寺”[8]。瑞像寺的建造,其使役人力之众,建造时间之长,居住僧人之多,都是一般寺院无可比拟的。
2. 隋代将瑞像寺改为“感通寺”,成为朝野重视的海内名寺。
瑞像寺建成后的第十年,即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遭“宇文灭法”之变,新建不久的寺院也罹其难,“废三教,敕使将欲毁像,像乃放光溢庭,使人惶怖”;“行至寺,放火焚烧,应时大雪翳空而下,祥风缭绕,扑灭其焰”[9],“周虽毁教,不及此像”[8]。到了隋代,由于隋文帝好佛,曾经一度遭到灭佛打击的佛教迅速得到了恢复,“开皇之始,经像大弘,庄饰尊仪,更崇寺宇”[10]。“开皇通法,依前置寺”[8]。凉州番禾县的瑞像寺仍然得到了如前的恢复。然后方有“开 皇九年(589)凉州总管燕国公诣寺礼拜”、“樊俭等至寺供养”[9]等礼佛活动。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故令模写传形”[10]。
3. 唐代感通寺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天宝年间,当将“感通寺”更名为“圣容寺”。
贞观十年,三藏法师从五天竺国来,讲述瑞像来历;朝廷重臣也先后到感通寺礼谒。神龙初,兵部尚书郭元振出任安西都护,曾诣寺礼谒,因画其像;不久,唐中宗又令御史霍嗣光持幡花、绣袈裟等物到寺敬礼[9]。由此可以看出,瑞像寺重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在隋炀帝大业五年(609)改为感通寺后,至杨播碑记的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之间,这里香火一直很盛。
至于什么时候将感通寺改名为圣容寺,由于文献资料缺乏,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问题还要从寺院前后现存两座唐塔的建造时间说起。有说唐塔建造于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7),时有僧人1500人,中宗又派特使到寺敬物;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以后吐蕃统治河西时,该寺由感通寺改为圣容寺(据敦煌莫高窟壁画)[11]。有说改圣容寺的时间是吐蕃占领时期,但唐塔中有“番僧一千五百人”的记载,这证明吐蕃占领期感通寺香火有增无减,并非唐中宗前后的寺院规模[12]。上述二说不无道理。就“番僧一千五百人”而言,开始我们也以为“番僧”是指吐蕃僧,后查阅有关资料发现,这里的“番僧”并非吐蕃僧,而是西夏时的党项族僧人。因此,这则题记并不能证明吐蕃占领期感通寺香火更盛,并将感通寺改名为圣容寺。寺院的名称多在寺院建成或大规模地重修、扩建后的竣工庆典时命名或更名。如此寺在北周保定四年(564)落成后命名为瑞像寺。也有在像皇帝驾临这样的重大事件时即兴改名的。如隋炀帝到此寺“躬往礼敬”,就改瑞像寺为感通寺。如果将“感通寺”的改名与该寺100多年以后的重修扩建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感通寺是在这种情况下改名为圣容寺的。
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与否以及历代帝王对宗教的好恶程度,直接影响着民间宗教活动的盛衰。唐天宝十四年(755)发生了安史之乱,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奉命征讨安禄山。“敕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唐永泰二年(766),吐蕃围凉州,凉州遂陷。吐蕃占领凉州后,广大人民深受战火之苦,背井离乡,迫切希望唐王朝能收复失地,重回家园。中唐诗人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这是吐蕃占领前凉州的繁荣景象。而此后则是“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西凉之道尔阻修。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大规模地重修、扩建凉州境内的番和县感通寺,并改名为圣容寺,只能在吐蕃占领前,在吐蕃占领期间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唐塔的建造时间可能不是在吐蕃占领前的唐中宗(705—707)前后,因为:第一,杨播碑镌刻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如果在此之前修建佛塔,碑文连朝臣诣寺礼谒的情节都未忽略,必然会将建造佛塔的这一重大事件记载下来;第二,感通寺后佛塔中有壁画数层,下层甬道的东壁青砖上有“乾元二年”(759)的墨书题记,这则题记,墨书在青砖上,可证建塔时间在乾元二年之前不久,因为题记上面还未被壁画覆盖。乾元为唐肃宗李亨年号,说明寺院前后二塔的建造时间在乾元二年之前。天宝元年(742)至乾元二年(759)相隔17年时间,这时候正值“开元天宝盛世”,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重修寺院,扩建佛塔,并将感通寺更名为圣容寺是很有可能的。
盛唐时改名圣容寺,到吐蕃统治的中唐时期于敦煌莫高窟开凿的第231、237诸窟中绘制御山石佛瑞像,并在“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的榜题中出现“圣容瑞像”的名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4. 永昌县圣容寺是一座备受河西人民崇拜的瑞像寺院。
圣容寺之所以驰名中外,主要是寺内有依山雕造的瑞像。外来教徒想摹写瑞像真容,却不能把瑞像的高低粗细准确地测量出来。因为瑞像有时高,有时低;时而粗,时而细。说瑞像一丈八尺,这只是个约数。因此人们都认为瑞像有灵,信教者和摹写、雕造瑞像者越来越多。月氏国的婆罗门专程来摹写瑞像带回去供奉。永昌县金川西村出土的北周瑞光石佛造像、红山窑乡水泉子村青龙山庙遗址发现的唐青龙山石佛造像[13]、敦煌莫高窟隋末唐初第203窟主室西壁的佛龛中和盛唐第300窟西璧的佛龛[14]中的塑像,都是御山石佛瑞像。
自唐德宗贞元六年(790)以后至9世纪中叶,凉州以西诸地尽入吐蕃手中。长期战争的创伤和河西地区不安定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向“消灾致富”的神灵瑞像和圣僧求助。加之吐蕃实行“罢黜异端,独崇佛教”的政策,所以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崇佛之风盛行,绘制以凉州御山石佛瑞像为题材的壁画就更多。在圣容寺后山佛塔内壁第二层壁画中以及莫高窟中唐时期开凿的第231、237窟的佛龛之顶都绘有此瑞像。五代时期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所开功德窟第98窟,曹元忠夫妇所开功德窟第61窟,主室佛坛背屏后面的壁画也是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变相。第72窟多以为开凿于五代末期,霍熙亮先生经过仔细考察,认为此窟建造于晚唐初期,后经五代、北宋重修[15]。该窟南壁以整壁的画面形同经变的形式描绘了一幅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变相。画面宏伟庞大,气势磅礴,情节繁多。它的下部因自然损坏而模糊不清,上部保存完整,存有榜题和画面30余幅(条),如“圣容像初下无头时”,“却得圣容像本头安置仍旧时”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永昌县依山雕造石佛瑞像的圣容寺在河西走廊人民心目中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二 永昌圣容寺与凉州大云寺
杨播碑主要记载的是番和县依山石佛的出现和圣容寺的变迁,按常理这种碑应该由圣容寺负责撰写、镌刻并立在圣容寺;可是此碑却由凉州大云寺出面完成,并安放在大云寺中。这是为什么?大云寺是什么样的寺院?它和圣容寺又有什么渊源关系?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来探讨。
1. 大云寺与圣容寺一样,都是皇家寺院,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变迁史。
凉州西夏碑之汉文碑铭记载:“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宝塔,奉安舍利,报佛恩重。今武威郡塔即其数也。自周至晋,千有余载,中间兴废,经典莫记。张轨称制(西)凉,治建宫室,适当遗址。”到张天锡时,“宫中数多灵瑞,天锡异其事。时有人谓天锡曰:‘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宫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锡遂舍其宫为寺,就其地建塔”。唐景云二年《凉州卫大云古刹功德碑》说得更详细:“大云寺者,晋凉州牧张天锡升平之年所置也,本名宏藏寺,后改为大云。因则天大圣皇妃临朝之日,创诸州各置大云,遂改号为天赐庵。”“花楼院有七层木浮图,即张氏建寺之日造,高一百八十尺,层列周围二十八间。面列四户八窗,一一相似。屋巍巍以崇立,殿赫赫以宏敞。”西夏时,天赐庵改为护国寺,七层木浮图称感通塔。据凉州西夏碑碑文记载,天祐民安四至五年(1093—1094)对寺塔进行了重修,“金碧相向,辉耀日月,焕然一新,丽矣壮矣”。1927年,除古钟楼巍然独存外,其余建筑均毁于地震。
2. 魏晋南北朝时期,凉州宏藏寺可能是凉州御山挺出石佛瑞像的主要策划者。
1981年在原大云寺旧址发现的杨播碑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北周明帝宇文毓元年(557),凉州“之东七里涧,夜有神光照烛见像首,众疑必是御山灵相。捧戴于肩,相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四众悲欣千里”。这些情节中,除去神化成分外,还包括命令工匠选择石材雕刻佛头,僧众肩舆佛头至御山,工匠安置佛头以及石佛瑞像身首合一后,官民僧侣大宴庆贺、伎乐百戏表演助兴。
当时御山谷中只有无头石佛瑞像,并无佛教寺院,上述这些佛事活动,包括40年前雕造的石佛像身在内,是哪个部门倡导并组织实施的?我们认为可能非凉州宏藏寺莫属。因为自前凉以后,凉州是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前凉建造的宏藏寺是凉州最早的皇家佛教寺院,也是我国早期的佛教寺院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在凉州御山谷中雕造石佛瑞像,是宏藏寺传播弘扬佛教,为后来在这里建造瑞像寺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3. 隋唐之际,永昌圣容寺与凉州大云寺两寺之间一度是上、下寺的关系。
天宝元年碑还记载:宏藏寺在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之前,“便以此处为白马寺,至宇文灭法,其地□俗居者多不安,遂复施为感通下寺”。建德三年(574)也就是瑞像寺建成的第十年,在宇文灭法的大潮中,新建不久的瑞像寺也在废除之列。好在“虽遭废除,像犹特立”,在“开皇之始,经像大弘,庄饰尊仪,更崇寺宇”[10],瑞像寺得到了恢复。尤其在大业五年(609)改名为感通寺后,香火兴盛,名扬天下。而这时的白马寺,虽然没有因“宇文灭法”,遭到灭顶之灾,但这里的“俗居者多不安”,于是将白马寺复又改为感通下寺,与隋炀帝改瑞像寺名为感通寺的“感通”下加一“下”字,以示与感通寺的区别。由此可见两寺之间相存相依的密切关系。
天宝元年碑上说:“大云寺僧元明先住彼寺”,“乃有灯光流照,钟声飞响,相续不断,莫测其由。”[10]说明在唐代,两寺僧人也许可以相互调动,往来不断。
4. 西夏时圣容寺与护国寺同是凉州的两大寺院,两寺僧众同归一个提举司领导。
从凉州西夏碑碑文可以看出,除护国寺的塔名仍沿用了隋炀帝御笔题额的“感通”二字外,在塔寺重修后的竣工典礼上,既有其他官员,还有“庆寺监都大勾当、行宫三司正兼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律晶赐绯僧药乜永铨”,这里说的感通塔即护国寺感通塔。药乜永铨不但是庆寺监修大勾当,而且是圣容寺与感通塔的两众提举。圣容寺与感通塔同属药乜永铨领导,只是圣容寺的地位更为显赫。
5. 大云寺杨播碑所记圣容瑞像和瑞像寺的变迁史不仅是河西诸多寺、窟塑像与壁画的重要题材,就连杨播碑本身也是佛教信徒们所崇拜的对象。
除了永昌县寺庙遗址外,在武威石佛崖、张掖马蹄寺、酒泉文殊山等石窟均有圣容瑞像的壁画。敦煌莫高窟第72窟南壁壁画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变就是依据天宝元年碑的内容绘制的。其中一幅画面上有一碑亭,亭前二信士一立一跪双手合十,一僧伏地叩首,一僧跪地拜读,其后有鞍马四匹,榜题为“罗汉见圣容碑记时”。据霍熙亮先生考证,此碑记应为唐天宝元年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碑[15](图3)。这充分说明了永昌圣容寺、凉州大云寺与杨播碑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它们在佛教徒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三 西夏时期的圣容寺
西夏王国自始至终都非常崇敬佛教,不惜花费巨资投入佛教。凉州西夏碑说得很清楚:“天地禋祀,必庄必敬。宗庙祭享,以时以思。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名迹显敞,古今不泯”的圣容寺自然是重点修葺的佛宇遗址。
西夏重修圣容寺的时间,没有明确资料可考。我们只能从以下两处题记中予以推断。一处是1978年8—9月,武威地区文物工作队在圣容寺西约一公里处的毛卜拉台地上发现了西夏千佛阁遗址,从遗留的残垣断壁上可以看出它是一座被焚毁了的佛教建筑,其阁中有塔、阁内及塔底层上四周绘有千佛。塔呈正方形,塔的底层之上又残存三级塔层,逐级内收。塔底层四周有墨书题记,有明确纪年的为“大德己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灵武人巡礼到千佛阁”。其中涉及年代最早的汉文题记有“丁 酉七年八月十六日……净信弟子,四人巡礼”;最晚的有“天 盛五年廿七日巡礼”。这一时期的丁酉七年,只有北宋徽宗赵佶政和七年(1117)与此相符,也就是西夏崇宗赵乾顺雍宁四年(1117)[1]230。另外一处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其北壁西侧禅窟后壁所绘的四位西夏供养人正捧花礼拜一方塔。方塔底层上有叠涩十层,其上方为树刹,刹顶有宝盖。塔下有墨书西夏文题记十行。汉译文略云:“雍宁乙未二年(1115)九月二十三日,麻尼则兰、嵬立盛山……一行八人,同来行愿。”[16]此塔形制似与敦煌莫高窟第76窟东壁宋初壁画八塔变中所绘之单层叠涩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17]。宿白先生把这种塔归纳在西夏兴建佛塔的第一阶段,即自西夏景宗元昊称帝建国迄仁宗仁孝以前(1138—1139)。
上述莫高窟壁画上所绘方塔与千佛阁内塔的形制极为相似,并且题记时间都在西夏崇宗赵乾顺雍宁年间(1114—1118),因此千佛阁的建造应在西夏建国到雍宁四年(1117)之前这一阶段。
圣容寺与千佛阁毗邻,这一时期西夏能够新建千佛阁,久负盛名的圣容寺必然会得到大规模的修复。如果此说不谬,圣容寺的重修也当在西夏建国至雍宁四年之间。
西夏时期的圣容寺规模宏大,盛况空前。从以下五个方面,大体能够窥见其当年的盛况。
1. 西夏时圣容寺的僧人超过已往任何时候。
寺后山顶上有通高16.2米的唐代七级方形砖塔。塔内有壁画数层,上有“番僧一千五百人”和“圣容寺”的题记。一座寺院有1500人的番僧,可见其寺院规模之大。北周保定元年(561),朝廷调集“凉、甘、肃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至三年功毕”,寺院僧人也只有70人,而西夏时仅番僧就有1500人,是当年僧人的20多倍。
圣容寺塔内题记中的“番僧”系指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僧。这种事例较多,如凉州西夏碑汉文碑铭提到“番汉四众提举赐绯僧王那征迁”,这里的“番汉四众”表明武威地区主要有四个民族:番(党项人)、汉、羌(即吐蕃人)和回鹘人。也有把西夏文字称“番”字者,如《番汉合时掌中珠》就是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词典;凉州西夏碑汉文碑铭中的“书番碑旌记典集令批浑嵬名迁”就是指浑嵬名迁是“书番碑”者,即西夏文碑的书写者。
西夏时凉州境内的四种民族都信仰佛教,因此圣容寺僧人中不仅有党项人,还有其他三种民族,假设汉、羌、回鹘僧人各占党项僧的三分之一,就是1500人,加上党项僧人1500人,合起来就是3000人的僧人阵容。如果没有宏伟、壮观的寺院建筑、量大面广的僧房僧舍、雄厚的寺院经济,这么多僧人是无法在这里进行佛事活动、居住和生活的。
2. 西夏时巡礼圣容寺的各族佛教信徒,东来西往,熙熙攘攘,香火一直不断。
圣容寺旁边西夏千佛阁遗址的题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千佛阁内残存的方塔底层四面都有密密麻麻的各种民族的文字题记,如党项族的西夏文,汉族的汉文,吐蕃族的藏文,回鹘族的回鹘文。其中仅汉文题记就有14则。这些题记的作者不仅有西凉州和甘肃省境内的巡礼者,还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灵武人;不仅有庶民百姓,还有如大都督府、鲍翁王这样的达官贵族;不仅有西夏辖区的佛教信徒,还有如政和七年(1117)由北宋来此朝拜的净信弟子。虽然在北宋的百余年间,西夏与宋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但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民间的往来还是不间断的。由此可以看出,各民族不分贫富贵贱,打破地域和政权割据的界线,友好往来,和睦相处,共同的宗教信仰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圣容寺和千佛阁同在御山峡谷间,一在中部,一在西头,相隔仅一公里,东来的佛教信徒要到千佛阁,必然经过圣容寺。千佛阁有一则汉文题记说“圣容佛至千佛阁记”。“圣容佛”指圣容寺的圣容瑞像。看来各族信徒主要还是冲着圣容寺慕名而来的。在千佛阁小小的一座佛塔底层上就有数十则题记,规模宏大的圣容寺内一定有数不清的净信弟子的题记,可惜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了。
3. 西夏时仁宗皇帝御驾巡行圣容寺。
今张掖市有一方黑水河建桥碑,西夏乾祐七年(1176)立于甘州黑水河边,碑两面分别用汉文和藏文镌刻。碑刻内容为仁宗希望诸多神灵保佑桥道长久,水患永息。其汉文碑铭云:“朕昔已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7]。从这里可以看出仁宗在乾祐七年以前曾亲临甘州祭神。仁宗到甘州,凉州是必经之路,尤其凉州有护国寺、感通塔,有番禾县石佛瑞像寺,笃信佛教的仁宗自然会到这里来。西夏文宫廷诗集中有一首《严驾西行烧香歌》,记载了西夏皇帝曾御驾西行到达凉州护国寺和圣容寺。歌词与凉州西夏碑汉文碑铭中谓感通塔“心计神妙,准绳特异,材用质简,斤踪斧迹,极其疏略,视之如容易可及,然历代工匠,营心役思,终不能度其规矩”的记载以及西夏文碑铭对感通塔的记载是相符的。凉州塔,当时被称为“凉州金塔”。所以歌词中的“巧匠手贤做塔庙,佛之眼目生香谚”[7]指的是凉州护国寺感通塔;“雕做番禾山梵王玉身佛,所雕像栩栩如生有神力,弥勒佛红孺衣”[7]指的是番禾石佛瑞像。
4. 圣容寺在西夏时期,当应仍属皇家寺院,在西夏国的地位是很高的,政府在这里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凉州西夏碑汉文碑铭记载,在重修护国寺感通塔后,参加竣工庆典的各级官吏中有“庆寺监修都大勾当、行宫三司正兼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律晶赐绯僧药乜永铨”,西夏文碑铭说药乜永铨是“解经和尚”,两者都说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行宫三司正是由解经僧药乜永铨担任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确规定:“国境内有寺院中圣容一种者,当遣常住镇守者正副二提举,此外不许寺中多遣提举。倘若违律,不应遣而遣时,遣者、被遣者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3]。同时,对其机构设置、等级也有明确规定,即专设圣容提举司,属中等司[3]363。一司圣容提举一正一副[3]369。由于僧人的政治地位很高,加之这里生活条件好,难怪一座寺院僧人就多达数千人。
这里有个问题令人疑惑:既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只能在圣容寺设置圣容提举司,为什么凉州西夏碑汉文碑铭中提到凉州护国寺有感通塔番汉四众提举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否这样理解:凉州西夏碑镌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在此之前并无此规定,40多年后的天盛年间,才改旧新定律令:除圣容提举外,诸司不许遣提举。说明在此之前像护国寺这样的大寺院是可以设提举的。
5. 圣容寺东面的花大门摩崖塔葬是西夏圣容寺盛况空前的实物见证。
花大门摩崖佛塔石刻,雕刻在长约50米的红砂岩山体上。佛塔刻在佛龛内,有50余座。佛塔中间有方窟,是存放圣容寺有身份的僧人骨灰的地方。与银川西夏王陵的塔式陵台、武威的木缘塔同属塔葬;所不同的是前者与土葬结合,后者与山葬结合,是西夏的另一种塔式墓葬(图4)。这种葬式在国内很罕见。这些佛塔数量较多,造型奇特,雕刻精巧,不仅反映了西夏圣容寺僧侣之多、气势之宏伟,也是研究西夏葬俗、雕刻艺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可知,在元代凉州的佛教寺院多遭兵燹,明清时才逐渐恢复。如明天启二年(1622)《增修大云寺碑记》记载:“凉州大云古刹,纪其巅末,有唐宋二碑仿佛可考。元末兵燹以后,重为鼎新,爰复古迹。”[18]明宣德五年《重修凉州百塔志》也说百塔寺“元季兵焚,颓毁殆尽,瓦砾仅存。宣德四年……乃募缘重修寺塔”[18]98。在圣容寺旁的西夏千佛阁遗址中,方塔底层的许多题记里未见有元代题记,封土堆中又尽是烧毁的木构建筑材料,因此千佛阁可能也在元代遭兵燹。若千佛阁如此,圣容寺必是同样下场。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圣容寺得到重修,但这时已经是日趋衰落,黯然失色了。
现在,圣容寺原有的木构建筑已荡然无存,但依山雕造的御山浮雕瑞像身躯犹在,凉州七里涧发现的像首尚存,寺院前后山上的唐代方形砖塔仍巍然屹立,曾经名扬四海的圣容石佛瑞像和以它为依托的圣容寺虽然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它在中国佛教史上、在河西诸寺、石窟中,尤其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宝库中,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党寿山.被埋没的西夏千佛阁遗址[C]//西夏学: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29.
[2]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61.
[3]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03.
[4]牛达生.西夏陵没有“圣容寺”[J].民族研究,2006(6);陈炳应.西夏探古[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77.
[5]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J].民族研究,2005(5).
[6]史金波.西夏社会(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13.
[7]梁松涛,杨富学.西夏“圣容寺”及相关问题[C]//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250-267.
[8]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C]//大正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17.
[9]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J].敦煌研究,1983(创刊号).
[10]释道宣.续高僧传:第25卷[C]//大正藏: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45。
[11]祝巍山.永昌圣容寺圣容瑞像和刘萨诃佛迹与敦煌莫高窟[C]//永昌县圣容瑞像寺.中共永昌县委宣传部,编.金昌市印刷厂印刷,2002.
[12]刘克文.半截残碑话瑞像:永昌圣容寺历史考析[C]//永昌县圣容瑞像寺.中共永昌县委宣传部,编.金昌市印刷厂印刷,2002.
[13]金昌市文物局.金昌文物[M].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150-154.
[14]孙修身.从凡夫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刘萨诃[J].文史知识,1988(8).
[15]霍熙亮.莫高窟第72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佛瑞像史迹变[J].文物,1993(2).
[16]史金波,白滨,吴锋云.西夏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图版405.
[17]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M].文物出版社,1989:图版106-109.
[18]王其英,主编.武威金石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