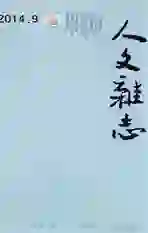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探究
2014-04-29周翔宇周国林
周翔宇 周国林
内容提要 纪事本末体既是史书编纂体裁,也是《春秋》经解的重要创作形式。结合学术史与文献著录来看,《春秋》纪事本末体大致经历了汉唐时期的“属辞比事”、唐宋时期的“事迹类编”、两宋之际纪事本末体裁创始、元明时期本末体持续发展、清代“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最终确立等环节。在每一环节中,《春秋》纪事本末体著作能够紧扣经学主题,形成有别于史学著作的鲜明特点。它们共同说明,一个独立于“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之外的“经解序列”确实存在。对这一序列进行探究,有助于考察《春秋》学以事解经的手法,能够更具体地研究经学在宋清之际的转变,还可以对纪事本末体的创始问题提出更丰富、更完备的新解释。
关键词 纪事本末体 经解序列 《春秋》学 以事解经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088-07
纪事本末体作为一种史书编纂形式,在史学史上具有与编年、纪传鼎足而三的重要地位。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下,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等书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①学者们通过对该序列的考察,系统论述了纪事本末体的创始、发展、流变、特点、编纂、价值等问题。②但是若对这一序列稍作区分就可发现,《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书或是对编年、纪传体史书的改编,或是从各种史籍中钩稽材料而成书,它们的创作都是围绕“史书”而展开的。而《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左传事纬》《左传纪事本末》等书却不是以普通的史籍、史料为依托,而是以《左传》为蓝本。《左传》虽然可以被视作一部记述春秋列国事迹的“史”,但它更是解《春秋》之“传”。在史学意义之外,它还有浓厚的经学意义。可惜的是,学界对纪事本末体的研究至今都未能突破史学范畴。以经学看待《春秋》纪事本末体的专文、专著尚付阙如。倘若我们能稍稍超出史学视野,从纪事本末体与《春秋》学之间的关系出发,证明学术史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纪事本末体著作,它们顺应《春秋》学解经需求而作,且足以构成一个前后相承的“经解序列”,那么,对其进行全新的经学解读或将成为可能。
一、从“属辞比事”到“事迹类编”
“属辞比事”是《春秋》学的解经传统。早在《礼记》成书时,经学家即已将其视作《春秋》之教的核心内容。郑玄称:“属,犹合也。《春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有相接之辞,罪辩之事。”孔颖达进一步解释:“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50“经解”,中华书局,1980年。可见在汉唐经学体系中,解读《春秋》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将文辞和事件从经传中摘取出来,通过属辞比事以发现异同,进而解释书法差异,辨析事件原委,判定是非褒贬,阐发微言大义。这种聚合、比次的解经方式,正是《春秋》学的特色。可以说在《春秋》经学诠释系统形成之初,就已经具备了拆分经传,突破编年限制,重构完整事件的解经趋势。同时,《春秋》学属辞比事的解经方法需要经师从二百余年分散杂乱的经传中钩辑相关内容,反复地整合比较,从而实现对书法的总结以及对事件的还原。这种繁难的工作又会对经学著作的编纂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春秋》学在汉唐间的不断发展,更大规模的、甚至涵盖全经的重新编次,成为中唐以后《春秋》学著作的创作潮流。个别的、偶然的属辞比事开始向着系统的、全面的“事迹类编”转变。今以《经义考》所载为据,可以将这些事迹类编著作统计汇列为下表:朱彝尊著、林庆彰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68~208“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下文《〈春秋〉纪事本末著作统计表》所据同此。
以上诸书绝大多数已经亡佚。表中所列的,也仅仅是借助《经义考》所载书名或序跋,能确切断定其为类编体例的一小部分著作。但通过这一份不完全的统计也能得出许多重要信息:从数量上看,类编著作在唐代以前不见著录;唐时始有高重“分国”、第五泰“事类”二书;宋代以后,事迹类编则大量涌现。这种随时间而呈现的数量差异说明:汉唐《春秋》学只是将属辞比事作为具体方法运用到解经实践中,对经传事件的整理还处于零散无序的状态。要通观经传,完成系统的类编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唐宋以后,分散孤立的属辞比事已不能满足经师们更深入的论事需求,事迹类编才应运而生。目录的著录情况与经学史的发展轨迹正相吻合。再从体例上看,类编著作或以国、以门类为划分标准,或按经传分主、属,或作类书性质的改编,方法是复杂多样的。但无论采用哪一种划分标准,其编撰形式却都是以“事”为重心。在同一门类下,经解者可以更容易地将相近事件进行比较,事与事之间的同异、是非在分类比较中即一目了然,清晰可见。从解经的角度而言,这种分类比较正是对属辞比事的发展,是带有系统性的大规模比事。综合来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体例上,宋代的类编著作都最为丰富,可见事迹类编的编纂方法在这一阶段已趋于成熟,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同时还应该看到,类编著作虽然在事件的横向比较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却仍然不便于对事件的经过进行纵向梳理。随着南宋学者更加重视对《春秋》之“事”的把握,要求“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看《春秋》,需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3,中华书局,1986年。如何照顾时间线索,在事迹类编的基础上做到“首尾贯通”成为了新的解经要求,纪事本末体呼之欲出。
二、《春秋》纪事本末体创始
现存最早的纪事本末体著作当属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此书的编撰动因是袁枢“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宋史》卷389《袁枢传》,中华书局,1977年。就历史编纂学而言,袁枢对《资治通鉴》进行创造性改编,使得史书编纂出现了纪传、编年以外的新体裁,从而在形式上创立了纪事本末体,这一传统认识无疑是成立的。不过,若从外在形式出发,进一步探究纪事本末体出现的内在学术动因,那么《春秋》学的发展其实也应该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事实上,在《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前后,还有两部纪事本末体著作影响较大且与《春秋》学直接相关。其一是两宋之际夹江人句龙传所著《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该书虽已亡佚,但在成书时间上却早于袁书,是当前可考知的第一部直接以“纪事本末”为名的著作。刘光祖《序略》称:“传,字明甫,精于《春秋》三传,博习详考,又分国而纪之,自东周而下,大国、次国特书,小国、灭国附见,不独纪其事与其文,而兼著其义。”朱彝尊著、林庆彰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结合书名与《序略》可知,句龙传是精于《春秋》的经师,其书先以大、次、小、灭分国编辑,又加入纪事本末的时间线索,正体现出《春秋》经解创作形式从“事迹类编”向“纪事本末”的过渡。更重要的是,该书不仅收载“其事与其文”,还“兼著其义”,这与纯粹的史学编撰明显不同。它既以全新的纪事本末体裁呈现,又在发明经义方面与传统的《春秋》传注一脉相承。这些特点都证明该书是《春秋》经学意义下的纪事本末体创始之作。
在句龙传、袁枢之后又有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章书是现存最早的《春秋》纪事本末体著作。由于刊刻晚于袁书九年,《四库全书总目》即据此推测其书“殆踵枢之义例而作。”《四库全书总目》卷49“纪事本末类”,中华书局,1965年。不少现代研究著作也赞同《总目》之说,称:“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首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后世踵作颇多。……模仿其编纂形式而成的还有章冲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刘海波:《略论纪事本末体裁的发展历程——以目录学为视角》,《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也不乏效法者。考诸史志目录,南宋著作中与之名目相近者就有:章冲《春秋类事始末》、句龙传《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葛焕礼:《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证》,《文史哲》2012年第2期。严格地讲,以上说法并不准确。且不论句龙传之书尚在袁书之前,即以章书而论,也未必是对袁书的效法。章冲曾自道创作缘由:“始冲少时,侍石林叶先生为学,先生作《春秋谳》、《考》、《传》,使冲执左氏之书,从旁备检阅。……冲因先生日阅已熟,乃得原始要终,攟摭推迁,各从其类。”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序。可见其书最初仅是为叶梦得(石林叶先生)三部《春秋》经解提供文献支持,是服务于解经的。而“原始要终”、“各从其类”的体例创新则是解经“日阅已熟”的自然结果,是从“属辞比事”到“事类”、“始末”的发展。这就与袁枢为了便于观览、记诵而改编《通鉴》有所不同。因此,崔文印先生即认为“与其说章冲受袁书影响,倒不如说他受叶梦得其人其书影响更确。”崔文印:《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若将崔先生之说进一步指实:叶梦得其人是《春秋》名家,其书是《春秋》经解,说章冲“受叶梦得其人其书影响”,其实就是指他顺应了《春秋》学的学术需求,从而创作了经学意义下的纪事本末体著作。
综合比较句龙氏、袁氏、章氏三书,虽然它们都产生于两宋之际的学术环境中,但却可以划分为经学与史学两大阵营。以《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为代表的纪事本末体经解在整体时间上要稍早于以《通鉴纪事本末》为代表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句龙传、章冲二书的书名中既包含“分国”、“事类”又标举“本末”、“始末”,正体现了《春秋》经解由事迹类编向纪事本末的转变。它们延续了《春秋》学的解经传统,上承属辞比事与事迹类编,下启纪事本末的新形式,将《春秋》纪事本末体一脉贯通,其意义和价值已经超出了“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据此可以认为,正是《春秋》学的解经需求推动了经解编纂形式的革新。纪事本末体的出现,除了可以借助《通鉴纪事本末》,在史书编纂角度寻求解释外,还可以在《春秋》学史中找到独立的发展线索。
三、《春秋》纪事本末体的发展与“经解序列”的确立
《通鉴纪事本末》成书之后,效仿其体例而创作的史书纷纷涌现,“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随之形成。反观经学阵营,南宋以后,只有清代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较为著名。但马、高二书与章冲之书悬隔四百余年,仅凭这两三部著作很难确证“纪事本末经解序列”的存在。故再以《经义考》和《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卷27~32、49“春秋类”、“纪事本末类”,中华书局,1965年。为据,对南宋以后的《春秋》纪事本末著作略作搜求:
《春秋》纪事本末著作统计表
著作名作者时代内容体例
三传分国纪事本末句龙传宋分国而纪之……不独纪其事与其文,兼著其义
春秋左传事类始末章冲宋原始要终,攟摭推迁,各从其类
春秋比事沈棐宋即经类事以见其始末
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李琪宋叙东周王、霸、大国之系……序其事变之由
左传纪事本末刘渊元
左氏叙事本末曹元博元案经以证传,索传以合经,为《左氏叙事本末》
春秋左氏传类编魏德刚元本末不相贯穿者,每一事各为始终而类编之
春秋本末傅藻明分列国而类聚之,……事之始终,井然有序
左氏始末唐顺之明人系其事,事归其汇……悉连属而比合之
春秋左传属事傅逊明用袁枢法而整齐之……国以次叙,事以国分
春秋序事本末曹宗儒明
左氏始末徐鉴明
春秋经传类事陈可言明仿建安袁氏《通鉴纪事本末》
春秋左传分国纪事孙范明原其事之所始与其所归……览一事之本末
左传事纬马骕清
春秋条贯篇毛奇龄清用章冲《类事本末》之意。冲类传而奇龄类经
左传纪事本末高士奇清因章冲《左氏事类始末》而广之
对上表略作分析可得出两方面结论:其一,从南宋到清代,《春秋》纪事本末代有继作,从未断绝。这些著作都是为解读《春秋》而作,且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前后承接关系。如《春秋本末》是懿文皇太子修习《春秋》时,苦其“诸国之事杂见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见”,乃命傅藻等人改编成书。宋濂:《宋学士全集》卷5“春秋本末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其后,傅逊又鉴于《春秋本末》与唐顺之《左氏始末》两书,一则藏诸秘府,流传不广;一则“事类不全又少注难读”, 才起意创作了《春秋左传属事》。傅逊:《春秋左传属事》,“潘志伊后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如毛奇龄作《春秋条贯篇》,多有对章冲《事类本末》的借鉴,不同之处则在于“冲类传,而奇龄则类经;冲于传有去取,奇龄于经则十二公事仍其旧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条之下”,《四库全书总目》卷31“春秋类存目二”,中华书局,1965年。在效仿中又含有创新。再如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同样是“因章冲《左传事类始末》而广之”,但“冲书以十二公为记,此则以国为纪,义例略殊。与冲书相较,虽谓之后来居上可也”。《四库全书总目》卷49“纪事本末类”,中华书局,1965年。这些记载都说明南宋以后的《春秋》纪事本末著作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后作对前作既有借鉴,也有变革和超越,其体例正在不断发展完善。其二,上述著作虽然都是纪事本末体,但其关注焦点却不是对春秋时期史事的汇编而是对《春秋》经义的阐发。其中,《春秋比事》《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春秋本末》《春秋条贯篇》等书本就是对经文的整列,之所以做这样的改编,当然是为了更好地贯通事件,诠释经义。其他以三传为名目的纪事本末著作,主旨也在“权衡其是非,合乎笔削之大义”,“通其明、祛其弊,而后圣人之经如日月之杲杲焉”,朱彝尊著、林庆彰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97“左氏本末序”、“春秋左氏传类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圣人善善恶恶之大法,所以荣黼衮而威斧钺者,不待考之义例之纷然,一开卷而了然如在目中”。唐顺之:《左氏始末》,“唐一麐序”,嘉靖四十一年唐氏家塾自刻本。这种注重明义、注重经学价值的创作动机与同时期出现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明显不同,它是经学著作独有的身份标识。既能构成连续发展的著作体系,又具有不同于史书的经学特征,上述两点可以证明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在元明清时期是存在的,且是独立的。这个序列是汉唐以来《春秋》学解经传统的延续,也是宋代以来《春秋》纪事本末体发展完善的结果。
此外,若借助目录学以考察纪事本末体的经、史源流,《四库全书总目》首设“史部·纪事本末类”,可以认为是纪事本末史体确立的标志。而长期流传的《春秋》纪事本末著作,如沈棐《春秋比事》、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傅逊《春秋左传属事》、马骕《左传事纬》、毛奇龄《春秋条贯篇》则仍被《总目》列于“经部·春秋类”。这种目录学上的分类很直观地表现出了两类纪事本末体著作在经与史上的差别。《总目》设立史部“纪事本末类”,恰是从反面证明了经部《春秋》纪事本末体的独立性和经学价值。如果将《总目》看作是纪事本末史体确立的标志,那么它同样也是“纪事本末经解序列”最终确立的标志。
四、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的价值
从汉至清,《春秋》纪事本末体大致经历了汉唐时期的“属辞比事”传统、唐宋时期的“事迹类编”著作涌现、两宋之际《春秋》纪事本末体裁正式创立、元明时期本末体著作发展完善、清代“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最终确立等几个阶段。每一阶段所产生的大量著作都能紧扣解经主题,形成有别于史学的经学特点;这些著作也能前后承接,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整体序列。那么,走出传统的史学认识模式,从经学角度对这一序列进行解读,挖掘其经学价值即是可行的。
首先,通过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可以更好地把握《春秋》学以事解经的传统。
自孟子揭示《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之后,历代经师对《春秋》的诠释一直有“文”、“事”、“义”三个向度。虽然《春秋》学的诠释体系是由这三个向度共同构成,不可偏废,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师的解释重心却有所不同。就论“事”而言,《左传》已开以事解经的先河,但是在汉唐学术环境下,经师更注重对凡例、书法的归纳和对文辞、名物的训诂,对“文”的诠释要远胜对“事”的考察。由唐至宋,《春秋》学进入摆落三传,阐发义理的新阶段,《春秋》之“义”在解经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宋儒解释《春秋》,绝大多数都是阐明《春秋》的‘大义”,“略事详义,或借事明义”。姚瀛艇:《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9~150页。总的来说,在宋代以前依经作注的传统经解中,事件始终是文例与义理的附属,没有成为经学研究的焦点。与汉人注重书法、训诂的传注,宋人阐发尊王、复仇义理的经解相比,以事解经手法似乎只在《左传》等早期《春秋》学传承中略有体现,缺乏长期稳定的著作形式。这就导致在现代经学研究中,学者们虽然肯定《春秋》以事解经的重要作用,并对“《左传》以事解经”、“子夏、董生以事说经”、“孔门以事解经”有深刻的论述,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4、186、231页。但却难以依托普通经解,对以事解经展开系统的考察。经解序列的确立,以经学为核心,将属辞比事、事迹类编与纪事本末体有序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脉相承的著作体系,为考察以事解经传统提供了切实的文献支撑。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纪事本末体经解,它们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经传中的事件,最便于学者们通过事件评价人物、确定是非褒贬,是以事解经最成熟的著作形式。研究这一经解序列,就能充分了解历代学者是如何运用具体事件来解释《春秋》,发挥经义的。
总之,研究《春秋》学史,应该兼顾文、义、事三种诠释方式;而研究以事解经,则更应该重视纪事本末著作。由此而言,对经解序列的解读,正是为《春秋》学研究提供了论“事”方面的新材料,是认识全面《春秋》学诠释体系不可或缺的三个向度之一。
其次,对“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进行具体的考察,有助于认识由宋至清经学考据的兴起与经学转型。
由南宋历元、明以至清初,《春秋》学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弃传”回归“用传”;从义理转向考据;从议论转向实证的过程。而《春秋》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发展、完善与这一学术转变过程也基本重合。
从取材上看,《春秋》纪事本末主要以《春秋》经和《左传》为对象,这本身就与《左传》学的复兴相呼应,有助于打破“《春秋》三传束高阁”的局面,使三传重新走入《春秋》学者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南宋以后,胡安国《春秋传》成为“最有影响的一部《春秋》学著作”,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22页。又在明初被著为功令,《明太祖实录》卷160“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具有了垄断性的权威地位。元明时期的普通经解,无论是尊胡、驳胡或兼论三传,都很难再恢复汉唐时精于一传的专门之学。然而纪事本末体的编纂则主要从事件出发,故而特别关注《左传》一家之书,使专门之学的再现成为可能。此外,在采择、编次经传的同时,为了疏通文意,落实与事件相关的信息以便观览,纪事本末著作往往还需要将注疏文字一并采入,且加以订正、补充。这又使得以《左传》为中心的训诂、注疏之学都得到了复兴。如傅藻等人编纂《春秋本末》,即称“训诂以杜预为之主”。宋濂:《宋学士全集》卷5“春秋本末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可言撰《春秋经传类事》,在编排《左传》外,也“释义主杜氏而多所损益”。朱彝尊著、林庆彰主编:《经义考新校》卷206“春秋经传类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这种在纪事本末著作中附入注疏训释又加以损益的做法正是对传注传统的回归。
从方法上看,成功的纪事本末著作在裁剪整合经传时还必须对事件有所考证。只有准确地掌握了与事件有关的人物、地理、礼制等信息,才能更好地还原事件,提炼出经文所蕴含的褒贬评价。因此,随着明清纪事本末体走向成熟,考据手法的运用也日益增多。早在傅逊作《春秋左传属事》时,就曾感叹其书:“于地理殊有遗憾焉。……如天假以缘,使逊遍搜天下郡邑志而精考之,复见于《左传》编年,本固大愿也”。傅逊:《春秋左传属事》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此不难看出,在明代时地理考证已成为提升纪事本末著作学术水平的重要手段。至清初,马骕《左传事纬》在正文之外又附以《左传图说》《春秋名氏谱》《左传字释》,对《左传》事件中所涉及的人物、地舆、山川、年表、职官、文字进行全面考证。马骕:《左传事纬例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也有“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专门条目,《四库全书总目》卷49“纪事本末类”,中华书局,1965年。将本末体中的考证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无论是回归《左传》、采用古注疏,还是附以编者自己的考证,元明以后的《春秋》纪事本末体著作都普遍表现出考据学的特征。与其他经解借助书法、义例揣测经义相比,本末体著作凭借考证事实以求是非的解经方法更具科学精神,符合经学诠释日趋理性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宋代义理化经学向清代考据式经学的过渡,是宋清之际经学转型比较集中的体现。因此,解读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对围绕事件而展开的考据手法进行系统研究,也将成为考察经学转型的重要途径。
最后,借助经解序列还可以更好地解释纪事本末体的创始。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近年来也有学者稍持异议而提出了《尚书》说、张东光:《纪事本末体再认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崔鸿《科录》说、王邵《隋书》说、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说、葛焕礼:《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证》,《文史哲》2012年第2期。《四库全书总目》说刘海波:《略论纪事本末体裁的发展历程——以目录学为视角》,《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等新说。但这些说法大多只是在“纪事本末体裁”、“创立”等定义上进行辩论,虽然言之成理,但多未能从纪事本末体著作出现之前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去进行考察。在《通鉴纪事本末》之前,无论是《尚书》还是其他几部著作,它们都与后世的本末体无太大关系:就外在形式而言,很难说本末体有对《尚书》的直接借鉴;就内在学术理路而言,《通鉴纪事本末》对《尚书》《科录》《隋书》等书更没有继承因袭。因此,《尚书》等书最多只能称为形似本末体或具有纪事本末的某些因素而已。
然而,若从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与经解序列出发,就外在的编纂形式与内在的学术动因两个方面一起探究纪事本末体的创始则可发现:这两条并行的线索其实都与《春秋》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一书“义经而体史”,文廷海教授从经、史两个方面概括了《春秋》的性质:“在经学家的视野中,因《春秋》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文本的义理诠释传统,因而属于经学;而在史学家的视野中,《春秋》是一种史学体裁的起源。” 文廷海:《义经而体史:〈春秋〉经、史学性质之争的再检讨》,《求索》2012年第4期。就“史学体裁的起源”而言,作为比较成熟的编年史著作,《春秋》可以说是后世同类史书编纂的典范。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创作就效仿了《春秋》的体裁而接续了《春秋》所载的事迹。而袁枢《通鉴记事本末》的出现,既可以说是对《资治通鉴》的改编,同样也可以说是对《春秋》以来编年史体裁的革新。从《春秋》《资治通鉴》到《通鉴纪事本末》及纪事本末史书序列,史书编纂形式的演进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外在发展线索。再就“义理诠释传统”而言,诠释经典、阐发义理的经学需求推动着《春秋》学由属辞比事、事迹类编向纪事本末及纪事本末经解序列发展,从而构成了一条内在的发展线索。结合这两个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将纪事本末体的创始解释地更加丰富、更加完备一些:从史学编纂说,袁枢《通鉴记事本末》仍然是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但从经学诠释说,句龙传《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与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同样具备创始的意义。同时,纪事本末体的创始并不是孤立偶然的,无论是史学形式还是经学动因,纪事本末体的出现都与《春秋》有着一定的联系。它是《春秋》经、史性质千余年持续发展的结果,是有着深厚学术积淀的革新与锐变。而这种创新的成果又被纪事本末史书序列与经解序列分别继承,在宋代以后的明清时期逐渐走向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的价值同样是十分巨大的。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