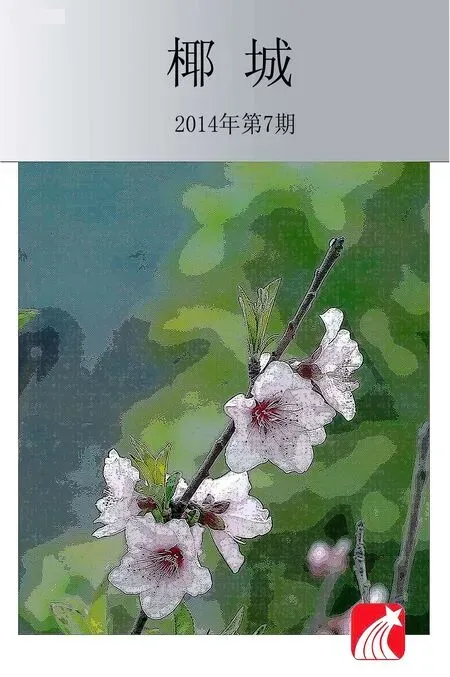固守村庄的怀斯
2014-04-29凌鹰
■凌鹰
固守村庄的怀斯
■凌鹰

一
一个非常怀乡的人是不适合读安德鲁·怀斯的画的。
一个没有乡愁的人是更不适合读怀斯的画的。
因为这两种人都会在怀斯面前感到悲凉和绝望。
我是属于第一种人。
我的乡愁是我强加给自己的。那时,我还只有十七岁,可我就开始像讨厌一件挂在土墙上的蓑衣一样地不喜欢我的故乡晓塘冲了。其实,我的故乡并不是一件蓑衣,它应该算得上是一件用家织土布做成的花衣裳。在这件衣裳上面,有许多的枣子树,还有一些竹子和苦楝树,还有一口很大的渔塘,还有许多的画眉鸟在枣子树上飞来飞去,并时常把它们的叫声像不同季节的雨点一样洒在我的头顶上。
这应该是件穿在身上蛮舒适的衣裳,可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就是总想把它脱下来,就是总觉得它像一件棕色蓑衣一样令我难受。
然而,当我真正脱下这件衣裳之后,当我想穿上它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了,已然成了一种奢望。在这十多年的时光里,我虽然像更换衣服一样到过一座座城市和乡村,但穿在我身上的那些衣裳都不是我自己的,都是别人临时借给我穿的。这些花花绿绿的衣裳看上去时髦而又鲜亮,但我穿在身上总是很不合身,滑稽而又别扭,就像我小时候在站立在稻田里的稻草人身上套上我母亲做新嫁娘时的那件花褂子。
然后,我就越来越想把它脱下来了,可我却再也脱不下了,它已成了我身上的一件铠甲,我已用它严严实实地将我包裹了十多年,我现在如果突然把它脱下来,把它从我的身上撕下来,肯定会将我的皮肉和我那被皮肉包裹的一些器官撕烂。
这时,我才发现挂在我故乡老墙上的蓑衣是那么的耐看和耐用,它是我和我村庄里的人在劳作和行走的过程中用来遮风挡雨的最好的衣裳。可是,我却把它弄丢了,丢到不知哪个我再也找不到的角落里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今年应该87岁了吧?我是一不小心昏头昏脑地一头闯进了这个老人住了87年的村庄之后,才认识这个伟大的老人的。
这个老人就是安德鲁·怀斯。
二
从2002年起,因为一家报纸给我开了一个“鹰眼看画”的专栏,我才开始系统地读了怀斯的绝大部分画,开始诚惶诚恐地走近怀斯。
当我像一只落荒而逃的野兔一样惊慌失措地闯进一个叫恰兹佛德村的临海的村庄的时候,怀斯正在这个村庄的一片玉米地里悠闲地散着步。这个80多岁的老人的步态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它们舒缓轻盈而又漫不经心,显得矫健而又自信。
站在那块玉米地的边缘,忧伤就像寒冬的白雪一样纷纷扬扬地洒进我的心里。看着这个从出生就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故土村庄的老人,我心里既嫉妒又绝望。我知道我只能站在玉米地的边缘,因为我无法走进这片玉米地,这片玉米地是怀斯的,这个村庄是怀斯的。虽然这个村庄无论从世界地图还是美国地图上都无法找到,但是,在世界许多国家美术博物馆里,这座不起眼的村庄却足可以让许多五颜六色的城市黯然失色。
这座村庄所散发出来的光芒,都是因为这个老人,都是因为这个伟大的老人一直就住在这里。
这样的村庄我又怎么能走得进去呢?这样的村庄只能让我仰视和膜拜。
在这一过程中,我又看见怀斯顺手扯了一株绿油油的玉米,将它捧在手里,像捧着一只随时可以放飞的鸟。然后,这个伟岸的老男人便迈着依然是那么散淡从容而又坚实自信的步履,走进了临近一条海湾的一株灰白色的小别墅。这个以画蓑草名世的大师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将碧绿的植物带回画室的嗜好?这让我突然看见他的那些蓑草似乎一直就在鲜活地生长着。
三
1945年我当然还没出生,我当然无法理解这一天对于一个奔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村庄的一片蓑草丛中的男人到底有多悲凉。但是,50年后的1995年,当我突然一下子也被卷进一股悲凉的漩涡,我才终于尝到了与那个在冬天的草坡上狂奔的年轻男人一样的悲绝滋味。
怀斯的《1946年的冬天》,向我们叙述的就是这么一个凄绝的话语。
1945年,当怀斯的父亲因一场车祸突然离他而去之后,年轻的怀斯用积蓄了一年的悲情画出了这幅画。现在,当我凝视那个从一片蓑草丛生的山坡上奔跑而下的戴棉帽穿棉衣的男人时,我很快又想起了1995年的那个初冬。那一年,我的父亲也离开我独自到另一个世界喝酒去了。他平时喝酒总有人陪着,我在家的时候就由我陪他喝酒。每次,当我从我父亲几乎一个也不认识的那些乌七八糟的城市回到晓塘冲,让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陪父亲喝酒。可那一年初冬的一天,父亲像等我等得不耐烦了一样,突然把酒杯一放就远走他乡了。待同样远走他乡的我回到晓塘冲的时候,我却连父亲喝剩的那最后一杯残酒都没见到,我只看见父亲留下的那个深不见底的酒杯,里面装着他还没有来及过完的生活和留给我的一些遗憾与牵念……
我不知怀斯的父亲爱不爱喝酒,也不知怀斯在父亲发生车祸的那个地方是否找到过他父亲留下的类似于酒杯一类可以装下一些抒情话语的容器。但是,我在怀斯的《1946的冬天》这幅画前,却看到画中那个穿着棉衣戴着棉帽的被寒冷包围的年轻男人就是怀斯自己。我已清楚地看到了被我认为是怀斯的年轻男人的惊慌与恐惧,听到了他因一路狂奔而发出的喘息声。在没有父爱的日子里,怀斯将怎样走过他脚下这片如蓑草一样的日子?他又将怎样才能从极度的悲伤中逃离出来?那时,忧伤肯定就像他脚下的蓑草一样铺满了他的内心。
这个时候的怀斯完全有理由离开他的故乡恰兹佛德。因为,作为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艺术家,怀斯早在1937年只有20岁的时候,就在纽约举办了个人画展,而这时的怀斯已然跨入了美国一流艺术家的首席位置,他完全可以走出宾夕法尼亚,甚至走出曾经在艺术上一度自卑过的美利坚,去与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的一些大师们高谈阔论。
可他没有。
或者,他根本就不屑。
怀斯晃动在他的故乡恰兹佛德村的巨大背影,委实就是他留给世界美术界的一句心灵秘语。
四
在怀斯的家乡周围,有许许多多的树。有树的村庄就像有月亮的夜空一样让我们心醉神迷。可是,在我所读到的怀斯的画里,我却很少看到他的家乡那些成片的树林,甚至很少看到三两棵完整的树,我看到的只是一些树的枝杆和根。比如《猎人》,比如《春天之美》抑或《秋日黄昏》。
对这些画,我基本上是把它们当作寓言来读的。
在那株枝杆虬曲的大树下,像一片叶子一样细小的猎人是否还能找到它的猎物呢?在那片粗砺的树根旁边开出来的那朵洁白的小花,是春天向人类发出的娇弱的问候吗?在那夕阳西下的黄昏,那只行走在昏黄的旷野里的小鹿好不容易在那棵光秃秃的树底下找到了两枚红色的果实。面对这两枚显然已经干瘪的果实,小鹿的满脸忧郁是否意味着,如果不吃掉这两枚干硬的果实,它在这个秋日的野地里就再也找不到果腹的食物了呢?
从这些画里,我看到了怀斯对自然生态的一种寓言式的凭吊和怀想。
怀斯在美术界被认定是个写实主义大师。在他的那些写实画中,虽然不乏人物画,但真正奠定他在世界画坛地位的,还是他的风景画。比如他在20岁的时候举办的首次个人画展,绝大部分就是风景水彩。
我不知道在怀斯20岁之前,他的家乡恰兹佛德村到底有多清新美丽?有那么多粗大的橡树,橡树丛里散落着一间间小木屋,村子前面是一片农庄,村子侧边还有一条海湾,这样的村庄毫无疑问应该是很美好的,可是,在怀斯众多的风景画里,我却看不到这种美丽,我只看到了一些美丽的碎片和残骸,它们就像我祖母剪下来的那根差不多有一米长的发辫一样,勾起我许多无边的臆想。在我十七岁之前还没有盲目地从我的家园晓塘冲出走的时候,我还在我家那个老式衣柜里经常见到那根乌黑的长辫。当我拿起那根长辫子傻乎乎地看着早已皱纹满面的祖母的时候,我就会极力想象,当时拖着那么一根长辫子的祖母,一定是个非常好看的女人。可是,我在我祖母的脸上,看到的却是一脸的忧伤的苍凉。幸好祖母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从这张发黄的老照片上,我才看到留着长辫子的祖母果然是个健康美丽的女人。祖母到底是什么时候和什么原因剪下那根长辫子的,我当然无法知晓。但那根油黑发亮的长辫子同我所见到的祖母形成了一道很大的豁口,我的那些无边无际的想象从此便像风一样在这道豁口里飘来飘去。
怀斯的这些风景画,又让我掉进了一道豁口,怀斯用他手中的画笔,像我祖母从她青春的头颅上剪下那根长辫子一样,将他的村庄真实地裁剪下来。
五
怀斯说,他最讨厌画中甜腻的气息。
我认为怀斯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因为怀斯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年轻,不再年轻的怀斯已经在他的村庄再也找不到能让他感知到甜美的意味。
当他的父亲纽·康·怀斯在他28岁的时候因车祸离世之后,家乡恰兹佛德村的所有美景便突然都变成一片清寂和萧瑟了,他觉得他所看到的任何一种景物都是父亲零碎的身影和哀怨的目光。
从此,在看村庄的一草一木时,怀斯几乎都倾注了对父亲柔肠百结的怀念和由此带来的悲伤。
怀斯最著名的画当然还是他在1948年创作的蛋彩画《克丽斯蒂娜的世界》。
我在读到这幅画时脑子里总是抑制不住许多的胡思乱想。我凭空设想过怀斯在创作这幅画之前的几种可能性。也许,怀斯刚好去看了父亲的墓园回来?也许,他刚好从离故乡不远的缅因州库村辛度假回来?也许,他刚刚做了一场梦,梦见父亲从遥远的不知叫什么名的地方旅游回来了,然后,怀斯就坐在他的小别墅旁边那条海湾边,海水打湿了他沾满泥土的鞋帮。然后,他突然听见村里人告诉他,他的邻居克丽斯蒂娜刚好去看了她的祖母的坟茔。
这个消息简直令怀斯感到震惊。
对邻居克丽斯蒂娜,怀斯一直就像关注村前的那片玉米地一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叫克丽斯蒂娜做他绘画的模特儿,让我总想起被他从那片农庄里带回画室的那些玉米棵。因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克丽斯蒂娜不就是一棵被风折断的玉米吗?
怀斯当然知道,他的邻居姑娘克丽斯蒂娜的祖母刚刚逝去不久。因此,当听到那个消息的那一瞬间,怀斯觉得克丽斯蒂娜对于死去的祖母的深切怀想,就像从玉米地的上空突然坠下来的一只受伤的小鸟,正好重重地砸在他的胸口上。
在读到《克丽斯蒂娜的世界》这幅画时,总觉得在那片巨大的草坡前那间木屋里,可能正坐着克丽斯蒂娜的祖母,也可能正坐着怀斯的父亲。
克丽斯蒂娜什么时候才能爬到那座木屋里去呢?我无法看见她的真实的面容,我只能看到她娇柔的背影和瘦小的双腿,只能看到她沉静坚韧的脸的侧面。无边的蓑草就像浑浊的海水一样在拍打着克丽斯蒂娜像一片树叶一样弱小的身影,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将这片叶子吞噬。
真实生活中的克丽斯蒂娜只是想爬到祖母的坟茔边去看看沉睡的祖母,只是想向祖母诉说自己的孤独哀伤和思念。可当怀斯听说了这件事后,就对这个不幸的邻居姑娘倾注了一种巨大的悲悯。画面尽头的那间木屋,不就是一间精神寓所吗?他不忍心让克丽斯蒂娜就那样没完没了地往前爬行,他祈祷克丽斯蒂娜的爬行是种让许多健全的人都感到汗颜的充满希望的精神的行走!
六
怀斯还有许多的人物画同样也成了世界画坛的精品,比如他以自己的妻子贝茜为模特儿的《泛滥》、《避难》、《发辫》、《羊皮衣》、《直泻而下的长发》、《白日的梦》。在读这些画的时候,我得到的是一种视角审美的快感和内心的宁静。这些画告诉我,怀斯一定非常热爱他的妻子贝茜,一个高大健康美丽恬淡的女人,她就像一盏油灯散发出来的光晕一样照彻着怀斯淡泊的生活,然后怀斯又用他的画笔和色彩照亮了她的村庄恰兹佛德。
怀斯除了偶尔到相距不远的缅因州库辛村去度假,就一辈子也没离开过他的故乡恰兹佛德村。从某种意义上说,怀斯像一个农夫。一个对乡村的情感死心塌地的农夫是怎么也不愿意离开他的故土的。既然离不开就得无怨无悔地在这块土地上耕作。
怀斯就是这样一个农夫。他一直就在他的画纸和色彩里精耕细作,种植着他的玉米小麦和其它一些不朽的植物。
就在怀斯这种慢长的耕作中,他的村庄恰兹佛德一点一点地变老了,老得比怀斯还快。那些蓑草,就像他的村庄灰黄的长发,在怀斯深情的凝视下飘飘洒洒,沉郁而又悲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