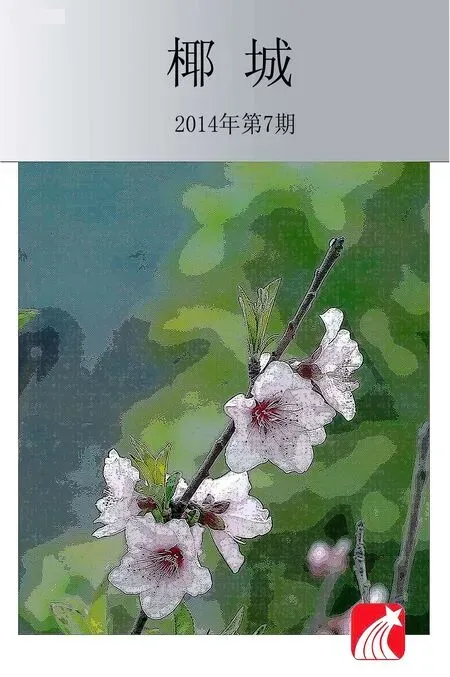寻找马治民
2014-11-17秋子红
■秋子红
寻找马治民
■秋子红
我走进了村子。大概是中午一两点左右,盛夏的太阳光毒辣辣地炙烤着村庄,我脚下的地皮上四处白花花的,一丝阴影都没有。
街道两边,那些伸出农户庭院或者长在他们家门口的白杨树、梧桐树叶片上泛着亮光,在阳光里静静的一动不动。几只鸡咯咯叫着在土墙根的阴凉里觅食,不知从哪里突然钻出来一条皮毛肮脏的大黄狗,呲牙咧嘴瞪着我,露出凶恶、警惕的目光。我跺了跺脚,那狗东西“汪汪汪”叫唤了几声,呲着牙呜呜呜向前跑远了。有些人家将他们猪圈、牛圈里挖出的粪土堆在街道边,一股股恶浊、难闻的臭味气势汹汹地扑过来,我紧走了几步,可那种粪土的臭味还是不屈不挠地钻进了鼻孔,不久,我的满心满肺里好像都是。
“顺着这条街道往前走,从前面那个巷口拐进去,马国权楼房对面的电线杆下,就是马治民家。”
当时,我就是按着村口小商店房檐下那个睁着一对乌溜溜的小眼睛,向村外的土路上一眼不眨地瞅着的老头所说的那样走进了村庄。没多久,在一个巷口,我看见远处一条通向村庄北边的街道里,那些挤挤攘攘的平房大房厦房中,一幢鹤立鸡群似的贴满白瓷片的高大楼房——这一定就是小商店里的老头所说的“马国权楼房”喽。楼房对面的电线杆下,是一幢这里的人家常住的那种两面淌水的“人”字形大房,从房顶苔藓斑斑的青瓦和房檐下发黑的椽头可以看出来,这幢房子很有些年头了,大门门框和门板上的黑漆很明显地已经泛白,门楣上已经褪色的红纸春联上,还隐隐可以看见“春光明媚”几个大字。门廊里,几个八九岁大的孩子在门廊下的水泥地上玩弹子,他们唧唧喳喳的吵闹声,简直比鸟叫声还要脆亮。
我站在大门口问:“马治民家是这里吗?”
孩子们停住了吵闹,他们用一双双黑漆漆的眼睛望了望我,然后将目光齐刷刷地落在门廊里一个满脸五麻六道布满污渍的孩子身上。这个孩子用惊恐的目光望了望我,忽然一低头,抓起水泥地上的两个玻璃弹子紧攥在手中,然后一转身向着门廊内跑了进去。不久,我听见,院子里响起了像案板上切菜的刀子一样快一样利的声音:
“谁找马治民呢?找马治民干啥?!马治民出车祸了,马治民死球了,马治民刚刚断了气……”
门廊尽头的阳光里出现了一个矮胖、敦实的女人,一边向我走近一边张着嘴恶狠狠地这样咒骂着,那一张五官挤成一团的布满雀斑的扁圆脸上,很明显地摆出一副跟人拼命、干仗的架势。门廊里孩子捡起水泥地上的弹子从我脚边向大门外跑了,但他们并没有跑远,一个个站在街道里,向着我和女人好奇地张望着。女人快要走到我跟前时,忽然一下吱了声。我想,一定是我手间那一只鼓鼓囊囊的食品袋里,花花绿绿的礼品堵住了她的嘴。
“你……你……是?”女人一下涨红了脸,眼珠从我头上扫到了脚下,目光疑疑惑惑地问。
“我是马治民的同学,我从周原市里来这里,专程来看他。”
我的话音刚落,就见女人转过了脸,朝门廊里那个满脸五麻六道满是污渍的孩子喊:“快叫你爸去,叫他别睡了,有人看他来了。”
门廊里的孩子望了我一眼,转身向门内腾腾腾跑了进去。我想,这个小家伙一定就是马治民的儿子!
我跟着女人从门廊里往里走,女人边从我手上接过食品袋,边不好意思地说:“我当又是要账催还贷款的,我当又是勾引娃他爸打麻将的。”
我问女人:“马治民现在做生意?”
女人耸了耸她那圆圆的短鼻子,一脸轻蔑、厌恶地说:“做亏他烂先人的生意!”
我跟着女人走进了院子。院子是泥地,院子西面是间厨房,比起门首两面淌水的大房来,这间厦房厨房要低矮得多,不过,与那几间大房一样,椽头发黑,打眼一看已有好些年头了。院子东面长着几棵梧桐树,斑驳的树荫里站着几只鸡,还放着架子车、铁锨、木杈之类的农具,远处一堵矮墙一个没有门扇的门框隔出的后院,大概就是厕所和猪圈。
女人招呼我进了门。
堂屋里很暗,墙壁下靠墙堆着几袋粮食,墙壁上挂着簸箕、筛子还有一捆装粮食的蛇皮袋,墙根的一个小方桌上,一只小香炉后供着两幅写在白纸上的牌位,房间里飘着一股粮虫净或者是灭害灵的刺鼻的农药味。我放下肩上的皮包,捡靠墙的一只方凳坐下来,女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抓过来一把破竹扇,递给了我,我便朝着自己满是汗水的脸上,一下下扇了起来。
女人给我倒了一杯水后,朝着堂屋东面的房间扯着嗓子喊:“起来,起来,看把你睡死了,有人看你来了。”
见我正望着她,女人脸一红,低着头向厨房里走去了。
我听见,堂屋东面的房间里,一个小孩“爸爸,爸爸,快起来”的清脆、稚嫩的叫声,还有一个人哼哼唧唧很不情愿的起床声,接着,一双拖鞋扑蹋扑蹋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接下来,我看见了我记忆里的那一张熟稔的脸,我看见了那张脸上总是沉默、寡言的神情,我还看见了那张脸上,那双眼睛里时常闪射出的好像总是捉摸不定的目光。
我一下从凳子上站起身,朝着他有些兴奋、激动地喊了一声:“马治民!”但他只是淡淡地瞅了我一眼,嘟囔了声“是你”,就将目光转向了别处,嘴唇紧抿着,嘴角连一丝笑纹都没有,脸上依旧是那种寡言、沉默的神情。
马治民走到了我身边,他端起刚才女人给我倒的那杯水,说你喝水你喝水。
我将杯子接到了手中。杯子里结满了茶锈,几片茶叶沉在杯底,黄黄的早已泡得没颜没色了。我朝马治民笑了笑,弯腰从脚边的皮包里掏出一只不锈钢保温水杯,又从一只小巧、精致的茶叶罐里捏了几根“巴山云雾”后,递给了马治民。马治民红着脸给我倒了水后,拉过一张凳子坐在了我身边。
马治民的儿子——刚才我在门廊里看见的那个满脸五麻六道满是污渍的孩子从房间里探出了头,睁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望着我,不久,他的目光就落在圆桌上,食品袋里那些花花绿绿的礼品上。我朝他招了招手,小家伙瞅了瞅马治民,有些胆怯、不好意思地低头愣了愣,最终还是怯生生地走到了我身边。我从食品袋里取出一袋奶糖递给他,孩子向我感激地笑了笑,拿着奶糖向门外跑了出去。马治民望着儿子跑远的背影骂了句“狗日的”,我看见,他的嘴角咧开了一道浅浅的笑痕。他忽然将头凑近我,压低嗓子说:“昨晚打了一晚上麻将,今年卖麦的钱快他娘的输完了。”紧接着,马治民向着门外厨房的方向大声喊:“中午炒几个菜,我老同学大老远来了,中午我俩好好喝几杯。”
我听见,厨房里女人爽朗的应答声,女人在案板上切菜的清脆的当当当的响声,铁锅里洋芋丝或者是菜花青椒倒进菜油中的嗞嗞啦啦的翻炒声;我还听见,院子里一只公鸡喔喔喔的打鸣声,后院里传来的猪圈里一头或者两头猪哼哼唧唧的叫声。阳光明晃晃地跳跃在院子里,房檐在门口将阳光切割出很笔直的一长绺阴影。堂屋里一下寂静极了,寂静得让我忽然不知今夕何夕,寂静得整个世界好像一下没有了年代没有了时间的存在,只有这样一座村庄,这样一个院子,我和马治民这样两个人。
我正这样胡思乱想着,女人用一只木盘子端着几碟菜进来了。马治民拉过一张圆桌,招呼我坐了下来。接着,他从堂屋旁边的房间里取过一瓶酒和两只酒杯,放在了圆桌上。酒有多半瓶,是我有好些年没有见过更别说是喝过的,一瓶至多三四块钱的乡下人逢年过节时喝的被人们叫做“普太”的白酒。女人将盘子里的菜摆上了桌,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炒青椒,一盘炒洋芋丝,还有一盘凉拌粉条。
马治民斟满了两杯酒,他端起酒杯说:“老同学,今天咱俩好好喝几杯。”
我和他碰了碰酒杯,马治民一仰脖,一杯酒“嗞——”一声就进了他的喉咙。我尝了一口,酒火辣辣的,冲劲很足。
我夹了几根洋芋丝,送进了嘴里,咀嚼了几下,我就感觉出了,马治民的女人做饭的手艺绝对要比她的长相要出色得多。
我笑着问马治民:“老同学,这几年生活还可以吧?”
马治民鼻孔里喷出一股酒气,用手中的筷子向着堂屋和院子里四处指了指,向我哼了哼鼻子说:“胡凑合呢,你看到了,日子过得背到家了!”见我正望着他,马治民“嗞——”一声又喝了一杯酒说:“这几天打麻将场场是输,前半夜赢多少,后半夜都会输个精光!今年卖麦的几千块钱,现在快没多少了。”
我不解地问:“你不会不打麻将吗?”
马治民“扑哧”笑了一声,忽然睁着一双发红的眼睛瞅着我说:“不打麻将?你怎么跟我娃她妈一个见识,不打麻将我能行吗?门口天天是要帐催还贷款的人,我整天愁起来头都没个地方放,一坐到麻将桌上,我才能将这些烦心事都他妈给统统忘光!”说完这些,他回过头问我:“老同学,你的生活不会不好吧?”
我说:“大学一毕业,我被分配进了周原市统计局,这是一个清水衙门,我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在各种报表上填那些领导喜欢看的各种数字,你知道,现在搞政绩靠吹,干工作靠嘴,想当官靠送,那些数字,鬼才相信它们没有水分!虽说是这样,但我很知足了,你知道,咱们高中的大部分同学不是在老家当农民就是在城里当农民工,我能有这样一份工作,真是很不错了,你说是吧?”
我刚说到这,马治民接过了话茬说:“前年,我办了一个养猪场,办养猪场的钱是我托亲戚找熟人从信用社贷来的。当时,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人靠养猪场发了,用我们村子里的人的话说,发得噗哧噗哧了。养猪场的猪是我从集市上花高价买的,当时猪贵得吓人,一对刚断奶的猪娃,将近一千块!”
我接着说:“工作几年后,我谈了好几个对象,但没有一个合适的,不是我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瞧不上我。你知道,像我这样通过考学走进城市的农村娃,城里那些家境好工作好的姑娘是看都不会看你一眼的,可那些从乡下来的打工妹,我死活都不愿意找!就这样,眼看就要三十了,我还是个单身!”
马治民边给我倒酒边说:“养猪场办起快一年,圈里的猪眼看就要出槽了,我粗略算了算,第一拨猪卖出去,贷款就还得差不了多少了,要这样下去,真像村子里的人说的那样,我马治民就要发得噗哧噗哧了。可谁知道,就这时,口蹄疫来了,先是几头猪蹄子烂了,没几天猪圈里好几头猪死球了,都被我晚上拉出去偷偷埋了,我想将猪快些卖了,可这时候街上肉价便宜得就跟白送人差不多,就这,满街的猪肉,根本就没人敢买!养猪场,后来就这样折爪了,我整整贴赔了三万块!”
我跟马治民一碰杯,说:“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打远一看人长得差不多,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可走近一看,我发现,她的左眼角上有一块胎记,黑乎乎的一大块,虽说被一绺头发小心地遮掩着,可它还是让那一张脸一下显得既恐怖又丑陋。我心里像吞下只苍蝇,马上有了吹的打算。介绍人后来将我带到一边说,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为老几,大学生算个球,城里打扫厕所的都说他是大学生!知道她爸是谁吗,说出来吓死你,就是咱们市里的副市长张市长,人家可是看准了你。我的嘴巴大张了半天,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马治民吃惊地瞅了瞅我,紧接着,他说:“前几年,我跟人贩过辣椒,忙死累活开着三轮车在附近的村庄里跑了整整一个冬天,后来雇大卡车拉到周原市的食品厂,卖后一算账,根本就没有挣钱!我还到新疆去了几年,从别人手里承包了一片地种水稻,几年下来,也没有挣多少钱。我这人就是这样,干啥都不挣钱,干啥不成啥!”
听马治民这样一说,我接着说:“一结婚,我发现,这门婚事我算是选对了。现在人都说,选对象跟买股票一样,我选的这对象算是‘绩优股’,虽说貌不惊人,可业绩好得惊人!我刚刚结了婚,张市长就说,你工作的事我给城建局的王胖子打过招呼了,你就去城建局吧,年纪轻轻的,在统计局能统计出啥名堂!就这样,张市长一个招呼,我进了城建局的开发公司,在王胖子手下任开发公司的副经理。”
马治民斟了两杯酒后,说:“我结婚时,早老大不小了,在我们村里,跟我一样大的人孩子早会跑了。别人给我介绍过几个对象,但没有一个成的,后来,豆村的我娘姨给我介绍了娃她妈。在豆村我娘姨家相面,我望了她一眼,冷笑一声饭没吃就回家了,回到了家,一进家门我发现自己哭了!我马治民不是瘸子跛子,怎能找那样的女人!我爹劝我说,你心比天高但命比纸薄,嫦娥好看得很可人家是仙女,你有本事找到吗?人家不缺胳膊缺腿,再好看能当饭吃吗,夜黑了灯一拉灭,世上的女人还不都一个球样?!我一想,我爹说得对呀,现在村子里长得好看的,不是嫁给城里人就是找有钱的主儿了,这样的女人就这样的女人吧,不到年底,我就结了婚,这个女人就成了我娃她妈。”
我望着马治民笑了笑,说:“一年后,我进了城建局,没多久就成了城建局的副局长。张市长说,在我退二线之前,你必须扶正,扶正了才有前途。朝里有人好做官,现在官场上就是这么回事,没权没势没后台,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都球毛不顶。”说完这话,我有些得意地望着马治民,我知道,官场上的事,他知道的肯定比他那满脸五麻六道的儿子多不了多少。
马治民却没有理会我,他自顾自说:“高中毕业后,我去东莞打过几年工,还在周原市的几个工地上干过小工,甚至在一个小区还当过保安,但都没有干长久。有一段时间,我整天整天晃荡在村里,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干什么?村子里人都说,马治民书没有念成大学没考上,还把脑子给念坏了。我时常在想,如果当初考上大学,那我一辈子将是怎样?”
我望了眼马治民,端起酒杯用舌头轻轻舔了舔,说:“张市长退二线前,我终于扶了正。我整天那个忙啊,市里这样那样的会要开,局里大大小小的工作要布置,那些开发商包工头的饭局要应付,我的七姑八舅的孩子的工作要安排要照顾。可忙完了一天,晚上怎么睡都睡不着,街上警车呜呜呜从楼下开过来,我心慌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我心里那个担心啊,要是我突然让人给叫去咋办?要是我让那些开发商包工头给举报了咋办?有时候,我想,如果当年我没有考上大学该多好,当个农民,没有人给你使绊子也用不着整天想着巴结谁提防谁,天高皇帝远,婆娘娃娃热炕头,这样一辈子不也是一种幸福……”
不知什么时候,女人早将一碗碗臊子面用木盘子端着站到了我们身边,马治民给我端过来一碗面后,忽然用一种跟刚才完全不同的腔调对我说:“你还记得高中时吗?”
我说我当然记得。
我看见,马治民的目光里流淌出一种眷恋、深情的波光,他嘴里的话语,像是在胸口暖过,一下子变得温情、柔润起来——
“你知道,上高中时我学习有多好,每回考试,我考第一是绝对正常的,如果不是,肯定是我考试时晕堂了。但高考那天,我真的晕堂了,就因为那么0.5分,我落榜了。我记得物理试卷上有一道题:时间具有永恒运动性和不可分割性。选‘是’或者‘否’。我知道选‘是’,可我偏偏选了‘否’。时间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是一种物质在无限时间中占有或长或短的有限时间,时间是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的命运,如果时间具有永恒运动性和不可分割性,那么马治民就是你,如果不是,马治民就是我!”
我一下睁圆了眼睛。我脸上吃惊的神情一定将桌边看着我和马治民吃饭的女人和孩子给弄懵了,他们用眼睛一会偷偷瞅瞅我,一会又偷偷瞅瞅马治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马治民一脸诡秘地望了望我,忽然,他沉着嗓子用一种很明显的嘲弄语气对我说:“其实,你就叫马治民,你也就是马治民,你一直要寻找的马治民……”
马治民刚刚说到这,忽然一下不见了,刚才还站在我身边的女人和孩子也不见了。堂屋、厨房、院子里的梧桐树、阳光和后院传来的一头或者两头猪哼哼唧唧的叫声,以及整座村庄,像忽然长了翅膀飞走了一样统统不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周原市河川监狱!
——昨天,两年前在周原市传得沸沸扬扬的周原市城建局局长马治民贪污受贿案终于宣判了,在这里,我也许将度过我的后半生。
秋记者,谢谢你来采访我。我刚才讲给你的,你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