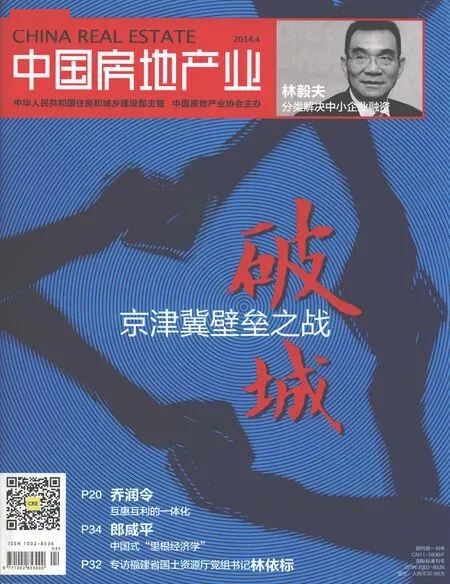拯救小农才能完成城镇化
2014-04-18范德普勒格
文│范德普勒格
拯救小农才能完成城镇化
文│范德普勒格
讨论中国的城乡一体化需要考虑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二元结构可能会长期并存,而且是不同形态的。要认识到中国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粮食主产区也极不均衡,中国小规模农业和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的事实,是近百年内都不会改变的基本事实;中国存在半工半耕(农民一边打工,一边耕种)是基本事实;生产与消费合一体是基本事实;家庭经营为主体也是基本事实。

中国的二元结构100年不会改变
不同场合不同人均已形成共识:中国新型的城镇化不是照抄运动,不是摊大饼似的建设,而是着眼于人的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核心也是人的一体化,人的一体化不是建筑一个模样,不是说着眼于城乡建筑的模样,而是着眼于城乡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等等。
我在中国考察时看到了太多工业侵蚀农田,听到并看到太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对比上面的大道路,中国的城镇化让我们很担心,它看起来是要消灭农村、农民,而事实是,几乎在每座大城市周边,都会有一大片半荒芜地带。这里的农民大多进城务工,由于缺乏投入,土地严重退化。如果将这些曾经的良田加起来,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千百年来,农民在土地上耕种,为什么在城镇化的高歌猛进中,他们突然丧失了对土地的兴趣?

因为在新的竞争中,农民失去了立足根本。中国在进入市场化经济时期,地方开始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也抽取农村的剩余,所以有另外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托达罗在1981年写道:有一个城市偏向型的制度安排和农村忽视型的制度安排,这是农村发展的一个难题、困境,或者叫悖论。
中国一位人口学家在他测算的各种各样的表格中提供了生育政策不变,调整的低方案、中方案、次高方案和高方案。现在中国已经明显进入了中等方案,因为中国已经开始放开生单独二胎。这种情况下,中国到2050年,人口规模约在15亿左右,保守估计届时中国的城镇化率约为70%。那时将仍然有4.5亿人生活在农村,相当于一个美国(3.09亿)加上日本(1.29亿)再加上加拿大(0.35亿),相当于三个大国还在农村里生活。即便是城镇化率达到90%,还有1.5亿人生活在农村,仍有相当于一个日本加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40年后,大量的农村人口仍然存在,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不能因为要走向城乡一体化,就否认农村还有居民存在就不去建设,就不让它有一个安定的基本的生活。
时间再往后推移,按照人口学家的估计,2100年中国的人口会降下来,按照现在的方案会回到13亿,印度超过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那时候即使达到95%的城镇化率,即使不考虑能源、地理、水、光、热等条件,也仍然有6500万人在农村以农为业,就是5%的人口。5%的人口耕地面积是多少?即使保持住18亿亩这条红线没有动摇,人均耕地也只有27.7亩,这是什么概念?是美国当前劳均耕地的1/67。很多人把中国的农业以美国为样本,做一个美国梦,这是有问题的。中国和美国当前的劳均的差异是357倍,这意味着美国一块地一个人生活,我们300多个人生活,所以美国农业永远不是中国农业要学习的样板。
除了简单的人口统计之外,中国的地理情况也决定了我们仍然会存在大量的乡村。中国的地理情况俗称“七山二水一分田”,水、光、热等资源配比的条件极不均衡,接近一半的国土面积是干旱与半干旱的地区,还有季风、海拔等巨大差异的原因,中国有若干不同的气候带,若干不同的农业类型。
所以一概而论地讨论中国城乡一体化是不合适的,参考美国式的大规模标准式的农业在中国也是不现实的,中国只有12%的土地适宜耕种,美国的国土面积和中国几乎一样大,但是耕地是中国的3.6倍,人口是中国的1/4。所以中国的大规模标准式的农业只能是东亚式的,日本、韩国式的适度规模,远远达不到美国式。
需要考虑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二元结构可能会长期并存,而且是不同形态的。中国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粮食主产区也极不均衡,小规模农业和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的事实决定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绕不开二元结构,绕不开城市和乡村同时并存的状况,这是近百年内都不会改变的基本事实。
远离市场
中国农村确实处在十字路口上,不鼓励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就会平庸化,丧失活力。小农经济效率太低,这是诸多现代偏见之一。其经典表述就是小农经济受生产要素(土地、水、劳动力、资金等)制约,必然“内卷化”,即投入劳动力越多,效率反而越低,最终将技术革新的成果完全吞噬。农业有无法突破的“天花板”,所以小农传统、保守且封闭。
近代以来,歧视小农一度登峰造极,几乎所有负面价值都指向他们,这种偏见还曾反映到制度层面上——只要当农民,则意味着丧失了迁徙权、经商权等权利。在许多人看来,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让农民这个职业消失。可问题是,这些认知是凭空架构,还是事实如此?
小农生产有它天然的特点,即相对远离市场,因为在小农生产的价值中,许多无法用市场的方式显现出来。比如美丽的田园景色,也是小农的产品,可市场对此没有定价。再比如可循环的生产方式,小农在投入下一轮生产时,使用的是上一轮生产的副产品,这不仅涵养资源,且保证了农业持续发展,可市场却无法体现这些劳动的价值。
农民可能去捡一天的牛粪,而不是用化肥,他们可能只穿自己纺织出来的衣服,而不是在衣柜中陈列几百件,这当然有价值,却也是市场所反对的。换言之,只有与市场不紧密结合,小农生产才能持续下去。东方之所以没出现再小农化,因为那里小农与市场结合更紧密,这意味着,东方小农承担着更多的市场压力和剥削。
然而,整个现代化的过程,恰恰是一个把小农逼入市场的过程。在市场中,小农原本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博弈地位,更麻烦的是,政府的那只看得见的手还常常参与其中,为了税收与稳定,政府通过限价等方式,迫使小农接受不平等的市场价格,并强制或引诱他们不脱离农业生产。而每笔来自政府的农业补贴,其实根本无法补足小农在市场上遭受的损失。
尤为可怕的是,随着城市资金的介入,“食品帝国”出现了,它彻底将小农们套牢在被奴役、被伤害的地位上。食品帝国像人类史上一切帝国那样,拥有一套似乎合逻辑的话语体系,它力主农业集约化,认为这是稳定农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农产品价格、预防农业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食品帝国的话语体系与现代社会的精英话语高度统一,因此具有很强的政策游说能力。
事实上,今天市场上80%的农产品都是小农提供的。很多事实说明,为主流学者所夸耀的公司农业模式,目的是从农民和消费者那里获得更多利益,指望它为农民带来更多实惠、使消费者更为节约,往往是天方夜谭。食品帝国才是粗放农业,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绿色环保等方面看,均无法与精耕小农相提并论。
然而,妖魔化小农改变了一切,错误的文化让每个人都成为加害者,我们已习惯于政策上的倾斜、文化上的歧视。这其中吊诡的是,现代政府莫不以预防大规模饥荒为己任,一方面纵容“食品帝国”掌控着话语权,另一方面为此形成了农业补贴制度,其结果是,小农生产什么、产品定价、销往哪里等都已事先被人为规定,他们没有参与市场竞价的权利,而由此遭受的损失,其实大大多于政府给予的补贴。
中国到了重新开始思考小农的意义的时候了:城镇化真的代表现代化吗?粗放发展造成农业失活,农业失活又会引发城市动荡,但愿中国发展能远离“拉美化陷阱”的困扰。
从最小单位开始
我注意到,中国在着力打造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的第三个超级城市群:环首都城市群。这是一件早就应该做的事情,发达国家首先出现的城市群都是围绕各国首都开始的。但对于打造环北京的城市群能对中国的城镇化起到多大的引领作用,我持怀疑态度。
因为中国的基础在乡村,不在已具备发展基础的城市群,我的意思是,这只是拉大城乡差距的另一案例,因为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远没有首都这样的辐射力,更不能指望能形成什么模式去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
中国大城市数目已经很可观并早已超过了美国,2013年,美国超过40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1个,中国近30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美国57个,中国146个。不可能让所有的农村都成为城市,中国必定要走差别城镇化的道路。
伴随着城镇化的提高,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会越来越失去它的吸引力,郊区、近郊区反而越来越有魅力。随着中国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大城市本身的吸引力也会开始下降。
德国的小城市是以小城镇与小村镇为主的,70%的人生活在1.35万个小村镇里,大部分人口在分散的居住。美国的人口主要生活在加州、东海岸、五大湖三个集中居住区,即使是这么集中的居住,仍然有近30%的人口分散居住在5万人以下的小城镇。
所以,城镇化走向大城市不是唯一的道路,城镇生态有很多种。中国应该着眼未来,打开视角。欧美国家几百上千人就是一个镇,放开思想,解放思想,如果参照欧美,中国超过1000人、2000人的村庄太多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很高了。中国有数万多个小城镇,是不是应该从最小的单位开始着手,从这里回到问题的根本,解决长期二元对立的关系导致的农村贫弱。
二元对立体现在:一是二元经济,二是二元社会,城乡户籍是隔离的,公共服务差异是巨大的,收入差异是三倍以上。农村对于城市的贡献体现为城市对农村的剥夺是三层剥夺:农业剩余、经济剩余(金融剩余)和利润剩余的剥夺。第一层剥夺是经济剩余的剥夺,以剪刀差的形式出现;第二层是金融剩余的剥夺,农村的金融体系不能为农村服务,常常扮演着抽水机的功能。比如说农村信用社,2/3的农村的资金通过农信社、邮政储蓄、农业银行等等被抽出去了。第三层利润的剥夺,贷款要付利息。农村的剩余不断的被城市拿走,不能留在农村。
解决农村问题就是解决多元城市形态问题。要考虑不平衡,东西工业化、农业地区、牧业地区、边疆地区的差别化,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差别化,要考虑人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让农村人口适度居住在一个地区的基础上,铺设公共服务,把它当作一个城镇来看待,那就不需要大规模的平移人口,带来那么高的社会成本。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系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农村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农业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等,为欧洲农业史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范德普勒格自2007年以来,数十次深入河北、四川、湖南等地的村庄开展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社会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