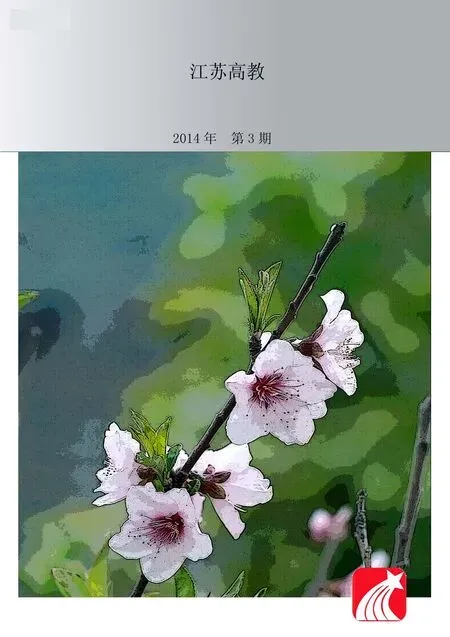大学学术管理组织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
——教授会视角
2014-04-17刘海燕
刘海燕
(苏州大学科学技术与产业部,江苏苏州215021)
大学学术管理组织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
——教授会视角
刘海燕
(苏州大学科学技术与产业部,江苏苏州215021)
目前我国大学教授会存在组织行政化、权力制衡机制设计不完善等问题。以学术价值取向规范组织建设,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纯化基层学术管理机制,推进学术权力制衡机制是大学教授会的发展策略。院系层面的教授会应当是大学组织建设的重点。
大学;学术管理组织;教授会
教授会的建立有助于发挥教授集体作用,它既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实际需要,又是回归大学学术组织本质的客观要求。
一、国内外教授会管理组织的历史考察
(一)美国研究型大学教授会的历史回溯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最早让教师参与大学管理的是耶鲁大学。在19世纪初,耶鲁大学就制定了一项政策,规定所有与大学有关的管理问题都在教师会上进行讨论,“如果没有教授会的推荐和支持,学院董事会就不能做出任何决策”[1]。“‘教授会立法,校长赞同,院董事会认可’,成为耶鲁大学治校‘格言’”[2]。在耶鲁大学的影响下,美国顶尖大学的教师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对学术事务的影响。1868年,加州大学建立了教授会。1889年,康乃尔大学董事会也建立了一个包括所有教授和大学校长的教授会。目前,美国包括两年制初级学院在内的所有高等学校都以不同的方式让教师参与学校的管理,其中,有90%以上的高等学校建立了教授会[3]。
美国成立教授会的大学都有经大学董事会批准的章程,对教授会的组成人员、下设机构、职责、权利和特权做出规定。19世纪下半叶,教授会在刚建立时通常包括校内所有的教师。但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和教师的增加,教授会逐渐变成了一个既笨拙且效率低下的管理方式,而且在学校管理过程中也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一些大学开始在教授会下设立分支机构,分别处理不同的问题,如康乃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学校的教授会都下设多个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s)。教授会的各项工作都由这些委员会来处理。
在美国不同的大学,教授会的权力的大小通常与学校的历史和声望呈正相关。在主要的公私立研究型大学和有声望的文理学院,教授会的权力要比其他大学的大。
尽管教授会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对学校行政部门或董事会管理职能的取代。作为大学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授会的主要作用在于:一是防止行政官员犯专业性的错误;二是它“有助于阻止一个独立的职业学术管理者阶层的发展,确保了教师在学术事务上长期的霸主地位……这在很多方面减少了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潜在的冲突。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教师高权威的制度广泛地保存并保护了大学的‘历史特征’和‘传统价值’”[4],“坚持学者决定学术事务的原则,评议会(教授评议会)控制大学的学术事务”[5]。这些都是抗衡和消解大学行政权力膨胀的有效方式。
(二)日本近代大学教授会的历史演进
近代日本的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诞生于1877年。东京大学是由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而成的国立综合大学,“1881年实施的东京大学组织体制改革设立了统一领导4个学部的校长及校部行政机构,并成立了咨询会,咨询会分为总会和部会两级,总会是校长的咨询机构,由各学部长和部分教授组成;部会设在各学部,由各学部教授组成,学部长为会长”(谷贤林,2007),开始形成统一的管理体系。咨询会是后来的大学评议会和教授会的雏形。
1893年,井上毅出任文部大臣后,通过修改《帝国大学令》和制定相关法规,对大学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大学设评议会,其“部分成员可以由大学教授选举产生,各分科学院设立教授会,教授会的主要权限为审议课程、讲座,审查申请学位的资格等”[6]。大学有关学问方面的诸权限渐次转向各分科学院教授会。井上毅改革扩大了大学评议会的权限和自主性,使帝国大学的部分管理权由政府转到大学,最大限度地完成了大学自治制度,形成了二战前日本大学管理体制的原型。同时,井上毅明确了教授会的地位和职责,使教授会和评议会合议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奠定了日本大学教授会自治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教授们在争取和维护教授会自治方面功不可没。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大学的教授会自治已基本形成,二战前的教授会自治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主要是作为一种惯例和大学的理想被传承下来。
二战后,日本的民主教育体制是建立在相关法律保障的基础之上。
(三)建国前我国教授会的历史状况
教授会在我国并不是新生事物。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就规定:大学要设立评议会、教授会。1924年由北洋政府颁布的《国立大学条例》再次规定:大学设董事会、评议会和教授会。在实际运作方面也不乏成功的先例。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时,为实行教授治校,在校、系两级分别建立了评议会和教授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成员由校长、各科学长、每五名教授中推选的一名教授代表组成。负责制定和修改学校的各项章程法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经费的预决算等。评议会的决定由行政部门负责执行。教授会设立由评议会决定,成员从教授、讲师中产生,教授会主任从成员中推选,各系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教授会主要负责本系的学术工作。与北大不同,根据1926年《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的规定:清华的教授会与评议会同为学校的两个重要权力机关。评议会的职权是:(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2)决议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3)决议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5)委任各种常任委员会;(6)审定预算、决算;(7)授予学位;(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各部主任之任免;(9)议决其他重要事件。教授会的权限是:(1)选举评议会及教务长;(2)审定全校课程;(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的事件;(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务。按规定,评议会在议决第1、2、3、6项职权前,应征求教授会的意见;评议会的决议,被教授会2/3成员否决时,应交评议会复议。这种相互制衡的机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教师在大学管理过程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为教授治校提供了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管理体制的变革,教授会淡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舞台。
二、当前大学教授会存在的问题
(一)组织行政化的倾向
目前的各样各级教授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组织行政化的倾向,教授会中学术人员参与学校重要事项的决策程度仍然不高,对决策的影响力不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院系主任为以行政官员的身份参加教授会,并担任教授会主任,承担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责任。二是教授会高级职称的人员比例不小,但不少是担任行政职务、拥有党政头衔的“双肩挑”干部。严格来说,这些人很大程度上隶属于行政系统,作用近乎于行政权力。在某大学一些院系,教授委员会几乎相当于“党政联席会的扩大会议”[7]。由于院级教授会多数实行代表委员会制度,规模一般在10人左右,因此无行政职务的教授或高级职称的学术人员通过教授会参与学术管理的比例是有限的。特别在教授数量多的院系,大多数教授缺失参与决策管理渠道的现象并没有完全得到改善。教授会的组织行政化倾向不仅偏离了学术组织民主化管理的本意,也丧失了教授集体分享学术权力的初衷,反倒出现了教授群体“学术管理失语”的现象。
(二)对教授会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尚不完善
当前各类教授会制度方兴未艾,制度建设还远远不够完善,尤其缺少必要的保证教授会决策的公正性有效手段。这既不利于教授会权力有效实施,又不利于避免不合理使用学术权力的出现。具体表现在:部分院校教授会的产生未经严格公开的民主选举,缺乏足够民意基础;教授会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公开化水平有待提高,程序公正性建设不足;教授会缺乏对不公正学术权力行为的监督制衡机制设计,尤其缺乏学术权益受害者维护合法权利的途径设计;教授会运行系统信息不对称,权力圈外和社会不能客观有效地参与对掌权监督。
三、建设学术本位价值取向的教授会策略分析
(一)创设教授会改革的良好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
从高等教育规律来看,一个新的学术制度能否存活和发挥作用,需要以科学的大学理念作为基础。教授会制度改革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文化环境氛围。人们要充分认识到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始终是学术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大学发展的前提。以教授、专家、学者为代表的学术人员在管理和决策系统中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只有在学术管理和决策中充分发扬民主,这项制度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实现学术的繁荣,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同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保障大学教授会规范运行机制,在制度层面明确教授会的地位、权利和责任,从而保证大学教授会作为学术管理机构的合法地位、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
(二)赋予学院自主权,院系教授会组织是重点
深化学院实体化改革,必然引起学院责、权、利结构的重构,形成推进教授会制度改革的强大动力。教授会制度改革有着广阔的体制改革背景,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推动这项意义重大的改革,当前需要继续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加快学校管理重心下移,明晰校院两级管理职能。转变校级管理职能与管理方式,落实学院办学主体地位,才谈得上实质性推动教授会制度的改革发展。“学者团体仍然力求获得属于所有真正专业团体的自治权,它必须拥有最后的权力来决定高等教育的内容和掌握它们的方法。”[8]
教授会主要设置在基层学术组织(即院系一级),作为学院一级管理机构的核心之一,发挥着学院学术事务的决策与非学术事务的咨询功能。作为以学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院系,其教授会的合法性基础是学术功能的有效释放。由于院系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学术事务,院系管理必须以学术管理为核心,行政管理要服从学术管理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在院系实行教授会制度,是有效和合法的学校权力下放后基层组织管理和决策改革的模式。院系教授会组织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从“教授治校”向“教授治学”转变的趋势,对教授会制度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三)加强学术权力,“纯化”学术管理机制
大学教授等学术人员主要集中在学院、系或教研室,教授会是教授行使学术权力的主要机构。只有保持大学的学术性,加强学术权力,大学的功能才能有效发挥。“在这一团体的相互关系中,所有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在这一群平等的人中,无论在学院还是在系里,原则都是‘一人一票’,没有任何例外,即使是院长或主席。在任何情况下,更可取的办法是通过说服做出决定,而不是靠权力或地位。”[9]由此笔者认为在院系一级教授会中,尽量保证其组织和人员的学术属性,“纯化”学术管理机制,减少和避免行政权力和政治因素等非学术性干涉的影响;同时,在校级教授会中可以适当的引进一定数量的党政管理人员,起到加强宏观管理和监督作用,这种分层构建教授会组织机制和组成人员有利于基层学术事务的工作开展和学校宏观工作管理。
(四)协调学术权力与党政关系,推进学术权力制衡机制的建设
由于受特殊国情和高校现有管理模式的影响,中国现行的大学教授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教授会制度,也有别于中国20世纪20、30年代建立的教授会制度,具有自身特点。我国高校不能照搬国外的形式。教授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既应借鉴吸收国际大学的通用做法,又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有所创造,灵活掌握,保证实效。除此以外,鉴于改革中出现的民主与效率矛盾,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的矛盾,还要加强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研究,寻找解决的办法。“通过建立教授委员会,很好地理顺了院系的管理体制与权力分配,特别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归属与划分,建立起学院一级学术权力的实现机制。教授委员会成为建立‘党委领导、行政负责、教授治学’新型高校管理模式的重要基础。”[10]
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有益经验,建立多方面的制衡机制,遏制学术腐败现象的发生。在制度制衡方面,从建全教授会制度,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建设规范议事制度、完善考核制度和外部同行评议制度等几方面进行,保证学术管理机构产生的民主与规范,学术权力运行的科学与合理;在权利制衡方面,赋予基层学术组织和专家自身合法学术权益,对违反相关学术规范、学术机构议事程序“暗箱操作”的不良行为有相应的检举权和控告权;在行政制衡方面,学校行政对学术权力机构做出的事关学校发展大局的决议具有监督权,行政权力对同级学术权力机构所做出的决定,如发现有明显不公正的裁断,应当具有提请学术权力机构复议甚至行使否决的权力;在道德制衡方面,要通过提高教师思想觉悟和师德建设,营造一种热爱教学、崇尚学术、端正学风、追求卓越的良好文化氛围,遏制学术腐败现象发生;在技术制衡方面,就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打破信息的不对称,以遏制学术权力失控的现象发生。
[1][2][8][9][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31-32.
[3][5]张德祥.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4]陈学飞.美国日本德国法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
[6]刘爱东.大学内部管理权力制衡的历史考察和现实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7,(6).
[7]席巧娟.院校管理:研究与探索[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10]张君辉.中国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论析[J].教育研究,2007,(1).
(责任编辑沈广斌)
G647
A
1003-8418(2014)03-0062-03
刘海燕(1975—),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科学技术与产业部助理研究员,高等教育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