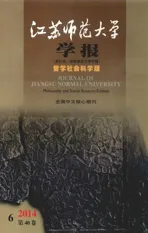明代苏州地区书画消费群体研究
2014-04-17杨莉萍
杨莉萍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明代苏州地区书画消费群体研究
杨莉萍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明代;苏州地区;书画消费群体
有明一代,苏州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人才辈出,尤其在书画领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此也促成了浓郁的书画收藏之风。民间的私家收藏,无论从数量、品种还是从质量上说,苏州地区都堪称海内之冠,而且形成了收藏家群体,共同赏鉴,互通有无。明代苏州书画市场的日益发展和成熟,突出地表现在书画消费市场层次的多样性。其消费的群体大致分为两大类:“鉴赏家”、“好事者”和其他身份的消费者;从其消费的目的来看,主要分为收藏鉴赏、附庸风雅、装饰房屋、艺术投资以及斗富等。明代苏州消费群体的形成与苏州繁荣的商品经济密切相关,在形成过程中及其收藏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消费心态、审美要求以及处事观念无不打上商业社会特有的烙印。这种消费群体的多样性正是明代苏州地区书画市场日益活跃的表现。
明代,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苏州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商品经济发达,而致人才辈出,尤其在书画领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该地书画收藏之风缘此而盛行,而消费群体的日益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书画市场的发展、成熟。
明代苏州地区书画消费市场的层次多样,消费的目的主要分为收藏鉴赏、附庸风雅、装饰房屋、艺术投资以及斗富炫富等。其中收藏鉴赏,前期主要以文人士大夫为主要客户群,如以沈周为代表的收藏群体。中后期由于商贾的大量加入,使得收藏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而以附庸风雅、装饰房屋以及显示财富为消费目的的消费群体主要是达官贵族、商贾以及普通的市民百姓。
按照消费的目的可将消费群体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富商巨贾、文人鉴藏家;二是贵族高官;三是市民百姓。前两者中存在身份重叠的现象,有的既是文人鉴藏家又是财力雄厚的富商,而不少高官贵族同时又精通鉴赏,更有甚者多种身份兼而有之。为了便于阐述,本文姑将其分为“鉴赏家”、“好事者”和其他身份的消费者。
一、“鉴赏家”与“好事者”之争
在收藏群体中自古即有关于“鉴赏家”和“好事者”的讨论。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专以“好事家”为题描述这一收藏群体:
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南郡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严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狭,而所收精好。盖人畏其焰,无敢欺之。……间及王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时所艳。[1]
沈氏将喜爱收藏的各种人物统统归于“好事家”一类,对懂鉴赏的“大法眼”和“门外汉”混为一谈。“好事者”在这里并不具有明显的褒贬色彩,指的是爱好收藏之人。同时,沈氏在“时玩”中又道:
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2]
文中有一个明显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耳食”。“耳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意思是不靠眼睛判断,仅凭耳朵风闻从事的人。讽刺那些只会人云亦云、没有审美判断能力的收藏者。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有关于两种收藏者类型的描述:
世家人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今之所称好画者皆此辈耳。其有能少辨真赝,知山头要博换,树枝要圆润,石作三面,路分两岐,皴绰有血脉,染渲有变幻,能知得此者,盖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3]
何良俊把“好古之家”与“好事者”区分开来。将“好事者”不懂真伪、不分好坏的特点刻画了出来,并对这类收藏群体持讽刺的态度。
关于“好事者”和“赏鉴家”界限和等级的划分,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云:
收藏书画有三等:一曰赏鉴,二曰好事,三曰谋利。米海岳、赵松雪、文衡山、董思翁等为赏鉴;秦会之、贾秋壑、严分宜、项墨林等为好事。若以此为谋利计,则临摹百出,作伪万端,以取他人财物,不过市井之小人而已矣,何足与论书画哉?[4]
钱泳虽意识到因好事者无知所导致的书画交易中的作伪现象及其产生的恶劣影响,但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好事者的参与,明代苏州地区的书画交易又怎能形成如此繁盛的局面?
与此同时,周应愿则有着与上述几位不同的看法。他在《印说》的“好事”中说:“自古称赏鉴、好事两家,鉴赏家往往薄好事。不有好事焉有赏鉴?……赏鉴家何尝不好事?”[5]周应愿明确提出“赏鉴”、“好事”两类,但却对两类人的分野持辩证的态度。他认为真正的“鉴赏者”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在不断的“好事”的鉴藏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今天的“好事者”也有可能成为明日的“赏鉴家”。
以上对于“好事者”和“赏鉴家”的争论,使得苏州地区书画鉴藏圈中形成普遍的共识,即真正的文物鉴藏家必须具备专业的素质:在出于爱好的基础上具有高尚的审美品位且精于识鉴、能阅玩、懂得装潢,还要能考量作品的等次。
二、“赏鉴家”和“好事者”中的代表人物
明代苏州的画家最多,书画著录的专著也很丰富,收藏之风盛于前代,引领审美风气之先,成为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中心之一。顾炎武《肇域志》云:“明人有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苏州地区之所以会成为周边地区鉴藏群体的核心,真正原因在于此地收藏家群体高度集中。清代张应文《清秘藏》“叙赏鉴家”列举了从古至明代的赏鉴家,明代凡30人,其中仅苏州地区就有徐有贞、都穆、王鏊、王延喆、王宠、王延陵、黄姬水、李应祯、沈周、吴宽、祝允明、陆完、陈鉴、朱存理、文徵明、文彭、文嘉、陈淳、史鉴、马愈、王世贞、王世懋、徐祯卿,达23人之多[6]。这些鉴赏家以文人士大夫为主,其经济状况不一,有富裕的,也有贫穷的;有致仕的官员,也有具功名未入仕的青衿和不乐仕进的处士,他们互相间有着师徒、世谊、姻娅、眷属等密切关系,形成了明代最大的地域性赏鉴家群体,代表人物有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徵明,宰辅王鏊,尚书吴宽、韩世能和“后七子”之一王世贞和他的胞弟王世懋等,可以作为收藏活动的领军人物。他们虽然也藏古籍善本、古铜彝器、古窑名瓷,但以收藏书画为主要旨趣。
沈周的鉴藏,从父祖辈算起,到他手上已很可观,曾闻名于当时。巨迹中有褚遂良《荐关内侯季直表》、郭熙《雪霁江行图》、李公麟《女孝经图》、苏轼《前后赤壁赋》、林逋《手帖》、李成和董源的《山水》中堂、陆游《自书帖》等[7],古铜器有商乙父尊。后来画家刘珏所藏的五代、两宋和元代的字画也归沈氏。沈周还拥有元王蒙的很多精品,那是因王蒙与沈周曾祖父沈良琛为莫逆之交。王蒙曾夜访沈良琛,留下了佳作《山水小景》,平时还赠送过为数不少的精品。沈周家也着意收藏王蒙的作品,《太白山图》就是其中最好的一幅。沈周还藏过一件举世名绘、“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作为当时书画鉴藏家群体的核心人物,沈周的鉴赏眼力令人折服,往往仅仅靠看画面风格,无须借助款识、印章便可判定作者,这在当时恐非沈周莫能为。沈周本身精通画理、画法、画风和画史,且熟悉掌握历史印鉴和历代的纸张材料及历代书画装潢的形制等。吴宽记录下的沈周鉴定其自藏《李龙眠女孝经图》的事例,就颇能说明此点:
初不知作于何人,独其上有乔氏半印可辨。启南得之,定以为李龙眠笔。及观元周公谨《志雅堂杂钞》云,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同伯机(鲜于枢)访乔仲山运判观画,而列其目有伯时《女孝经》,且曰伯时自书不全,则知为龙眠无疑,启南真知画者哉![8]
此外,沈周还十分重视旧画的修复和装潢。程敏政题沈周所藏《郭忠恕雪霁江行图》中写道:“石田沈君最博雅,重购所得人皆惊。装潢完好无璺裂,入手坐见增光荣。”[9]
文徵明出身官宦世家,虽不贫困,但也谈不上富有。家传书画藏品并不多,其父文林及叔父文森都将主要精力放到仕途上,所以少有闲暇顾及书画雅玩。目前笔者所见文献中只找到文林所收的《赵孟頫临智永千字文》以及文森所收的《赵雍临李公麟马图》两幅作品。到文徵明时,虽然其文章与书画都很出名,但靠鬻文、鬻书画赚来的钱与那些世代累积的大地主或富商的财产还是无法相比,因此他购求古书画也只能是量力而出。文徵明收藏的书画没有详细的著录,只在他的文集以及同时代人的集子中有零星提及。从这些线索中,我们才统计出大约十来幅曾归属于文徵明的书画藏品,当然其中一定疏漏极多,不过文徵明藏品的难以统计性,恰好反映了文家的藏品是不断流动的,即来即散。这种赏玩但不必长久占有的鉴藏观在苏州地区藏家群体中是相当普遍的。同时也证明了文徵明收藏的一大特点:不以藏品数量闻名,他在书画鉴藏圈中崇高的地位得自于他出众的鉴定法眼。
文徵明高超的鉴赏眼力首先来自于沈周、李应祯、吴宽等前辈对他的培养。文徵明从吴宽学文,从李应祯学书,从沈周学画,十分勤勉好学。其《题张长史四诗帖》云:“此旧藏长洲金氏,予数年前尝与沈石田先生借观,竟不肯出。今归王舍人子贞,因借留余家数月。惜不能起石田与之共论其妙也。”[10]在为华夏作《跋通天进帖》中回忆道:“吾乡沈周先生从华夏假归,俾徵明重摹一过。自顾拙劣,安能得其仿佛?”[11]均可说明沈周对文徵明的培养。临摹、观画既是提高书画创作能力的手段,同时,在这些求观、借观的过程中沈周也必然会将自己鉴画赏画的方法传授给文徵明。李应祯对文徵明也多有培养:
徵明少时尝从太仆李公应祯观于吴江史氏。李公谓:“鲁公真迹存世者,此帖为最。”徵明时未有识,不知其言为的。及今四十年,年逾六十,所阅颜书屡矣,卒未有胜之者。[12]
李应祯是与沈周同时代极其活跃的一位鉴藏家,他将自己的目见经验告之文徵明。
同时,文徵明全面的知识结构,是他成为书画鉴赏大家的最重要因素。王世贞《文先生传》云:“吴中人于诗述徐祯卿,书述祝允明,画则唐寅伯虎,彼自以专技精诣哉,……文先生盖兼之也。”[13]在诗文方面,文徵明与唐寅、祝允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出色的诗文功底,不仅使他在释读文献、了解历史掌故与书画史论上胜于旁人,更使他自己的诗文、题跋阐述问题清晰透彻。绘画方面,文徵明山水、人物、花鸟、鞍马诸题材兼善,山水尤精。书法方面,文徵明兼善各体,正、行、草、隶、篆样样精通,这可能是缘于他对赵孟頫的崇拜,进而模仿。文嘉在《先君行略》中说:“公(文徵明)平生雅慕元赵文敏公,每事多事之。”何良俊曰:“乃知自赵集贤后,集书家之大成者衡山也。”而赵孟頫在诗书画印全方位的造诣可能对文徵明亦有所启发。在书画创作上的全面才能,使得文徵明在鉴定古代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作品时都能给以精准到位的判断,作伪者难逃其法眼。
文徵明在吴门艺坛崇高的声望,使得天下的名迹有如“龙鱼之趋薮泽”(语出安歧《墨缘汇观》端方序)般汇聚到他的眼前,所过目的历代名迹数量惊人,不下几百上千件,而且其中令人惊羡的传世巨迹比比皆是。在不断的寓目、鉴定的过程中,文徵明的经验日益积累,眼力也随之变得更加精准。他在书画鉴定领域中全面而精深的学识反映在其书画题跋中。《文徵明集》中收有230余段书画题跋及大量的题画诗,这是研究明代苏州的书画鉴藏状况及文徵明的鉴藏方法和观念的重要文献。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成化壬辰科状元,官至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定。吴宽藏善本古籍,且亲手抄书,自署“吏部东厢书者”,同时以藏古名砚、藏宋元古书画名满海内收藏界。慕名前来请其题跋古书画者络绎不绝,在《匏庵家藏集》中有记录的就有近百幅。吴氏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大开杀戒之时,正因为没有涉足官场而得以保全。吴宽父亲吴孟融是苏州富商,经商发家后,便将在明初兵灾中毁坏的吴氏老宅修缮一新,名之曰“东庄”。根据现藏南京博物院的沈周所绘《东庄图》册页可知,内有振衣岗、耕息轩、朱樱径、知乐亭、全真馆、艇子洴、鹤洞、拙修庵等二十四景,规模之大几乎囊括了现苏州大学本部南半部分。那块地方是五代吴越国钱元燎、钱文奉父子的别业遗址。吴宽正是在父辈家富饶财的基础上得以一意读书仕进,并收藏古物。
吴宽的书画收藏远不及沈周,但在他的藏品中有两类是其极为珍爱的:一类是苏东坡的书迹或拓本。因吴宽酷爱苏轼的书法,遂专攻此路,他自己的书法便是以绝类苏东坡而立足明代书坛的。第二类是挚友沈周为他所作的画卷。沈周一生为吴宽绘制的画作难以记数,且件件饱含深情。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数成化十五年,吴宽服丧期满返京时,沈周为其绘制的长达五丈的《送别图》。此图现为日本东京角川家藏,卷后沈周饱含深情的长题,令人动容:“赠君耻无紫玉砄,赠君更无黄金箠。为君十日画一山,为君五日画一水……”[14]另一套传世佳制即上文提到的沈周为吴宽家的庄园所绘制的22开册页《东庄图》,质朴的写生手法,移步换景,笔触间透露出恬静、安详的情愫。
吴宽位高权重,他的题跋可以为书画抬高身价。苏州在朝为官者颇多,又有各种好事者的走动,于是常有人将苏州地区某家的藏品或沈周等人的新作带到北京,请吴宽题识。吴宽与一般官僚的区别在于,他的书画赏鉴能力堪称一流,这从他的《家藏集》中近三百篇的题跋便可窥得。他的题跋常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对某位先贤事迹的追述,或对某段故实的钩沉考辨;二,记述书画作者的某段语录,并由此引起对时风的针砭;三,陈述一件作品的流传经过;四,考证一件作品的真伪;五,分析书画作者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风格的由来及传递[15]。
韩世能(1528—1598),字存良,长期任官京师,官至翰林学士,是明末书画家、鉴藏家董其昌的老师。韩世能鉴藏书画独具慧眼,是当时收藏界数一数二的人物。他趁当时书画流动频繁的机会,在京师一带和南方搜求了不少名迹。据张丑、茅维编的《南阳法书表序》载:“维时韩存良宗伯,以妙年登讲席,位帝师,爵元老,兴灭继绝,人文攸系。生平别无嗜好,绝意求田间余事,俸薪所入,悉市宝章,晋、唐、宋、元之奇,所收不下数百本。多与名流品定甲乙。”
关于韩家的藏品,韩氏本人未作详细著录,这对后世了解其收藏状况造成了相当的困难。所幸,在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容台集》和詹景凤《东图玄览编》等书中有相关的记述。韩世能跟当时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张丑有着密切的联系,张氏《清河书画舫》还对在韩家所见藏品作过详细的记载,这对了解韩氏收藏也有一定帮助。大概韩世能在严嵩父子倒台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收购其大半藏品,这是一般官僚收藏家购置藏品惯用的手段。
张丑《南阳法书表》、《南阳名画表》上所列韩世能藏魏、晋、隋、唐巨迹,为数虽不及权相严嵩家,但其中却有不少艺术价值极高的名品。如法书有西晋陆机《平复帖》、晋人《曹娥碑》、王羲之《行穰帖》、王献之《冠军帖》、南朝梁武帝《异趣帖》、唐颜真卿《自书吏部尚书诰兄帖》、《鹘等帖》、怀素《论书帖》、柳公权《翰林帖》等25人共72帖。又另撰《书画铭心表》,其中法书47帖,有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袁生帖》、王献之《鸭头丸帖》、王珣《伯远帖》、唐颜真卿《祭娘稿》、怀素《自叙帖》、唐玄宗《鶺鸰颂》等绝品。
总的来说,韩世能十分注重法书收藏,他本人也十分喜好、精通书法,并有相当的研究。他对名画也十分看重,《南阳名画表》中所列亦多赫赫之迹,如魏曹不兴《兵符图》、晋顾恺之《洛神图》、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韩干《照夜白图》、《双骑图》、五代王齐翰《勘书图》等,凡47人,计99图。另撰《书画铭心表》中的38图,都是《名画表》中所没有的,如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巨然《萧翼赚兰亭图》、李成《茂林远岫图》、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等皆为历代流传有绪的名作,传至今天,有的仍保存在民间,大都庋藏在国内博物馆中,也有少数流往国外。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侍郎。王世贞是中国文学史上“后七子”领袖之一,在文学上主张复古,其著作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等。
王世贞书画庋藏处名尔雅楼,法书珍品有钟繇《荐季直表》、王献之《送梨帖》、颜真卿《送裴将军诗》、范仲淹《道服赞》、苏轼《烟江叠嶂歌》和《洞庭春色》、《中山松醪》,赵孟頫《千字文》、《洛神赋》;名画有唐周昉《美人调鹦图》、宋李公麟《十六应真图》、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王诜《烟江叠嶂图》、郭熙《树色平远图》、马远《十二水图》、元高克恭《夜山图》、明王履《华山图》、杜堇《九歌图》等。
王世贞对苏州收藏界追新逐奇的现象曾发出疑问与感叹,在他的文章《觚不觚录》中讲到:“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瓒,以逮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杀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根据王世贞所述收藏界实况,当时一般士商对当代沈周之画、成化之窑已相当重视。从今日此两种文物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来分析,应当说当时收藏家眼光和需求已走在前列。
除了上述一些鉴赏家,书画收藏圈中也存在一些购求画作以附庸风雅者,宦官参与收藏就是明代比较突出的现象,为前朝所鲜见。他们凭借特殊的身份肆意搜求书画,其实属于收藏群体中的“好事者”。王加、钱能、王赐、冯保等都是当时有名的爱好收藏书画骨董的宦官,对此明人多有记载,如:
成化末太监钱能、王赐在南都,每五日异书画二柜,循环互玩。御史司马公里见多晋唐宋物,元代不暇论矣!并收云南沐府物,计值四万余金。[16]
宦官购藏书画“原非酷好,意作标韵”,本来不是为了获得审美的愉悦,甚至怀有其他的目的。明代中期陆容在《寂园杂记》中就谈到了当时宦官的收藏习气:
京师人家能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辄谓之爱清。盖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绅之好事者往来,壮观门户;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润以行其私;溺于所好者不悟也。锦衣冯镇抚珐,中官家人也,亦颇读书。其家玩器充聚,与之交者,以“冯清士”目之。成化初为勘理盐法,差扬州,城中旧家书画玩器,被用计括掠殆尽,浊秽甚矣!吾乡达有为刑部郎者,素与往还,亦尝被其所卖。[17]
不但收藏动机不纯,获取手段更是极其卑劣。《七修类稿》中另有一则记载说:嘉靖初,南京守备太监高隆,人有献名画者,高曰:“好,好,但上方多素绢,再添一个三战吕布最佳。”人传为笑。宦官购藏书画,却能够闹出如此笑话,实可谓“好事者”。
收藏群体的壮大也促进了绘画市场的繁荣,两者相得益彰。收藏家与书画家结缘,往往是两种身份集于一人。书画家不但能用售画的收入来丰富自己的藏品,还因其有着较丰富的书画鉴别能力,成为富有见识、藏品卓著的收藏家。
三、其他身份的消费者
明代还有大量藏品较少的普通消费者。明中叶以后城镇工商业的发展,使得文化修养不高的市民阶层和有闲阶层对符合自身审美趣味的非经典艺术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他们购买绘画作品既不是出于赏鉴,也没有赚钱谋利的目的,主要是出于实用的日常装饰。
明人沈春泽在为文震亨《长物志》所作的序中说:“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明人都穆《寓意编》记载的四十余位收藏者中既有官员,也有一般的士人,甚至还有医生、裱褙匠和僧人等。有的藏主因财力有限,藏品数量非常少,但他们仍乐此不疲,与以文人士夫为主的藏家共同构成了消费的主体。可见,收藏风气辐射面之广,是明代收藏群体构成的特别之处。
在这些普通的消费者中,虽然有像王复元“每独行阅市,遇奇物佳玩与嫌素之迹即潜购之。值空乏,被衣典质不惜”以及“于节庵养子于康”那样名不见经传的“颇好聚图画”者,但其中不乏一些好事的消费者,购藏书画不是“欲真有所得”。这样的消费者应当不在少数,他们与上文所说的“好事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不过有一类人我们是应该特殊对待的,就是那些市井谋利之人。他们的购藏动机好似多样:既有赏鉴爱好的成分,同时也是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明代中晚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藏品市场的兴盛,抱有这种双重目的的消费者日渐增多。《万历野获编》中说:
骨董自来多质,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毅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18]
名人文士尚且不能免俗,何必因为“谋利”二字去苛求那些普通的购买者呢?明代逐利之风日盛,“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无论是作为书画中间人的牙侩、开设骨董店的商人,还是走街串巷的鬻古者,购藏画作都有谋利的因素搀杂其间。
明代书画在当时也受到外国使者和商人的欢迎,如明代中期以后,文徵明的作品不但受到国内藏家的喜爱,就连外国使者也特别希望得到。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说:
四方乞诗文字画者,踵接于道。……外国使者过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见为恨。文笔
遍天下,门下士质作者亦颇多,徵明亦
不禁。[19]
可见,明代民间的私家收藏,无论从数量、品种还是质量上说,苏州地区堪称海内之冠,而且形成了收藏家群体,共同赏鉴,互通有无。
四、结语
明代苏州书画消费群体是书画市场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费群体的研究有利于正确把握当时书画市场繁荣的面貌和根源。明代苏州消费群体的形成与苏州繁荣的商品经济密切相关,在其形成过程及收藏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消费心态、审美要求以及处事观念无不打上商业社会特有的烙印。
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书画收藏家众多,收藏数量和质量提高,使苏州成为全国书画私家收藏中心之一,收藏之风的盛行,收藏家、好事者的积极参与才使得画家们看到了市场,意识到绘画具有商品性,从而开始了绘画交易的行为,促进了书画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消费群体的多样性正是明代苏州地区书画市场日益活跃的表现。
[1][2][1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4、653、655页。
[3][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7页。
[4][清]钱泳:《履园丛话收藏·总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1页。
[5][明]周应愿:《印说·明万历刻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23页。
[6][清]张应文:《清秘藏卷下“叙赏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7][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王式鉴古书社,1982年版,第120页。
[8][明]吴宽:《家藏集》卷四十八,吉林出版集团,1983年版,第8页。
[9][明]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1页。
[10][明]文徵明:《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8页。
[11][明]文徵明:《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7页。
[12][明]文徵明:《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0页。
[13][明]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二,王世贞文先生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4页。
[14][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五,王式鉴古书社,1982年版,第123页。
[15]黄朋:《明代中期苏州地区书画鉴藏家群体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16][明]汪柯玉:《珊瑚网·画据》,上海神州图光社,1913年版,第56页。
[17][明]陆容:《寂园杂记》卷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页。
[19][明]王绂:《书画传习录》,《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76年版。
The Research o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nsumers of Suzhou in Ming Dynasty
YANG Li-pi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Ming Dynasty;Suzhou;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nsumers
In the Ming Dynasty,the commodity econom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more talents at Suzhou,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ainting,which had achieved great success,romoting the prevalence of the collection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The quantity,variety and quality of private collection were the first in the country.The collector groups were formed,then they appreciated and exchanged their collections from each other.In the Ming Dynasty,the deal of th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developed rapidly and became increasingly mature,especially in the consumption diversit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market.The consumer group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connoisseurs","amateurs"and others.From the consumption purposes,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llection of appreciation,arty,housing decoration,art investment and flaunt wealth and so on.The formation of 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nsumers of Suzhou in Ming Dynasty wa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During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its collection activities,consumer psychology,aesthetic requirements and concept of work of its collection activities all had their special brand of commercial society.The varieties of consumer groups only reflected the active performance i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market of Suzhou region in the Ming Dynasty.
K248
A
2095-5170(2014)06-0055-06
[责任编辑:刘一兵]
2014-03-11
本文系2012年度江苏省社科研究文化精品课题“明代苏州地区书画市场研究”(项目编号:12swc-044)、2013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明清苏州地区书画作伪与代笔现象研究(1753-1820)”(项目编号:2013sjb760015)阶段性成果。
杨莉萍,女,安徽淮北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