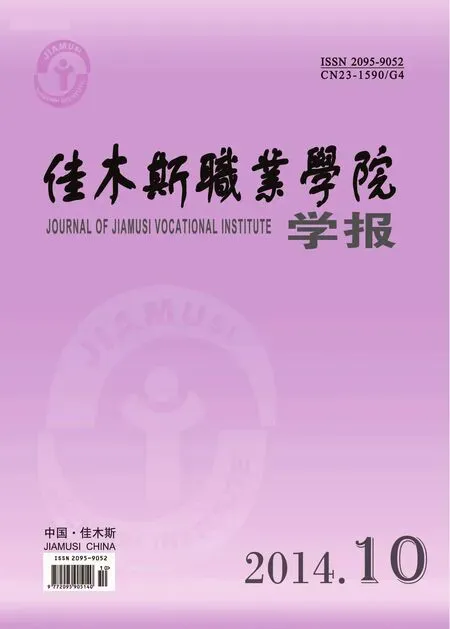论黄佩华小说《生生长流》的叙事艺术
2014-04-17黄雪婷
黄雪婷
(百色学院中文系 广西百色 533000)
论黄佩华小说《生生长流》的叙事艺术
黄雪婷
(百色学院中文系 广西百色 533000)
《生生长流》是广西作家黄佩华的重要长篇小说,讲述了桂西北山村农氏家族几代人的命运,揭示出了特定历史状态下的人生命运与人性内涵,体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即生动展现红河家族的变迁,朴实、自然的语言风格,意识手法的运用,多元化的叙事视角等。
生生长流;家族小说;心理时间
壮族作家黄佩华是文学桂军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是广西第一届和第六届的签约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责任意识。他不仅把目光聚焦于家乡桂西北,创作出了一系列的红水河文化小说,呈现出一幅幅独具特色的乡村风景图,而且聚焦都市人生,表现都市人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困境。在艺术上,他孜孜不倦地追求,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广泛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技巧,使其小说的艺术风格多样化、丰富化。长篇小说《生生长流》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讲述了桂西北山村农氏家族几代人的命运,揭示出了特定历史状态下的人生命运与人性内涵。就叙事艺术来说,《生生长流》不论在题材的选择、语言的运用,还是在结构技巧和叙事视角上都体现出了黄佩华小说创作的成熟与鲜明的艺术个性。
一、红河家族变迁的生动展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自身所处的环境(包括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导思想,无不在其作品中留下深深的印记。这种印记,可以是孙犁笔下富有诗意的荷花淀、芦花荡,是“鬼才”贾平凹笔下人杰地灵的陕南商州,同样也可以是沈从文笔下令人心驰神往的凤凰古城,莫言笔下苦难深重的山东高密。作家有意无意间总会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自己的创作倾向,黄佩华的小说创作也不例外。他以红水河为自己的精神故乡,自觉建构起了一个独特的红水河文化世界。无论早期创作的中篇小说《红河湾上的孤屋》、《涉过红水》、《南方女族》、《百年老人》、《回家过年》、《远风俗》,还是后期创作长篇小说的《生生长流》、《杀牛坪》,都是讲述红水河流域桂西北壮族地区的乡村故事,即使表面上是都市题材的《公务员》,其主人公吴启明及其活动背景依然是红水河边的。因而,具有浓郁的红水河地域文化色彩。
《生生长流》是一部典型的家族题材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壮族小说。小说中的农氏家族是红水河流域无数个家族的代表之一,它通过描写百岁老人农宝田为核心的壮族农氏家族几代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真实再现了红水河畔诸多家庭的生存状态。在农宝田的身上,有一种壮民族特有的野性和剽悍,这种民族性格是壮民族人民在特定条件下对艰苦环境的本能反应。作为一部家族小说,《生生长流》具有鲜明的特色,这是因为“它既不展现《家》那样强烈批判的锋芒,不表达《红旗谱》般阶级斗争的激烈对抗,也不见《白鹿原》般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更没有《丰乳肥臀》对感官的肆意宣泄”[1]、“作者的写作雄心并不是以个人命运写时代风云,他更关注的是这些从红水河的自然世界进入了现代社会的农氏传人在现代社会的命运沉浮”[2],《生生长流》选取的题材作家熟悉且擅长的壮族乡村生活,采用的是一种细水长流式的叙事基调,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评价,远离宏大叙事,把普通人的平凡人生推到前台,将历史融注到老百姓具体、感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方式中,着重描写壮族民间原生态的生活。小说中农宝田对历史的追述,更类似于传统的野史,是片段化的历史,是属于个人的关于历史的叙述。“红水河是桂西北壮民族芸芸众生赖以生存的命脉,这条河流孕育了桂西北壮民族的生命,也缔造壮民族的文明,红水河不仅是民族的生命之托,是家族关系的精神纽带,更是民族人文精神的寄托与象征。”[3]小说之所以命名为“生生长流”,作家在开头便道出了其中的深刻内涵:“很多年以后,当我惟一的儿子降生人世之时,我站在南宁第一医院的阳台上,怀抱着一个粉嫩的小生命遥望西天,极力感受远在桂西北黄土下长眠的农宝田的气息。一种属于红河的律动便如约而来,轻轻拍击着我们父子的心房,我感觉到那是一种血液的流动。”波涛汹涌的红水河不仅孕育了生活在这里的壮民族,更使得这里的人们形成了一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红水河式的民族特质。农宝田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具备这种特质的壮家子弟,他的品质在农家后代的身上得以延续,正如孕育了无数壮族儿女的红水河一般波涛汹涌,生生不息。
二、朴实、自然的语言风格
语言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因而,文学也被称为语言的艺术。特定的语言不仅决定着文学的最终样式,而且体现出文学背后的文化精神。文学语言一般包括经过艺术加工的、规范的书面语言和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口语。黄佩华长篇小说的叙事语言遵循朴实、自然的原则,并且大量地使用壮族民间的日常口语。
《生生长流》中,在介绍“我”三公农兴良从事的“魔公”一职时,这样写道:“红河两岸的山村,常年忙碌着若干靠做鬼事谋生的队伍。他们像阳光和空气一样,伴随着人们的生老病死。山里人从出生到婚娶直至死去,整个一生都把握在无所不能的魔公手里。”[3](P77)语言十分自然,丝毫没有斧凿痕迹。“我”七公农兴发早年被抓了壮丁,几经周折最后“稀里糊涂到了台湾”,小说描写他三十多年后回到故乡,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时,“原先相当潇洒颇有风度的七公,在他日思夜想的人面前却失却了往常的神态,倏然间变得畏缩起来。他不停地点点头,又搓搓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极为传神地描绘出了七公因为紧张、激动而不知所措的神情。
黄佩华长篇小说中叙述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大胆使用民间日常口语。《生生长流》中农宝田的语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农宝田出生在晚清时期,干过船工、赶过马帮,做过土匪,社会阅历较为丰富,并且是农家最年长的长辈,威望和地位自是不言而喻,他的话中带有许多方言、脏话,如“妈个×呢,年猪都杀过了,你们才回来”、“你老祖看累了,你来帮老祖看一下”、“1968年,武装部刘部长的小吉普车认不得路,翻下了红河……嗯,那年村里那帮笨卵仔,以为鱼冻死了,潜到河里去看,冷得卵都落。嘻嘻……”。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不同人物的身份特征和生活经历,通过大量的方言俗语,突出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充分彰显了作家深厚的语言功底。
黄佩华小说中上述语言风格的形成是有深刻原因的。一是他的文字同他的为人一样不事雕琢、朴实无华的。他以冷静的笔触,有条不紊地向读者讲述着故事,而他自己则犹如一个旁观者,平静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生活中的黄佩华深沉憨厚,不苟言笑,恬静淡泊,可谓“文如其人”。二是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深情,黄佩华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壮族民间的日常口语。这些口语,不仅简洁明了,而且微言大义、源远流长,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语言不仅仅是工具,“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认为语言是思想思维,语言即世界观,语言是存在之家,不是人说,而是‘语言说’,话语即权力,语言与民族精神具有内在的联系”[4](P4)。当语言在人们的对话、交流中发挥作用时,语言本身也就成为了思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虽然进入文学作品的语言必然经过作家的选择与过滤,但作为最基本的讲述工具,语言在要求满足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们理解之外,也不可避免地凸显自己民族思维的影子。《生生长流》中的语言,尤其壮族民间口语也彰显出壮族的文化特色。
三、“意识流”手法的运用
黄佩华在叙事结构上的探索深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最早可追溯到“五四”前后,鲁迅、冰心、周作人等人的作品中都包含着西方现代文艺思想的元素。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文学思潮更是以潮水般的速度涌入中国,在文艺界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现代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等成为人们争相谈论的热门话题。包括黄佩华在内的众多广西作家,均被这种潮流裹挟其中,外来思想与本土创作相融合,客观上促进了广西文坛的繁荣与发展。长期以来,线性叙事结构在中国文坛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按照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叙述,是线性叙事结构的显著特点,然而,随着人们对自身及外部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一叙事结构越来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缺乏扣人心弦的悬念气氛的营造;重视外在情节发展,难以对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入微地描绘。与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相比,黄佩华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理论,打破了单一线性叙事结构,往往是两条或多条线索齐头并进地发展,并将过去和现在相互糅合,在“空间时间”的整体架构下,大胆探索“心理时间”叙事。
《生生长流》在叙事结构上富有鲜明特色。一是以家族为叙事结构,将家族中具有代表性的8个传奇人物依次缀连在一起,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农家百年的荣辱兴衰。这不禁让人想到纪传体的开山之作——《史记》。司马迁用他的如椽大笔,洋洋洒洒地书写了五十余万字,记载了从皇帝到汉武帝年间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生生长流》虽然没有《史记》的博大精深,但采用纪传体式的结构谋篇布局,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农氏家族不同成员的性格特征。二是采用了“心理时间”叙事。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曾说道,“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所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的。”[5](P35)“心理时间”叙事,最早由法国的伯格桑提出,与“空间时间”相对,指的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相互渗透,“心理时间”叙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回忆在文章中占有很重的位置,《生生长流》就不乏这方面的例子。比如,“我”的曾祖父农宝田在某天晚上“又一次想起了我那两位早死的曾祖母,两个人的面貌和身姿不停地交替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随后作家以近两千余字的笔墨,让农宝田回忆了迎亲场面的无限风光、初为人父的喜不自禁、面对依月依达的深深愧疚以及两姐妹不幸遇难后自己撕心裂肺地疼痛;再如,当外乡人高昌健问起农宝田与望远镜有关的故事时,“我”的曾祖父饶有兴致地从他与“一个外号叫山毛驴”的人去滇东南闯荡的经历讲起,紧接着的万余字都是与此相关的故事回忆,并以“这是农宝田反复讲了无数遍的一段故事,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人生片段”作结,将读者的思路拉回到现实中来;还有,小说在讲述“我”七公农兴发时,通过“我”与农才生的好奇询问,引出七公的辛酸遭遇,故事情节在回忆与现实中不断穿梭,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可见,意识流手法在《生生长流》得到了较好运用。黄佩华运用蒙太奇方法来剪辑、组合文故事,使文章的结构朝着作家预想的结果向前发展。
事实上,意识流手法是剖析人物内心世界、展示人物意识活动的利器,它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将人物的观察、回忆、联想的全部场景与人物的感觉、情绪、愿望等,相互交融地糅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黄佩华在借鉴“心理时间”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空间时间”的叙事结构,“而仅仅是在叙述手法上使用了一些新的技巧,使得小说在叙事层面上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但是,在小说内部,故事本身仍然是按照‘空间时间’发展的。”[6]在西方作家笔下,“心理时间”强调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叙事,是挣脱了理性束缚之后,呈现出的自然、本真的心理状态,这与包括黄佩华在内的广西作家乃至大陆作家有着本质区别。在“空间时间”的框架下,采用“心理时间”的叙事技巧,是黄佩华长篇小说叙事结构的重要特点。
四、多元化的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是叙事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叙述的角度,采用不同的视角讲述相同的故事内容将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西方理论家认为,叙事角度是小说技巧的一个关键问题:“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角度问题——叙述者所占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的调节。”[7](P208)一般来说,叙事视角有三种类型: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中国传统小说往往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模式,黄佩华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并不拘泥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追求多元化叙事。
《生生长流》的叙事视角有两个,一是农家第四代孙农明即“我”,另外一个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首先,黄佩华选取农家第四代孙农明作为叙事者,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易于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迅速进入“我”这个角色。“我”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在讲述七公农兴发时,是“我”和农才生将七公接回老家,并且通过“我”和农才生的询问,引导七公说出了他数十年颠沛流离、跌宕起伏的遭遇。实际上,在《生生长流》的楔子部分,作者就以“我”的口吻,向读者交代了写作这部小说的背景,况且,作为农家的一份子,“我”与农家的每一位成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用“我”这一当局者来讲述这些故事,便于快速铺展开来,同时也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和可信度。其次,作家并未抛弃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作为乡村叙事,其最特异的地方还是乡土族系生命的自然生存状态,包括每个人在来自外界的天灾人祸当中的搏击、挣扎和沉沦。”[8]《生生长流》是以家族为叙事题材的小说,家族中的关系错综复杂,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讲故事”,进而最大程度上地掌控全局。如对“我”叔农才生如何“从一个县城人变成省报记者”的过程,用的便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农才生曾是县委宣传部长,为了获得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做一个城市人,他历尽艰辛,终于如愿。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黄佩华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将农才生在换工作中的艰难遭遇娓娓道来,真实再现了身份转变的艰辛与不易。在全知视角叙事时,“我”被作家巧妙地隐藏了起来,“我”的视角与全知视角在小说中相互变换使用,具有重要意义。全知视角使得作家凌驾于一切人物之上,降低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度,“我”的视角由于其叙事的优势,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我”的视角在场面的叙述,特别是家族式错综复杂的关系叙述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这正是全知叙事视角所擅长的。
黄佩华长篇小说在叙事视角上明显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是借鉴意识流技巧,在叙事上采用了与之相对应的多元叙事视角。在传统小说中,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单一视角叙述故事,缺乏根据情节发展与故事需要来调整叙事视角的意识。例如中国古代的众多小说,在叙事上采取了全知视角的叙述模式,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从宏观上掌控众多的人物、复杂的情节,最终将多个看似无关的小部分有机联系起来,实现叙事的目的。但是,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如果全盘采用全知视角,则显得活力不足,难以激起读者深入阅读的兴趣。黄佩华的小说往往采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叙事视角,在作品叙事视角的不断变换中,突出了叙事主题。
总之,《生生长流》作为黄佩华表现红水河文化的重要代表作品,不论在题材的选取、语言的运用、叙事的结构、表现的技巧上都体现了作家的艺术个性,也体现了作家驾驭长篇出色的能力。
[1]张颐武,师力斌.家族,一台永恒的游戏机[J].南方文坛,2003(3).
[2]伟林.从自然到社会——论黄佩华小说红水河三部曲[J].民族文学研究,2010(1).
[3]温存超.桂西北叙事与红水河情结——黄佩华小说论[J].河池学院学报,2012(9).
[4]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刘纪新.破碎的情节之链——论当代壮族小说叙事方式的演变[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7]罗钢.叙事学导论[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8]马相武.红河家族叙事与乡村现实主义[J].南方文坛,2003(3).
The narrative art skill of Huang Pei-hua’ novel “The ever-flowing river”
Huang Xue-ting
(Chinese Institute of Baise, Baise Guangxi, 533000, China)
“The ever-flowing river” is the important novel Guangxi writer Huang Pei-hua. The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mountain village northwest Guangxi NongShi‘s fate of the family for generations, reveals the fate of life and human nature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 connotation, embodies the writer's unique artistic personality. Vividly showed the change of the family of the red river, there are simple, natural language style, using the means of consciousness, diversification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 etc.
“ The ever-flowing river”; family novel; psychological time
I106
A
1000-9795(2014)010-000028-03
[责任编辑:刘 乾]
黄雪婷(1971-),女,壮族,广西平果人,百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