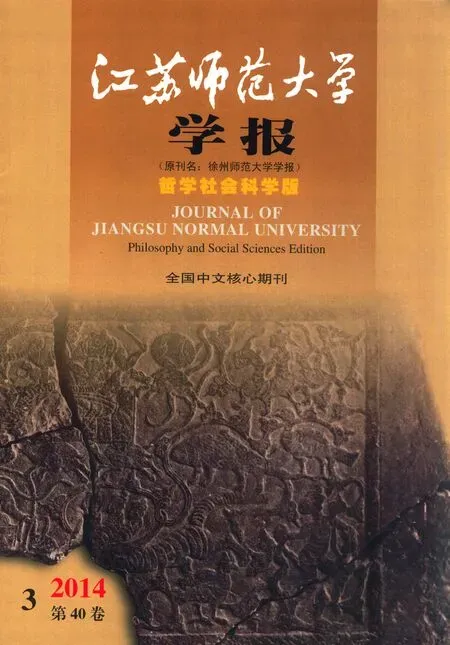论杨逵青年文化心理的形成
2014-04-17梁伟峰
梁伟峰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在“红色的三十年代”中,台湾地区左翼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以小说《送报夫》蜚声大陆和日本文坛的杨逵,其存在使人感受到一种“青年”、“青春”特有的氛围和一股生命力的热源。“永远不老的人”[1]这不仅是杨逵的夫子自道,也堪称其生前故交新知对他的共有印象。而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可以说,一种青年文化心理一以贯之地统摄了杨逵在追求民主、自由、和平路途上的“身”“心”。
青年文化心理是以青年人格心理为基础的,鲜明地标示了青年的文化个性,它指向“青年”年龄层次的对待外部和自我的综合心理,表现和认同了青年文化的基本特征。而且这种文化心理并不总是与个体相应的年龄步步相随,而是在个体与环境的各种互动中产生变化,即所谓“文化心态主体的个人生命是发展的,而且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递进的也是交叉的。老年人可以有青年人心态,青年人也能老年化。文化历史的发展同样如此”[2]。通过探讨杨逵的青年文化心理的形成,可以了解到以他为代表的那一批台湾时代青年,是在怎样的具体环境中,以一种崭新的风貌现身于台湾的社会运动和文学运动的舞台上。
一、“学习成为一名青年”
杨逵的青年文化心理是在他的社会化过程中,在学习和成功进行“自我表达”的路途上形成的,是在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中,与其他青年日益广泛的横向联系上建立的。他的青年文化心理的形成和强化、变化,也都是在个体与环境的各种互动中产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杨逵作为生命个体,当摆脱了童稚状态,进入“学生”行列后,就开始进入到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更密集频繁的社会交往的环节中,进入一种传达青年文化信息的互动过程中。
幼时的杨逵“身体非常瘦弱,在同龄的孩童之中,成了很突出的弱小者”[3]。当时杨逵孤独敏感间或有之,却无怎样的孤僻表现,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如戴国珲所谓“杨逵先生小孩时代,相比较,相当自由”[4]的缘故。比起很多大陆同时代青年来,其成长经历压抑苦闷的气息较少,即使是他的阅读经历,起初也“只是为快乐而读罢了”[5]。杨逵这种“自由”成长的童年经验,对于他日后并不过于愤激的性格和思想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当杨逵1915年进入公学校,开始在众多同龄人的聚集和交流中生活时,则无论从年龄意义上还是从文化心理意义上讲,都意味着渐渐接近“青年”。杨逵真正开始了他的社会化的进程。因为在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学校事实上成了脱离家庭的年轻人的一块“飞地”,是“青年”的养成所,“年轻人进入学校,与其说是学习知识和技术,毋宁说更主要地是在学习成为一名青年。”[6]
1915年发生的西来庵事件,对当时才进入公学校的10岁的杨逵的刺激是很深的。等他晚些时候读到秋泽鸟川所作《台湾匪志》时,“这才明白了统治者所写的'历史'是如何地把历史扭曲,也看出了暴政与义民的对照”,“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7]。这说明将要成为“青年”的杨逵,当时对处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开始否定和拒斥。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当社会化的过程不能对新的一代交代出具备逻辑连贯性的理由,使他们乐于向成年人看齐时,文化破裂便到了无可避免的地步”[8]的道理。
在杨逵一生所接触到的日本籍人士中,对他最有影响、帮助最大的是沼川定雄与入田春彦,这已经被公认。就他接触并受他们影响的时间点来看,他们两人均是以不折不扣的“青年”身份来与杨逵产生互动的。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杨逵青年文化心理形成过程的独特视角。
在杨逵就读大目降公学校六年级时,沼川定雄为班上教师。“年轻时候的沼川定雄是所谓文学青年”[9],他形象高大,爽朗热情,富有人格魅力,无论是在台湾还是日本任教,都颇能引起学生的仰慕之情。[10]杨逵回忆:“沼川定雄先生,刚学校毕业大概是二十一、二岁吧!当时他还没有结婚。”[11]当时他刚刚毕业任教不久,满怀着青年热情,在台湾任教时“强调必须理解台湾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背景,必须要尊重台湾人的情感”[12]。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更是在青春激情的鼓舞下,他对杨逵十分眷顾,常在其宿舍免费给杨逵讲授英语、代数等课程,并提供很多文学名著供杨逵阅读,并因没有家眷的缘故甚至容许杨逵在其宿舍留宿。如张季琳所言,“沼川定雄成为少年的杨逵立志于文学的关键契机,为杨逵的文学修养奠立根基,在杨逵的文学生涯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3]也因为与沼川定雄的接触,使杨逵初步建立的对日本人的观念开始有所修正。
二、左翼“青年”的“诞生”
少时的“自由”成长的环境,为杨逵青年时代的人格塑造和培育指明了基本方向。他是在台南二中迈入18岁这样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青年”门坎的,而在日本则真正成长为一名左翼青年。
杨逵17岁时进入台南州立第二中学,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让他“最感动的是描写对过去的因袭与社会罪恶的抗议或反抗,以往的社会矛盾,底层社会悲惨的人们的作品”。这对已经青年的阶段的杨逵影响极大,内村刚介曾感叹:“这就是文学青年杨逵的诞生呢!”[14]
1924年,19岁的杨逵离开台湾到日本留学,其主要原因,一是要解决家庭强加于他的“童养媳”问题,二是寻求新的精神价值和人生道路。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此时的杨逵已有“青年”的生命个体的自觉。童养媳梁盒早在他12岁时就进入了这个家庭,“非常困扰”[15]他。他何时开始对这种不合理不人道的童养媳制度有了抵触情绪已不可考,但19岁时他因逃避旧式包办婚姻而走上反抗家庭的道路,却是中华民族现代“青年”的作为。他也和千千万万同时代青年一样,从反抗家庭到反抗社会,踏上一条以情感的彻底性和行动的纯粹性来体现自己的激进道路。无论是对童养媳制度的逃避和反抗,还是对精神生活、灵魂世界的追求,对自我人生道路的设计,都能够反映杨逵作为青年的人生觉醒以及不妥协精神。这说明,“青年”杨逵已经诞生,其青年文化心理已经初步形成。
杨逵留学日本时,正是日本的青年文化和青年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左翼文化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如旋风般席卷了千千万万青年。在这股旋风中,杨逵的青春之火也开始燃烧。日本的青年文化和青年运动在东亚国家中兴起较早。早在1887年尾崎行雄的《少年论》和德富苏峰的《新日本之青年》出版期间,有关少年崇拜及青年角色的意识,在日本社会就已经得到一定传播。同时,自藩政时代以来存在于乡村共同体的“年轻人小组”,也自中日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被改组、改名,到处被组合成“夜学会”、“青年会”[16]等。1924年,杨逵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青年文化十分发达的日本社会环境。
怀着对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衫荣一家被害的义愤,杨逵到日本后,广泛阅读左翼社会科学和文化方面书籍,从大衫荣、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不一而足[17]。“社会大学”的历练,失业狂潮的冲击,左翼书籍的阅读,青年运动的号召,都使青年杨逵的热情、信心、勇气极大地激发出来。他不名一文而心忧天下,以一种青年特有的正义感和除旧布新的激情,接受了左翼社会文化思潮、社会主义思想。他以激情、开放、乐观的青年文化心理来面对一切。在当时校园自由学风和时代精神浪潮的推动下,他的交际圈不断扩大。就他与其他“青年”的横向交流而论,已非此前在台湾时可比。他结识了秋田雨雀、岛木健作、叶山嘉树等日本左翼作家,并以自己的做工经历为素材,创作了《自由劳动者的生活剖面——怎么办才不会饿死呢?》,而获得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他积极参加在日本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参与组织文化研究会,参与演剧研究会,参与在东京的台湾青年会的社会科学部,还曾支持朝鲜在日学生演讲会活动,也曾遭到逮捕。这是那个时代青年参与社团运动的典型路径。也正是由于他在日本青年文化和青年运动中的活跃令人瞩目,后来台湾青年文化和青年运动骨干分子便邀请他回台。
往往不被注意的是,根据杨逵的自述,他到日本后跟一位“井上熏小姐”有着短期的朦胧的感情[18]——这对“青年”来说再正常不过。这虽然与一般印象中的杨逵的左翼思想和社会活动无甚关联,但从青年文化心理的视角看,这种“恋爱”感情体验却让我们眼中的这个时期的“青年”杨逵的形象更加完整。
几十年后,杨逵回望他的这段日本留学经历时如此感慨:“十九岁到二十二岁的年轻时候,如今回想起来却都是值得怀念的回忆。”[19]想必对这时的杨逵而言,真正“值得怀念”的是“青春”,是他在日本时的那种炽热和单纯的青年文化心理。
三、台湾青年的“革命+恋爱”
如同杨逵后来的文学创作是他社会运动的延伸一样,他回台湾后在社会运动和农民运动中的表现,也是他在日本业已燃起的青春之火在台湾的延烧。
1927年,回到台湾后,杨逵从事社会运动、农民运动的事迹,包括在“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等组织中的情况,已有不少论述,此不赘言。杨逵后来在回答“你哪一个时期最活跃、最有成就”的问题时,曾言:“就是从日本返台后到1932年的一段期间,那时斗志很好,不管是写作或反日的实际行动都是勇往直前。被捕入狱与作品被禁与杂志被停刊都吓不倒我。”[20]虽然有研究者指出“这个回忆有点错误”,其中的“1932年”有可能为“1942年”[21]之误,但1927年返台后的几年是杨逵的“青年”革命者形象最闪耀光芒的时期,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此一时期,他以青年式的果决和勇气作出了许多人生重要选择。
早在1921年,一个结合文化运动、社会运动,而目的在政治诉求的台湾知识分子社群就已经形成[22]。此一社群以青年为主干,为青年的横向交流、声应气求提供了基础平台。杨逵从日本回国后,融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基本属于青年的社群。与日本时期相比,此时杨逵的青年文化心理中更增添了行动和实践带来的信心和勇气。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因左、右派的争执而分裂,杨逵以青年式的果断毫不迟疑地作出了自己的重大选择而加入‘台湾农民组合’,“这一点成为他一生的重要分水岭。”[23]而在“台湾农民组合”最活跃的1927年到1928年间,具有较多社会运动实际经验的杨逵身兼多项重任,仆仆奔走于台湾道途。而杨逵与叶陶基于“志同道合”而互相吸引,自由恋爱,以至于被开除出台湾农民协会,正是典型的青年文化心理的表现。
杨逵和叶陶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直接踩到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一条最敏感的神经上。杨逵也曾承认,“对那个时候的固有性道德观念和婚姻制度并不重视”[24]。他是这样解释他和叶陶当时的婚恋的:
我们都是很成熟,有自己的主张,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只问是否相爱,是不是好伙伴,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看法。我们未结婚而同居,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25]
可见他和叶陶的情爱洋溢着那个年代青年们特有的大胆破坏、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他们确实达到了“不计较得失”[26]的程度。
还必须强调的是,至迟在1928年,杨逵已经通过对大陆新文学期刊的阅读,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当时杨逵与赖和过从甚密,常常去赖和家中。据考证,赖和当时摆在客厅供文友们阅读的杂志有《语丝》、《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奔流》、《莽原》、《大众文艺》等,绝大部分为新文学杂志,所以“赖和家中的中国白话文杂志对杨逵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可以确定的,只是影响层面多大意见难以估计”[27]。虽则如此,仍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在杨逵的青年文化心理塑造过程中,大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青年之死”的冲击
1932年,杨逵27岁,已经是一般意义上即将走出“青年”状态的年龄,而各方面压力也迫使他无法再像几年前那样肆意燃烧青年激情。他曾自述:“1932年前后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各种组织都被破坏,好多人被捕,杂志被禁停刊,一切公开活动都被迫停止,也许就是我最失意和潦倒的时候。但是生活上最潦倒的时候,却是我写作热情的盛季。”[28]在他旺盛的创作欲背后有着思想和心态的某些转变。有研究者认为,1932年“之后,则是他用前阶段社会实践过程中遭挫的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为基底,通过殖民帝国语文向殖民政权发出战斗之声的文学书写年代”[29],这是很有见地的。
1937年,已经脱离“青年”年龄阶段、32岁的杨逵,迎来了又一次命运的严峻挑战。那时他创办的新文学刊物被查封,多项补救活动无果,文学事业似乎无以为继,且从日返台后,罹患肺疾,咳血数月,还因欠款被起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一切似乎都在围困和打击杨逵。这时候日本青年入田春彦“神奇”般地出现在杨逵生活中。
诚如研究者所言,“杨逵与入田春彦交往的时间虽极短暂,却为杨逵的文学生涯带来重大转机”,“入田春彦对杨逵的影响比历来所能想象的更大、更多。”[30]需要强调的是,他带给了杨逵青年文化的冲击。入田春彦与杨逵订交时还是一个28岁的左翼青年,他当年的上司对他曾这样描述:“年轻的美男子,文静稳重。印象中我总觉得他看起来似乎是个寂寞的孤独青年。”[31]入田春彦在1938年自杀后,台南《台湾日报》曾以“文学青年因孤独感和生活不安,留下异常遗书自杀”为题报导入田自杀事件,说他“是极端的孤独主义者”,“因为精神和物质上的紧迫困苦,以及孤独的哀愁感愈为深刻严峻,而加剧神经衰弱。可以看出是要和春天共逝,抱着必死决心的自杀”[32]。在杨逵的追悼文中,则以“那大个子的男人”,“说要决斗、要战斗的这个热情男人”来指代入田春彦,称赞他的“伟大、慷慨、勇猛”[33]。入田春彦的遗书中自比“怀抱炸弹,欣然勇赴死地的一个士卒”,说他的死“是战斗。我不希望被认为是卑怯的行为”,又承认他有着“三分”“芥川式的虚无”。而他生前就有很多“记述着身心俱疲的、严厉的自省和自责的文字”。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入田春彦的诚实人品和容易受伤的性格。”而其死亡原因“除了他和警察间的纠葛之外,他确实也怀有身体健康、思想和私生活上的苦恼。”[34]
显然,入田春彦是一个可用如善良、进步、敏感、脆弱、细腻、冲动等字眼来描述的那个时代的苦闷着的“青年”。在政治面目上,据考证,他“即使不是真正的左翼运动家,至少应该也是对当时左翼思想有所共鸣的知识人”[35]。其自杀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除了“作为转向者的苦恼”外,“另一可能原因,或许也有女性问题的成分”[36]。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他就是因为无法承受来自现实中警察身份带来的内心冲突和苦闷,以及某种男女情感苦闷而自杀的。换言之,他是因为可概括为“革命+恋爱”的苦闷——典型的“青年”式苦闷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入田春彦的自杀身亡对杨逵的思想和心绪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它使杨逵“仔细地思考”“人性的问题,也就是要活得像个人的苦恼”,“品格高超的人的思想多么受到束缚!品格高超的人一旦受到时代或制度的限制,会变得多么的卑下!”[37]这应该如何理解呢?
入田春彦和杨逵之间的关系有微妙的因素存在。两人并非无话不谈,如前者从不谈自己的过去。就其遮蔽自己的经历这一点而言,他的形象带着几分“神秘”,但就其参与日本左翼文化运动的背景和具有的左翼文化认同而言,他的形象又非常鲜明。纵观他与杨逵的交往,应该说既有当时左翼青年多有的政治上的自我保护意识,带有现实性和关于经历、身世等的匿名性,又有当时左翼青年所特有的活泼率性和浪漫性、“抒情性”的交往。这些都说明入田春彦身上带有浓厚的那个年代的青年文化色彩。
曾有研究者精辟地指出,入田春彦的自杀身亡迫使杨逵“从生的对立面寻找生的意义与价值,从生命的暗影里寻找残余的阳光”[38],可以看出,从青年入田春彦第一次拜访杨逵就令人惊讶地以超出自己两月月薪的一百元相赠的“冲动”起,一直到他那青年的浪漫和冲动气息极浓的自杀,他带给杨逵的冲击力,始终是一种青年特有的率性、浪漫的文化心理。“令入田春彦主动接近杨逵的力量,也就是《送报夫》所提示的乐观行动主义,以及日、台被压迫者与被榨取者的团结行动主义。”[39]而杨逵从青年即殁的入田春彦身上所获取的,一定包括对他的青年文化心理的“高超”性质的体认,和对摧折这种青年文化心理的“时代”的“制度”的控诉。就根本而言,入田春彦之死对杨逵的影响,是一种青年文化心理的冲击,这对当时身心交悴、遭遇严重挫折的杨逵而言,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后来杨逵辟设“首阳农园”,在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始终不坠“青年”的力量和勇气,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会把诗“用铁锹写在大地上”[40]。这可以看作是对当年入田春彦的“高超”青年文化心理的呼应。
综上所述,从反抗家庭到反抗社会,从投身左翼运动到尝试文学创作,从社运领袖到归农园丁,在此过程中青年间的广泛交往和丰富的青年运动经历,塑造和强化了杨逵的青年文化心理,使他获得了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定力、毅力和勇气。而随着1937年后进入了一个沉潜时期,杨逵开始了“首阳花园”的隐居生活,慷慨激昂的社会活动和激扬文字的文学活动,都全面收缩而以“园丁”为本业,已过而立之年的杨逵的青春时代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化过程也都宣告告一段落。但如前所述,虽然文化心理并不总是与个体相应的年龄步步相随,杨逵虽然迈向中年和老年,但其青年文化心理却一以贯之,成为他“永远不老”的精神内驱力,成就了他的人格魅力。
[1][7][40]杨逵:《杨逵全集》第10卷,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台湾),2001 年版,第282、386、388-389、376 页。
[2]杨洪承:《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3]杨逵:《杨逵回忆录》,陈芳明:《杨逵的文学生涯》,前卫出版社(台湾),1989年版,第147页。
[4][5][11][14][15][17][18][19]戴国珲、内村刚介:《一个台湾作家的七十七年》,叶石涛译,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前卫出版社(台湾),1989 年版,第 178、182、180、181、182、182、186、187 页。
[6][16]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4、44 页。
[8]理查德·弗拉克斯(R.Flacks):《青年与社会变迁》,区纪勇译,巨流图书公司(台湾),1975年版,第21、32页。
[9][10][12][13]张季琳:《杨逵和沼川定雄——台湾作家和公学校日本教师》,《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湾),第24期。
[20][24][25][26][28]梁景峰:《杨逵访问记——我要再出发》,《杨逵》,黄惠祯编,台湾文学馆(台湾),2011年版,第142、147、147、147、143 页。
[21][22][29]林淇瀁:《一个自主的人:论杨逵日治年代的社会实践与文学书写》,《20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第六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胡健国编,国史馆(台湾),2002年版,第470、464、471 页。
[23]陈芳明:《放胆文章拼命酒——论杨逵作品中的反殖民精神》,《杨逵》,黄惠祯编,台湾文学馆(台湾),2011年版,第206页。
[27]黄惠祯:《左翼批判精神的锻接:四〇年代杨逵文学与思想的历史研究》,政治大学(台湾)2004年博士论文,第50页。
[30][31][32][33][34][35][36][39]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湾),第22期。
[37]杨逵:《杨逵全集》第9卷,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台湾),2001年版,第589页。
[38]杨翠:《杨逵的疾病论述——以〈绿岛家书〉为论述场域》,《杨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静宜大学台湾文学系(台湾),2004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