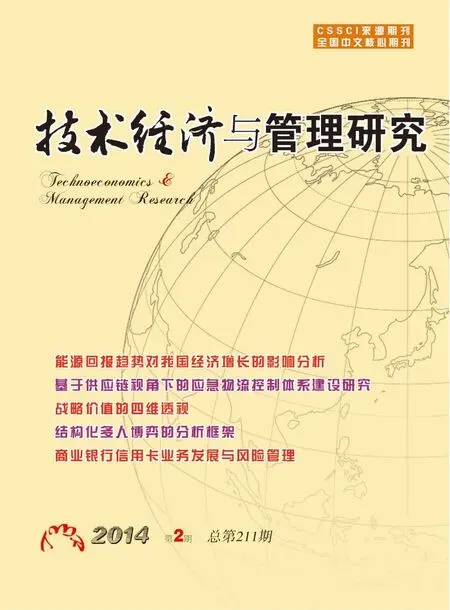战略价值的四维透视
2014-04-16李宏伟
李宏伟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48)
战略价值的四维透视
李宏伟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48)
战略价值是指战略理论、战略知识、战略思维的存在、属性对于战略学习者和实践者的意义。正确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增强分析复杂形势的战略思维能力,是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必修课。登高则可望远,望远而致思深。优秀的战略家不一定是卓越的领导者,但卓越的领导者必须是优秀的战略家。而对于战略价值何在、为何研究战略、为何学习战略知识等问题,却大都莫衷一是。要知道,明确学习意义与目的是学习任何知识的前提,明确战略价值是领导者与管理者学习战略、运用战略的基石。沿用“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属性对于主体的意义”的分析理路,以个体、政党、国家、人类为主体,战略的价值可以概述为:求知明智、获取权力、完善政策、引导历史。
战略价值;战略管理;战略思维;战略理论
战略价值是指战略理论、战略知识、战略思维的存在、属性对于战略学习者和实践者的意义。正确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增强分析复杂形势的战略思维能力,是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必修课。明确学习意义与目的是学习任何知识的前提,而对于战略价值何在、为何研究战略、为何学习战略知识等问题,却大都莫衷一是。但万变不离其宗,因为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属性对于主体的意义。于是从个体、政党、国家、人类等主体视角去分析,战略的价值可以概述为:求知明智、获取权力、完善政策、引导历史。
一、个体视角:求知明智
任何知识都是既定问题的答案,面对现成的战略理论,对于个体而言,学习与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求得知识、开启智慧。在此,知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知的意义即为系统化的战略知识体系;作为动词,知的意义则为求知的过程;其目的又非仅只是知道而已,而更应深入到领悟的层次,即智的层次,如孔子所言“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是知识的时效化、灵活化、行动化和自由化,是在实践层面对于知识的运用与发展。
作为一个孕育智慧的过程,战略知识为设想多种可能性所必需,并将各种可能性缩减为一个可意识到的行为过程。理性战略者的行为过程一般为:“首先对于可能的得失,以及敌方行动的几率作冷静的计算,然后再根据计算结果来选择一条对于自己可能最为有利的行动路线[1]。”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都会对学习者以知识的扩展和智慧的启迪,而战略知识无疑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任何理论的主要目的都是澄清观念和思想,否则它们会变得混乱和纠缠不清[2]。”基于战略知识的引导,即可充分利用已有的信息和经验,打破陈旧观念模式、知识体系的禁锢。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人历来重视理论武装,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曾言“只有用人类全部文化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其结晶)武装起来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理论作为一种求知的途径,它能梳理零散现象、解答有意义的问题,并提出创设性的前景存在。古典战略学家克劳塞维茨曾指出,理论是“所有想从书本上学会打仗的人指南,可以照亮他眼前的路,加快他的进步,训练他的判断力,帮助他避开陷阱[3]。”而一旦形成理论思维,就能站在一定理论高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理性认识是“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4]”。
一旦掌握战略理论,我们就可发挥其如下功效:
首先,循规律而简化。简化是处理问题的方法之一,正如《孙子兵法·势篇》所言:“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理论是对存于万事万物之中规律的抽象与概括,经受理论的熏陶就能简化纷繁复杂的事物,就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其次,抓本质而拓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理论具有统一性与普适性,学习理论能起到触类旁通之效果。毕竟战略的形成是一个受控的、有意识的思考过程,学习前人、未雨绸缪可以适应和预测环境变化。基于此,战略推演的理性成分会愈发强烈,即战略的产生是一个有意识的、程序化的正式规划过程,“分析—选择—实施”成为必经阶段。贯穿战略理论的本质规律也可见一斑,其一是线性和因果关系,即每一阶段都是前一个阶段的后续。其二是分析、选择与实施融合,知识与战略也变成了行动与实践。
最后,因存疑而创新。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求新”的工具,使研究者保持敏锐的眼光,能够发现新的问题和新的看法。“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5]”。批判精神意味着不盲目的崇拜权威、不教条的搬弄论断、不固执的相信真理,一切都应接受理性的审判,一切都值得怀疑,唯一不变的是怀疑本身。尤其是在当今的自媒体时代,互联的世界中人人都是信息的参与者,信息“大爆炸”与谣言“满天飞”并行,能在批判与质疑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是立学治世之本。当然,批判不是批评,更不是目空一切,真正的战略者要保持一个谦卑的“求学”之心,只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自谦为“最无知的人”,才能步柏拉图的后尘,勇敢的去开启智慧之门。
实际上,战略理论既是知识体系的呈现,更是一种思考方式的推演。战略理论并非准则也非公式,其功用不是教人怎样做,而是教人怎样想。法国战略理论家博弗尔曾经明确指出,战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其目的为整理事象,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不同的情况应有不同的战略。此乃基本真理[6]。而所谓战略思维方式,就是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具有战略的视野和层次,能够从长远性、全局性、根本性上去把握事物的自身特点和发展的规律性。一般而言,战略思维具有三维向度:在实践维度上具有目标与手段的效用性结构;在空间的维度上具有全局与局部的整体性结构;在时间的维度上具有现在与未来的预见性和发展性结构[7]。现代系统论和复杂性思维认为,开放、异质、非线、偶然、不确定、自组织等是组织管理的常态。特别是建立在组织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超循环、分形论、分维论、混沌理论等新兴学科基础之上的现代复杂性管理科学的兴起,使得人们对基于“世界简单性”而建立起来的战略管理理念日加怀疑,还原论、机械论、构成论、目的论、实体论与线性思维等工业时代对于战略管理的预设正得以扬弃。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战略管理正推动管理概念的复杂化、多样化和时态化,引导管理理论与实践更加富有变化柔韧。战略制定者与管理者需要多边思维和逆向思维,战略思维越来越成为一个集智商(IQ)、情商(EQ)、胆商(DQ)、逆商(AQ)的综合过程。一方面,需要重视运用理性思维、定量方法和精确模型来分析问题,注重战略规划的精确性;另一方面,善于捕捉灵感、直觉、顿悟、潜意识等在战略决策时的作用,“战略管理离不开理性和知性,离不开事实与数据,但战略决策者要始终注意保持决策直觉与决策质感,注重激活右脑,强调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悟性和灵性的张扬[8]。”
二、政党视角:获取权力
获取政治权利是执政党实施政治统治的前提,权利的获取可分为世袭、独裁、民主等方式,但执政党执政权力的强与弱、长与短与执政绩效直接挂钩。从政治学角度解读,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需要显著的政绩来支撑,显著的政绩为合法的权力赋予权威,而权威才能令民众服从。任何一个执政党统治权利的长久性都是建立在对社会政治资源的充分认识和有效配置基础上的,毕竟资源具有有限性和选择性,这就决定了在有效动员和配置各种社会资源时,需要执政党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执政党在战略抉择时,必须兼顾两项基本要素:效用(Utility)和几率(Probability)。当执政党决定选择某种行动路线时,一定是对于此种路线的效用作最高的期待(Anticipation),同时又对于其失败的几率作最低的期待。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战略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知识,换言之,亦为创造权力,诚如英国战略家弗里德曼在《核战略的演进》中所指:“战略为创造权力的艺术[6]。”以权力获取为导向,执政党在战略部署时需考虑三个基本要素(Elements):能力(Capabilities)、行动(Acts)和反应(Responses)[9]。其中,能力是某一国家可以用来影响另一国家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在内);行动是一个行动者(Actor)在企图影响其对方时所采取的步骤和关系;反应是对方受到影响之后,所采取的行动。而从理论上讲,战略的本质即为指导行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概而言之,一切战略理论都是行动学。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执政地位的获得与不同时期不同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一方面,具备理论上的先进性才能保证执政的科学性。我们党必须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能力,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另一方面,保持战略上的前瞻性才能保证执政的牢固性。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党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国家和社会所起的整合、凝聚、引导作用上,表现在党所制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上,表现在党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上。必须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先后提出了“改革开放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扩大内需战略”、“富国强军战略”,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等。在此指导下,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充分展现了我党执政的有效性,也使我国经受住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各种风险考验,维护并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经济利益多样化,人们生活方式多样化。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因此,要强化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加强社会管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要重视民生问题,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利,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国家视角:完善政策
《孙子兵法·计篇》有言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略的“第一存在”本体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维护与获得依赖于科学完善的政策支撑。学习战略知识,核心任务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不断完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国家战略可分为三个层次:国内、周边、全球,其中国内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基础。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指南针,政府决定其政策或战略时,其主要的考虑即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正如《孟子·梁惠王上》中所言:“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正所谓“上兵伐谋”,战略决策是国运昌盛、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国家政策的出台、治国方略的实施需要战略思维,需要综合考虑环境资源、经济实力、社会心理、文化传统、世界趋势等因素。管理学大师西蒙认为,管理决策可分为两大类型: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从本质上讲,在完善政策,制定科学的国家战略时要协调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不确定性)的平衡。理性视角中,战略思维是一种复杂的分析推理方式,它表现出建立在严谨推理基础上的理性。每一战略决策过程包括四个阶段:一是“情报活动”阶段,即查明外在环境,积淀决策条件;二是“设计活动”,即制定和分析可行性活动方案;三是“选择活动”,即从备选方案中选出特定方案;四是“审查活动”,即对过去的抉择进行评价。非理性视角中,战略思维需要打破正统的信条和思维模式,进行富有创造性和非常规的思维。因此,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权衡成了战略制定的关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发起人布尔曾告诫说,政府对于有关和战大事所作的决定,经常没有经过精确评估和远程思考……政府所注意者常为眼前的事务,而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则几乎是视而不见[12]。因此,在战略分析中,既要关注理性主义假定,也要注意非理性因素的潜在冲击、防化风险,增强对不确定性的预见。就每一个具体的决策环境而言,条件的有限性必然会限制备选方案的内容和数量,从而设定了实现目的的最大可能程度。因此,“科学的决策只能是满意和最优的辩证统一,用满意准则对决策过程和结果进行衡量和控制,全面考量决策过程中动机与结果两方面的因素,才能促进决策过程的优化[11]。”
就具体的国家发展战略而言,步入新世纪,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世界各国纷纷做出战略回应,以军事战略为主的战略扩展到大战略或国家战略,全球性问题越来越成为战略领域的突出问题。而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战略可谓是成绩斐然,十二大提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五大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再到十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步骤上从“三步走”,到新“三步走”,再到21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穿这一过程的是战略政策与战略思维实现了从单一型向综合型的转变,从重点发展到统筹兼顾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当前,兼具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十二五”规划谋划出了我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牢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此,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
四、人类视角:引导历史
“战略不是为今天(For today)而设计,而其一切都是为明天(For tomorrow)着想[14]。”战略面向未来,战略家必须去引导历史。孔子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博弗尔认为战略家的理想是控制历史的潮流,改变历史的趋势,换言之,不是被动地随着历史走,而应主动地引导历史随着我们的理想走。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过:“在农业社会阶段,在时间观念上人们习惯于面向过去,工业社会的时间倾向是注意现在,而在信息社会里,人们的时间倾向是将来。”历史的根本形态就是变,我们既不能假定历史演变的趋势一定是有利或一定有害,更不应断言人类必须追随历史的潮流而不可抗拒。战略家的思考不一定要追随历史的趋势,而是应该预知正在发展中的演变趋势,然后因势而利导之,使此种趋势变得有利无害,或至少是利多害少。
需要正视的是,未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任何情况都有发生的可能,而其形态和时机也常出乎意料之外。战略制定以现实世界的因果律、确定性和必然性为基础,但与之伴随的是相对性、无序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在可预见、可控制和程序化的战略管理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本质上,不确定性源自社会系统本身固有的、内在的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相干性、非线性性、临界性、自组织性、自强化性和突变性[12]。”特别是在当代世界,随着全球化深度的推进,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经济一体化、经营虚拟化、生产社会化、商务电子化、贸易自由化、资本国际化、偏好个性化、关联网络化等早已蔚然成风,不确定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已渐成共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以环境不确定、未来不可预测、系统复杂性和演化动态性为基础的“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林德布罗姆、奎因(逻辑渐进主义)、明茨伯格(应急战略)、沃特斯、钱德勒、哈默尔、吉尔斯等。“后现代”战略管理强调了对理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的反叛和解构,试错、应急、学习、自组织和自适应成为“后现代”战略管理的应有之义。克服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持续创新以应对“万变”,以此打破路径依赖性,获得柔性和持续性竞争优势。“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15]。”“战略灵活性”工具成为新时期应对战略悖论的有力选择,即完整的战略过程要包括四部分:预见——构造对未来的预期情景;规划——为每种情景预设一种最优战略;累积——决定所需的战略期权;运作——管理各种期权的组合。
当然,前瞻未来的前提是不能忘记历史,即“欲知未来,先知过去”。只有熟悉历史,才能推陈出新、有的放矢,实现“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霍华德说,假使不首先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这里来,则对于今后应向哪里走的问题,也就会根本无从考虑[6]。钱穆在《国史大纲》前言部分就告诫读者,“对本国的已往历史要充满温情与敬意”、切忌“抱有偏激的虚无主义”,唯有如此,“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14]”。所以,任何战略思考者必须有充分的历史知识,然后才能掌握历史的未来脉搏。然而,历史的趋势又非完全命中注定,恰如欧阳修在《伶官传序》所言:“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确实,人固然不能预知未来,但有权选择未来,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意蕴也正在此处。
肩负历史使命与发展重任,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担纲意识,善于抓住机遇,引导历史发展潮流。毛泽东曾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讲过:“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战略思考贵在整体性、过程性、系统性、复杂性、不确定性、有机性思考,战略思维的创造性集中体现为领导者能推出新思想,提出新认识,发明新方法,制定新的切合事物变化发展规律的战略目标和规划。不仅强调其思维成果的独创性,而且还特别重视其思维成果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力。战略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及早采取适当行动以改变未来的历史走向,换言之,即为企图控制历史的演进或发展。即使不能控制,也应努力适应历史的潮流,或至少也应设法缓和历史洪流的冲击,并使其不利影响减到最低限度。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董事长威尔逊曾这样说过:“我整天没做几件事,但有一项做不完的工作,那就是计划未来。”
当前,我国正在启动实施“十二五”规划。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登高则可望远,望远而致思深。优秀的战略家不一定是卓越的领导者,但卓越的领导者必须是优秀的战略家。学习战略、感悟战略、掌握战略、运用战略,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当然是一种崇高而伟大的理想,在此还是引述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开讲词》中的一段话作为警醒:“人应该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15]。”
[1]G.H.Snyder.Deterrence and Defense[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25.
[2]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at[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89.
[3][德]克劳塞维茨著,张蕾芳译.战争论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83.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7.
[6]转引自:钮先钟.战略研究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8,318,80,102,108.
[7]段培君.战略学何以可能 [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1):22.
[8]徐飞.不确定性视阈下的战略管理 [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9.
[9]Kal 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M].Prentice-Hall,1983:164-168.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11]孙枝俏,王金水.新制度主义决策优化理论辨析 [J].政治学研究,2010(05):114.
[12]徐飞.不确定性视阈下的战略管理 [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6.
[13][美]迈克尔·雷纳著,耿帅等译.战略的悖论:企业求成得败的原因及应对之道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3-14.
[14]钱穆.国史大纲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5][德]黑格尔.小逻辑 [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6.
(责任编辑:WDY)
Four-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Value
LI Hong-wei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Strategic value refers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istence and property of strategic theory,strategic knowledge,strategic thinking to the learners and practitioners.Correctly grasping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world and China and enhancing of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 ability are the compulsory courses for leaders and managers.Climbing leads to telescope,telescope leads to think deeply.An outstanding strategist is not necessarily an outstanding leader,but a great leader must be an outstanding strategist.However,there are not the same answers on what the value for the strategy,why researching strategies and why learning strategies.The clear meaning and purpose is the premise to learn any knowledge.Knowing strategic value clearly is the cornerstone for leaders and managers to use and learn strategies.Value refers to the meaning of the main body from the presence and attributes of objects.From individuals,political parties,nations and the main human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strategy can be summarized as wisdom,power,perfect policy,guiding the history.
Strategic value;Strategic management;Strategic thinking;Strategic theory
F120.4
A
1004-292X(2014)02-0040-05
2013-08-02
李宏伟(1982-),男,山东沂源人,博士后,主要从事管理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