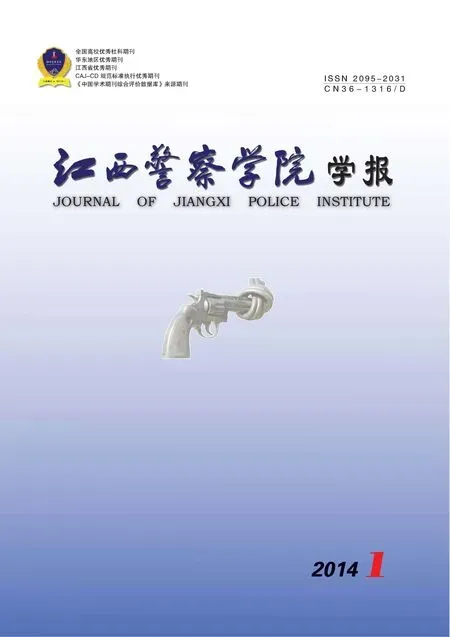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
——兼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
2014-04-16刘涛
刘涛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4)
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
——兼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
刘涛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4)
身份犯中的纯正的身份犯是指身份具有不法构成要件要素性质的犯罪,如贪污罪,非具有身份者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正犯。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并不在于形式的不法与有责身份分离说,也不能从基础单薄的法律拟制说中找寻正当依据。承认非身份共同正犯责任的连带属性,可以为处罚找到适当依据,解决相关身份犯罪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困境与错误做法。
纯正身份犯;非身份者;身份分离;拟制身份;连带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第382条是有关贪污罪的规定,其中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其中的“前两款所列人员”,也就是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款的规定是有关共犯与身份的规定,也就是一般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一般人成立贪污罪共犯的刑法规范。贪污罪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身份犯。所谓身份犯,在学理上是指在构成要件上,以行为人具有一定身份为必要之犯罪。所谓真正的身份犯,系指其身份构成犯罪之身份犯而言,即因具有特定身份才产生犯罪。其与具有减轻或加重刑罚的身份犯区别。[1]428关于共犯与身份,主要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真正身份犯的场合,非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应当如何处理。二是在不真正(加减)身份犯场合,对非身份犯的处罚。[2]395第382条第三款的规定主要涉及第一个问题,①对于第二个问题,相应的司法解释有所涉及,其解释是否合理也是本文所关注的。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30日《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亦即,与有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勾结,进行贪污犯罪的一般人主体,应当如何处罚的问题。
这里需要解决的主要是有关共同正犯 (共同实行犯)的问题,因为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特殊身份仅就正犯(实行犯)而言,至于教唆犯与帮助犯,则完全不需要特殊身份。[2]396林山田教授也认为,真正特别犯虽然必须要具有特定行为主体资格者,始能够实现该罪的不法构成要件,成为该罪的行为主体(正犯),但是并不排斥其他不具行为主体资格的参与者成立共犯,因为在逻辑上,共犯本身并非刑法规定的不法构成要件的行为主体,无资格者仍然无法成立正犯,却仍可以从属依附正犯而成立共犯。因此,无资格者原本即有可能成为共犯,无须通过法条规定,拟制为共犯。[3]87
而且根据从属说,不具行为主体资格者,对于具有行为主体资格者的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原本在理论上就可因其参与犯罪,而成立该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无待于法律的明文规定。[3]87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由于共同正犯并无从属性问题,[4]共同正犯(实行犯)应当如何处罚,具体到本款规定上,就是是否在此种情况下,将一般行为主体也当作贪污罪进行处罚,这一条规定的法律性质与处罚依据是什么。
二、不法与责任分离:通说的困境
(一)身份犯的总则性规定
我国刑法没有对于身份犯的总则性质的规定,第25条是关于共同犯罪的含义:“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26-29条是总则有关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刑法”、日本刑法以及德国刑法均有明确的关于身份犯及其处罚的总则性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刑法”第31条有明文规定。其中第一项规定:“因身份或其他特别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行、教唆或帮助者,虽无特定关系,仍以正犯或共犯论。但得减其刑。”[5]503-504再如,日本刑法第65条第1项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然不具有这种身份,也是共犯。”这也是明确的有关纯正身份犯及其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刑法规定。德国刑法的规定有所不同,其第28条第1款规定:“正犯的可罚性取决于特定的个人要素时(第十四条第一款)时,共犯(教唆犯或帮助犯)欠缺此要素的,依照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减轻刑罚。”
比照台湾地区“刑法”与日本刑法,可以认为,虽然我国刑法中,没有直接规定有关身份犯共犯的处罚规定,但是从第25条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结合第382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说间接上也有了相似的规定。虽然我国刑法(与日本刑法类似)没有直接的有关“实行”的规定,但是可以认为第25条以及之后的26-29条中的“犯罪”应当是指故意犯罪中的实行概念。①德国刑法由于在规定上直接排除了共同正犯(仅包含帮助犯与教唆犯),对于此类问题,用间接正犯的理论可解决。所以,这三国的刑法学都面临无身份的共同正犯如何处罚的问题,理论上也有借鉴的可能。
(二)通说的困境
对于此类问题,在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界以及日本刑法研究中,虽无一种特别有力的说法,不过一般认为应当将无身份者的行为的违法性当作认定为特殊身份犯罪的理由,而将刑罚的个别性作为处罚每一个犯罪人的原则,并将二者进行有意识的分离,以消解刑法规定上这些看似不和逻辑和可能产生不正义处罚的规定。只是学者的个别表述并不一致。
具体来说,以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作为对应的见解,台湾学者黄荣坚认为,所谓的特别犯之所以成为特别犯,如果要有意义,理论上最后只有构建在不法要素与有责要素的概念区分上。这就需要肯定:1.不法要件可以间接实现。2.有责要件必须亲自具备。对于有责要件,必须就行为人本身的情况做判断,而不能透过其他人的关系来实现。事实上,对于此一原则,即使不做规定,理论上也是一样。因为有责性概念本身就是对行为人个人的期待可能性,而和行为侵害性的客观价值判断是两个不同角度的问题。此处所谓有责要件,不仅包括刑法总则所规定的有责要件,也包括刑法分则对于个别犯罪类型之构成中所包含的有责要件。而“刑法”第三十一条的解释是:第一项的从属原则规定,仅限于不法意义的身份等特别要件,而不及于有责意义的身份等特别要件。第二项的独立原则规定,仅限于有责意义的身份等特别要件,而不及于不法意义的身份等特别要件。[5]507、510黄荣坚教授还认为,台湾“刑法”有关特殊身份犯的规定是不合理的,似乎只能违背身份犯的法理,从字面和实际判决进行解读,而不得已只能接受。其认为:“不管‘刑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和不和于犯罪构成的基本法理,从其中第一项关于犯罪之构成的规定来看,上述所谓特别身份等特定关系的犯罪概念应有的效果(欠缺特定关系不可能构成正犯),在刑法的明文规定里,已经明白地被推翻掉了。因为按照“刑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事实上不具备特定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者,并非不能构成共同正犯。”[5]503-505黄教授还针对公务员的公务身份特别指出一种“特别的信赖关系而来的高度的非难可能性”来说明处罚具有特殊身份的主体的个别责任问题。[5]510
另有学者也将此说称为“基于违法之连带性、责任之个别性原则。”[1]430-431陈子平教授认为,为了使得台湾“刑法”第31条规定两款趋于合理,应当放弃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之形式区别,主张第1项系有关“违法身份”(不法意义之身份)之犯罪成立与处罚之连带性作用之规定,第2项则为有关“责任身份”(有责意义之身份)之犯罪成立与处罚之个别性作用之规定,此所谓“违法身份”,指对于行为之法益侵害性赋予影响之身份而言,所谓“责任身份”之对行为人之非难可能性赋予之身份而言。[1]430-431
日本学者基于其本国的相似的有关身份犯的规定,所持的多数观点大体一致。例如,大谷实教授认为,刑法第65条规定:“实施由于犯人的身份而构成犯罪行为的时候,即便是没有身份的人,也是共犯。”(第一款),由于身份而特别影响刑罚的轻重时,没有身份的人按照通常的刑处罚。”(第二款)。第一款表明,单独实施的场合,不能作为身份犯处罚,但是作为共犯实施的场合就成为身份犯,可以处罚,即认可了身份的连带作用;相反地,在第二款即有无身份成为影响量刑轻重的要素的场合,是根据共犯有无身份来个别决定刑罚的,级承认了身份的个别作用。[6]这是因为,作为对法益的侵害的违法性在共犯之间可以是连带的,没有身份的人和有违法身份的人能够成为共犯,但责任必须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评价的,具有个别性。但是,他也指出,如此解释,似有牵强,因为对违法身份犯和责任身份犯的区分相当困难。[6]
再如,山口厚教授认为,违法身份意味着能够引起(惹起)成为相应犯罪之处罚根据的法益侵害这一地位。就以违法身份为要素的违法身份犯而言,非身份犯虽然不可能单独地引起法益侵害,但若是介入身份者则可能(间接地)引起法益侵害,在此意义上,就能奠定非身份者成立关于违法身份犯之共犯的基础。在违法身份犯的场合,即便存在着对非身份者的处罚规定,那也是根据身份的有无而将不同的法益侵害作为处罚的对象,而并非仅仅是针对所引起的同一个法益侵害的单纯的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在此意义上,违法身份犯(即便看上去像是加减的身份犯)全部都是构成的身份犯。与此相对,就责任身份犯来看,在不存在对于非身份者的处罚规定的场合,就意味着是对于所引起的同一个法益侵害,只有在能够肯定更重的责任非难的场合才作为处罚的对象,非身份者因为欠缺可罚的责任而不可罚。在此意义上,责任身份犯(即使看上去像是构成的身份犯)全部都是加减的身份犯。[7]331-332若是共同正犯属于和单独正犯同样意义上的正犯的话,那么身份者大概就不可能成立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但是,共同正犯即便是属于“一次责任”类型,在共同惹起了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意义行,其也是单独正犯的扩张形态,属于是共犯的一种。在此意义上,就像欠缺身份者也可能通过参与身份者的行为而成立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那样,可以认为,存在身份并不是成立共同正犯的不可欠缺的要件。也就是说,尽管单独不能成为正犯,但若和身份者一起的话,就可能共同地惹起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故而非身份者亦可能成立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但是,这一点仅在违法身份犯来说是妥当的,对于责任身份犯则并不妥当。[7]335山口教授以有身份的行为人为说理起点,认为存在有身份人的正犯行为,并且由于非身份者的“加功”,而使得犯罪得以形成,似能说明处罚非身份者的依据,再根据责任身份确定每个人的责任问题。
松宫孝明教授认为,之所以除了处罚有身份的正犯,还处罚共同实行的非身份者,乃是为了满足保护法益侵害应有的程度。处罚构成身份犯之无身份的共犯,并非由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一起攻击了法益,而是无身份者诱惑或促进了有身份者违反了其特别承担的义务(特别义务)。亦即,在仅仅处罚有身份者的义务违反而被认为对于法益的保护不充分时,通过处罚无身份者对有身份者的义务违反的诱发、促进行为,可以说更能达到充分保护法益的目的。[8]
从上述学者对于有关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的适用的解读,可以看到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学者有感言:“由于此种特别犯类型之成立,必须限制行为主体之适格,故在参与形态的认定时,乃产生诸多疑惑性之问题,特别是关于共同正犯认定的问题,似乎是学理上相当棘手难解的问题。”[9]141上述学者对于不法与有责的身份要素的分离的解说,也是有牵强的成分所在,难免会使得读者与实务人员产生困惑。笔者认为,这里使得众学者颇为纠结的问题还是在于此种分离的解释无法解释构成要件行为的认定与责任的承担分离,而与刑法规范本身不能契合的问题。
关于不法与罪责,从行为人的角度来看,不法要问的是我们做错了什么,罪责要问的是我是否该对错误的行为付出什么代价。从规范的角度来看,不法要问的是,我所设定的行为界限是否遭到逾越,罪责要问的是,我应该对逾越界限的行为采取什么反应。[10]44不法层面包括构成要件一致性与构成要件违法性,所要解决的是行为人的行为由那些要素构成,又有哪些因素阻却违法。从身份犯的角度来看,假设没有有关身份犯(总则或者分则)的规定,则按照构成要件符合性,非具有身份的行为人当然不能(单独)构成犯罪或者构成共同正犯。这个结论即使在没有身份要求的犯罪的认定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每个犯罪其实都预设了身份要素,大多数的犯罪对于主体身份的要求就是自然人 (在不法阶段不考虑责任能力、期待可能性等问题,而是任何人)。例如,如果要完整地构建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是:“自然人故意杀他人的,处......”刑法规范力求精练,除了例外,不会特别说明这些隐含的身份要件,一般刑法理论也不涉及这个问题。而因为身份犯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身份问题作为考量的因素,进入了学者(不法)构成要件的范畴。
而对于有责性来说,基于的是不法确认基础上对于行为人个人非难可能性的追问,这里面包括了刑事责任能力、期待可能性等问题,责任的认定必然是依据每一个犯罪人而决定。基于这样的关于刑事责任认定的原则,当然需要对于每一个行为人进行个别的分析。两个问题虽然涉及的要素不经相同,但是终究是为了结局对于行为人进行处罚的问题。分层的意义也在于认清特定的案件当事人的应罚性(不法)与需罚性(责任),犯罪论的递进式分析路径经过长久的演变,始终呈现这样的基本形态,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学者区分所谓的不法身份 (确实存在)于有责身份(值得商榷)也没有不妥之处。那为什么学者的论述中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笔者认为,问题不在于分析的路径上,而是在对于规范的性质理解上,学者无法摆脱在进行了递进的阶层分析后,将犯罪人的责任问题落脚在行为个人上,而造成难以自圆其说或者基本放弃对于此问题实质的解释,而建立在实务判决的简单说明上,承认这一看似不合理现象的存在,进而呼吁取消类似的规定。
三、拟制说:难以找寻的处罚依据
除了上述占多数意见的不法与责任身份分离说,关于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也出现一种拟制说,也就是将上述类似的刑法规定解读为一种法律拟制,非身份人被规范拟制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进而予以评价。
拟制说的代表是台湾刑法学者柯耀程,柯教授对于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的解读主要观点认为,在纯正身份犯的场合,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其共同意思形成,透过共同之意识活动实现特别犯构成要件,且彼此间亦非上下隶属或是支配的关系,故形态上似乎是接近共同正犯的形态,唯因不具行为人资格者,本然上均非正犯,故仅能以法律将其共同性关系拟制为共同正犯。是以不具行为主体资格之行为人,因其欠缺特定行为人资格,故无由单独成立特别犯类型之正犯,但如其与具有特定资格之人共同为之,且符合特别犯成立之基本要求,虽不得成为本然特别犯之正犯,但因其共同性存在,在参与关系中,其参与角色已然等同正犯,故或许得以将其参与角色拟制为类似正犯之地位,而得以成为特别犯之共同正犯。[9]143
柯耀程教授在此又不敢用无疑的口吻肯定他提出的这一观点,在脚注出写明:“此处所称拟制者,系指该犯罪事实参与人本质上并非正犯,然因具有特殊条件的关系存在,等同于正犯角色观察之谓。此种拟制关系的实质意义,恐怕仍有待学理深入加以探究。”[9]143似乎在此柯教授也受到了台湾地区“刑法”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的影响,即使在不法层面承认了犯罪的拟制,在归责层面则必须回到个人答责上来。柯文而后叙述了有关将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视为法律拟制的缺陷:法律拟制的正当性何在?而此一正当性问题,似乎又是刑法参与关系的误解难题。是故,不论法律如何对于行为主体资格加以拟制,首先必须先确认出拟制的正当性,然此一正当性并非任意透过立法的作用而存在,而是必须得以确认其得以取得实质之行为主体资格,方得以在参与角色上认定为正犯,且在处罚上引用正犯之处罚罚之。由此观察,“刑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拟制规定,似乎在正当性的要求上,显有不足,欲以此一规定来确认所有类型的共同正犯与资格,进而借以正犯之刑罚之,在正当性基础的认定上似乎力有未逮。一方面并非法律的拟制,即得以使原本不具行为主体资格者取得该资格;另一方面,参与角色亦非决定不法内涵的机制,是以法律的拟制似乎无法作单向涵盖式的规范,“刑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已然偏离法律拟制关系的基本要求,因此导出的认定关系可能发生偏差。[9]144
在此基础上,由于认为将身份犯的规定视为法律拟制缺乏正当性,故而对于法律拟制的观点又提出进一步的解释,甚至推翻了之前的拟制说,而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一种“刑罚放射效应之规范”。在共同正犯之认定上,系一种由具有行为主体资格之行为人的结合效应,不具主体资格者根本无由成立共同正犯,其所以得以视为共同正犯,似乎此等行为共同性放射效应所涵摄之故,但在理论上,仍旧充斥着问题。是以特别犯中的共同正犯,参与角色并非得以拟制所成,而系一种涵盖关系,此种涵盖关系,将行为人纳入同一参与角色(正犯)来观察,进而将对于正犯处罚之刑罚放射至不具有身份关系之人身上。是故,“刑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所应有之规范意义者,并非参与角色之拟制,而是刑罚放射效应之规范。借由此种规范,而得以罚及不具行为主体资格者,但此种处罚的正当性关系,如仅构建在放射的涵盖效应上,显然有所不足。[9]145故而,对于参与形态的拟制,恐滋生不必要之问题,且对于处罚不具特定主体资格之人者,其刑罚正当性易受质疑。在处罚上,必须反映出其差异性,亦即不具主体资格之人,虽得经由拟制而成为共同正犯,但在处罚上,应较适格正犯处罚为轻,故在法律处罚规定上,应使主体资格之人得按正犯之刑减轻之。[9]145是故现行法所规范的方式,显然系将主体资格以法的拟制所然,在解释上似乎应认为,拟制关系系适格主体所为适格行为之后,所产生之放射效应,并非主体资格存在,即得以将所有共同参与人拟制为正犯,而是须等到特别犯得以实现以后,方具有放射效应,始得以拟制为正犯之繁育与形态。[9]147
林山田教授对于拟制说提出了否定的意见。其认为,就所谓的拟制共同正犯而论,由于其已忽略定位在不法构成要件的正犯概念,使本来无法成为不法构成要件的行为主体的参与者,通过法律的拟制而被视为构成要件的行为主体(正犯)。[3]87倘若刑法对于两种截然不同评价的无资格者与有资格者,作出同为正犯的评价,使两者同其处罚,则显有不妥,故不宜通过法律规定,使不具行为主体资格的参与者拟制成为纯正特别犯的共同正犯,实非妥适的立法,而宜删除。此外,无行为主体资格的参与者所构成的共犯,其可非难性究不如具有特定资格的行为人,故在法律效果上亦应低于具有特定资格的行为人,而应减轻其刑,方符事理。[3]88
纵观柯教授的论述以及林山田教授对于拟制说的否定,可以发现其实两位学者的担心是一致的,最终的落脚点也是一致的,也就是此种法律拟制的合理性问题。柯教授的法律拟制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拟制,柯教授始终不能放心处罚,也就是林山田教授所提到的身份者与无身份者非难可能性存在差异的问题。如若柯教授真的承认此类规定是一种法律拟制,其就不会认为“角色亦非决定不法内涵的机制”(不然,应当将由有身份人与无身份者等同视之),也不会去寻找所谓的“共同性放射效应所涵摄”与“刑罚放射效应之规范”。柯教授所提到的放射效应,其实可以视为是对于刑罚的连带作用,也就是连带责任这一此类规范的实际效果的含蓄称谓。只是柯教授或能在不法领域承认法律拟制的存在,而在责任阶层则是在他心中打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虽然实际的判例说明此类规范具有法律责任连带的效果。
四、连带责任:不愿承认的现实
刑法理论中的责任理论始终认为责任应当是以个人责任为原则。“刑事责任属于典型的个人责任,即刑法惩罚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能够控制的具有公共危害性质的行为,并只能就自身实施的行为对行为人进行非难,不能实行‘连带’。”[11]刑事法的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如果实行团体责任,对于没有实施犯罪的人也处以刑罚,就意味着刑罚不以犯罪为前提,意味着可以没有根据地适用刑罚,意味着对任何人都可以适用刑罚,意味着任何人的自由都没有保障,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自由。”[12]刑事法当然应当坚守责任自负的原则,那种连坐、家庭受到成员犯罪而受罚的情况在文明社会中当然是应当全面废止的。只是针对真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笔者始终认为类似的规定对于行为人承担的责任问题,表达出一种与有身份者相似的、与有身份者有关联的连带责任属性,①这里的连带是一种形象的定义,以表达法律拟制的效果,而绝非行为人的责任完全基于有身份人,这是任何刑法研究者都不会得出的结论。这也是众学者不愿承认的一个立法现实和处罚根据。承认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之间的责任具有连带关系,能更好地解决不法与有责层面不统一的问题,而且绝无造成“连坐”的效果。
首先,非身份共同正犯的连带责任认定,类似于教唆犯与帮助犯的责任归属原则。如前所述,纯正身份犯处罚教唆犯与帮助犯,与其他犯罪处罚教唆犯与帮助犯的理由无异,乃是因为从属性问题。所谓的从属性问题,归根结底是责任替代的问题。美国刑法原理中就明确无误地指出,共犯(accomplice)的责任是替代的、衍生的(derivative)。帮助犯等的责任来源并不是其从事了独立的帮助等类型的犯罪,而是由于首犯(primary party)的责任继受的来。首犯的行为成为他的行为,但是这也是建立在帮助者对于首犯的有意识、意欲帮助的行为基础上。从处罚帮助者的角度来观察,即使帮助行为人没有实行犯罪,但是由于共犯(教唆、帮助)的从属性,责任的衍生性,仍旧可以进行处罚。非身份的共同正犯虽然缺乏从属性,但是可罚性与需罚性角度来考量,并不比帮助犯低,且正犯同样具有一定的意欲同谋或者帮助的犯罪主观构成要素,将其的责任解读为一种衍生责任并不不可。台湾的许玉秀教授也指出,从刑法理论上来看,共同正犯并无从属性问题,台湾“刑法”第31条第1项的矛盾在于对共同正犯亦采取了个人责任原则所致。对共同正犯采个人责任原则使得共同正犯的概念失去意义,如果对共犯采连带责任,则第31条的规定反而可以合理说明。[10]189
其次,将非身份共犯的责任解读为连带,可以消解不法与有责身份分离的解释困境。所谓的不法身份与有责身份分离的学说,只是一种形式解读,由于刑法规范存在类似的规定,为求得对于既判例的合理解释,将非身份行为人的身份要素进行分离,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身份应当是不法的一个构成要件要素,所谓有责的身份,是学者对于责任个人化的一种解说,有责层面的要素基本上是十分明确的,可非难性是关键因素。根据类似的刑法规定,在承认非身份者责任衍生的同时,以非难可能性确定非身份者是否有得减其行的法律依据。另外,采法律拟制说,虽然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不法与责任两个问题,不过正如上述教授所担忧的一样,这样的法律拟制,正当性依据存在怀疑,“将无法实现身份犯构成要件的人也拟制成身份犯,法理依据不明。”[10]189唯有将此处非身份者的责任理解为一种与正犯连带性质的责任,才得将有关刑法规范置于合理的理论框架之下,并在实际适用中得以明确。
最后,将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归责理解为一种连带责任,也可以对现行刑法中有关贪污罪共犯的规定及其司法解释作出合理的判断和解读。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30日《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与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者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职务便利犯罪的,以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的共犯论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务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纪要》再一次明确了这一解释的处罚规定。上述司法解释以及贪污罪(382条第三款)有关共犯的规定都确认了非身份者的刑事责任应按有身份者(共同正犯)的刑事责任来进行衡量。需要注意的司法解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人员分别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犯罪以实际的贡献大小来确定犯罪的解释。张明楷教授认为这一解释值得商榷。其认为,事实上,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的财产非法占为己有,其都已经触犯了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的原则,应当按照贪污罪共犯论处。[2]298笔者认为,张明楷教授这一解释的出发点仍旧是将刑法第382条第3款视为注意规定。如前所指,张明楷教授将这一规定视为共犯处罚的当然解释,只是涵盖了帮助犯与教唆犯,而并没有解决非身份的共同正犯的处罚问题。共同犯罪行为人有可能同时触犯两种身份犯,而根据总则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以及对于382条第3款注意规定的提示,可以将不具有其中一种身份的行为人的行为规制为身份犯罪。而从主犯的身份进行定罪,也反映了在纯正身份犯的场合,责任连带的性质:不同的行为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如果在犯罪的实施过程中,一种身份得以起到对于犯罪的决定作用,则从贡献大小依相应的罪名进行定罪,另外不具有此身份的犯罪人由于责任的连带性,也认定为此种身份犯的从犯。由于从犯比照主犯量刑较轻,此一司法解释也注意到了对于不同共同正犯在身份犯中个人需罚性大小差异的问题,建立在身份犯共同正犯责任连带说基础上,此一司法解释并无矛盾之处。
更进一步,连带责任说之理论也可以运用到对于其他身份犯罪的解读上来。如前所述,张明楷教授所指出的第247条可能出现的漏罚以及处罚不当问题,也可以从对于贪污罪共犯条款及其司法解释的解读中得到启发:刑讯逼供罪是一种纯正的身份犯,特殊的不法主体要件是司法工作人员,但这并不妨碍利用责任连带说,将可能参与刑讯逼供的普通人身份的共同正犯进行适当规制。而且,在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应当作出主从犯的区分。可以看出,若是一般人单独实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达到轻伤害的刑讯逼供,其单独并不能构成刑讯逼供罪(有可能构成第238条非法拘禁罪,但是刑讯逼供的犯罪形式更多,要求的暴力程度更低),第247条规定在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可见其主要侵犯的还是被害人的身体权利,而加重对于司法工作人员的处罚则是对于这一特殊主体在职务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对于普通公民的人身安全不遭到权力机关侵害做了强调和更严厉的防范。可见,在多数刑讯逼供的场合,由于有了国家司法人员的参与,其性质比起一般公民对于他人的伤害更为恶劣,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公民法益的侵害更不能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司法工作人员也利用其易于接近被害人的便利,更易侵犯其人身权利。所以,多数情况下①不排除特殊情况下普通行为人是此类犯罪的主犯情况,但往往在此种情况下,少数普通人可能并不构成犯罪(轻伤以下的刑讯逼供),罪责问题仅需在有身份人之间进行探讨。应当将司法工作人员认定为主犯,犯罪行为整体认定为刑讯逼供罪,并运用连带责任说,对普通人刑讯逼供罪的责任在从犯的意义上进行考量,方能得到较为合理正义的结果。并且,由于247条还存在法律拟制(对于重伤情况拟制为故意伤害罪,对死亡情况拟制为故意杀人罪),可立法者力求各个法条之间合适的关系,并不是一味的从轻或对免责,而是希望对照不同情况,合理确定刑罚尺度,这也在另一侧面反映了连带说的正当性。
五、结论
共同正犯的理论颇为复杂,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由于涉及了-身份这一特殊的不法构成要件要素更显得乱象丛生。以我国刑法有关共同犯罪以及贪污罪有关正犯的规定,以及其他地区刑事法律对于身份犯罪的规定试分析,将身份犯的身份做不法身份与有责身份做分离的解释,只是对于刑法规范作出一种形式解释,并不能说明对于非身份者进行处罚的实质依据。而法律拟制说,由于明显缺乏有力的拟制条件与理由,并不能得到多数意见的支持。将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的责任解读为一种连带责任,能够合乎刑法的规定并且不至于产生不法与有责的问题的矛盾,在具体司法适用中,还应当注意区分有身份正犯与非身份正犯的主从犯关系,从而解决这一处罚难题,使得罪与罪,罪与非罪之间的区分有据可依、当显合理。
[1]陈子平.刑法总论(2008年增修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
[3]林山田.刑法通论(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189.
[5]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
[6][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410.
[7][日]山口厚.刑法总论[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
[8][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M].钱叶六,译.王昭武,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231.
[9]柯耀程.刑法的思与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
[11]姜涛.风险社会之下经济刑法的基本转型[J].现代法学,2010,(7).
[12]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111.
责任编辑:黄永强
科研简讯
根据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公布2013年度江西省高等学校科技落地计划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赣教高字〔2013〕79号),李湘屏副院长主持申报的《基于AFLP遗传标记技术的植物物证在检索中的应用研究》和熊小敏教授主持申报的《无线多媒体传感器网络高能效图像传输机制研究》获批立项。
根据公安部《关于做好2013年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执行工作的通知》(公科信传发[2013]245号),杨璐讲师申报的《视频监控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研究》获准立项。
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江西省教育厅《关于2013年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立项的通知》(赣教党字[2013]48号),张婷讲师申报的《基于认同理论的高校学生社团党建研究》获准立项。
D924.1
:A
:2095-2031(2013)05-0072-07
2013-12-10
刘涛(1987-),男,安徽巢湖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研究生,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法学院法律硕士,从事刑法学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