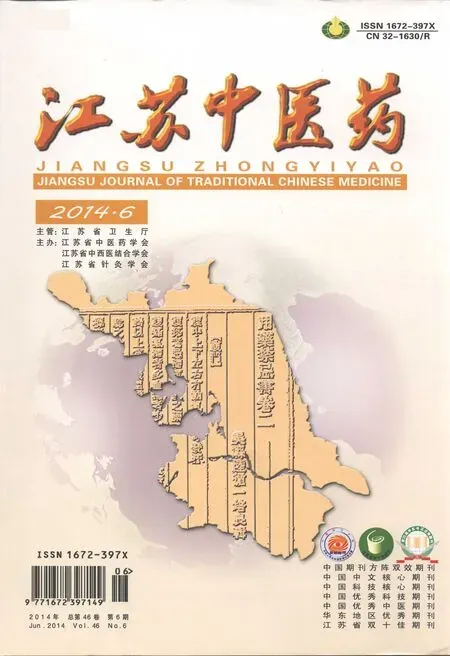中医“瘀热”病机理论证治·外感篇
——周仲瑛国医大师“瘀热”相关学术经验发微之二
2014-04-15唐蜀华严冬
唐蜀华 严冬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南京 210029)
中医“瘀热”病机理论证治·外感篇
——周仲瑛国医大师“瘀热”相关学术经验发微之二
唐蜀华 严冬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南京 210029)
周仲瑛教授认为,瘀热为患可见于外感热病过程中的严重阶段,其形成与外感六淫化火或温邪疫毒入侵有关。瘀热互结,病情深重,多具有严重的火热见证。辨治时当详察血热、血瘀分别存在的症候,还要通过深入症候特点的分析来掌握瘀热的整体存在。治以“凉血”与“散血”(化瘀)法联用,传统以犀角地黄汤为代表,自拟丹地合剂。临床常分为热瘀里结,营血同病证;热毒壅盛,血瘀水停证;热瘀内闭,阴津损伤证;湿热毒瘀,蕴结肝胆证;瘀热蕴肺,兼夹痰火证。透过所列举病案可见周老对外感瘀热病证进行了广泛的实践。
外感瘀热 中医病机 辨证 中医药疗法 名医经验
瘀热为患可见于外感热病或内伤杂病病程中的严重阶段。由外感六淫化火,甚至酿毒,或温热疫毒,致火热炽盛,由气及血,血热内壅,热与血搏,血热互结所致的外感病证,临床常见于传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如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脑炎、肠伤寒、急性重症病毒性肝炎、急性支气管炎、中毒性肺炎、禽流感、急性化脓性胆囊炎或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坏死性胰腺炎、中毒性菌痢、过敏性紫癜等。
1 外感瘀热的形成
外感瘀热的形成常与外感六淫化火或温邪疫毒入侵有关。
六淫之中,风、暑、火、燥为阳邪,侵入人体之后,既可直接阳盛化毒,壅遏血分,又可耗伤阴津,炼血为瘀。寒、湿虽为阴邪,但若久留不去,亦可郁而生热。因此,刘河间力倡六气皆能化火,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也说“风寒燥湿,悉能化火”。火热一旦形成,一方面可以波及营血,致气血壅滞,血流不畅,另一方面,也可劫灼营阴,耗伤血液,致使血液稠浊,停滞为瘀。最终,热与瘀壅滞在血分,相互搏结,难舍难分,酿成瘀热。
外感温热火毒疫疠之邪,既可以直入经脉,侵及营血,也可以由表入里,随经传变,波及血分。因温热疫邪火热之性尤为酷烈,热愈炽则毒愈盛,热毒深入营血,不仅耗伤营阴,而且熏蒸煎熬,更使血液黏稠,血液不能随经畅行;同时热入血分壅遏不散,与有形之血相搏,留滞于脉络之中,遂致瘀热互结。此即所谓“邪热久羁,无由以泄,血为热搏。留于经络,败为紫血是也”。
2 外感瘀热的病机病证特点
以感受外邪为始动因素所形成的瘀热,其瘀与热的关系多为因热致瘀,故而热重瘀亦重,热轻瘀亦轻。但若体内素有瘀滞,则更易与外来之热互相搏结。外感之中,因感受温邪疫毒由表入里者,病情深重,多具有严重的火热见证。
若邪热犯肺,蕴结不解,或风寒外袭,入里化热,热伤血脉,肺气壅滞,肺脉瘀阻,热壅血瘀,酝酿成脓,则形成肺痈(如肺组织化脓症);若瘀热搏结,壅塞气机,熏蒸肝胆,胆失疏泄,胆汁不循常道,泛溢肌肤,可导致黄疸(如急性重型病毒性肝炎);若血蓄肠腑,可致血便伴发热、腹痛(如急性出血坏死性肠炎);若温热毒邪由表入里,燔灼气血,致热壅气滞,肺失通调,或热入下焦,瘀热与水气互结,膀胱气化失司,可导致癃闭(如急性肾衰竭);若瘀热阻于下焦,肾与膀胱蓄血,可致尿少、尿闭、尿夹血块(如流行性出血热并急性肾衰竭);若瘀热相搏,阻于脉络,血热则迫血妄行,瘀阻则血不循经,络伤血溢,导致各种血证(如过敏性紫癜等);若温热毒邪,热毒内蕴营血,搏血为瘀,瘀热相搏,血热则迫血妄行,瘀阻则血不循经,可致脉络广泛损伤,表现为多脏腑、多个部位的出血,势急量多,血色深紫或暗红,甚或九窍齐出;瘀热外郁肌肤孙络,则伴肌肤瘀斑成片(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若瘀热互结,血热炽盛,耗气伤津,血液凝滞,致气机阻遏,阴阳之气不相顺接,可致厥脱(如感染性休克)。
3 外感瘀热证的辨治原则
周教授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强调疗效的提高,必须重视辨证的准确。
3.1 辨证依据周教授指出,不仅要详察血热、血瘀分别存在的症候,还要通过深入症候特点的分析来掌握瘀热的整体存在。
3.1.1 血热征外感所致者发热是必见之症,热势高低随病邪轻重及正气强弱而不同,或身热夜甚。
3.1.2 血瘀征可表现局部固定疼痛(刺痛、灼痛等)或胀满、结块,小腹硬满、疼痛拒按、小便自利,口唇、面部及眼周紫黑,颧颊或上身皮肤显布赤丝血缕,咽喉软腭、球结膜等处可见瘀点、瘀斑,神志昏愦、如狂、发狂。
3.1.3 出血征各个部位均可出血,量多势急,甚则九窍齐出;或迁延反复发作,血色黯红,深紫,或鲜血与紫暗血块混夹而出,质浓而稠;或肌肤外发瘀点,甚至瘀斑成片,大便黑亮而黏,小便短赤。
3.1.4 舌苔、脉象舌质暗红或红绛,舌体青紫,或有瘀点瘀斑,舌下青筋暴突,舌苔黄或焦黄,脉象细数、沉实,或见涩、结、代。
以上征象凡血热与血瘀参见,结合病史分析,具有因果关系者,即可断为“瘀热”。再加某些症、征有鲜明特点者也可作为重要依据,如热病黄疸,本色鲜明,逐渐加深而肤色转为晦暗;出血量多与少量交替,血色鲜红与紫暗瘀块互见,瘀斑鲜红与紫黯错落;热病谵、狂转为神昏不语,而并无“痰”象;等等。此外,在外感热病中结合检验有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依据,可作辨证参考。
3.2 辨治要点周教授认为外感瘀热辨证一般要掌握以下几点。
3.2.1 明辨外感一般而言,外感所致瘀热,凉血应配清热解毒之品,祛除致瘀之源,散血可酌加通瘀之品,以使热无所附,若血热来自阴虚,尚需滋养为伍。
3.2.2 区别瘀、热轻重由于致病因素不一,病理阶段先后不同,患者素体差异,往往表现瘀与热的轻重有别。为此,必须辨别孰主孰次,选用相应药物。热重于瘀者当以凉血为主,化瘀为辅,伍以清热泻火(解毒)之品;瘀重于热者则应加重行血活血之品,必要时还可配用下法下其瘀热。
3.2.3 详察兼证、变证瘀热搏结证在病变过程中,每易出现伤阴、动血、窍闭、厥脱。血热炽盛,极易耗伤津液,耗损营阴;血热血瘀,动血出血,亦易导致阴血亏耗。为此,当配合养阴增液之品;阴虚风动,又当参入凉肝熄风。若瘀热阻窍,内闭心包,神昏谵语,可配伍开窍醒神之品。瘀热壅盛,耗气伤阴,阻滞气血,阴阳之气不相顺接,易致内闭外脱;瘀热动血,血出过多,气随血脱,亦每有厥脱之变,治应同时合以益气养阴,扶正固脱。
3.3 外感瘀热证的治疗大法和基本方药
3.3.1 治疗大法针对“瘀热”的病理,叶天士即已提出“凉血散血”的法则,实际是一种复合治法,将“凉血”与“散血”(化瘀)法联用达到既清血分之热,又散血中之瘀。使血凉则热自清,不致熬煎血液成瘀。化瘀可以孤其热势,使热无所附;而消瘀又可使脉络通畅,阻止瘀郁生热,化火酿毒。若由热生瘀,热重于瘀者,可配清热解毒或清热泻火,使血热无援,毒去而热自消,热消而瘀自散。若由瘀化热,瘀重于热者,在一般凉血散热基础上可加重化瘀之品,直至破血消积、虫蚁搜剔等法。
而瘀热的外感病种每属急危重症,多需中西医结合治疗,判断疗效从结合组与单独常规西药组多点比较,可体现其潜在优势。
3.3.2 基本方药传统以犀角地黄汤为代表,峻剂可用抵当汤、下瘀血汤,药如水牛角、生地、赤芍、丹皮、丹参、制大黄、桃仁、虻虫、虫等。
4外感瘀热证分型论治
以下介绍周教授分证辨治的经验,并各附医案1则。在各证之主要症状项内,凡属一般瘀或热的有关症状从简。
4.1 热瘀里结,营血同病证主症:急骤起病,高热持续,大便秘结,按腹胀痛,斑疹隐隐或显露可有多系统出血。舌脉:苔黄,舌质红绛,脉细数。参考:血象白细胞增高,DIC有关检查阳性,甲皱微循环异常。治法:清热解毒,凉血散血,攻下逐瘀。方药:清营汤、丹地合剂、桃仁承气汤等;药如银花、连翘、鸭跖草、大青叶、紫草、水牛角、生地、丹皮、赤芍、山栀、制大黄、紫珠草、桃仁、枳实、芒硝、煅人中白、白茅根等。
案1:疫斑热(流行性出血热),热瘀里结,营血同病证。
张某某,女,40岁,农民。住院号6740。1982年11月27日入院,12月9日出院。
4天前突起恶寒、发热,当晚寒罢,高热持续,头痛,眼眶痛,腰痛,烦渴,不思纳谷,大便干燥,小便黄赤。诊断为流行性出血热发热期收入住院。查体温39℃,软腭、腋下有出血点,酒醉貌,“V”字胸,球结膜充血水肿,两肾区有重度叩击痛。尿检查蛋白(+++),血查白细胞总数17×109/L,中性0.85,淋巴0.14(其中异淋0.06),血小板68×109/L,尿素氮34.5mmol/L。
经用免疫抑制剂及其他基础治疗,体温有所下降(波动在37.5~38.0℃之间)。但斑疹显露,密集成片。舌质红绛、苔黄中剥,脉细数。病未静止,乃转中医治疗。
辨治经过:初从营血热盛,投犀角地黄汤(以广角粉代替犀角)、清营汤加减,未效。斑色加深呈紫赤色,病至7天,口干不欲饮,舌绛无津,心烦不寐,按腹胀痛,大便秘结,小便赤少。发热、少尿两期重叠。病入营血,阳明瘀热里结,转方凉血活血护阴,更加硝黄通腑,逐血分郁结之瘀热。处方:
生大黄30g(后下),芒硝15g(分冲),枳实、桃仁、丹皮各10g,鲜生地60g,麦冬30g,怀牛膝10g,白茅根30g。
药后大便得解,色黑如羊矢,后为稀便,日行3次,腹胀痛消失,次日斑色转淡。原方去枳、硝,大黄改为10g,并加玄参、竹叶各15g,续服。斑疹渐渐退,小便增多,胃纳大增,舌质不复红绛,热退脉静。复查尿素氮10.6mmol/L,尿蛋白阴性,血小板90×109/L,白细胞3.6×109/L,中性0.74,淋巴0.26。继以竹叶石膏加减调治获愈。
4.2 热毒壅盛,血瘀水停证主症:急性发热,腰痛,尿少或闭(24h少于400mL,甚至少于50mL),便干,便结,斑疹显露,多系统不同程度出血或有浮肿。舌脉:苔黄或焦黄,舌质红绛,脉细数。参考:血压升高,尿有蛋白、红细胞、管型,血尿素氮、血钾升高,DIC有关检查阳性,甲皱微循环异常。治法:清热凉血解毒,泻下通瘀逐水。方药:同4.1,酌加牛膝、车前子、猪苓、泽泻等。
4.3 热瘀内闭,阴津损伤证主症:急骤发热或热势渐降,烦躁谵语扬手掷足或神志不清,斑疹显露,口干,尿少。舌脉:苔焦黄或生芒刺,舌质红绛或光红、少津。参考:血压偏低或在休克水平,DIC有关检查阳性,甲皱微循环检查异常。治法:凉血化瘀,清热开闭,养阴解毒。方药:丹地合剂、牛黄清热丸、增液汤等;药如生地、大黄、水牛角片、丹皮、丹参、赤芍、山栀、人中白、白茅根、玄参、天麦冬、北沙参、白芍、石斛、芦根、鳖甲等。另以牛黄清心丸口服,或醒脑静、清开灵、增液注射液等滴注。
案2:疫斑热(流行性出血热),热瘀内闭、阴津损伤证。
蒋某某,男,35岁,农民。住院号12006。1982年12月27日入院,1983年1月10日出院。
5天前突然畏寒,继则发热,不恶寒,频繁恶心呕吐。颜面潮红,目赤且有出血斑,口渴唇裂,口秽喷人,上腭、胸、腋密集红疹,呈条索状,头痛、目痛、腰痛拒叩,唇紫。舌苔黄,舌质红绛,脉小数。诊断为流行性出血热低血压期。入院时体温正常,血压0/0mmHg。经扩容纠酸,血压升至130/80mmHg,但皮肤红疹进行性增多,臀部出现瘀斑,烦躁谵语,扬手掷足。血检:白细胞21.8×109/L,血小板84×109/L。凝血象:凝血酶时间大于正常对照61s,白陶土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大于正常对照78s,纤维蛋白原1.44g/L,血尿素氮49mmol/L。尿检:蛋白(++)。
辨治经过:热毒犯营,势将动血,热瘀蕴结,内闭心包,病情重笃,亟先清心凉营,开闭防脱。牛黄清心丸1粒化服,1日2次。翌日神志仍然欠清,时有谵语,眼结膜见出血瘀斑,尿少。舌面芒刺,舌苔焦黄,舌质深绛。治拟凉血化瘀,养阴解毒,清心开窍。处方:
鲜生地60g,玄参、丹皮、赤芍各10g,水牛角30g(先煎),石斛15g,麦冬、连翘各10g,大黄15g,龙胆草3g。另用牛黄清心丸1粒,1日3次。
连投前法2日,神志转清,尿量较多,皮肤潮红仍然明显,红疹甚多,舌质光泽。守前法续清其邪。处方:
生地、玄参各15g,水牛角30g(先煎),丹皮、紫草各10g,赤芍15g,大黄10g,茅芦根(各)30g。逾日进入多尿期,皮疹减少,他症亦轻,再予凉血化瘀,养阴解毒,经6日进入恢复期。各项检验恢复正常,症状消失,痊愈出院。
按:流行性出血热重证虽有热结、水停、内闭、阴伤等不同侧重,但均有“热瘀”的共性病理基础,治疗以清热凉血为主,配合泻热逐瘀、利水、开窍、养阴等法。周教授课题组根据凉血散瘀法研制的丹地合剂、地丹凉血注射液,在该病中见机应用,观察有明显出血者41例,显效率达97.50%。联合应用泻下通瘀法,治疗少尿期蓄血、蓄水重证202例,病死率3.96%,而西药对照组77例,病死率22.08%,两者差异显著。证明辨证应用凉血散瘀法治疗外感瘀热证确有价值。
4.4 湿热毒瘀,蕴结肝胆证主症:目睛、皮肤明显发黄;急骤高热,烦渴,呕吐,腹胀口秽,如狂,发狂,便结,尿赤;唇舌爪甲青紫,皮肤瘀斑,神昏痉厥,谵语;吐、衄、便血,血色紫黯或黑。舌脉:苔黄燥或黄腻,舌红或紫暗,舌背青筋紫黑;脉数有力。参考:检查肝功能严重损害,如凝血酶原时间(PT)延长,血清胆红素(T-Bil)和谷丙转氨酶(ALT)上升,总胆固醇(TC)、胆碱酯酶降低等。舌微循环异常。治法: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方药:清肝解毒注射液(由犀角地黄汤合茵陈蒿汤加减组成);药如水牛角片、茵陈、大黄、生地、赤芍、丹皮、山栀、煅人中白、桃仁、虎杖、猪苓、茯苓、车前子等。
案3:急黄(亚急性重症甲型病毒性肝炎),湿热毒瘀内蕴结营血证。
沈某,男,14岁,学生。1992年7月24日入院,9月3日出院。
2旬前开始感觉乏力、纳差,食量较正常减少一半,恶心厌油,上腹饱胀隐痛,尿色黄似浓茶,面目皮肤黄染逐渐加深。经当地医院治疗病无好转。查肝功能:ALT 52U/L,麝香草酚浊度(TTT)8U/L,TBil 362.52μmol/L。神萎,皮肤深黄,巩膜金黄,肝肋下2cm、剑突下3cm、质Ⅱ度,轻压痛,叩痛,脾(-),腹软,无移动性浊音。诊断为病毒性亚急性重型甲型肝炎。曾用苦黄、肝炎灵、丹参等注射剂治疗5d,病情仍进行性加重,出现高度乏力,萎靡,恶心,低热(37.8℃),便黑粪1次(约500g),皮肤黏膜黄疸进行性加深,肝肋下触及,剑突下2cm,质Ⅱ度,有压痛,脾肋下1cm,质Ⅱ度,无压痛,腹水征(-)。复查肝功能:ALT 318U/L,TBil 382μmol/L,碱性磷酸酶(ALP)156U/L。证属湿热瘀毒内蕴营血,治以化瘀解毒退黄,慎防瘀热湿毒内闭动血等变。先用清肝解毒注射液(水牛角,大生地黄,牡丹皮,赤芍,大黄,黑山栀,茵陈,血余炭,煅人中白)40mL,加入5%葡萄糖250m L中静脉滴注,每日1次。经治4d病情好转,精神食纳改善,低热不显,肝区痛减,腹胀不著,肌肤黄染减退,小便转淡。用药7d后,改用口服中药清肝解毒汤剂,治疗至8月24日复查肝功:ALT 80U/L,TBil 47.02μmol/L,乙肝两对半(-),甲肝抗体(抗HAV-IgM)(+),丙肝抗体(抗HCV)阴性,病情恢复稳定。
按:本例患者起病急骤,目黄、身黄、尿黄迅速加重、加深,属感受疫毒,深入营血,瘀热在里所致的“急黄”范畴。患者除出现高度黄疸外,尚见有极度乏力、严重消化道症状,更有瘀热动血之便下黑粪、瘀热阻窍之精神萎靡,且有内闭之势,故非一般清热化湿法所能取效,必须凉血化瘀,直清血分之热,解血分之毒,散血中之瘀。方选清肝解毒方,以犀角地黄汤合茵陈蒿汤加血余炭、煅人中白,共奏清热、凉血、散瘀、止血、利湿、解毒之功,并且先用针剂直达病所,继用汤剂。药证相符,疗效斐然。
另外,周教授指导的博士生研制成清肝解毒静脉注射剂,临床治疗重型肝炎38例,存活率为63.16%(24/38),与对照组单用西药常规综合治疗的存活率40.00%(14/35)相比,有明显差异,治疗组在总有效率、黄疸消退时间、止血时间和主要实验室检查指标改善情况等方面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其疗效达到了目前国内外先进水平。
4.5 瘀热蕴肺,兼夹痰火证主症:身热、振寒,胸满烦躁,胸痛,咳嗽,咯吐腥臭脓血浊痰,或咯血。舌脉:舌质紫气、紫黯,或舌上有瘀斑、瘀点,舌底脉络色黯,曲张显露。脉象可为细、涩、数、结、代等。参考:血浆黏度升高;甲皱微循环异常;血小板黏附和聚集率增高;血白细胞计数增高,反复咳血可有贫血。痰培养可有多种化脓菌混合感染,继发于活动性肺结核,可发现结核杆菌。胸片表现为肺纹理增多、紊乱或呈网状,可伴有小斑片状模糊致密影,或有结核所致的肺部改变表现。治法:凉血化瘀,清肺解毒。方药:犀角地黄丸、桃仁承气汤、千金苇茎汤;药如水牛角、生地、丹皮、赤芍、桃仁、丹参、白茅根、红藤、败酱草、制大黄、山栀、瓜蒌、贝母等。
案4:支气管扩张,痰热瘀血阻肺证。
王某,女,26岁,江都人。1998年5月15日初诊。
支气管扩张史3年。咳嗽,咯吐大量腥臭浓痰,每日需体位引流2次,苦不堪言,胸闷胸痛,口中干苦,舌苔黄厚腻,脉弦滑。证属痰热蕴肺,久病入络,肺失清肃,有瘀搏成痈之趋势。治宜清肺解毒,化痰祛瘀。处方:
炙桑皮10g,炒黄芩10g,金荞麦30g,鱼腥草30g,冬瓜子10g,红藤15g,败酱草15g,大贝母10g,前胡10g,桔梗10g,桃杏仁(各)10g,皂角刺10g,薏苡仁30g,炙紫菀10g。
二诊(1998年5月29日):药服14剂,痰色由黄转白,但仍量多,胸部有时闷痛,舌苔黄腻,脉弦滑。治守原法。上方去皂角刺,加猪牙皂3g、海浮石15g、瓜蒌皮15g。
此后以上方增损治疗,前后共半年,咳痰明显减少,已无需体位引流,每日咳痰1~2口,不咳嗽。治守原法巩固,并配以健脾化湿之品善后。
按:此例患者为支气管扩张证,根据其证候表现,相当于中医学“肺痈”,常因邪热郁肺,蒸液成痰,痰阻肺络,血滞为瘀,痰热与瘀热郁结,酝酿成痈,血败肉腐而化脓。治疗亦按肺痈“有脓必排”的原则,用清肺解毒、化痰祛瘀排脓法,并结合体位引流,脓痰排出,则病情缓解,最后以健脾化湿,杜生痰之源而收功。本案以桑白皮汤为主,清肺化痰,同时配合金荞麦、冬瓜子、红藤、败酱草、桔梗以解毒排脓,用猪牙皂、海浮石、大贝母等涤痰泄浊。胸痛不止是痰热壅阻、络脉瘀滞而致,在清肺化痰排脓的基础上,加用桃仁、皂角刺化瘀散结之品,以促进瘀去痰消。其中红藤与败酱草相配原用于治疗肠痈。红藤“温入血分,疗扑损伤积雪病,破瘀生新止痰血,膨胀鼻衄金疮疬”(《草木便方》);败酱草“能清热泄结,利水消肿,破瘀排脓,惟宜于实热之体”(《本草正义》)。周教授常用于支气管扩张痰瘀热互结,咳吐脓血者,与鱼腥草、桔梗、薏仁等同用,以解热毒,化瘀血,祛痰排脓,体现异病同治之意。
综上可见,周师运用自拟丹地合剂等对外感瘀热病证进行了广泛的实践。结果证明,不仅流行性出血热“热入营血”证,支气管扩张、肺结核、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伤寒、急重型肝炎所致DIC,溃疡病、胃炎等引起的消化道出血,其属于“瘀热型血证”者临床已经取得初步满意的疗效。在外科、伤科、妇科、眼科、五官科、肛肠科等也不乏机会。临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凉血化瘀法不仅对高凝状态的瘀热病证有效,而且对低凝状态下的瘀热病证也有效,这就充分反映了中医“调和阴阳”、“以平为期”的整体治疗优势。
编辑:王沁凯
R228
:A
:1672-397X(2014)06-0001-05
唐蜀华(1941-),男,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名中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擅长中医内科急诊和心脑血管疾病的诊治。
严冬,y12d12@163.com
2014-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