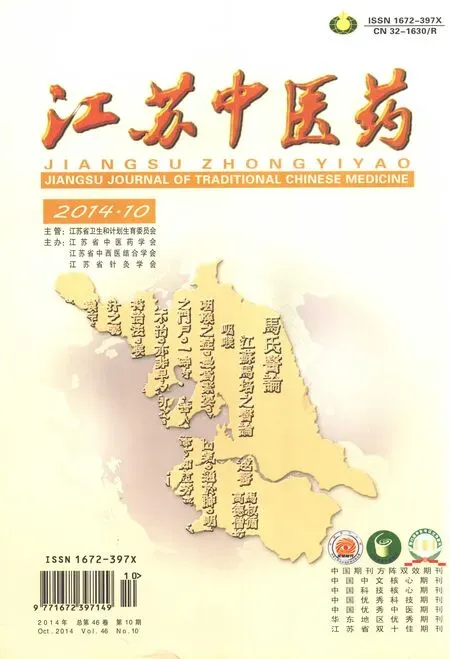史锁芳六经辨证治疗外感发热的经验
2014-04-15王刚周奎龙
王刚 周奎龙
(1.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 210029;2.邢台市人民医院,河北邢台 054031)
史锁芳六经辨证治疗外感发热的经验
王刚1周奎龙2
(1.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 210029;2.邢台市人民医院,河北邢台 054031)
史锁芳教授治疗外感发热宗仲景六经辨证,遣方用药灵活多变,常取佳效。辨太阳经发热,卫强营弱自汗用桂枝汤,阳气闭郁无汗用麻黄汤,虚人外感用参苏饮、人参败毒散等方。辨阳明经高热,见大渴以白虎汤加减为主,石膏量重多则100余克,阳明腑实发热且见潮热予承气汤辈。辨少阳经寒热往来,治以小柴胡汤为主,重用柴胡30g辛透外邪。辨太阴病发热多属虚人外感,推崇薯蓣丸,伴阳明热盛口渴喜饮用石膏,腹中大实痛加制大黄。辨厥阴病发热,实肝阳虚馁,形成寒热错杂之证,治以乌梅丸、吴茱萸汤、通脉四逆汤为主。辨少阴病发热,素体肾阳不足,复感外邪,有汗用桂枝加附子汤;无汗者用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等。附验案1则以说明。
外感发热 六经辨证 中医药疗法
史锁芳教授系江苏省中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中医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师从李石青、曹世宏、单兆伟等名中医及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深得其传。史师从事肺系疾病的中医临床研究20余载,对肺系诸多疾病,如“感冒”、“咳嗽”、“哮病”等均有系统的辨证思想与治疗思路。对于外感发热,史师多宗仲景六经辨证,遣方用药,师古而不泥古,灵活多变,常取得较好的效果。笔者有幸侍诊左右,兹将其对外感发热的六经辨治精粹介绍如下。
1 辨太阳经
邪气外扰,首犯太阳,太阳为身体之藩篱,诸阳之属也。太阳脉连于风府,为诸阳主气,故邪犯太阳,则出现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脉浮等症状,此即太阳病之“太阳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尤其是“恶寒”,此乃辨治太阳病之关键,“有一分恶寒即有一分表证”,此“恶寒”又多兼有太阳经表证,如四肢关节痛、颈项强等,此又当与少阳“寒热往来”之“恶寒”相异。传统上太阳病分为太阳中风及太阳伤寒,此二类辨别的要点为有无汗出。卫强营弱,自汗出者,为中风,方选桂枝汤;阳气闭郁,无汗出者,为伤寒,方以麻黄汤为主,自当区别,不可混用。史师临证用药,虽常用此二方,然不拘于此,临床常根据病人体质及临床表现随证治之。虚人外感,选用参苏饮、人参败毒散等方,又为创建,常谓仲景示人以法,而并非一两张方剂。太阳病又多有兼夹及变证,夹湿者,头重、四肢关节酸重者,病势多缠绵难解,史师宗九味羌活汤之意,药选羌活、防风、苍术、甘草等;咽痛因寒邪痹阻者,加半夏、桂枝等,由热结者,加桔梗、甘草;头项强者,加葛根;口干不甚者,加黄芩;烦躁而渴者,加石膏;头痛者,根据部位,各取引经药;咳喘者,加杏仁、厚朴等。
2 辨阳明经
外邪不解,邪入阳明,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此期发热多为高热,为邪正交争的极期。阳明经的辨证多分为阳明经证和阳明腑证。
阳明经证的辨证着眼于“大热、大渴、大汗出、脉洪大”之“阳明四大证”。史师指出,尤应重视“大渴”这一症候,阳明里热炽盛,欲饮水以自救,故而“大渴”,方以白虎汤加减为主,其中石膏的用量宜重,多以40~50g开始,酌情加大用量,多则100余克,但一定要顾护脾胃。阳明热盛日久,多有阴伤之象,酌加西洋参补益气阴;阳明日衰,气阴两伤,余热不尽,多选用竹叶石膏汤加减。
阳明腑实证,一般表现为发热、大便难、腹胀等,而发热多以“日晡所发潮热”为特征,史师认为潮热在日晡之时发生,对于诊断阳明病,特别是对诊断阳明病的腑实证,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阳明腑实证中大小承气汤的运用,尤其是大承气汤的运用,更是以潮热为第一指征。“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治疗上,一般选用大小承气汤及调胃承气汤,但常又取法温病,兼有肠燥津枯者,选用增液承气汤、黄龙汤等;兼有喘促不宁者,选宣白承气汤;兼小便赤痛者,选导赤承气汤等。
3 辨少阳经
少阳病,辨证以少阳的提纲“口苦、咽干、目眩”及“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为主,结合“但见一证便是”,抓主证,抓符合少阳病机的主要症状加以辨证。少阳病为邪犯少阳,枢机不利,治以和解少阳为主,方以小柴胡汤为主。小柴胡汤在使用时应注意柴胡的用量,要打破“柴胡劫肝阴”的思想禁锢,史师认为古书谓“柴胡截肝阴”,可能由两种原因造成:(1)不该用而用;(2)该用而用不得法,包括未顾及患者肝阴虚之体及长期大量使用,未护肝阴。对于外感热病,史师常谓,小柴胡汤若要发挥其和解少阳、畅达三焦的作用,需重用柴胡,且柴胡用量要绝对大于黄芩,因为只有柴胡重用,一般达到30g,才能发挥辛透外邪的作用;而中等量,如10~20g则偏于疏肝理气;轻用3~6g则偏于升阳举陷,均不能使三焦邪郁得以透散。少阳为阴阳出入之枢机,故常兼三阴三阳证,兼有太阳表寒者,予以柴胡桂枝汤;兼阳明热盛者,予以柴胡白虎汤;兼阳明腑实者,予以大柴胡汤;兼太阴虚寒者,予以柴胡桂枝干姜汤为主;邪郁本经,引起肝络不和者,原方增入香附旋覆花汤等,随症加减应用,变化无穷。
4 辨太阴病
对于太阴病,多为素体脾气虚弱,感受外邪,属虚人外感的一部分,实际上为三阳经外感发热,而兼有脾胃虚弱之体,临床上除了三阳经外感发热的表现外,又有腹满时作,时腹自痛,食冷腹泻等临床表现,治疗上与三阳经又有所不同,以扶正祛邪为主,史师宗“实人外感发其汗,虚人外感建其中”之旨,方以小建中汤、理中丸为主。史师临证尤其推崇薯蓣丸,《金匮要略》云:“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方以八珍汤为底方补益气血,健运脾胃,另配以柴胡、桂枝、防风祛风散邪,杏仁、桔梗、白蔹通宣肺气,寓攻寓补,寓散寓收,为不寒不热,不攻不泻,不湿不燥之平剂,临床予气血两补,内外并治之中,具有佳效,可以常服。但患者兼有阳明热盛,口渴喜饮时,石膏又当使用,史师常取法麻黄升麻汤之意,以白虎汤配伍理中丸,标本兼顾;腹中大实痛,难以忍耐,又遵桂枝芍药加大黄汤之旨,于补益脾胃方中,加制大黄等,但顾护脾胃贯穿治疗始终。
5 辨厥阴病
厥阴病,史师认为厥阴病实质上是肝阳虚馁,形成寒热错杂之证。肝阳馁弱,则肝用不及,失却其升发、疏泄、调达之性,因而产生广泛的病症。肝虚之体,复感外邪,“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气内入,更加影响肝用,强调辨证除三阳经外感热病的表现外,仍有肝阳虚所引发的病症,比如四肢逆冷、巅顶疼痛、疲惫、胃脘痛等表现,治疗上以乌梅丸、吴茱萸汤、通脉四逆汤为主。
6 辨少阴病
此多为太少两感之病,素体肾阳不足,复感外邪,辨证要点为发热、恶寒甚,脉微细,舌苔润等。治疗上有汗者,用桂枝加附子汤;无汗者,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等。史师临证尤注意附子的用量,轻则6~9g,重则40~50g,甚则百余克,常药到病除。史师常谓:陈寒痼冷,投以轻剂,如隔靴搔痒,不能却病,反惹病进,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只要辨证准确,煎煮得当,就放手去用,常有意想不到之效。临床运用大剂量附子应把握四点:(1)把握运用指征——①畏寒怕冷、困倦嗜睡;②舌质淡胖或有齿印、舌苔润滑;③面色灰黯带有青色;④痰液多为白色清稀痰或泡沫稀痰。①②为必备,③④为兼夹,临床只要出现①②两主症就可应用。(2)注意煎法,久煎、先煎;<50g,先煎60min;55g~75g,先煎90min;80~100g,先煎120min;105~125g,先煎150min;130~160g,先煎180min;170~250g,先煎210~240min。(3)掌握祛毒配伍,常配甘草15~30g,干姜10~30g,并用鲜生姜10~20片,绿豆20~30g。(4)重视特殊服法,附子用量在120g以上,加蜂蜜两勺冲服[1]。此外又多有变通,肾阳虚甚,浮越于上,当用温潜法,附子配磁石、酸枣仁等;阳明燥热,口渴甚者,宗舒驰远之法,附子配伍石膏;中阳闭郁,热逼血分,附子配伍水牛角等。
史锁芳教授指出临床上很少有单独一经之病,往往两经或多经并病,另外也不可孤立六经辨证,往往还要和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综合起来应用。
7 验案举隅
朱某某,男,40岁。2014年3月19日诊。
患者因咳嗽伴胸痛10天,发热3天收入院。入院前曾在南京某部队医院诊断为双肺肺炎,予以头孢、阿奇霉素等治疗,病情不退反进,出现全身过敏性皮疹,高烧不退,另有膜性肾病史。刻下:发热40.3℃,恶寒,无汗头重,无头痛,无关节酸痛,咳嗽,咯吐白黏痰,痰中有少量血丝,伴咽痒咽痛,轻微胸痛,口干甚欲饮,口苦,全身乏力,胸闷不显,无恶心呕吐,食欲差,咳甚腹满,夜寐欠安,小便偏黄,大便尚调,双下肢轻度浮肿,全身皮肤散在红疹,舌质暗红、苔薄燥,脉细数。听诊:右肺中下部明显湿性罗音。血常规:WBC:13.60×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95%。从风寒外感,郁而不解,邪传阳明,波及少阳,三阳合病辨证。治宜疏解三阳邪气,解肌清热为主。方以柴葛解肌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化裁。处方:
葛根15g,春柴胡35g,石膏50g(先煎),杏仁10g,生甘草5g,炙甘草5g,连翘10g,赤小豆20g,蝉衣6g,苦参10g,知母10g,黄芩10g,法半夏10g,党参10g,川连3g,厚朴10g,荆芥10g,苏叶10g,薄荷6g(后下)。2剂。水煎服,每日2次。
二诊:服上药1剂即汗出热退,2剂药服完后患者恶寒消失,肺部罗音渐消,腹胀渐消,感胸闷,咳嗽,仍有皮疹,咽喉疼痛,痰中带血,舌质红、苔薄,质偏红。处方:竹叶15g,石膏30g(先煎),党参45g,麦冬10g,生苡仁20g,冬瓜子15g,茅芦根(各)40g,瓜蒌皮10g,蝉衣6g,地肤子15g,荆芥10g,水牛角30g,丹皮10g,仙鹤草20g,平地木15g,野荞麦根25g,赤小豆20g,谷芽10g,六曲10g。3剂。3剂服完,皮疹渐退,咳嗽、胸闷、咯血均除,口渴亦止,汗较多,胃纳正常,舌苔薄干、舌质暗红,脉细。复查胸片:右肺少量斑片影,血象正常,准备出院。
按:患者此次发病,先因风寒外感,郁而不解,致使邪传阳明、波及少阳,三阳合病,予疏解阳经邪气、解肌清热治疗后,继而出现阳明气分余热未清,气阴两伤,邪入营分,迫血妄行,气营同病,予清热肃肺,益气生津,兼佐凉营之品后,患者余邪渐清,正气渐复,疾病向愈。本案例充分说明:患者肺炎高热,血象高,因抗生素过敏出现全身过敏性皮疹,正规部队医院不治而转入我院,不能使用抗生素,单用中药1剂热退,3剂肺部罗音消失,血象正常,疗效出奇。中医药治疗急症并不慢,只要辨证准确,方药得当,肺炎也能运用中药获效,同时中药对抗过敏亦疗效确切。
[1]史锁芳.运用大剂附子治疗难治性哮喘探讨.中华中医药学刊,2011,21(8):1844
编辑:傅如海 吕慰秋
R254.9
A
1672-397X(2014)10-0022-02
王刚(1988-),男,医学硕士,从事呼吸系统疾病临床诊治工作。
周奎龙,dgy1983@aliyun.com
2014-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