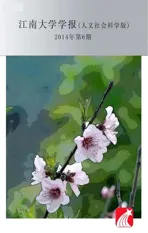从“美刺”到“情理”
——论《文心雕龙·比兴》的思想矛盾与文学史意义
2014-04-15郭庆财
郭庆财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临汾 041004)
从“美刺”到“情理”
——论《文心雕龙·比兴》的思想矛盾与文学史意义
郭庆财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临汾 041004)
“比兴”是我国古代诗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而多歧的范畴。汉代经学家论“比兴”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在郑玄那里,譬喻而兼美刺乃是“比兴”的意义所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一方面受毛、郑的影响,肯定了“兴”负载的“刺过讥失”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更从情理之异、隐显之别来区分“比”、“兴”,从而凸显了“比”、“兴”本身的美学意味。这两种观念的夹杂和歧出,实际反映出毛、郑诗说的深广影响与南朝文学摆脱政教约束而独立的倾向之间的冲突。由此,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强调教化功能的“比兴”说与强调美感意义和艺术效果的“比兴说”乃呈现出双水分流的状态。
比兴;美刺;隐显;情理
“比兴”是贯穿于我国古代诗学批评中的一个十分重要、但又众说纷纭的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人那里,“比兴”所负载的意义也不太一样。大致上,我们可以将历代有关比兴的论述分为两大类:一是用以强调诗歌的社会意义与教化功能,一是用以强调诗歌的美感意义和艺术效果。前者集中体现于经生的诗论中,后者则散见于文人讲论“比兴”的文字中。但是从“比兴”说的发生和演变来看,强调其感发意义和美学特质的文人“比兴”说出现较晚,其早期内涵是与经生家的《诗经》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演变和分野十分模糊,并非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中设有《比兴》篇,便兼摄了文人和经生的诗学观念,昭示了南朝时期诗学思想演进的痕迹。
一
“比兴”这一范畴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795-796这就是被公认为有关“比兴”最早起源的“六诗”说,是着眼于诗歌乐律而说的。至汉代经生的《诗大序》中,乃有“六义”之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2]271《诗大序》是汉代经学诗论的总结,所以尤其引人注意。“六诗”与“六义”的内容完全一致,亦可以互相参照。但是《诗大序》作者仅对风雅颂三者作了解说:“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2]272而对于什么是赋比兴则未言及。那么古人说的赋比兴究竟有何涵义?其给后人留下了种种猜测和评论的空间,致使在整个诗学批评史上的解说纷如聚讼。
聚讼的焦点在于“赋、比、兴”与“风、雅、颂”性质是同是异的问题;进一步讲,在于“赋、比、兴”到底是诗法还是诗体。其中一种重要的看法是赋、比、兴皆为“诗体”说。其代表人物是章太炎。他在《六诗说》一文中追根溯源,根据《周礼·春官·大师》的文字,认为风、赋、比、兴、雅、颂六者皆是诗体,即都是《诗经》早期的形式分类,但赋、比、兴却是不入乐的诗篇,后来孔子删诗时被删去了。[3]390-393郭绍虞在《“六义说”考辨》一文中也以入乐不入乐之分提出了类似的看法。[4]359-365这些说法着眼于六义的发生学,带有一定的推测性;其立足点在于认为《周礼》的“六义”与《诗大序》的“六诗”并不是一回事,两者的内涵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汉儒来看却不是如此,他们倾向于将“六义”做了“诗法”和“诗体”的二分。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然后又引郑司农(即郑众)的解释:“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1]796
无论“取比类以言之”、“取善事以喻劝之”,还是“比方于物”、“托事于物”,无一不是把赋、比、兴归为诗歌的表现手法。实际上这一点在毛传那里已经很明显了,因为毛传往往在诗的首章次句之下标明“兴也”,这显然是对《诗经》的创作技法和手段的归结,而不是什么与风、雅、颂相并列的“诗体”。郑玄的说法也正是这种意思的延伸。到孔颖达为毛诗作《正义》时,则更明确地以体用言六义:“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2]271这便是“三体三用”说,明确指出除了三体诗外没有其他篇卷了。这是对郑玄等汉儒诗学观念顺理成章的归纳。这是我们从汉唐经学家那里所得到的信息。下面我们结合《诗经》中附有毛传、郑笺的几首诗,就能看得更清楚:
《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兴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2]273
《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兴也。……国君尊严,如南山崔崔然。”郑笺:“兴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为淫佚之行,其威仪可耻恶如狐。”[2]352
《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客。兴也。……”郑笺:“兴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来助祭于周之庙,得理之宜也。”[2]594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无论毛传或者是郑笺,我们都可以从“如”、“喻”等用词上看出:“兴”肯定含有譬喻的意思。一向奉行疏不破注的孔颖达在为《关雎》一诗作正义时说:“兴是譬喻之词,意有不尽,故题曰兴。”[2]273另外“兴”又“起”之意,且大多发兴于首章,因此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说:“‘兴也’的‘兴’有两个意思,一是发端,一是譬喻,这两个意思合在一块儿才是‘兴’。”[5]49至少这种认识是符合汉儒对“兴”的理解的。
第二,从被譬喻的内容来看,均未脱离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等内容,阐发的是政教人伦的正统观念。《小序》往往以“美”、“刺”揭出之,即对顺应或违逆人伦的史事表达赞美或批评的态度,其作用在于引导人们理解《诗》的“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2]262的政治效果。所以譬喻而兼美刺,这便是毛、郑等经生所理解的“比兴”的意义所在。
第三,毛公、郑玄在具体解诗时仅言“兴”,而不言“赋”、“比”,即刘勰所说的“独标兴体”。对此,清代学者惠周惕解释说:“毛公传《诗》,独言兴而不言比赋,以兴兼比赋也。人心之思,比触于物而后兴,即所兴为比而赋之,故言兴而比赋在其中。”[6]卷上大概正是着眼于“比”和“兴”在譬喻上的共通性,毛传乃以“兴”统而称之。
但是郑玄与毛公又不同,他已经有意识地对“比”、“兴”做出区分。“赋”是铺陈直叙的写法,对这一点学者没有太多分歧;而“比”、“兴”都含有譬喻意,要区分清楚就比较麻烦。郑玄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将“比”、“兴”分别与“美”、“刺”相联系,“比”含讽刺而“兴”寄褒美。之所以如此理解“比”“兴”,据孔颖达的分析,因为“比”必托于事物,而不直言,似有所畏,故宜于讽喻;至于“兴”,由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来看,乃是认为诗能感发人之情志,使人心向善,故多美意善言。[2]271但郑玄的这一区分标准在其笺注中并未得到完全贯彻,即他视为“兴”诗者,其所表述的人伦政事并非均值得赞美,比如上面举的《齐风·南山》一例,本来是对齐襄公淫乎其妹的贬抑和讽刺,郑玄仍以“兴”标出之,与他前面的说法不相符合。之所以如此,既是由于郑玄对“比”“兴”的区分,是以政治功能来讲诗法,未免太过机械,孔颖达便认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2]271;另外亦是由于笺注体所限,毛传的“独标兴体”在前,使郑玄只得尽量迁就,而不得自畅其说,四库馆臣就指出,虽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然则康成(郑玄)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7]120
故综上可以看出,“比”、“兴”被汉代经师们赋予了浓重的政治寄托和道德寓意。其中,郑玄认为“比”、“兴”是诗人对政教得失的不同反映方式,以启发和匡正君主之心为目的,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虽然如此,但在毛公、郑玄那里,“比”、“兴”毕竟都被视为诗歌表现手法,无论是郑玄说的“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还是“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都指出:既然诗歌要上达君主耳目,故表意应当委婉含蓄、中正平和。郑玄所说的“比方”和“寄托”,更是撇开了政治含蕴,突出了借物以寄意言志的手法,从而在比兴的政治功能背后隐含了某些审美形式的因素。
二
刘勰《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当时经学虽衰,但仍不绝如缕,其中治《诗经》的学者大多尊奉毛、郑。《北史·儒林传序》中提到南朝经学风气时说:“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诗》则并主于毛公。”[8]2709据《隋书·经籍志》,《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授者,唯《毛诗》一家独盛,从《隋志》中《诗经》部分的著录中亦明显看出毛、郑之学的流行和影响。刘勰学识博大淹通,对毛、郑的笺注不可能没有深研。《文心雕龙·序志》篇说:“敷赞圣旨,莫若治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9]726这里将马融、郑玄的注经事业提高到彪炳千古的崇高地位,并申明了通经致用的思想。这与刘勰征圣、宗经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其中都明显带有汉代经学观念的印记。
具体到“比兴”一义,刘勰《文心雕龙》设有《比兴》篇,其中便可以看出毛、郑以“兴”比附政教伦常的思想的影响。首先他认为“兴”是“托喻”,藉物以喻意,又“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9]601藉王雎的“挚而有别”以“兴”后妃之德,藉尸鸠因鹊巢而居有之,以“兴”国君夫人来嫁之后其德均一,乃是毛公、郑玄的说法,是汉儒解诗时发挥微言大义的路子。对此刘勰是接受的。讲到汉赋的兴盛时刘勰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在他来,“兴”确是最能体现讽刺之道的,“讽刺道丧”和“兴义消亡”之间互为因果:若“论功颂德”、“刺过讥失”的讽刺之道不存,那主文而谲谏的“兴”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比兴》篇中还提到楚辞“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的特点。“比兴”的产生乃源于人们对《诗》的理解,以“比兴”论楚辞则往往扞格难通。刘勰之所以如此,乃是本于东汉经师王逸论楚辞的宗旨。王逸《离骚章句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丑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0]2-3王逸认为在讽谏美刺、以物托事,从而有益于人伦教化这一点上,《离骚》的“讽兼比兴”与《诗经》并无大异。对此刘勰亦予认可。这可以说是刘勰受两汉经师通经致用思想影响的又一例证。
但是《比兴》篇并非简单地继承了汉代经学家“比兴”说的政教导向,而且另外的角度对“比”和“兴”做了更细致的区分。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和毛传、郑笺的独标兴体不同,刘勰往往将“比”“兴”两者平行论述,论述篇幅大体上相当。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从情、理之别来区分“比”“兴”,以为: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其中,“兴者,起也”,诗人触物起情,形成意象,而后发为兴诗,显示了“兴”的寄托无端、随兴感发的特点。“比”就不同了:“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乃是诗人先有了某种思致,再选择合适的事物来加以比附,藉草木鸟兽以见意。前者是情以物迁,“随物婉转”,着眼于情感的发动;后者则是以物比理,以心之思理为主。就像王季思先生分析的那样:“比、兴在创作程序上实有先后之不同,如《关雎》一诗,是诗人先有感于雎鸠之合鸣,因而起了求淑女以配君子的意象,这便是兴。如《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是诗人先有了不可转和不可卷的意象,才拿石和席来反比的。”[11]29-30刘勰由情、理角度对“比”、“兴”的区分,注意到了创作中的心理因素,区分了心物交融中或偏于情、或偏于理的不同倾向,将文学艺术中心、物、言三者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拓深。
其次,既然“兴”源自感情的偶然触发和情绪萌动,“比”源自于思理的安排,相较之下理显而情隐,据此,刘勰明确地指出“比显而兴隐”,“兴之托喻,婉而成章……明而未融”,“比”是“切类以指事”,“兴”是“依微以拟议”。即,“比”应该是以切合所写事理的类似事物为比喻;“兴”是因微小之物触发情思,托以取义。他在文中举的几个例子,可藉以体会“比”“兴”的隐显之别:
比例:“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卫风·淇澳》)
“颙颙昂昂,如圭如璋。”(《大雅·卷阿》)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曹风·蜉蝣》)
“执辔如组,两骖如舞。”(《郑风·大叔于田》)
兴例: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召南·鹊巢》)
(按:《鹊巢》毛传:“兴也。……鸤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郑笺:“兴者,鸤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一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
比较刘勰所举的“比”和“兴”的例子,凡“比”的几例中均有“如”字,如同我们常说的“明喻”:构成譬喻的两种事物分明并举,有某些相似点,且以譬喻语词绾合两者。而上举的“兴”例则不然:要理解其意义,必须借助于传笺才行,否则我们根本不会从鸠占鹊巢这件事联想到国君夫人的美德,所以其特点是“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这颇有似于黑格尔所讲的“隐喻”:“隐喻是一种完全缩写的显喻,它还没有使意象和意义互相对立起来,只托出意象,意象本身的意义却被勾销掉了,而实际所指的意义却通过意象所出现的上下文关联中使人直接明确地认识出,尽管它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12]127因为“兴”是触物而兴感,甚至只写即目所见,并不指实,有时甚至隐去了正文,其主旨更难以参透而模糊难定。刘勰从隐显之别来区分“比”、“兴”,同郑玄以“美”、“刺”区分“比”、“兴”已大异其趣了,“比”“兴”本身的美学意味得以凸显出来。刘勰尤其表现出对富于隐约之美的“兴”的偏爱,声称:汉代辞赋“日用乎比,月忘乎兴”,是“习小而忘大”,使得汉赋质直而缺少余蕴,这也是汉人不及周人的地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兴体诗词微旨远,往往不落言筌,只能意会”,含有象征性,而“‘比’则不像有象征性的诗那样暧昧难寻。”*郑郁卿《诗集传之赋比兴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76年版,第142页。刘勰对“兴”的曲譬色彩的揭出,启发了古典诗歌中含蓄风格的营造,以达成一种含蕴不尽、意在言外的美感。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刘勰的“比兴”论是新旧观念夹缠在一起的。一方面他认为“比兴”离不开政教讽喻,难免落入经生论诗的套子里,比如《比兴》篇一开始就指出“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寄讽”,把“比兴”的情感倾向和讽谏内容联在一起,从诗的政教功用来言“比兴”,这不过是对毛、郑“比兴”说的变相复述而已。另一方面他以隐显、以情理、以感发性质之不同来区分“比”、“兴”,关注了“比兴”的形式因素,使之具有了一定的美学色彩。他尊奉汉儒的“比兴”说,其原因除了“原始以表末”、追流溯源的文学史观涵有的崇古观念外,更源自于经学文化不自觉的影响;而刘勰的“比兴”新义,则本于在时代精神触发下形成的审美理想。政教讽喻与诗歌审美两者似乎矛盾,但又一直是“比兴”说的一体两义:因为郑玄以“美”、“刺”讲“比”、“兴”的同时,已开始从“诗法”角度关注“比”、“兴”婉曲蕴藉的特点;刘勰除了论“比”“兴”的讽刺意义外,更以情理、以隐显区分两者,使得“比”、“兴”的情感因素、艺术特质进一步揭示出来,使得“比兴”这一经学命题渐趋文人化。所以,从二郑到刘勰“比兴”义的演变,不过是《诗》学的政教色彩逐渐淡退后的自然结果。
三
《文心雕龙·比兴》篇中两种观念的夹杂和歧出,从大的文学背景看,实际反映了毛郑诗说的深广影响与南朝文学摆脱政教约束而独立的倾向之间的冲突。
东汉末年以来,处士横议,士与大一统政权渐渐疏离,经学独尊于世的地位就开始动摇,经过魏晋玄风的冲击,经学之势愈趋衰弱,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谓:“案南朝以文学自矜,而不重经术;宋齐及陈,皆无足观。唯梁武帝起自诸生,知崇经术……而晚惑释氏,寻遘乱亡,故南学仍未大昌。”[13] 125经学虽在梁武帝期间亦有重振,但其思想控制力远远难与两汉相比;简约任达的玄学到了南朝与东晋相比虽有弱化,但是余风仍炽。*参见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第一章第五节《南朝玄学与经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经学的思想约束减弱,重感情、重个性、高自标置的社会风气既开,便为人们感情世界的觉醒、对文学特质的关注准备了适宜的条件。从魏晋时期起,许多诗人的创作主旨已不再拘泥于“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而逐渐转向“缘情绮靡”的唯美追求;南朝以来,摇荡性情、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作品更受到了文人的崇尚和青睐。刘勰生活于经学重振的梁武帝时期,受其影响,《文心雕龙》中乃以“征圣宗经”、“依经树则”为基本框架;同时它更反映了当时众多士人的文学好尚和风气。如《声律》、《章句》、《丽辞》、《夸饰》、《练字》等篇对用词造句、文章词采的细致探究,《情采》篇对于情感与文采的同时强调,对“为情而造文”的吁求,无不触及了文学精神的最本质处。罗宗强先生谈到刘勰思想的矛盾性时以为:“他是看到任自然的文学思想发展潮流了,他是那样地重感情、重才性、重自我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但是他又是那样的崇拜圣人,特别是儒家的圣人周公孔子。……他处处想把这二者统一在一起,并且以此来建构他的体系。”[14]282那么,这种心态不仅体现在“文之枢纽”中以“自然之道”与“圣人之道”相接榫的驳杂,也体现在《比兴》篇中同时以经生和文学家的眼光看待“比兴”这一传统命题,这难免也会造成“比兴”阐释的不够圆通——“讽喻”、“起情”、“婉而成章”等几方面的描述毕竟很难统一于“兴”中。
刘勰文人化的“比兴”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南朝诗学领域,在六义的框架中阐发吟咏性情的诗歌思想逐渐成为风气。早于刘勰,齐梁之际的文学领袖沈约便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指出:“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15]1778虽然用的仍是“六义”、“四始”的旧范畴,发挥的却是抒情寄兴的新道理了。与刘勰大约同时的钟嵘作《诗品》,其显著特色是“深从六义溯流别”[16]559,将五言诗的源头追溯至《国风》、《小雅》、《楚辞》,但值得注意的是,《诗品序》从儒家经典话语中发掘出了深刻的诗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7]2揭出“比兴”的兴发感动之价值,不仅同郑玄的说法殊异其趣,即使同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相比,也不再是以经生之说遮遮掩掩,而是以文士的眼光来论述“比兴”了。即以探究对象来说,前人谈论“比兴”,探讨的是儒学经典《诗经》,而钟嵘《诗品》所“品”的是“众作中之有滋味”的文人五言诗,且认为诗歌不过是用以抒发一己之情怀罢了:“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他因此能够摆脱经生的论调,而赋予“比兴”以独立的地位和抒情价值。我们看后代文人论诗,凡是强调诗歌自身的美学特质,强调诗歌中惝恍邃远、超乎言意之表的美感时,往往使用“兴”一类的词去描述。无论是唐代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里的“兴象”说,还是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所讲的“兴趣”,均是对诗歌内在的美感效果的把握和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比兴”思想的两种传统绝非截然兴替之关系,更无所谓后来居上。实际上,在钟嵘当代和稍后,以政治讽喻寄托说“比兴”的经生言论依然兴盛,使这两种传统长期处于双水分流的状态。齐梁之际的许懋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撰《风雅比兴义》十五卷盛行于时。[18]1486-1487此外,简文帝萧纲曾在与弟弟萧绎的书信中批评文风浮滥:“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疎,争事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19]690萧纲提出的“比兴”,乃是藉经生的“比兴”旧说阐发“诗教”义,针对流荡不返的文学风气加以反拨。由此看来,以政教为本的“比兴”观念作为诗学传统,仍然是许多文人论诗的先在视阈和立论根本。
这两种比兴传统沿至唐代亦然。比如,唐初刘知几《史通·叙事》中说:“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20]178这可以说是经生家论调的延续;而略晚一些的中唐诗僧皎然和尚亦曾谈比论兴,其《诗式·用事》:“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21] 31乃是以“比兴”讲诗歌物象,析求诗艺,明显是文人说“比兴”的风貌。因此综合刘勰以后的诗学研究来看,对“比兴”的解说和评论已呈现为两条路子并行,一种是儒家学者论“比兴”的经学眼光;一种是文学家强调“比兴”对情感的感发意义和美学效果,前者所论述对象主要是《诗经》,而后者则是泛论古今诗歌了。而在经学家诗经研究的内部,又有持守毛、郑之说的一路(如南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摒弃毛、郑,径从赋、比、兴入手探求《诗经》本义(如朱熹《诗集传》)的两条路子。当然,经学家的思路和文学家眼光并非截然对立,即如朱熹对于赋、比、兴的严格解读,摒弃了经学家的成见,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解释学体系,就有集大成的色彩。对此时贤研究甚多,本文不拟赘论。*参见张万民《从朱熹论“比”重新考察其赋比兴体系》,《复旦学报》2014年第1期。
通过对“比兴”范畴沿波讨源、因枝振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比兴”研究史上,经生论“比兴”与文人论“比兴”的分歧,是探究“比兴”思想的一大关捩,而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实肇其端倪,对我们具有重大启发。
[1]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章太炎.六诗说[M]//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 郭绍虞.“六义说”考辨[M]//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 朱自清.诗言志辨[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6] 惠周惕.诗说[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 李延寿.北史:卷81[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刘勰撰,范文澜校注.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0]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王季思.说比兴[G]//王季思全集:第四卷.古典文学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12] 黑格尔.美学: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3] 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5] 沈约.宋书:卷67[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 钟嵘撰,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8] 李延寿.南史:卷60[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 姚思廉.梁书:卷49[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0] 刘知几撰,浦起龙注.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1] 皎然撰,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程晓芝)
From “Praise or Irony” to “Emotional or Reasonable”——On the Thinking Contradiction and Literary History Value ofWenxindiaolongBixing
GUO Qing-c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Bixing is an impotent and divergent concept in Chinese ancient poetic criticism. Scribes in the Han Dynasty showed a strong political utilitarian when discussing “Bixing”. Zheng Xuan’s description of “Bixing” contains both metaphor and “praise or irony”. Effected by Mao Gong and Zheng Xuan, Liu Xie’s Wen Xin Diao Long Bi Xing confirms the signification of satirizing political fault on the one hand, and distinguishes “Bi” and “Xing” in the standard of emotional or reasonable, obvious or implicit on the other hand, thus highlights the aesthetic interest of “Bi xing”. The hybridity and divergence of the two concepts, reflect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fluence of Mao, Zheng and the independent tendency when breaking away from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From then on, the theory of Bixing emphasizing on indoctrination and stressing on aesthetic value artistic effect showed the situation of running parallel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Bixing; Praise or Irony; Obvious or Implicit ; Emotional or Reasonable
2014-04-28
郭庆财(1978-),男,山东无棣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和唐宋文学研究。
I206.2
A
1671-6973(2014)06-01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