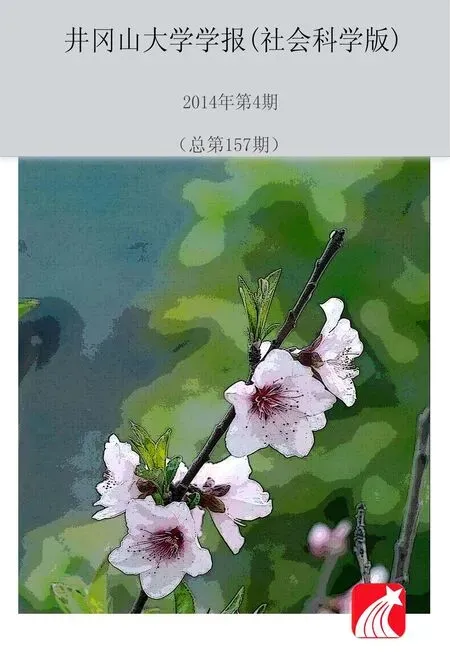论陇东红色歌谣的文化学阐释
2014-04-14张文诺
张文诺
(商洛学院中文系,陕西商洛 726000)
论陇东红色歌谣的文化学阐释
张文诺
(商洛学院中文系,陕西商洛 726000)
陇东红色歌谣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传唱,不仅因为陇东红色歌谣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愿望,而且因为陇东红色歌谣接通了劳动人民潜藏的集体无意识,激起了他们的情感共鸣。陇东红色歌谣在进行革命主题诉求的同时,也保存了特定的方言土语、民俗风情、民族宗教等文化学资料,具有丰富的文化学价值。正是在文化学的意义上,才能解释陇东红色歌谣的魅力,否则,可能得到一种一般化、简单化、肤浅化的结论。
陇东红色歌谣;阐释;文化学;集体无意识
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提高农民的革命思想觉悟、教育农民参加革命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视。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农民方面的确做得非常成功,这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共产党的善于宣传是它的敌人都不得不佩服的,而其高明之处既在于善于掌握群众的心理,也在于善于利用农村各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1](P198)民间文艺因为和农民的天然联系而受到中国共产党与延安文艺界的重视。在20世纪四十年代的革命根据地,民间文艺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从边缘文艺形式逐渐变为主流文艺形式。民间文艺在对农民的思想塑造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功效。恩格斯指出:“民间故事书还具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2](P401)民间歌谣同民间故事一样,因为最能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需求而具有建构劳动人民记忆、培养他们道德情感的作用。红色歌谣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或者解放区产生的反映劳动人民革命斗争历程的民间歌谣。红色歌谣把革命主题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形成革命意识、革命文化与民间意识、民间文化的成功对接,完成了对农民世界观的革命性改造,实现了革命意识的民间表达。陇东红色歌谣指的是产生于陇东这块土地上的革命歌谣。陇东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革命歌谣,拥有大量受众。陇东红色歌谣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传唱,不仅因为陇东红色歌谣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愿望,而且因为陇东红色歌谣接通了劳动人民潜藏的集体无意识,激起了他们的情感共鸣。陇东红色歌谣在进行革命主题诉求的同时,也保存了特定地域的方言土语、民俗风情、民族宗教等文化学资料,具有丰富的文化学价值。
“文化”一词几乎无边无际,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首先提出“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了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3](P1)美国学者怀特认为:“在心理学及大部分社会学之外,存在着另外一类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传统的风尚习俗、典章制度、工具、哲学、语言等等,这些我们统称为文化。”[4](P69)泰勒与怀特的文化的概念虽然很宽泛,但都倾向于把人类的精神产品看作文化。不过,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应该包括物质制品、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阿兰·布洛克与奥利弗·斯特伯拉斯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群的‘社会继承’,包括整个物质的人工制品(工具,武器,房屋,工作,仪式,政府办公以及再生产的场所,艺术品等),也包括各种精神产品(符号,思想,信仰,审美知觉,价值等各种系统),还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生活条件下以及代代相传的不断发展的各种活动中所创造的特殊行为方式(制度,集团,仪式和社会组织方式)。”[5](P150)这个定义相当宽泛,把人类所有的实践及其产品都置于文化里面,有泛文化主义的倾向。现在的文化定义倾向于更明确地区分现实的行为和构成行为原因的抽象的价值、信念以及世界观。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文化由抽象的价值、信念和世界观构成。价值、信念和世界观是人们行为的理由而且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之中。社会成员共享这些东西,当人们遵照它们行动时,它们形成其他社会成员可理解的行为。”[6](P35)笔者认为,文化首先指人类的精神产品。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文化行为,都是通过社会习得的,都具有文化意味。任何一种简单平常的行为都有可能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密码,其深层藏有丰富的文化意义。比如说陇东方言中,对事物的称谓中叠音特别多,如娃娃、袋袋、绳绳、线线、红豆角角、山丹丹、灯花花等,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言说习惯吗?为什么山东、河南、江苏、北京就不这样说?陇东地处偏远内陆,物产不丰富,他们对一切事物都很珍惜,看得很重,这种叠音称谓折射了当地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喜爱。陇东红色歌谣保存了很多文化学资料,对其进行文化学阐释,并不是阐释其保存了哪方面或者哪些文化学资料,而是重点分析其保存的文化学资料所揭示的人们的思想信仰、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探寻其民族、语言的深层密码,进而揭示陇东红色歌谣广泛流行的深层原因。
二
从歌谣发生学上看,歌谣的产生同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所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可见,歌谣是心之忧时的产物,是劳动者的心灵被触动时的产物。何其芳认为:“民歌,特别是抒情的民歌,这种形式最容易为不脱离生产的人们所掌握,并且常常是他们不吐不快的时候的产物,就自然而然很多是真挚动人地书写劳动者的胸臆的作品了”[7](P4)方言土语与特定地域的气候、地形、特殊习惯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关,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大小不一的语言共同体,不同地域之间的语言有非常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方言都有自己的特征,因而方言具有很强的“乡土根性”,“‘乡土根性’使一个很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它自己的传统。这些习惯是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顽强。”[8](P287)方言与文学的关系很密切,因为最早的文学就产生于方言。“语言和方言的差别在哪里,这很难说。人们往往把方言称为语言,因为它曾产生文学。”[8](P284)由于歌谣是特定地域的劳动人民在表达自己最诚挚的需求,所以方言土语成为歌谣的首要载体。陇东红色歌谣就保存了很多带有地域特征的方言土语。
陇东红色歌谣与陇东的方言土语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陇东当地的方言发音使陇东红色歌谣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格。陇东当地劳动人民在抒发自己情感的过程中,不自觉地采用了为当地老百姓所熟悉的共同语,从而使陇东红色歌谣打上了特有的陇东方言的印记,这集中体现在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陇东红色歌谣多用衬字,尤其是以“来”字最有特色,并且用法也非常灵活。有的“来”在句中为语气词,如“刘志丹来是清官”,“刘志丹来本事大”,“刘志丹来好主张”,“刘志丹来真勇敢”,“毛泽东来真威风”,“毛泽东来真英明”,“二月里来刮春风”,“三月里来三月三”,“东面山来西面山”等;有的“来”字在句中是动词,但也能起到调整音节的作用,如“共产党来了跟上走”,“工农红军来革命”,“沟里出来些游击队”,“红军来了盼晴天”,“红军来了革命大发展”等句中的“来”都是动词,也能起到衬字的作用。其它如“哟”、“呀”“嗨”等也用得较多,在句中起舒缓音节、调整节奏的作用,声调可以更为悠长,唱起来更加押韵、上口。
最能显示陇东红色歌谣地域风格的是陇东红色歌谣中的方言词汇。有的词汇因为指涉的是陇东特有的事物或者是陇东本地特有的称谓,读来颇觉晦涩难懂,如“裤腿缏在大腿弯,走路实好看”中的“缏”字,读作“piān”,意思是挽起或卷起,像这样偏僻的词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方言词汇反映了具有陇东地方特色的事物、习俗,如“赶快压饸饹”中的“饸饹”,就是陇东地区特有的一种面食,用饸饹床子把和好的小麦面、荞麦面、高粱面等轧成的长条,煮着吃,面条柔韧劲道,再加以萝卜、葱、豆腐、肉末、红油做成的臊子,味道鲜美,是当地人们最爱吃的食物之一。《绣荷包》中的荷包指的是庆阳香包。香包,古名香囊,又叫荷包。庆阳民间有绣香包的悠久历史,香包上一般绣着寿星、人物、金鱼、青蛙、老虎、狮子、螃蟹、龙凤、荷花等吉祥的事物图案。这些图案浸溶着古代哲学的神秘色彩,隐含着人类童年时期的多神崇拜和原始图腾的历史记忆,是远古的文化遗存,是生命、活力的载体。香包还是古代陇东青年男女定情的信物,一般是女青年把自己绣的香包送给自己的情人,表达自己情有所依,寄托了陇东劳动人民的美好情感。“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的山丹丹花是带有陇东地域特色的一种花朵,开起来特别鲜艳。陇东方言中叠音词特别多,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名词,如“梁梁”、“山尖尖”、“娃娃”、“红豆豆角角”、“红布条条”、“红绳绳”、“线线”、“灯花花”;一类是形容词,如“红艳艳”、“热腾腾”、“乱哄哄”、“滚滚”、“喜洋洋”、“闷沉沉”、“金灿灿”;一类是量词,如“一面面”、“一道道”、“一把把”。方言土语折射了某地域的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表现出一种集体的意识。叠音名词表达了陇东人民对其所指涉的事物的喜爱、珍惜;叠音形容词则言其状态的饱满、明艳、丰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句形象地写出革命的大好形势,像烂漫的山花一样红红火火;叠音量词则形容事物之多,“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写出了陇东山脉纵横、山河相间的地理形势,极为准确。叠字的运用对表达情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增强了摹景状物的艺术效果和音乐节奏的和谐。陇东地区地处甘陕宁三省交界之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交错,交通阻隔,形成了相对封闭完整的语言生态,这里的方言较少受到外来影响,能够保留较多的语言原貌。陇东红色歌谣保存的大量的陇东方言土语成为研究陇东方言的活化石,对于陇东方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技术方面看,所有的方言都是语言——在语言方面,没有什么分语言或次语言这种东西——而且两种不同方言成为不同语言的关键点,大致在于说一种方言的人几乎不能与说其他方言的人交流这一点。分界线可能在心理、地理、社会或经济的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往往不是很清楚。”[6](P117)方言土语的运用的确可能引起其他方言区的读者的费解,但是方言土语往往折射该方言区的人们的思想、心理、思维以及一些原始生命信息等。“语言学家已经发现,虽然语言一般来说是可变的和可以适应的,但是已经确立的术语确实倾向于使其自身永存下去,它们反映并展现社会结构、共同观念和群体及人民关心的事情。”[6](P116)“用方言方音来歌吟地方事,是革命歌谣的一大特色,同时也因为借鉴了山歌方言俗语的特点,使之更能被群众所接受,从而起到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的作用。”[9](P126)陇东红色歌谣大量采用陇东方言土语,不仅真实地反映了陇东地区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心理状况,而且也拉近了歌谣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心灵距离,消解了接受者心中的陌生感,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与接受,实现了文学与普通大众的沟通与交流,把文学的民间化、大众化落在实处。
三
民间歌谣与民俗风情是相互渗透的,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是民间歌谣反映的重要内容,陇东红色歌谣同样也反映了陇东特有的民俗风情。“民俗”一词作为专门术语,来自于英文单词“Folklore”。民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10](P2)如果陇东红色歌谣不以民俗风情为载体,那么它根本不能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处,进而发挥其教化作用。陇东红色歌谣广泛地反映了陇东地区的农业生产、饮食、服饰、节日、婚姻、信仰、舞蹈、小戏等方面的民俗风情,展现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陇东民俗画面,从中可以窥探陇东地区的社会状况以及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
陇东红色歌谣如《刘志丹》(打宁夏调)、《咱们的红军到南梁》(信天游)、《后山里下来些游击队》(信天游)等反映了陇东地区的农业生产习俗,从这些歌谣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陇东劳动人民以旱作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冬小麦,间种糜子、谷子、豆角、冬瓜、荞麦;男子种田,女子纺线织布;饲养的牲畜有牛、猪、羊。从《刘志丹领导咱闹翻身》(信天游)、《拥护刘志丹》(走西口调)、《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劝夫当兵》、《拥军小唱》等我们可以知道陇东劳动人民吃的食物有饸饹面、油糕、大白馍、豆腐粉条、米汤,尊贵的客人来了吃大白馍、吃牛羊肉,喝米酒。如“千家万户哎咳哎咳哟,把门儿开哎咳哎咳哟,快把亲人迎进来,咿儿呀儿来吧哟。热腾腾油糕哎咳哎咳哟,摆上桌哎咳哎咳哟,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既通过招待亲人的场面表现了军民鱼水之情,又透露出陇东人们的饮食习俗。其中“大白馍”在陇东红色歌谣中多次出现,如“请吃猪羊肉,请吃热馍馍”,“鸡猪牛羊肉,还有大白馍,吃起来真香”等,大白馍象征了陇东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对革命战士的深情厚谊。陇东地区干旱少雨,小麦产量不高,再加上苛捐杂税的盘剥,一年吃不上几顿大白馍,所以他们盼望每天能吃上大白馍。《三十里铺》等歌谣反映了陇东地区的服饰习俗,女子一般穿红挂绿,男子一般穿青,如“青袄青裤青围巾,头戴白羊肚手巾”。在节日期间,陇东人民挂花灯、扭秧歌、闹社火。如《劳军歌》唱道:“正月里来是新年,家家户户真喜欢。正逢上劳军运动月,秧歌旱船闹得欢。”“正月里来正月正,曲子社火闹得凶。群众热心一起办,为了拥政和拥军。”社火是祭神时为神表演的舞蹈,“社”为土地之神,“火”能驱邪避难。祭祀社神,施放烟火,是民间盼丰收、庆太平、祈平安的宗教仪式。耍社火的人穿红挂绿,装扮成历史上各类英雄人物。表演时,敲锣打鼓,唢呐伴奏,燃放烟火,凸显热闹,讲究红火。庆阳社火的主要形式有跑旱船、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跑纸马、马故事、霸王鞭、地故事、秧歌、打腰鼓等。社火表演时,男女老少满怀喜悦,随着社火队伍,走遍街头村庄,挨家挨户给人们送去新年的祝福。社火活动一般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开始排练,正月表演,直到正月十五方才结束,这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热闹的时间。《妇女放脚歌》、《封建制度是祸根》、《识字歌》、《边区的姑娘人人爱》、《建设边区运动歌》、《放脚歌》等揭示了一些鄙风陋俗给陇东妇女带来的沉重灾难。“活肉缠成个死肉疔”、“疼得人几难动弹”、“咯喀拧拧摇摇摆”是陇东妇女对“缠脚”这一陋俗的血泪控诉。在旧社会,妇女必须缠脚,正是这一习俗把妇女的活动范围压缩在很狭小的世界之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在根据地内大力推行放脚运动,把女性解放落在实处,陇东红色歌谣形象地反映了放脚运动这一新习俗给女性生活带来的勃勃活力。
陇东红色歌谣通过对陇东民俗风情的书写,真实地反映了陇东人民的生活、思想、情感、心理、思维。陇东红色歌谣把民俗风情作为革命思想的载体,对当地人民的情感宣泄、精神补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11](P2)我们看到,正是因为工农革命的胜利,古老的民俗风情更为红火、热闹,没有革命的胜利,古老的民俗风情也慢慢失去了活力。陇东红色歌谣把民俗风情与革命巧妙地结合起来,人们在享受热闹的红火的民俗风情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会体悟到工农革命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民俗风情在塑造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精神与行为,渗透着革命意识的民俗风情也在慢慢塑造着接受者的革命思想。
四
陇东红色歌谣主要以歌颂革命、歌颂政党、歌颂革命领袖为主题诉求,充分发挥了宣传教育功能,不可避免地对展示男女自然生命力的情爱歌谣、娱神歌谣的遮蔽。然而在陇东红色歌谣中,歌唱农村青年男女爱情的红色歌谣为数并不少,只不过是陇东红色歌谣中的爱情歌谣与传统的爱情歌谣有着不同的特质,歌唱爱情的歌谣与歌颂革命领袖的歌谣形成了陇东红色歌谣中最有特色、艺术成就最高的两个部分。
陇东红色歌谣中歌唱农村青年男女爱情的有《送郎当红军》、《送上荷包表表心》、《跟上哥哥走南梁》、《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红军哥哥要出征》、《当兵要当八路军》、《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粮》、《送郎歌》、《送夫参军》等,这些情歌的情节是写农村青年女子激励、欢送自己的情人或者丈夫参军,这些情歌把男女情爱与革命事业联系起来,表达了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美丽爱情的主题,讴歌了农村青年男女重儿女之情更重报国之情的高尚品德。红色情歌之所以被广大群众喜爱,不仅是因为它们艺术成就高,而是因为这些情歌唤醒了人们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我把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12](P39)荣格这句颇有点神秘的说法的确揭示了人类心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意识,它是与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与所爱的人离合是每个人心中都曾经经历过的情感,这是一种既痛苦又美丽的情感,也是一种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从中国文学史上看,人们很早就抒发了这种刻骨铭心的“怨别离苦”。《诗经》中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丈夫离开了,自己不愿意打扮自己了,多么真实的一种情感。《汉乐府民歌》唱道:“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丈夫出门远行,对丈夫的想念以致自己茶饭不思,令人为之动容。《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一个“生”字写出了女主人公的思念之痛;“脉脉不得语”表现了有情人不能相见的惆怅。杜甫在流亡途中盼望与妻子“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对自己妻子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把男女思念之情写得多么温馨与幸福。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道离别之境让人肝肠寸断;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则写出了爱情的热辣。男女离别之情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感原型,超越了具体的个人与时代的审美情感,能引起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共鸣。“之所以是‘共鸣’或者‘回响’,就在于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灵碰撞,不是一种精神因素所致。它来自无数前人的无意识的原型‘声音’,又渗进了现时的社会文化因素,个人后天的文化无意识因素。”[13](P192-193)这些情歌的情感抒写,接通了人们心中潜在的情感结构,因而能引起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心灵颤动。如《三十里铺》(探家调)就是一首优秀的抒写男女情感的作品。这首歌唱道:
三十里铺靠马路,拆了马路修公路,三哥哥今年整十九,嗬儿嗨哟,粉英今年一十六。前沟里下雨后沟里晴,毛主席命令来征兵,三哥哥要当八路军,嗬儿嗨哟,粉英心里格咛咛。推荞麦,旋荞皮,粉英要穿个织贡呢,一身贡呢八万几,嗬儿嗨哟,三哥哥没钱扯不起。红日头,天上挂,你叫三哥哥说实话,只要革命成了功,嗬儿嗨哟,你要穿啥就穿啥。要穿红,一身红,红袄红裤红头绳,红鞋头上红缨缨,嗬儿嗨哟,你看粉英能不能。要穿绿,一身绿,绿袄绿裤绿鞋袜,绿衫子外套绿夹夹,嗬儿嗨哟,谁不把咱粉英夸。要穿青,一身青,青袄青裤青裹身,脖子里围上青围巾,嗬儿嗨哟,你看三哥亲不亲。煤油灯,不招风,白生生豆芽一条心,只要咱俩个不变心,嗬儿嗨哟,三年五年都能行。芦花子鸡,跳上墙,我送三哥上前方,上了前方莫想家,嗬儿嗨哟,早日得胜转回乡。
这是流传于陇东镇原县的一首歌谣,可分三层。第一层写二人的纯真情感,一句“嗬儿嗨哟,粉英心里格咛咛”写出了征兵命令在粉英心理上激起的情感涟漪、心里矛盾,表达粉英对情郎的依恋与挂念。这首歌谣并没有回避青年男女的情感,把情感写得细腻、委婉。接着通过二人对革命胜利的憧憬,把儿女之情转化为报国之情,把这种情感变化渲染得极其细腻入微而又真实自然。最后写粉英对情郎的激励、安慰与嘱托,一句“上了前方莫想家,嗬儿嗨哟,早日得胜转回乡”写出根据地农村青年女子识大体、顾大局的美好心灵以及为情郎参加革命军队的骄傲与自豪,既缠绵难舍又乐观豪放。这首歌谣把男女私事、革命大事与家庭琐事结合在一起,把送郎参军融于男女送别之中。在根据地,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男女为了保护革命政权、为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告别自己的未婚妻或者妻儿,走上前线,他们同样感到了这种“怨别离苦”。《三十里铺》等抒发男女之情的情歌激活了遗留在他们心中的离别之情,在不同时代的人们中间都能引起情感共鸣。
英雄情结也是人们心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14](P189)在社会不稳定的时期,普通人的英雄情结更为普遍与强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整个中国处于战乱之中,长期的战乱让普通民众热切盼望有一个英雄人物能救万民于水火,能救万民出苦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在根据地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分了田,分了粮食,根据地民众过上了和平安定的新生活,他们便由衷地歌颂革命领袖刘志丹、毛泽东。歌颂革命领袖的歌谣有《南梁来了刘志丹》、《刘志丹》、《刘志丹领导闹翻身》、《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歌颂领袖毛泽东》、《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高楼万丈从地起》、《十绣金匾》、《人民救星人民爱》、《太阳出来照地红》等。如孙万福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唱道: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五谷万物生,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断了穷根翻了身。为咱们能过好光景,发动了生产大运动,人人努力来生产,丰衣足食吃饱饭。边区人民要一心,古树开花耀眼红,千年古树盘了根,开花结籽靠山稳。
这是一首在陇东地区乃至全国都广为传唱的陇东革命歌谣,这首歌谣通过挖断穷根、穷人翻身、发动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等几个典型事例表现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比兴手法的运用使情感表达更为强烈而真挚,同时也使形象更真实、更生动。两句之间的内容与情感变得浑然一体,产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如:“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前三句既是兴又是比,没有前三句的比兴,很难想象咱们领袖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这些歌谣在当时被根据地群众广为传唱,激起了根据地民众心中的英雄情结。“崇拜英雄、崇尚英雄主义或许是人类的固有本性之一,因此英雄豪杰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之高是无与伦比的。”[15](P1)当时的根据地面临着内忧外患,普通群众期待着救星能一夜之间使自己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期待着高楼万丈平地起。“‘救星情结’就是‘英雄崇拜’情结,作为一种无意识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灵结构之中,而这种‘英雄崇拜’的‘救星情结’不仅是对‘他者’的期待,希望他人成为英雄来拯救自己于苦难或者带领人们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且也是自身的一种内在要求,使自己也能成为一个英雄屹立于人间,所以人人都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它源于个体的无意识‘英雄情结’”[16](P8)这些歌谣接通了人们心中潜藏已久的无意识英雄情结,激发了人们心中的英雄豪情,在当时起到了非常大的激励作用。陇东红色歌谣“善于运用中国传统的夸张手法、丰富想象和比喻,来表达群众最灼热最深层的情感。”[16](P126-127)把革命领袖比作天上的“日月星”、“红太阳”,恰恰表现了老百姓思想的朴实,因为老百姓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日月星与太阳的巨大作用,他们实在想不出其它的比喻。我们不能把这种比喻理解为浮夸,这实际上反映了长期处于动乱、贫困的农民们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望、一种幸福焦虑。
毋庸讳言,陇东红色歌谣在根据地乃至全国被广为传唱,固然有革命政治推动的因素,但是,一个文艺形式真正受到接受者的喜爱与接受,并把其传达的主题内化为接受者的思想观念并付诸于行动,那绝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17](P19-25)。陇东红色歌谣之所以广受欢迎,在于这些歌谣以老百姓熟悉的方言土语反映了他们熟悉的生活,在于他们以接受者耳濡目染的民俗风情反映了他们的愿望需求,更在于这些歌谣激活了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与隐形的审美结构。这时“我们就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和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12](P227)正是在文化学的意义上,我们才能解释陇东红色歌谣的魅力,否则,我们可能得到一种一般化、简单化、肤浅化的结论。“革命歌谣脱胎于传统民歌,如火如荼的战争岁月赋予了它清冽的政治生命,群众鲜明的阶级观点又把革命歌谣的思想内容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飞跃,而这一切又是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民动员政策息息相关的。”[9](P126-127)陇东红色歌谣的兴起是陇东丰富的民间文艺资源与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战时条件下,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要提高农民的革命思想觉悟,采用民间文艺作为教育农民的载体是执政党的必然选择。革命对民间文艺的改造也促进了陇东歌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我们不能把陇东红色歌谣的兴起看作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从艺术上看,陇东红色歌谣朴实而不粗俗,豪迈乐观而不浮夸做作,但同作家诗歌相比,有的在艺术上还是比较幼稚、粗糙,语言也有不够凝练之处。我们不能因为陇东红色歌谣艺术上的粗糙、内容上的简单、思想的意识形态性而否定其价值,我们应该总结陇东红色歌谣的成就及其不足,对这一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考量,总结出其创作经验,以促进民间文艺的成长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担当的责任。
[1]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2]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3]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4]怀特.文化科学[M].曹锦清,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5]Alan Bullock and Oliver Stally brass,eds.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M].London:Fontana,1982.
[6][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瞿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7]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中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8][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桑俊.红安革命歌谣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11][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2]荣格.荣格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13]胡潇.文化的形上之思[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14]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15]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16]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17]张文诺.论陇东红色歌谣的主题诉求[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On the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the Red Lyrics in Longdong
ZHANG Wen-nu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 726000,China)
The popularity of red lyrics in Longdong is due to two main reasons.One is their reflection of working people's lives,thoughts and wishes,the other is their expression of the working people's collective unconscious which stimulates the people's emotional resonance.In addition to their revolutionary appeals, the red lyrics record local cultural data likes dialects,folk customs,national religions,which are valuable to cultural studies.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leads us to explanations of the lyrics'charms which is not available via other general,simple and superficial approaches.
red lyrics in Longdong;explanation;cultural studies;collective unconscious
I206.6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4.004
1674-8107(2014)04-0021-07
(责任编辑:曾琼芳)
2014-04-17
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农耕文化与陇东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研究中心项目“陇东红色文化研究”(项目编号:GSMS13-12-06)。
张文诺(1976-),男,山东阳谷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