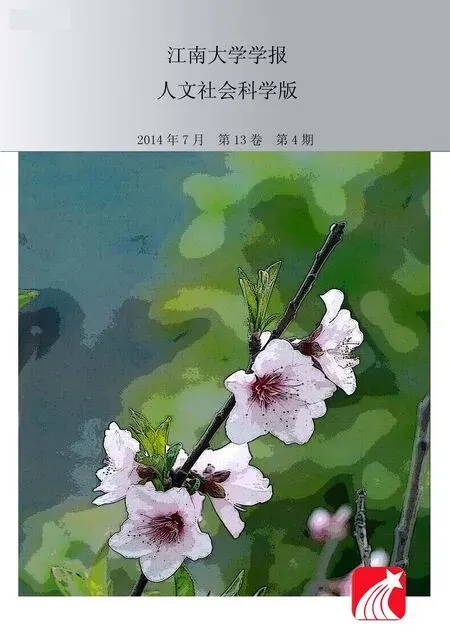从“直觉”到“理性”
——梁漱溟哲学方法论的转向考察
2014-04-14陈永杰
陈永杰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梁漱溟用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选择世界文化的未来出路上,其长处是将与道德有关的直觉意蕴揭橥得较为清晰,对工具理性、理智之蔽的揭示准确到位。但由于其所理解的直觉倾向于本能,德性成了先天具足、已然完成的东西,导致儒家仁智勇并举的修身进路中的智与勇付之阙如。其后,他发现了问题所在,主动进行了理论转向。转向后的梁漱溟扬弃了柏格森生命哲学和泰州学派中强调本能冲动的方面,融进了儒家的理性的内容,这是其哲学方法论转向的关键。这种转向客观上也推进了中国近代哲学。然而,从学理上来考察,其方法论依然存在较多弊病和缺憾。与其说这种方法论转向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信仰、情感的偏执和对传统文化的眷恋。
一、即体即用的本能直觉
依照梁漱溟,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实为直觉与知性的对峙,知性思维、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是造成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惟有直觉的生活才符合生命本性,因此需要直觉来救治。所以,其哲学方法论是以显扬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为旨归,表现出了对传统的依恋和对现代性价值的置疑。就探寻人类自身存在意义的方法而言,在梁漱溟那里,直觉即本体即方法,是本体与方法的一体化;直觉既是本体即价值之源,亦为通达形上本体的方法,“要认识本体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方生活的直觉才行,直觉时即生活时,浑融为一个,没有主客观的,可以称绝对。”[1]406。显然,直觉被梁漱溟提高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赋予了本体的意义,成了超越的普遍的存在,也是人的行为的形上依据。
所谓“浑融一体”、“没有主客的绝对”就是梁漱溟即本体即方法的直觉。本体论意义上的直觉,梁漱溟将其等同于儒家的道德本体——仁或良知良能,“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人类所有一切诸德,本无不出自此直觉,即无不出自孔子所谓‘仁’,所以一个‘仁’就将种种美德都代表了。”[1]454儒家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也被梁漱溟诠释为“任直觉”、“随感而应”,人遇事原不须你操心打量的,当下的随感而应就是对的。显然,依梁漱溟之见,人们的生活应该率性、顺着本能去走,只要听任直觉,从心所欲,就自然通达、流畅活泼。追问其思想出处,我们发现梁漱溟沿袭了“本能冲动即道德”的泰州学派思想,因此,经过他的现代转化,直觉成了沿着这个理路,梁漱溟主张唯有直觉才可以体认宇宙的生命,内里生命与外面通气的只有经直觉这个窗口。其直觉就又被赋予了方法论意义。依据梁漱溟,从直觉自身的规定性来说,直觉不同于现量(感觉)对事物纯客观的反映,也不同于比量(理智)对感觉所得进行分析综合得到关于客观对象的必然性知识。直觉中包含着主体的意味、感受、情趣、价值判断等非理智的因素,相对于运用理智的方法得到的纯客观认识而言,直觉不是隔绝于经验的感性规定,避免了存在成为缺乏现实品格的抽象存在。相反,直觉能将人理解为包含多方面规定的具体存在,所以,唯有直觉才是真正的玄学方法。过度依赖理智分析乃是误入了唯科学主义的路径,“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是‘生命’、是‘绵延’,宇宙现象则在生活中之所现,为感觉与理智所认取而有似静体的。直觉所得自不能不用语音文字表出来,然一纳入理智的形式即全不对,所以讲形而上学要用流动的观念,不要用明晰固定的概念”[1]406。如果用理智的方法加以肢解分割、静态地分析生命,那么所得只能是僵硬的、支离破碎的、毫无生趣的东西。
梁漱溟早期的哲学方法论受柏格森哲学影响颇深,梁漱溟激赏柏格森哲学,“迈越古人,独辟蹊径”,认为只有其才能与孔子的精神生活相比拟。柏格森继承的是叔本华、尼采贬抑理性、颂扬直觉,认为理性只能认识凝固的物质概念,而万物和人都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的表现。梁漱溟将柏格森的直觉方法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仁(天理)”、“人欲”叠加起来,使直觉获得了在柏格森那里所没有的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建立起了以道德情感为本体的形而上学。那么,直觉顺理成章地不仅仅只是单纯抽象理智的对立面,并且成了“良知良能”。[2]虽然梁漱溟也认可理智的价值,但主张理智本质上不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而是反本能的,并不能承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不过是利用厚生之工具而已。他将近代以来出现的“精神迷失”、“存在困惑”、“意义危机”通通归咎于理智的生活态度,只有复活儒家的直觉性的生活,使人生生趣盎然、生命深厚富有,才能克服近代人面临的“精神迷失”。其所谓“以直觉的情趣解救理智的严酷”,正是此意。梁漱溟不遗余力地揭示理智方法的有限性,与他对科学主义的批评立场是一致的。
不难发现,梁漱溟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他断言哲学形而上学的方法只能是直觉,因为直觉不违背宇宙生命之真,所得非对象性的知识,体悟到的是一种形上境界。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宇宙观必然导致把宇宙看作外在于人的静态实体,而实际上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生活过程即为宇宙的内容,非此还有别的宇宙,这是一个活泼泼的、动态的、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过程,是生命的发用流行。因此,直觉作为“玄学的方法”可以体悟生命的形上意义,体察“内里生命”的唯一通路。这种理解是梁漱溟的创见,富含理论价值。但可惜没有深入细致地研究直觉本身,“始终只限于描写直觉生活如何美满快乐,未曾指出直觉如何是认识‘生活’及‘我’的方法”[3]。
二、对关于其本能直觉的批评
显然,梁漱溟对直觉的这种本能式理解有浓厚的理想化意味。在本体论维度上,梁漱溟视直觉为一种与人的生命共同健动不息、活泼灵动的东西,即原初的善的本体。在方法论意义上,直觉也是体悟本体的方法,因为直觉所得异于抽象静态的概念,是一种“活形势”,能呈现宇宙生命的本性。这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立场,目的是体悟德性的良知本体,而非客观本体之真,依赖本能直觉就能直达德性本体。事实上,儒学既非一个狭义的知识论系统,亦非单纯的思辨哲学,儒学所崇尚的与其说是如何思考,不如说是如何践履、如何生活。在儒家那里,行动远比思考重要,实践高于知识,为人重于为学。儒家的目标是去体悟生活世界无限丰富的伦理道德意义,实现人生的理想追求,最终达到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作为当代新儒家的发轫者,梁漱溟亦未违背儒家哲学的基本关怀,所关注的也是直觉的实践品格,强调直觉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具有实践力的本能。应该说,就儒学的实践性而言,梁漱溟的把握比较到位。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梁漱溟只注意到了具备善本能的直觉锐敏地“随感而应”,忽视了德性在实践中的提升和进阶,也遮蔽了理智的思辨以及各种具体情景下的修身工夫,那么,儒家的仁是先天具足的吗?若如此,儒家的知就变得可有可无,修身的工夫将如何安放?在梁漱溟那里,直觉是本能的、已然完成的东西,直觉与理智相对峙而存在,凭人的自然本性率性而为美德就能实现,一切的恶都出于直觉的麻痹迟钝。如此一来,我们发现,梁漱溟一开始就将反对唯科学主义与批判所谓“害仁”的理智当作同一回事来处理。这种做法本身还有诸多讨论的余地。因为按照梁漱溟的逻辑,可以推出“无私欲”与“仁”是等同的,如是,其理论之蔽是将十分复杂的问题做了草率地简单化处理。此说理由如下:其一,任直觉、无私欲只是成“仁”的充分条件,而不能自动成就“仁”;其二,“仁”是一种理想目标,人欲能否去尽、人欲是否都应该去除、人欲是否等同于恶?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说明不应把“去人欲”无批判无反省地等价为“仁”;其三,梁漱溟强调了“人欲”与“仁”不共戴天,去除了人欲也只是条件,道德良知不会自动发动人的行为,理想人格也不会自动实现,其间还需要很多工夫才能达到“仁”。其实,在儒家那里,把为“仁”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用工夫从根本上消除恶之源,并不排斥理智,依靠内在领悟即“直觉”以及性情气质的修养,通过日常践履中的综合,即知识、情感、意志、思考和价值追求的一体平铺、活泼无碍,才是儒家经过工夫而通达良知本体的向善之路。
进而言之,在方法论的层面,梁漱溟对儒学的这种“纯任直觉、随感而应”的诠释也与儒学体系存在诸多扞格之处。他将儒学的人性论理解为性善是既成的、绝对的,道德先天地存在于个体中,只要祛除“算计”的生活,不计较利害,回归人的先天本能,“纯任直觉”就能达到“仁”。事实上,人的德性自我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不是已然实现的东西,只有通过一系列转化工夫过程,才能将其实现,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转化工夫就是修身。在先秦儒家那里,已明辨承认一个义务与能履行义务并非一事。儒家将修己的工夫非常缓慢艰苦,是个漫长细致的过程,甚至还要经历生死的考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 如此方能成就德性完善的圣贤君子。即便孔子也不敢轻言已具备德行,这充分说明儒家历来重视成圣过程的艰辛并视之为人存在的方式,而并非梁漱溟所谓完全听凭本能的直觉,自然就能不失规矩而“合天理”。
因此,梁漱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直觉是否可以脱离理智而独立存在?理智进行认识活动时产生的主客二分的确带来割裂人的整体性之忧,但人恰好是在理智认知的过程中展现自身,呈现自我。德性之完成亦非单纯的主观内在性领域之事,必然要在“成己成物”、“开物成务”的理智的客观性活动中才能实现。当然,固执于理智,产生的只是关于人的各种外在的规定性,人自身是被遮蔽的,这就需要通过直觉体悟来扬弃理智的各种规定性。但扬弃不意味着全盘抛弃,而是超拔出理智僵硬的规定性,复归于人的本真。在这个意义上,直觉是对理智的扬弃和消解而复归统一的过程,即消解理智和显扬人的本真是一体之两面,这也说明了直觉与理智处于一种统一的张力关系之中,都不可或缺。如果抛弃理智单纯强调直觉体悟,就破坏了这种张力,变成独断论的变相。
三、转向的动因
作为当然之则的天理不是通过理智计算出来的,这一点梁漱溟是有所见的。然而,早期的梁漱溟为了凸显中西文化的差异,将是否运用理智上升为两种文化的分水岭。这个说法本身大可置疑。有学者就批评道,他为了为自己的文化哲学思想寻找方法论依据,因此过分压抑了理智的作用,而随意抬高了直觉的地位。在此两者之间的褒贬抑扬清楚地反映了其理论创作上的偏颇随意。 这种批评虽然稍显严厉,却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哲学是排斥理智的,视理智为人之所以被分离的根源,进而对象化的活动导致人之本真被遮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目的是要以一种独断的方式说明:直觉为善,理智为恶。他大体上是把“恶”的起源归结为理智,由于理智的分别作用而产生了物我、人我种种计较,私心人欲随之而起,由此得出“人之不免于错误,由理智”的结论。
早期的梁漱溟主张人的本能冲动顺畅流行发动就好,反对加以抑制摧残,抑制本能会使人生缺乏活力,人生要顺着本能欲望走。在受佛学唯识学的影响之后,梁漱溟渐渐发现了本能欲望的不自觉的一面,即其天然的盲目性、机械性和被动性。当人的欲望强烈之时,生死非所顾,更何谈利害得失?也就是说,人生所有种种之苦皆从欲望来,必须去除本能欲望才消除了苦,达于彻底无欲之境。显然,此时的梁漱溟对本能中蕴含着先天的善的观念产生了动摇。当下的随感而应却导致人生的苦,是他始料未及的。这对鲜明的矛盾使梁漱溟意识到了过度强调直觉的先天本能这一度的缺陷所在,诚恳地进行了自我反省、择善而从之,“单明孔家走一任直觉随感而应的路还未是,而实于此一路外更有一理智拣择的路,如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便是要从过与不及里拣择着走。……前后这许多话我现在都愿意取消。现在更郑重声明,所有这一段话我今愿意一概取消。”“而我在此书中谈到儒家那里,尤其喜用现在心理学的话为之解释。自今看去,却大半都错了。”[5]321-324所谓的拣择其实就是一种理智的分析和判断工夫,这样,原本就包含在儒家思想里的智的因素,在被梁漱溟简单化地剔除之后又重新纳入了其理论视野之中。
晚年的梁漱溟逐渐修正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的疏漏,指出早年(写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时期)同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一样只注意到了人们欲望的自觉层面。后来却发现人也有不自觉的一面,认为“研究人类心理正应当向人们不自觉,不自禁,不容己……的那些地方注意。于是我乃大大看重了本能及其相应不离的感情冲动。”[5]603这可以看作是早期哲学方法论中非理性倾向的由来。梁漱溟承认自己滥以本能一派的心理学为依据,去解释孔学上的观念和方法论,却大半都错了。于此,他将早年对人性的论证划归为社会本能,属于“自然我”的范畴,然后另立了与理智相对的“理性”概念,确立了人类生命体中“自然我”(本能)、“功利我”(理智)与“道德自我”(理性)三分的模式,以理性与理智来说明东西方文化之异,构建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理性”的道德本体论。他认为这样就既能坚持原有理论对良知本心的那种“情意之知”的理解,同时也清除了早期“直觉”观念中混入“本能”的思想因素。这种理论上的变化可以视为梁漱溟对受欧洲大陆哲学中非理性主义及深层心理学影响之后的一种转向,转向其实就是一种回归,回归到了先秦儒家成就理想人格的仁智勇并举的进路上。
此时的梁漱溟(写作《人心与人生》时期)主张,理智是相对物理而言的,指认识客观之理,而理性是指情理,偏于主观;理性与理智是体与用的关系,从本能到理性的历程中,必然要经过理智这一阶段。“从生物进化史上看,原不过要走通理智这条路者,然积量变而为质变,其结果竟于此开出了理性这一美德。人类之所贵于物类者在此焉。世俗但见人类理智之优越,辄认以为人类特征之所在。而不知理性为体,理智为用,体者本也,用者末也;固未若以理性为人类特征之得当。”[5]618也就是说,一方面,没有理性的产生,人类永远不能真正脱离动物界,而人类的理智也无以正常使用。另一方面,没有理智,就不会产生理性,理智是理性的充分条件,理智为理性进行选择和判断提供了抽象思维的基础和能力。如果没有理智将本能松开,“本能突出而理性若失者,则近于禽兽”,人类便不能开出所谓“无私的感情”,也不可能从动物式的本能生活中解放出来。理性的含义非常复杂,梁漱溟认为儒家的理性是一种道德理性,与西方的思辨理性、科技理性不同,儒家的理性核心是“仁”和“良知”,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人内在精神的完善和充实,须臾不可疏离。要把握“理性”,向外寻觅是无济于事的,深切真实地向内用力才是正途。因为,人从来都不是一架逻辑严密的机器,而有血肉、有意志的、既有理又有情的复杂系统。
四、舍弃直觉而转向“理性”
转向后的梁漱溟以“无私的情感”界定理性,主张理性作为情意表现是一种“不失于清明自觉的情感”,也包涵“知”、“理”,但理性之知与理智之知不同,是以情的观照所体现出来的知、一种自觉的澄明状态。理性之情感表现是无限向上的“通”,与生命相通而无隔。理性虽为人心所本有,却必须经由修为工夫才能呈现。就他对理性的界定来看,显然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迥异。在他那里,理性有两种:物理和情理。物理是科学之理,是静态的知识,没有发动人的道德行为的力量;情理却有这种力量,指示着人们行为的方向。情理尽管是抽象的,没有特指当前某人某事,却有巨大的驱人向善的力量。
按照梁漱溟,理智是静以观物,其所得为物理,不夹杂感情(主观好恶)。理性反之,要以无私的情感为中心,即从不自欺其好恶而判断,其所得为情理。如正义感,就是对于正义欣然接受之情,而对于非正义则嫌恶拒绝。离开此感情,能得到所谓正义吗?一切情理虽然一定在情感上表现,却不是冲动,而是一种不失于清明自觉的感情。无私的感情一发动,此即一体相通、一体平铺、无所隔碍的伟大生命表现。无所隔碍的感情虽秉赋自天,为人所同具,然而往往此人此时具有活泼性,而其他人却不尽然;甚至同一个人也是时而发动,时而不发动,情感的状态是杂多不一的。这与动物本能显然不是一事,而恰好是由本能解放出来的自由活动,这种争取自由、争取主动不断向上奋进的本性,只有人类身上才出现过。在梁漱溟看来,既然本能、理智的两分法失之于简单,不足以说明问题,于是就在理智之外增加理性这个词代表从动物式本能解放出来的人心之情意。理性与理智双举,岂可少乎?
依梁漱溟之见,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儒家的“仁”是超越了理智分别和思虑计较的敏锐感通的情感。而“仁”即为感通流行形上之体,亦为孟子所谓“良知”、“良能”;情感作用盛之时,是“良知”、“良能”的发用流行,仁或良知由体而发用,亦即为“情”的流行与感通。梁漱溟声言孔家相信恰好的生活中最自然,最合宇宙自己的变化——谓之“天理流行”,即情感的流行感通,方能体证“天理”。梁漱溟称此为“心安”。所谓“安”与“不安”,就是道德情感的一种表现。梁漱溟强调的是以“天理”面目出现的本能情感,依他之见,儒家所谓性善,实质为情善,只要顺着天理自然流行,情与理皆善。梁漱溟的论证是否周延和严密我们暂且不论,但通过其对“仁”与直觉的关系的论述,以不安、情感、不计较、不算账、生意盎然来释“仁”,应该说,展现了孔子的“仁”的要义,是对 “仁”的诠释的一种推进。
梁漱溟自信地宣称,中国人精神之所在,即是“人类的理性”。显然,他将“情理”的内容注入理性之后使得理性概念具有明显的人文色彩,与西方的理性主义有所不同。西方的理性主义的“理”较多地讨论事理,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虽与行为有关,相对人而言,是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而中国人的理性主义的“理”,则是有力量的活动性,能够发动行为的“情理”。由于渗透着情感,就具有引发行为的力量,人的思考、言行乃至于价值取向亦如此。中国人的这种“不教通晓而有情”的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儒家的道德智慧。应该说,中国人的理性主义远比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复杂,中国人的“理”倾向于任何事物都秉有的天理,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者、全体大用之理,为一、为整体,而具体事物的分理“万殊”则是由此“一理”化分出来,是天理之流行,为其所规定。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梁漱溟的问题归结为:人的行为是理性发动的呢,还是被一种内心的情感、通过反省时自然而然地呈现的某种情感所驱动?根据梁漱溟哲学,认知意义上的理性只能发现这些义务,却不能产生这些义务,而儒家的理性是人的理性的整全有发动行为的力量。那么,一个行为、一种观念有德还是无德,如何判断?梁漱溟依据的是看见这个行为时产生的快乐与不快的情感,只要说明产生情感的理由,就能区分德与不德,有德是由于一个行为、一种观念带来的一种特殊的快乐。无疑,转向后的梁漱溟难以避免关于德性与情感关系的讨论,只是他没有深入思考,尚待我们继续探究。
结论:当梁漱溟发现人们由直觉而行并非都趋向于善,直觉难以承当引导人们生活方向的职责,自然地,理智和理性进入其视野,将理性作为概括中国人特殊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观念。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梁漱溟的方法论中提到了理智的功用,但依然将理智界定为“算计”之用,只有“理性”的生活才符合生命本性。他视理性为一种道德情感生活的真理,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理性即儒家所谓的“良知良能”、“仁”,儒家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寻找内心的“理性”,并视之为最后准则,“道德的根本在理性”。我们大致可以说,梁漱溟哲学方法论的选择从“直觉”到“理性”的过渡和延展,昭示了其思想走向成熟的历程。然而,梁漱溟对“理性”概念的分疏和清理还不令人十分满意。迄今为止,关于直觉、理性的本质的研究还在进行中。
[参 考 文 献]
[1]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 郭齐勇.梁漱溟哲学思想[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3]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 胡军.中国儒学史:现代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