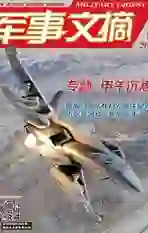一场战争改变了两国命运
2014-04-12徐焰






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日本发动了为时8个多月的侵华战争,日方称“日清战争”,中国则称“甲午战争”。甲午耻、犹未雪,多少年总是华夏热血青年感到未灭的恨事。不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又表现为理性化水平,而不是情绪化的简单激愤,对历史上的败绩灾祸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得到启迪,才能使坏事变成好事。如同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日本经过此战野心膨胀,发动日俄战争侥幸获胜后又进一步向大陆和太平洋扩张,决定了最终在1945年彻底失败投降的命运。甲午战争对中国是一场大灾难,从另一方面看又极大地促进了我们这个尚在沉睡中的古国的觉醒,最终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
日本“脱亚入欧”,清王朝陈腐依旧
120年来,有多少国人对甲午战争之败发过不尽的感慨─有指着颐和园船坊的吟诗之责,有大骂李鸿章卖国的口诛笔伐,也有对帝后不和、督抚难协的叹息。其实,历史表象后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经济体制,国家或民族的主导观念又与其伴生。19世纪中叶,中日面临着同样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命运时,两国理念的差异引致双方走向一强一弱的道路。
2000年夏天,我作为赴日本参加亚太各国军官研讨班的中方军队代表,曾穿着中国军装,在路边日本人多少带有些诧异的目光下到日本最大的军港横须贺南面的九十九里滨,参观了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这里是美国“黑船”以武力登陆强行索要权益的地方,相当于中国鸦片战争时的虎门。不过日本人却在此地树立着一座当年由著名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开国纪念碑”。对强国入侵本国不反感反而表示佩服、认为给自己带来文明进步并值得本国努
力学习,我深感此点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惊、可怕之处!
我也参观过国人在广东虎门所建的纪念馆,里面讲的只是外来“入侵”和自身的“抵抗”,感到其主题固然是对的,却缺少了另一方面的内容。早在1853年,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便说过:“英国在印度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同样,西方殖民者打开了中国、日本的大门时,带来的也是两个使命、两个机会。结果日本以投机取巧(主要是利用美英对抗俄国的矛盾去当打手)和维新变法的方式,避开破坏而抓住了建设机会。中国清王朝挨了英、法的打却仍冥顽不灵,只买些西洋枪炮而不做政治、军事体制上的变革,在洋务运动30年间白白丢掉了建设的机遇期。
自日本于1854年同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后,俄国、英国也接腫而来逼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在横滨等港口让西方开租界(“居留地”),允许外国驻兵,并给予领事裁判权。直至日本进行甲午战争及随后打赢日俄战争后,才以国威军威为后盾废除或修改了不平等条约。
19世纪后期西方入侵东方时,日本一度与中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日本人
的选择是挤进西洋人的行列,凌驾于同为亚洲人的邻国之上,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所走的正是这样一
条道路。后来中国人称日本为“香蕉帝国主义”,不仅是痛恨它欺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太甚,又在于它口喊“同文同种”、“大东亚共存共荣”,心里却以高于亚洲人之上的西方白种人自居,只是那张黄皮肤无法改变,如同黄皮白心的香蕉。
如今还印在1万日元钞票上的人头像,便是被称“近代东洋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明治维新之前此人便访问了美国,回国后大力宣传“脱亚入欧”、吸收西洋文明优胜劣汰的思想、加入西方行列而与东亚邻国绝交。这位日本近代思想的引领者,从西方并未学到人道主义等文明成果,引进的是弱肉强食的殖民观念。这种舶来品再同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又被改造成为一种狂热邪教式的侵略观念。福泽谕吉的理念从明治时代一直影响到今天,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却进入“西方七国集团”,安倍晋三等人媚从美国而与亚洲邻国对抗的行为都是沿袭这种指导观念。
而清朝,自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之后,也进行了一点改革,即实行了购买外国武器、建一些兵工厂和工矿业、创办新式海军等的洋务运动,却因守旧观念的包袱太重远远落在日本后面。1872年日本首都开通了火车,较中国首都通火车早了25年;1873年日本建立第一座近代综合性大学,比中国也早了25年。在下达剪发令和使用阳历方面,日本比中国早41年;在废除银两制而实行新货币制度方面,日本则比中国早65年。
1894年甲午之战开始时,清王朝在日本面前已是一只腐朽的“纸老虎”,表面上有人口、经济总量、军队总数和部分武器的优势,实际上在国家的近代经济成分、军队的战术、技术、先进装备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若仔细分析双方的“硬实力”,此刻已是日强中弱,在“软实力”方面,双方的差距更悬殊,胜败属谁在战前便勿庸龟卜。
日本巧妙利用列强矛盾,清王朝“以夷治夷”却失败
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宣称要冲出狭小的本土向外扩张,按明治天皇的诏旨便是“开拓万里波涛”。这一“开拓”有陆、海两个方向─其“大陆政策”便是入侵韩国、中国并且还要打败俄国;向海洋扩展首先便是占领台湾,接着还要向南洋扩展。这一国策决定了日本维新变法后一旦自感羽翼丰满,必然首先要同中国开战以夺取台湾、控制朝鲜和南满,甲午战争这一仗就不可避免。强盗抢掠得手后只会刺激进一步的犯罪欲,日本进而又同俄国开战争夺东北亚霸权,几十年后最终演变成同美英争夺太平洋的战争。
当然,自从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体后,日本的扩张野心也会受各方面的制约,只是它
在明治维新后几十年巧妙利用了各列强之间的矛盾,得以富国强兵并打赢了对中国、对俄国的战争。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与清王朝统治的中国命运不同,与列强的容忍和帮助密不可分。中国始终是列强盯上的肥肉,进行洋务运动也受到西方挤压,日本的维新变法却受到美国、英国以及德国的支持。从当年的国际战略利益上看,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年的西方列强盯住中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却认为日本地少民刁没多少油水;二是英国、美国想利用日本抗衡俄国,多年间采取扶日抗俄政策。德国在1871年打败法国后,最担心俄国援法,也希望日本能在远东牵制俄国。日本陆军就此得到德国教官训练,全面学习了德式战术和编制。
俄国自1856年同英法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向西方扩张受阻,便向东方夺占领土,这又引起英国、美国的极大不满。1867年美国依仗实力从俄国“购买”了阿拉斯加,消除了俄罗斯在美洲的占领地。英国也想阻挡俄国的力量进入西太平洋,却又不可能选择中国来充当帮手,于是看中了日本。日俄在19世纪后期便对南千岛群岛的归属产生争执,1891年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日本朝野纷纷叫嚷将来难免对俄一战,在此之前又必须打败中国。当时在海参崴主持完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仪式的俄国皇
太子路过日本游玩,被日本负责保卫的警察砍了一刀。接着,日本顶住俄方开战的威胁,对凶犯不判死刑而只判无期徒刑。这些举动恰恰迎合了英国、美国遏制俄国东进的需要,日本的“大陆政策”由此得到或明或暗的鼓励。例如1893年英国刚下水的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其时速达24节,远高于中国的“定远”、“镇远”14.5节的航速,马上便卖给日本被命名为“吉野”号。1894年7月,在日本发起甲午战争前十几天,英国虽对中日剑拔弩张的状态表示愿意“中立调停”,却在7月16日宣布废除同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而订立平等新约,明显是偏袒日本。
从甲午战争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看,能协助对抗日本的只有俄国,清政府也曾提出“以夷治夷”,寄希望于沙皇政府“调停”,却对是否请求其军事援助顾虑重重。俄国在19世纪中叶曾利用清王朝内乱外患夺取了中国北方大片土地,而且还在觊觎富裕和相对温暖的满洲,以实现“黄色俄罗斯”的梦想。若是求它出兵帮助,真会“请神容易送神难”,前面驱狼后面会进虎。不过此时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刚开工不久,在远东驻扎的几万哥萨克军队及随军居民的粮食靠马车根本无法万里运输,当地屯垦因气候条件不好收获不多,多年间需要从中日两国进口粮食,这样很难打大仗。若是西伯利亚铁路修通,马上便可保障几十万军队调动和供应。日本抢在1894年对中国开战,除了看到经济实力具备、海军装备占优势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又是认为在西伯利亚铁路修通前俄国难以调动很多部队到远东。
1894年中日开战后,曾在日本遇刺负伤的俄国皇太子刚好继位。这个头上留着刀疤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想乘机打垮他时时咒骂的“野蛮的猕猴”,起初却坐山观虎斗。俄国的如意算盘是,待中日两败俱伤,再以援华之名出兵,这样既能控制满洲、朝鲜,又可消灭日本军事力量,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出乎尼古拉二世预料的是,开战后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和辽东,清朝惨败后在《马关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沙俄认为此举绝不能容忍,尽管其远东陆军兵力还不足,却马上下令驻烟台、长崎的舰队揭下炮衣并升火,准备攻击日本舰队和港口,并拉上法、德两国要求日本向中国归还辽东(原来支持日本的德国参加干涉是想挑唆日俄对抗并向中国索要报酬)。此时日军激战8个月已感疲惫,军需品也消耗大半,不得不同意俄国的要求。
俄国牵头的“干涉还辽”,使清朝将其视为救星,第二年李鸿章赴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今后若对日本开战两国将协同作战。可是沙俄随即以“还辽有功”索要报酬,派舰队强占了日本吐出来的旅顺、大连,并向清政府强行“租借”,作为自己在东方扩张的基地。俄国这一示范动作之后,德国强占并“租借”青岛和胶州湾,英国强租日本退出的威海,法国强租广州湾,中国沿海口岸几乎尽遭外国瓜分。后来日俄为争夺中国领土,还以东北大地为战场。清王朝遇外侵不能自强而乞求他国相助,不仅不能“治夷”,只能使自己的国土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可悲境地。
日本侵华捞到“第一桶金”,中国在灾难中觉醒
甲午战争进行了8个月,中国海军仅同日本进行了两场海战便躲入港内避战,陆战实际成为战争的主
体。由英国、德国教习训练的北洋海军还能同日本对等交锋,保留着古老军制的清朝陆军同日本陆军相比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从平壤之战起几乎每战必溃。日军从陆地横扫辽东半岛,还以登陆抄后路的方式攻占旅顺、威海两个军港,主要以陆军消灭了北洋海军。过去国内谈起甲午战争大都只注重讲甲午海战,很少提起更重要的陆战,这就出现以偏盖全的认识误差。
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大多还迷信清朝已实现了“同治中兴”,对中法战争期间海军大败和陆上损失多少倍于敌的不光彩之事尽力回避,只将边境一场小胜宣传为“镇南关大捷”而自我陶醉。到了1894年至1895年中日两国军队实施决战时,清军的腐朽无能便暴露无遗。日军战前只有7个师团、7万人的陆军常备军和不足1万人的海军,战时迅速扩编至24万人并将其中17万人投入战场。据日本靖国神社的灵牌统计,甲午之战日本共有13619人死亡,不过按记载大多数是病死而非阵亡。1895年4月,害怕日军进攻北京的清王朝完全接受了日本苛刻的勒索条件,签订了《马关条约》。这场侵略战争的获胜,不但奠定了日本军事强国的地位,其经济也获得了起飞的资金。
过去国内一些书籍称,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夺了2.3亿两白银,这只是条约上的表面计算,按实际情况计算远不止此数。因《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随后“还辽”又索要了3000万两,而且日方在条约中规定要一次性付款,拖延便要付利息。此时年收入仅8000万两白银的清王朝财政已入不敷出,只好向英俄法德借款,3年后才交付完赔款,本利相加共支付2.6亿两。此外,日本在战时还缴获和掠走大批中国军械和民用物资,估算价值为6000万两。这样计算,日本总计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掠夺了3.2亿两白银。
日本政府宣布在这场战争中的花费是2.3亿日元(折合白银1.5亿两),其实这包括发展军工产业的投入,真正的作战费用是1.3亿日元(折合9000万两白银)。日本在战争中扣除耗费等于净赚了2 .3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战前日本政府4年多的财政收入。战争结束后,首相伊藤博文便向明治天皇上奏说:“官民上下都感到无比的富裕。”
掠夺到这笔钱,日本一面兴办教育,一面发展产业,并从英国采购世界上吨位最大的铁甲舰“三笠”号(排水量1.5万吨)等新型舰只用于下一次扩张战争。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去台湾这个中国富饶的宝岛,还迫使中国对其开放长江流域供其轻纺织业商品倾销,这又大大便利了其发展经济。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崛起的“第一桶金”,正是通过甲午战争掠夺而来。尝到侵略甜头的日本当权者在1900年又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华,1904年至1905年又发动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1914年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攻占青岛,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夏天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外,日军还在1938年和1939年向苏联的远东军队挑衅引发局部战事,遭痛击后又转头南下,1940年侵入法属印度支那,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夺取了南洋广大地区……甲午战争后日本滋长起的这种扩张欲,最终导致了“大日本帝国”在1945年的最后崩溃和投降,可谓是自食恶果。
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使中国落入更为苦难的深渊,却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当年先进的中国人心悦诚服地向外学习,而且首先向日本学习。20世纪初,几万国内学子赴东洋留学,其中既包括国民党多数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西方的先进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经日本传到了华夏大地,日语还成为现代汉语引进外来词汇的主要渠道。中国的变法、革命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又是以日本为坐标开始进行。
1960年6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曾说过:“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
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坏事往往能转化为好事,日本侵华的本意是奴役中国,结果反而促成了中华民族走向抗日和民族解放的道路,并最后迎来了新中国。
物换星移,甲午战争的硝烟早已逝去两个甲子,人们回首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与日本为邻既是不幸又是幸运,抗日与学日相互交织,中华民族才走向了复兴。历史上的中强日弱,自甲午后变成日强中弱,目前又由“两强并立”转向中强日弱,这正是历经沧桑的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