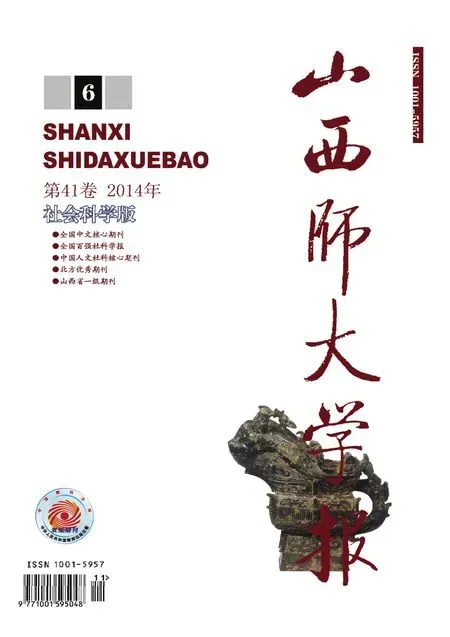建设和平: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学人的教育和平观
2014-04-11朱大伟
朱 大 伟
(赣南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反法西斯盟国于二战中后期开始构建的战后世界秩序与和平体系,在一定意义上确保了战后至今世界的整体和平。然而,当下学界对该时期盟国战后世界和平建设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美英的战后和平规划,而专门探讨中国对战后世界秩序建设所做的思考与努力的相关研究成果则较为少见。
抗战后期,中国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跻身于世界四强之列。大国地位的获取激励着中国学人勇于担当“起世界之沉疴,挽人类之浩劫”的救世责任,并进行了诸多建设战后和平的思考。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跳出既往国际社会和平建设路径的窠臼,从教育层面来构建战后世界永久和平。具体来讲,在对二战爆发的教育层面起源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他们对教育改造在战后和平建设中的价值与方法等问题做出了广泛探究。例如,1944年5月,在重庆召开的中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三届联合会,就把“世界和平与教育改造”列为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围绕该问题,与会专家提出了12件提案,对战后世界教育的目标、原则方案、措施等进行了检讨。[1]该会议的主旨表明,战后教育重建与和平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问题已进入中国学界的关注视野。本文试从中国学人对二战教育层面起源的反思、教育之于和平的独特价值、战后教育改造的主要理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战后教育重建中的价值等方面,对中国学人于特殊历史情势下生成的教育和平观做一初步探究,以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揭示中国对影响至今的战后世界秩序构建所做出的贡献。
一、对二战起源之教育层面的反思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学人有关战后和平建设的构想首先源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教训的反思与总结。一战刚过去二十年,为什么二战就接踵而至?他们多认为在世界走向战争的过程中,相关国家非理性的的教育体系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固然有政治、经济、种族和宗教诸项,但战争根源与教育关联最深”[2],“今日世界之血战根源与教育关联最深,教育不啻为推动战争破坏和平的利器,散播恐怖浩劫的种子,摧毁文化的毒素”[3]。以上观点反映了其时中国学人对二战教育层面起源的关注和思考。
具体而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一战后国际社会和平建设存在的一个缺陷,即未对各国教育,尤其是战败国教育制度的制定和运行予以应有的注意和监管,致使侵略性的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在相关国内得到实施。而“政治是教育的延长”[4]200—201的逻辑则驱使着这些国家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关炎章在谈及一战后国际社会和平建设的失败原因时指出:“未能及早以教育的力量来指导各国国际道德及义务,致令侵略国得以教育为侵略工具,造成民族偏见,各以优秀自居,彼此嫉视,殆为主要原因。”[5]喻智微对此的解释是:“凡尔赛和约剥夺了德国一切权力,唯教育权安全无恙,此乃德国之大幸,抑或英美之失策。”[2]在考察日本法西斯主义泛起的原因时,陶联城认为:“其教育实予以莫大之支持,即除外交与军事上之阴谋外,日本尚有教育上之阴谋。”[6]基于此,罗忠恕提出了战后和平化改造轴心国时的一个注意事项:“对德、意、日诸国之教育,应加以监督,必须重新教育其人民,改正其黩武思想,消灭其侵略野心,洗刷其谬误观念,培养其爱好和平之精神,此种工作,虽至艰巨,实属必要,决不能以教育乃一国之内政,而不加以干涉也。”[7]这一认识的形成无疑是直接吸取一战后国际社会和平建设失败教训的结果。
此外,学人们也对在轴心国挑起战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法西斯主义教育的特质做了概括归纳。毕竟,正是这些特质推动了相关国家走上了对外征服之路。近代中国知名教育哲学家瞿菊农认为,法西斯国家的教育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性,即反理性反科学的、种族优越的、全体权威的、反民主的以及武力征服压制的。[8]李武忠在考察世界教育思潮时也指出:“法西斯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狭隘的国家观和自大的民族意识,此种狭隘的观念与自大的意识实为引起战争的主要毒素。”[9]企平在谈及对战后日本的改造问题时说道:“德日的教育实质是一种麻醉国民的教育。在国家的立场则以战争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和解决国际争端的途径;在个人则以战争为专业,为光荣的死所,自杀飞机也,集团切腹也,其背后最大的动机莫不出于教育的原因。”[10]刘独峰则把法西斯国家反动教育的中心思想总结为崇拜武力、种族优越和领土扩张等。[4]204由上可以看出,在中国学人眼中,正是法西斯主义教育体系所具有的这些特性造就了相关国家民族沙文主义、种族优越论、黩武主义和扩张主义等反和平的民众心理基础,进而推动这些国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二、对教育在战后和平建设中价值的认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反法西斯盟国相对战略优势的取得和胜利曙光的初现,如何构建战后世界的持久和平开始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官方和学界的规划议程。抗战后期日本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更是标志着国际政治开始进入原子时代。这一可能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核恐怖时代的来临,使得维护战后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和更具有紧迫性与现实性。基于这种情势,教育学家雷香庭认为:“怎样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怎样寻求真正的永久世界和平,便成为当下教育上一个最紧迫、最重要和最远大的时代命题。”[11]那么,何以应对这一关系人类文明存续的时代挑战?中国学人向教育求解。如瞿菊农就认为:“教育活动作为一种以社会力量影响个人行为的过程,从教育的本质上和变形上讲,具有时代性和永久性的任务特征。”[12]38故而,在中国学人看来,教育应对这一时代命题负有积极回应的历史责任,教育开始被学人赋予建设战后和平的特殊时代使命。
中国学人对教育和平建设价值的认知首先源自对教育的本质、社会效用以及目的的认知。红色教育家钱亦石在论及教育的本质时认为:“教育是一种工具,在某种社会条件下,它是帮助人类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13]22瞿菊农也提出:“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也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8]萧孝嵘则把教育的目的直接定位为:“控制人类的行为和它的发展。”[14]程懋圭还强调了教育社会价值的和平向度,他通过对教育本质横的和纵的方面的探讨,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教育并非专重社会效率或能力之发展,而主要在倾向普天之下的人道生活之和谐,谋整个环境之内外近远的因素之调适。所以,社会效率或能力之发展等,也必须在助长和谐生长的条件之下,继有意义。”[15]其中“和谐生长”一词可解释为他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理念的倡导和希冀。由上可得知,学人们把教育视为国际政治新时代国际社会进行社会控制和维持国际社会稳定,进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有效工具,并认为工具性是教育固有的属性。
其次,中国学人对教育之于和平建设价值认知的形成还基于一个逻辑前提,即战争根源于人类的精神和心理层面。陈友松认为:“盖世界问题,本来是一个哲学与思想的问题。如果过于强调物质因素而忽视了精神因素,则不管我们新世界建设是如何努力,恐怕结果还是功亏一篑。”[16]故而,“毫无疑问的是,永久和平的基础必须深深地奠立于人类的和平心理”[17]。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常道直看来:“锋利的兵器并非引发人类好战心理的重要因素;反之,好战的心理确然足以促成新杀人利器的发明、制造和使用。”[18]近代中国著名心理学家谭维汉也总结道:“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深感以战争求和平不是好办法,以政治、经济、军事来解决世界和平问题,也不过是理想而已。因战争起于人心,如果人类不良心理不根本改变,战争永不能消灭。”[19]
故而,在学人们看来,教育之所以为战后和平建设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它能直接作用于人类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观念,是人类培养和平文化与和平心理的有效且重要的工具。对此,近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张君劢从心理与军事、经济、外交相关联的角度做出了阐释:“教育者,全人类心理之所由以形成也,心理倾向和平,斯无不平和之军事、经济与外交;心理倾向战争,斯扰乱世界之军事、经济与外交因之而起。然则谓,新世界之能否出现,视乎教育可也”。[20]此外,陈科美、雷香庭和蔡彰淑等学人也表达了此类见解,诸如:“教育的作用在于改造旧的心理,故个人或集体的心理(如自大、自私、恐怖和成见等)需要改造时,亦必从教育入手。”[21]“战争是人类的一种集体的行动,一种有意的行为,该行为受人类意志所指使,所以人们必须先平了自己的心,然后,世界才可以望和平。想平了人们的心,转移人们的意念,厌恶战争,崇尚和平,教育实为唯一的法宝。”[12]“欲求世界和平,必先从教育入手,因为教育是在人类思想上用工夫,人类的基本习惯上用工夫,它可以建立和平的思想,博爱的精神,在无形中消弭战争。”[23]17学人们的以上论点皆表达了他们有关教育能够构建人类和平心理,进而影响其外在行为模式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正是基于教育改造人性,诱导人类心理止于至善的社会建构价值,中国学人在要构建和平必先改造人类心理,欲改造人类心理,必要借助教育和改造教育上达成了共识。
三、战后以和平为旨归的教育改造新理念
在对二战的教育层面起源以及教育之于战后和平建设重要价值形成基本认知的基础上,中国学人提出战后世界永久和平建设有效性的取得必须兼顾到对世界传统教育哲学、教育方法和教育目的的改造。张治安代表性地列举了传统教育思想体系之于世界和平的危害:(1)养成国民自私自利心理,爱己国不爱人国,遂至彼此争权夺利,而不顾他国他民族的生存权利;(2)造成崇拜侵略英雄主义,直接、间接鼓励青年霸道为荣,遂使世界公理无存;(3)造成民族偏见,各以优越自居,遂至互相敌视;(4)隔绝世界潮流,忽视人类之互助合作,互尊互爱的理性启发,遂至人类善良本性淹没。[3]观念决定行为,朱炳乾提出,要改变这些导致人类战争行为的世界观,必须借助于教育改造,原因在于:“世界观的改组与重建关乎个人与社会行为的改变,而教育表现于个人与社会的生长与持续过程的各方面,与人类世界观的改变息息相关。”[23]2为改造各国狭隘的具有民族主义和黩武主义特性的教育体系,使教育在战后担负起建设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有着大国责任感的中国学人们提出了战后教育重建的新理念。
首先是教育制度的国际化设计。战时中国学人在论及战后教育的改造方向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思路便是战后教育制度的国际化安排,也即战后把各国教育运行置于一个超国家机构的监管、指导之下,如国际教育局、国际大学以及世界教育学院等制度的创设。汪家正在论及战后教育的趋势时,曾警告道:“假如我们要想保证战后的永久和平,那么,对于各国的教育措施,我们就不能不加以注意,精透的研究和严格的监察。”[17]楚图南也提出:“将教育,至少将大学这个阶段的教育,置于国际性的设计、组织和管理之下,不使任何野心家、侵略性的政治家,甚至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所得而私有,所得而利用,歪曲真理,又非使教育置于超国家关系,超国家利害之上而不能实现。”[24]王云五在谈及战后国际和平组织建设要义时,也建议道:“战后国际组织,宜特设国际教育机构,对各国教育宗旨与所采教材积极上导以国际合作、互助、尊人之旨,消极上矫正流于促狭主义之弊,教育为百年大计,永久和平实多赖之。”[25]胡鸿烈则把国际教育视为战后国际机构建设的重要原则,并认为它是促进和平的最妙的方法。[26]总之,基于“战后教育问题已不再是一国的事情,而是一个国际问题”的认知,中国学人们视教育制度的国际化创设为构建战后世界持久和平的关键。
其次是以培养世界公民为教育目标。世界公民教育的实质是对二战前各国传统偏执的狭隘国家主义教育的一种矫正。随着近世人类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世界整体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近代中国著名哲学家罗忠恕看来,传统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教育已经不合时宜,他指出:“目前为止,所有国家的教育目的不外是造成本国之良好公民,从无有以造成世界公民为理想者。近世因科学之发明,交通之便利,交换知识与思想之迅速已使分割人类之空间与自然之障碍日益消除。无论居何地域之人民,皆已成为比邻,世界一家,为必然之结果。”[7]基于同样的理由,常道直认为新时代的国民需要一个新的国民精神,“前此所要求于国民的只是平时勤力生产,战时保卫国土,当代的国民还需同时自觉是一个世界的公民,深切的体认本国最高利益与全人类的最高幸福是一致的,并对于国际正义之伸张有切实的贡献”[27]。
关于世界公民教育的内涵,中国学人从教育的目的和理想上进行了界定。此种世界公民“首先使其与国际思想相协调,有为人类一份子的自觉,在这自觉的过程中,去掉自私与狭隘的国家观念,以最善的努力协同创造人类的安全与幸福”[28]。张治安认为,世界公民教育“在目的上,应以启发人性,培养善于合群的健全公民为宗旨。并以消灭狭隘的爱国主义、个人主义和含有危害人类集体安全的教育为急务;在理想上,更树立崇高而远大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的教育思想,培养其对国际关系之正确认识,以及对世界和平之神圣责任。不仅是一个爱己爱国份子,而且也是一员爱世界爱人类的份子”[3]。中国学人这些有关世界公民教育内涵的界定与战时美国学者詹姆斯5奎林的定义基本吻合。奎林认为:“世界公民教育的目标包括理解、理想与能力。具体表现为:能对合作的需要和取得它的可能加以理解;能勇于担负人类的一员所应抱有的提高人类福利的个体责任的理想;能用他的智力而非不受限制的暴力和盲目的歧视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愿望和能力。”[29]
再次,倡导以教育公平为诉求的平民教育。近代中国学界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是以平民大众为对象的全民教育运动,其追求的是教育机会的平等及其社会意义的实现。在二战中后期谋划战后世界永久和平的过程中,中国学人赋予了其独特的国际政治价值。早在一战结束后,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蒋梦麟就认识到了平民教育的和平建设价值,“平民主义愈发达,则其和平之基础愈固。故欲言和平之教育,当先言平民主义之教育”[30]。对此问题,近代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论道:“社会上如一天没有承认平民教育的重要,不把平民教育作为立国的生命,立世的生命,社会就不平一天。非社会平等,人人受教育,世界决不能和平。”他并且认为:“和平要永恒,就要基于民众之上。人类历史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洗人心,人们站在新的旅程上,迎接新的世纪,这是一个最新的契机,也是一个最后的契机。”[31]邹鲁甚至把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全人类知识的平等视为获取战后和平的捷径,并把其视为解决战争问题的治本办法。[32]这些主张反映了中国学人试图通过教育的力量对大众进行理性启蒙的观念,进而打下和平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最后,提倡国际和平教育的儿童化。中国学人倡导战后国际和平教育的开展应从教育对象的幼年时期做起,他们对需要向儿童灌输的和平理念也做了梳理和提炼。张怀认为:“由儿童教育做起,以平等互助精神为儿童教育的基础,建设儿童心理,才是在根本上解决国际和平,防止人类斗争的彻底办法。”[33]近代教育家赵廷为则提醒参加远东区基本会议的代表:“欲根本消灭战祸,须从基本教育入手,使下一代的儿童明是非之辨,客观的事实必须要尊重,欺人之言必须要揭穿,成见必须破除,能用正确的思考来研究国际问题。下一代的儿童应了解白皙人种的优越乃是一种偏见,‘强权即公理’一语实属谬误,爱自己的国家而损害他国利益完全是偏狭自私。使知人类的相互依赖世界的不可分割性等。”[34]2蔡彰淑在论及教育与人类的和平关系时也强调道:“尤其在人类儿童期,我们如能用教育发展其慈爱和同情的美德,遏止其自私和倔强的偏性及发怒争胜的本能,把世界上各种族的儿童教育成具有互助合作、平等博爱、同情牺牲、舍己为群的美德和无类无界的伟大人生观之人,则可奠定人类和平基础而使和平永存于世。”[22]
四、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教育改造价值的解读
抗战后期,中国忝列四强之一的情势激发了中国学人身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自信心,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进而促使他们重新认识和挖掘中华五千年的本位文化所蕴含的和平教育价值。并把其视为汪叔棣所提出的“人类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之一:什么是我们全人类应该接受的教育精神”[35]这一课题的答案选择。
在论及战后世界教育建设的指导思想时,中国学人基于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倡导打破地域畛域,以世界而非以国家或地区为中心的教育思想。而这种教育思想的践行成效在他们看来,关键在于中国儒家大同文化的推广。其原因正如黄玉璋所论述的:“中华文化特质是天下为公的博爱精神,其反映于教育者为大同主义之人生。”[36]周绶章则通过对欧美各国教育思潮的考察,得出世界各国的教育思想都趋向于偏狭的国家主义、自私的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点。因而,战后“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便有了新的价值和作用,可能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要义以“公天下”为重,“在修、齐、治、平的大同教育大纲中,以平天下为最高的归宿。要谈真正的世界和平,则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思想应为各国教育思想的极则,否则不能大同,也就难保和平,更谈不上永久了”[37]。王之平把导致人类相残的观念原因归结为三点,即偏重物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认为它们的消除只有借助中国的大同学说。原因在于大同主义所具有的特性,即“政教本于五伦,人人皆得其所,人人皆化于善,精神物质并重也;货不藏己,力不为己,资产公有也;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破种族国家之畛域也”[38]34。陈劭南甚至把大同主义教育理想元素视为人类世界教育的最高原则。[39]以上可看出,学人们对中国传统大同文化所蕴涵的和平精神内核与和平建设的价值予以了充分肯定。
此外,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所承载的和平教育价值也受到广泛认可。何为王道?在张齐贤眼中,王道的基本精神为:“在博爱、忠恕、亲仁善邻,在世界大同。遵之,则人类安定,弃之,则秩序混乱。”[40]喻智微对王道的解释是:“以中国数千年的固有道德,仁、义、礼、智、信为基础,不仅以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为手段,且进而以预谋发展各民族文化为目的。”他对比西方的霸道文化后得出结论:“只有从中国的王道文化做出发点,继能开创世界和平的新天地。只有用王道文化的手段去消灭集权国家的侵略思想,继能实现永久的真正的和平。”[41]何健在比较王道与霸道的内涵时,特别强调了中国王道文化以及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地位,他指出:“将来世界和平之日,自是王道大行之时。我国是王道政治与大同思想发祥之地,更应该发扬传统的优良文化,以顺应世界潮流,为人类造福,为万世永保和平。”[42]
五、结语
“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善政之,不如善教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先贤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教育在改变人类观念和行为方面积极的社会价值。随着近代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人类世界日益发展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人类的思想观念,尤其是民族观、国家观和国际观的发展却落后于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表现为种族优越主义、黩武主义和独夫式英雄主义等狭隘、偏执和极端的观念依然在世界盛行,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意义上即可溯源于此。如何祛除这些导致国家间走向战争的思想观念,进而建设战后世界的永久和平便成为20世纪40年代世界的时代命题。胸怀传统“平天下”入世情怀的中国学人做出了自己的探索。他们在借鉴中国先贤智慧的基础上,致力于以教育改造的方式来奠定人类和平的心理基础,进而构筑战后世界永久和平大厦之基。
鉴于一战后国际社会和平建设失败导致二战再起的惨痛教训,战时中国学人,尤其是教育学人前瞻性地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战后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先进和平教育理念,如倡导天下为公的世界公民教育,消除民族间存在的歧视、偏见和畛域的国际理解教育,进行跨文化教育以及和平教育等。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以建设和平为导向的教育改造方案多少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充分注意到各国教育思想民族主义本位现实的顽固性,并且缺少具体的、系统的、操作性强的实践措施,但仍不失理性思考的特性,并成为国际社会探求建设永久和平的一条富有建设性的路径。他们的这些思考为今日世界和平发展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启迪,也为国际政治学中的和平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诸如教育与和平的内在关联机制,和平教育的内容体系建设,和平教育的实施方法、教育如何帮助人们树立起理性的国际观等,都是当下国际和平学应深入探讨的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学人对战后世界和平建设的贡献并未止于理论思考层面,他们也代表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盟国战后世界和平建设的实践工作。1944年10月朱家骅、梅贻琦以及赵廷为等代表中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盟国教育部长会议,研讨战后世界的教育建设问题,主要商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筹建工作。1945年11月盟国教科文组织预备会议在伦敦召开,胡适、瞿菊农、杨公达以及赵元任等作为代表出席。1946年11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会议暨成立大会在巴黎首次召开,知名教育家竺可桢、赵元任、瞿菊农、胡天石等出席了筹建会议。他们在这些会议上都做了相应发言,并提出了改良性建议和提案,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声音,为盟国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 汪家正.提倡战后世界教育的研究[J].文化先锋,1944,(1).
[2] 喻智微.国际教育与世界和平(上)[J].智慧半月刊,1948,(44).
[3] 张治安.社会教育与世界和平[J].教育与社会,1947,(2).
[4] 刘独峰.国际学大纲[M].重庆:平民书屋发行,1946.
[5] 关炎章.战後世界教育的改造[J].新风周刊,1946,(4).
[6] 陶联城.日本教育之缺陷[J].新教育旬刊,1939,(7).
[7] 罗忠恕.国际教育与世界和平[J].学生杂志,1945,(11).
[8] 瞿菊农.战后世界教育的趋势当然是民主的[J].华声,1944,(4).
[9] 李武忠.世界和平与教育改造[J].现代周刊,1946,(5).
[10] 企平.日本教育的彻底改革[J].中国建设月刊,1945,(2).
[11] 雷香庭.和平与教育[J].广州大学校刊,1947,(17).
[12] 瞿菊农.抗战七年来的教育学[C].孙本文.战时中国学术[A].重庆:正中书局,1946.
[13] 钱亦石.现代教育原理 [M].上海:中华书局,1949.
[14] 萧孝嵘.战后的教育建设与心理建设[J].教育杂志,1947,(2).
[15] 程懋圭.战后教育的改造之基本原理[J].东方杂志,1944,(10).
[16] 陈友松.新世界建设的展望[J].东方杂志,1945,(8).
[17] 汪家正.战後世界教育的归趋[J].新中华,1945,(2).
[18] 常道直.基本教育与世界和平[J].教育杂志,1947,(3).
[19] 谭维汉.国际教育的新境界[J].广东教育,1947,(5).
[20] 张君劢.国际会议中之战后世界教育方针[J].东方杂志,1944,(14).
[21] 陈科美.和平的教育与战争的政治[J].申论,1946,(5).
[22] 蔡彰淑.教育与人类的和平[J].教育半月刊,1946,(5).
[23] 朱炳乾.新教育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24] 楚图南.战后和平与教育问题[J].民主周刊,1945,(10).
[25] 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J].东方杂志,1943,(4).
[26] 胡鸿烈.战后国际和平组织之调整与建设[J].新认识,1942,(3).
[27] 常道直.基本教育与世界和平[J].教育杂志,1947,(3).
[28] 陈礼江.世界教育建设献议[J].教育与社会,1945,(4).
[29] I James Quillen. Education for World Citizenship[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35,(Sep., 1944).
[30] 蒋梦麟.和平与教育[J].教育杂志,1919,(11).
[31] 晏阳初.为和平而教育世界[J].新教育,1947,(11).
[32] 邹鲁.教育与和平[J].东方杂志,1944,(21).
[33] 张怀.国际和平与教育[J].广播周报,1948,(96).
[34] 赵廷为.向远东基本教育会议代表请教——兼论基本教育与国际和平[J].教育杂志,1947,(3).
[35] 汪叔棣.迎接战后新世界[J].东方杂志,1943,(1).
[36] 黄玉璋.教育与和平——献给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首届大会[J].豫教通讯,1946,(2).
[37] 周绶章.教育思想与世界和平[J].文化先锋,1946,(2).
[38] 王之平.大同主义之研究[M].重庆:天地出版社,1943.
[39] 陈劭南.明日的世界教育[J].民族文化,1944,(1).
[40] 张齐贤.东方王道精神与世界大同[J].江苏月刊,1941,(1).
[41] 喻智微.国际教育与世界和平(下)[J].智慧半月刊,1948,(45).
[42] 何键.王道与霸道[J].新中华,1944,(1).